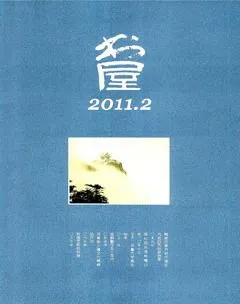利国无能但利身
2011-12-29王学斌
书屋 2011年2期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在其《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中有这么一首诗:
利国无能但利身,虚名开济两朝臣。
笑他药性如甘草,却负黄花号菊入。
此诗所揶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张氏之意,徐身为清末显宦,一味利己,利国不足,徒具两朝重臣之虚誉。更为可笑的是,徐之性情本似中药之甘草,“其圆滑机变,当过于长乐老”,偏偏却给自己起个“菊残犹有傲霜枝”的“菊人”雅号,实在是沽名钓誉,自作清高,“有负黄花矣”。考虑到张氏家族与袁氏家族的姻亲关系(其父张镇芳乃袁世凯表弟,徐世昌同袁、张二人关系均甚密切),故诗写得虽不免有些刻薄,但距离实情似也八九不离十。近来笔者有幸读到徐世昌未刊的《韬养斋日记》,阅罢这长达一百五十余万字的私人记录,更使我深感张伯驹之言不虚。
一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水竹邨人,祖籍浙江鄞县,落籍直隶天津卫,出生于河南卫辉府。据其家谱记载,徐世昌呱呱坠地之际,“其状貌端秀,头角峥嵘,长老皆许为大器”。然而,徐的脑子却并不灵光,尤其是应试能力较差,科考每每积极参与,成绩次次名落孙山。白驹过隙,一转眼徐世昌已近而立之年,往日的那股锐气消磨大半,他也感到人阁拜相的理想似已距自己渐行渐远。一次,徐乡试结束,几位挚友相邀聚于相国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人问徐世昌将来有何志向,徐醉眼迷离,举杯苦笑道:“他日或大祧,或议叙,或幸成进士为即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县、太康,必师孟尝君广纳食客。”河南旧有“金杞县、银太康”之称,堪为各州县中之上等肥缺。可见徐世昌此时颇为务实,在他看来,能管辖一:县、衣食无忧已实属难得,什么声名显赫、位极人臣之类是绝对不敢奢望的。
就在徐混沌潦倒之际,生命中的贵人袁世凯不期而至。为了生计,徐四处奔波,为人充当幕宾。一次,徐赴陈州谋职,恰袁世凯亦居此地。袁本一纨绔子弟,终日呼朋引伴,骑马喝酒,临到考试之际,便请人捉刀代笔,此行径颇招致当地士绅之微阋。袁于是有所收敛,“纠集同志立丽泽山房及勿欺山房两文社,分门讲习,公主其事,捐资供给食用”,从而“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一郡望”。徐世昌自然慕名而来,他与袁世凯的终生交谊也由此开始。至于二人初次见面之情形,在陈灨一的《睇向斋秘录》中,被描写得极具戏剧效果:
一日,(徐)往游袁氏别墅,阍者阻之,若
弗闻也者,昂然径入,至仰山堂。是为项城读
书所居,时方执卷朗诵。徐进室,向之一揖。项
城起立还揖,延之上座,讶问:“客从何处来?”
徐详告之。坐谈良久,慷慨论天下事,互相倾
服,遂订交。徐返署,对令曰:“吾今识一人,他
日必成伟业丰功。”令询何人?徐大声曰:“项
城袁世凯也。”
从此,富家公子与穷酸书生一见如故,惺惺相惜,联手将清末政局搅了个天翻地覆。
相识不久,徐又要赴京赶考,但苦无川资。身为“富二代”,袁世凯自然不能坐视不理,遂慷慨解囊,替徐买单,二人也不得不依依惜别,这一别竟是整整十六年!此后二人天各一方,情形迥异。袁投笔从戎,于行伍中始崭露头角,渐成朝廷新宠;徐一再落第,屡败屡战终金榜题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十年寒窗苦读终有回报,徐世昌自然百感交集。在接到朝廷任命上谕当天,徐于日记中写道:“君恩高厚,受宠若惊,益当努力有为,以期报国承家也。”大概彼时的徐世昌还是想为清廷做点实事。不过,残酷的现实很快便让徐明白所谓的抱负仅是一厢情愿而已。按照清制,每三年都要对庶吉士进行甄别考试,成绩优等者授编修,次等者授检讨,合格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县。如果成绩不及格,不好意思,那就请您继续学习,再等三年。当时掌院学士为翁同鄶,他博雅好学,特别喜欢提携江浙一带的人才。而徐世昌不通古学,文笔一般,自然不受翁老爷子待见。徐在这个清水衙门一待就是六年,竟未曾获得过一次外出主持地方乡试的差事,甚至连当副手的机会都没有。一次,好友严修外放贵州学政,这令徐颇为慨叹,“览镜见鬓已有白发,不禁感慨人生如驹阴过隙,何必日事劳劳”,其内心之失落跃然纸上。
好不容易结识了天津老乡王文锦侍郎,徐请他帮忙介绍新差事。王为人倒也通融,打算将徐推荐至南书房,孰料大学士潘祖荫认为徐不学无术,难堪此任,不予接纳,又将他撵回翰林院。当时翰林院有所谓“八红八黑”之称,“红翰林”自然是官运亨通的那一类,而“黑翰林”则是指仕途坎坷的官员们。徐即位列“八黑”之一,其文采之平庸,运气之不佳可想而知。最令徐无奈的是,熬到第八个年头,他终于可以外放河南,谁成想还未等朝廷颁发委任状,母亲突然病逝,徐只得暂弃升官念头,回家奔丧去了。
如果将徐世昌喻作一只股票,据其前半生宦海只跌不涨的表现,可将他视为“垃圾股”。至1895年,这只股票已经基本跌停。不过,跌停见底未必是件坏事,只要有经验丰富、手法老练的操盘手跟进,全部买入建仓,一番运作后,其股值定会强势反弹,大幅上扬。徐世昌恰恰就是这支濒临谷底的股票,而逢低买进的庄家也刚好到位,此人又是袁世凯。徐世昌即将否极泰来1
二
1895年9月3日,徐、袁二人于阔别十六年后重逢。两人此时身份已是判若霄壤,一个仍是可有可无的七品闲差,一个则为朝廷新晋的练兵大臣,不过彼此间那份手足情谊却如同藏于地窖中的陈年佳酿经久弥香,愈加醇厚。眼见老大哥(徐年长袁世凯四岁)处境尴尬,袁世凯自然心有不忍,决定好好拉兄弟一把。袁世凯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带徐世昌广交朋友:
晚赴嵩云草堂巽之之约,议开书局。同座
陈次亮、陈养园、康长素、叔衡、子培、子封、慰
廷。席罢又谈至三更后始归。
午后同其(袁世凯)赴强学会宴集,巽之
承办,座有于惠若(式枚)、文芸阁、梁卓如、汪
伯唐、沈子培、英人李提摩太(字菩岳)、美人
李佳白(字启东)、毕德格(字子明)。二李皆能
读中国经史,启东作山东浜海语,菩岳仿佛中
国官话。言及立志向学,万国会通同享升平,
令人有无限河山之感。
晚赴鹤泉之约,座有叔衡、子培昆仲、张
君立、杨叔翘、巽之。饭后同叔衡、子培访郑苏
龛司马(孝胥),夜谈。三更后归,写定兴信。郑
通知时事,议论明决,当时之俊才也。
正是凭袁之引介,徐世昌与陈炽、康有为、文廷式、梁启超、沈增植兄弟、李提摩太、李佳白、杨锐、郑孝胥等人交往,很快融人当时主流社交圈中。
之后的故事似乎大家都耳熟能详,袁举荐徐人自己幕府,助其小站练兵。经过几番锤炼,徐终成大器,一跃成为清末政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应当说,若无袁之倾力提携,绝对不可能有日后之徐世昌。但假使徐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那就算袁再关照,他也难以于官场上爬得如此之陕,短短数年间便完成了由七品小吏到一品大员的飞跃。故徐本人的综合素质也至为关键,尤其是他卓越的人际交往能力,让人不禁啧啧称奇,这在其日记中多有体现。
中国的官场,向来有“以乡谊结朋党”的不良风气。如果一个人能在上层官僚中找到自己的老乡,那就如同傍上了靠山,只要对他毕恭毕敬、百倍殷勤,高官自然会时刻罩着你,保你官运亨通。徐世昌同鹿传霖之间的交往即典型案例。鹿传霖(1836~1910),字滋轩,号迂叟,直隶定兴人。《清史稿》记载,“传霖起外吏,知民疾苦。所至廉约率下,尤恶贪吏,虽贵势不稍贳。其在军机,凡事不苟同,喜扶持善类”。徐世昌与鹿传霖的侄子鹿瀛理乃进士同年,又是直隶同乡,于是经常来往,私交甚笃。刚好1888年鹿传霖因病暂辞陕西巡抚一职,返乡疗养。于是徐世昌得以有机会见到这位直隶老乡。据《韬养斋日记》载,9月16日那天,“(徐世昌)到乔笙(鹿瀛理)处,代其写屏对,适鹿芝轩世叔自定兴来,因拜谒焉。曩见季和宗叔祖谏铁路奏章,甚向慕焉。今日拜谒,其言论风采果有超乎流俗者,良可敬也”。
此后,徐便成为鹿府的座上常客,并代鹿传霖拟志书序和信稿,二人关系因之越走越近。应该说鹿传霖还算是清末为数不多的良吏,但也有马虎大意的时候,他完全被徐老实巴交的表面形象所蒙蔽,认为其是个可造之材。日后徐世昌能够进入军机处,与鹿的力挺密不可分。故沈云龙先生认为“传霖亦以乡谊,遇之(徐世昌)甚亲,机要辄引与共谋,非荣(庆)、铁(良)所能及”,殆非虚言。
协助袁世凯小站练兵,徐世昌自然少不了四处奔走,联络军务,这也为其结识各地显宦提供了极大便利。比如1897年9月底,徐赴湖北出差。按日程安排,徐本不必经过武汉,但为了结识湖广总督张之洞,他还是找个由头不请自来。出于礼貌,张之洞派人接待甚周。张本以为徐小住几日便回津复命,谁成想他居然待了足足一个月。更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一个月内,徐、张二人来往频密,打得火热。熟悉晚清史的人大概都了解,张之洞这人怪癖颇多,不易相处。胡思敬在其《国闻备乘》中曾总结:“闻其性情怪癖,或终夕不寐;或累月不薙发;或夜半呼庖人具馔,稍不惬,即呼行杖;或白昼坐内廷宣淫;或出门谢客,客肃衣冠出迎,偃卧舆中不起。”这种怪异的日常习惯,想必一般人是吃不消的。不过,徐世昌却丝毫不受张之怪癖影响,反而如鱼得水,极其适应,一个月内几乎天天同香帅彻夜畅谈。有一日二人夜饮,张“论中西学术,论西政、西学之分,论时人之愚暗,太息痛恨”。然后问徐有何学术志向。徐早已提前做足了功课,对张之喜好摸得一清二楚,答日:“目前新学中年通籍,以后之人以讲求西政为先,西学随其性之所近而涉猎之,仍以中学为主。因论中学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为。”
这恰恰与张“中体西用”之主张甚为吻合,故张之谈兴更浓,与徐推杯换盏,执手言欢,一直侃到凌晨四点多。经过此番交往,徐世昌给张留下了极佳印象,甚至张一度想聘徐作他的幕宾。1901年,张之洞响应朝廷保荐人才之谕令,上书推荐了九名官员,其中就有徐世昌。其推荐词如下:“翰林院编修徐世昌,该员志趣端正,持躬谨饬,明达时务,办事精细。前在山东巡抚袁世凯军营有年,于兵事甚能考究,实为今日有用之才。拟恳恩交部带领引见,优予录用。”
正受益于张之推荐,当然还有袁老弟的暗中运作,徐世昌得以于次年人宫面见慈禧太后。人对时,慈禧发现徐世昌“体貌英挺,音吐清扬”,是位不折不扣的老帅哥,自然满心欢喜。第二天,慈禧便对荣禄讲:“徐世昌或足继李鸿章后乎?”可见其对徐期许之高。而这一年,徐世昌已四十八岁。
清末官场,有两条所谓仕途之终南捷径:一是商部,载振把持;一是北洋,袁世凯掌控。载振乃庆亲王奕劻之子,袁世凯同奕勖早已沆瀣一气,与振贝子也是拜把子兄弟。作为袁的好哥们,徐世昌也尽享近水楼台之便利,有机会染指这两条捷径,成为潜规则的受益者。1903年,载振出任商部尚书,开始招兵买马。他屡次听袁世凯讲徐如何贤能,怎样高明,于是特保授徐为商部左丞,这在当时政界可谓轰动性事件。徐之前仅是六品撰修,一跃破格升为三品商部大吏,这在整个清代也堪称异数。虽获此殊遇,但对于徐而言似是意料中事,并未显现受宠若惊之态,反倒于日记里流露出些许遗憾:“擢进升阶,悲我母未之见也,怆恻于怀。”可见徐也算是位孝子。
此后徐之仕途可谓一片光明,其为官之道也愈发纯熟老练。宣统元年,以载沣为首的那一批年轻皇室贵胄上台,他们对西方的武器、建筑、工艺、科技等颇为推崇。当时徐恰恰担任东三省总督,于是揣摩皇室心思,大搞形象工程。据曾在东北任职的丁士源爆料,“徐世昌赴东三省总督任时,携中央款二千万两,两年以来铺张颇甚”。单单建造奉天公署大楼一项,就消耗白银三十余万两,所盖“西式楼数十楹,缭以复廊,其中廉幔几榻,灯屏皆用舶来品”。同时采购各种西式物品又花费十余万两,因而其办公场所之华丽宏伟,其他省份无能出其右者。此外,公署出行则必须乘坐双马之车,宴请客人采用全套西餐器具,并伴奏西乐。一次载涛自欧洲考察归来,途经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及驻宿公署,俨然欧式”,使他“直把沈阳作巴黎”,于是对徐世昌的市政工作大加赞赏。等他回京后,更是在五哥摄政王载沣面前表扬这位“市政建设标兵”。当然,徐如此大张旗鼓的透支财政搞城建,自然有人看不下去。当时载泽掌管度支部,曾派人细察徐世昌的账目,发现其财政收支上存在巨大漏洞。于是几次上书载沣,请求彻查。此时载沣已把徐世昌树为全国学习的典型,加上像载振、载洵、那桐等皇亲国戚早已被徐的贿赂喂饱,天天在载沣耳边说徐的好话。于是载沣始终相信“徐世昌是个好同志”,就象征性地派赵尔巽前去查办。赵与徐私交甚笃,自然帮徐极力洗脱嫌疑,强调东三省“建设官制复杂,必须改革”,故而开销巨大。徐手腕之高明,于此可见一斑。
正是依靠诸多手段,徐世昌于短短几年内神奇地完成了由一名默默无闻的潦倒翰林向天下皆知的国之重臣的华丽转身。这支垃圾股一路狂飙,俨然已是行家眼中纷纷看好的绩优股,而徐取得这一切的代价却是让本已风雨飘摇的清廷距离灭亡更近了一步。
三
来自基层,熟悉社会各种势力的运作机制;位极人臣,洞察朝中皇亲国戚的实际情形;工于心计,深谙政治斗争的游戏规则;深藏不露,终日一副老成持重的忠臣形象。具备如此出众的综合素质,袁世凯自然将徐世昌引为心腹,让其参与北洋诸项大计。
自从被载沣罢免后,袁世凯便蛰伏彰德,垂钓洹上,静观时局,伺机复出。而为他暗地里运作此事者正是徐世昌,他实乃袁安插于清廷内的线人。1911年5月8日,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徐被授为协理大臣,该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地位仅次于总理大臣奕勖。按理说,换了别人,受此殊荣早就感激涕零,入朝谢恩了。徐则不然,他在日记中写道:“蒙恩授为内阁协理大臣,时艰任重,拟具疏恳辞。”第二天,他便上折请朝廷收回成命,并同另一位协理大臣那桐一道上书请起用袁世凯。对此举动,明眼人一看便洞悉个中缘由,如载涛便认为“徐世昌本是袁一手提拔的私党”,此举是欲逼迫载沣召回袁世凯。不过徐的过人之处在于,即使被人怀疑,却不留下一丝与袁来往的痕迹。载沣虽心中不悦,也奈何不了徐世昌,只得退回他的请辞奏折,命其留任。
不过袁世凯又岂是池中之物,终有卷土重来的一天。武昌首义爆发后,举国响应,清廷顿时方寸大乱。徐与袁心中早有默契,听闻风声有变,立即活跃起来,他联合奕勖、那桐,四处散播“收拾残局,非袁不可”的论调。载沣出于无奈,只得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让他主持大局。孰知袁世凯奉诏后,却故意徘徊观望,以“步履维艰”为借口迟迟不上任。这可急坏了徐世昌,他赶忙微服出京,赴彰德劝袁出山(一说是朝廷命徐世昌到彰德请袁复出)。此事在其日记中只字未提,可见极为隐秘。
看见徐老哥赶来,袁心知时机已到,遂接受任命,独揽大权。而徐世昌这边,则继续充当“内鬼”。可笑的是,清皇室居然依旧蒙在鼓里,先是破例赏赐徐世昌人值用膳之特权,后又授予他太子太保之殊荣,大有托孤之意。孰料徐并非妙手神医,实为催命郎中。正是他忙前忙后,打通关节,袁世凯逼清室退位的计划才得以进展顺利。甚至在溥仪的退位诏书上,徐也做了手脚。诏书末尾有这么一句:“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远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游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据《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云:
此诏实为有清一代之最后结束。原文系
由南中将稿电来,该稿乃张季直手笔,后经袁
左右增加授彼全权一笔而发表,其插入诸语,
于后发生不少影响,亦言民国掌故者所宜知
也。又末三语为天津某巨公所拟,末一语尤为
所称道,盖分际轻重,恰到好处,欲易以他语,
实至不易也。
环顾袁氏左右,籍贯天津且号称“巨公”者,似不过严修与徐世昌二人。严修虽与袁为至交,但其“公私分明,贞不绝俗,所谓束身自爱,抱道循义者,庶几近之”,堪称一代完人。故袁世凯对严实尊而不亲,非能与之共商大事。徐世昌则不然,他与袁患难之交,祸福与共,且身为太子太保,徐自然得以对退位诏书事先寓目,并有权提出增改意见。偷偷加入一句“私货”,绝非难事。通览此句,徐意在强调袁之政权乃取之于清廷,并非得之于民军。万一革命党人中途反悔,不兑现让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承诺,那么这诏书即为其食言之明证。也就意味着如果真到了那一步,袁世凯就可以“名正言顺”撇开革命党,单独组织新政府。徐世昌实在是老谋深算,棋高一着1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徐世昌在日记中仅淡淡的留下这么一笔:“今日奉旨宣布共和政体,组织临时政府。”
清廷在他心中之分量,可想而知。
或许不少人还在纳闷:身为堂堂的大清相国,荣华富贵、权名钱色皆已紧握在手,徐世昌何苦要助袁世凯搞垮清廷呢?此举于己于人有何益处?若是真的详加权衡,恐怕民初的徐世昌较之清末,似乎失去的更多。这当如何解释?对此民国掌故名家费行简的剖析堪称精到:
世昌,官僚也,其不欲改帝制为共和,情
也;以踪逖小臣数年即跻宰辅,其不欲清室之
亡,亦情也。而清室之亡,不亡于他人,实亡于
其总角论交、同膺显贵之袁世凯,以清较袁,
觉袁为亲,于是不得不割其向清之心以向袁。
且世昌固知袁最深者也,以其跋扈贪恣,断断
无实行共和的思想,特藉之为假面目以酬其
代清之宿愿,事成则面具脱而共和取消矣。是
临时之假共和于官僚党亦无所害,以是二者,
故清室之亡,帝制之终,世昌皆不甚措意,唯
壹志以助袁氏之成功……袁氏攫得此席,其
愿餍,而徐氏之愿亦餍。
兄弟义气大过天,帮袁世凯就是帮自己,这便是徐世昌的行事逻辑!
四
待到江山易手、袁氏当国之际,徐世昌这位功勋卓著的幕后卧底却没有走向台前,与老弟一同享受胜利果实,而是独自远赴青岛,俨然以清室遗老自居。当然,徐氏此举多有掩人耳目之意,以消弭世人对他助袁篡权行径之怀疑。实际上,在泡海澡、吹海风、赏海景、尝海鲜之余,徐无时不忘出山一事。一次,徐已故好友贺涛之子贺葆真前来拜见,曾提及出山一事。贺问:“此时公可在政界有所施为?”徐答曰:“现在政界诸公方事竞争,内容甚乱,宜少避之。”贺又问:“国事方棘,我公正宜有所尽力。今新进之士多无经验,国事将谁属乎?”话至此处,徐世昌借故转移话题,避而不谈。可见徐虽自称遗民,但仍对权力充满渴望。1914年,徐终于耐不住寂寞,就任袁政府的国务卿。
虽然深知袁世凯并不真心倾服共和,但一向自信对老弟知根知底的徐世昌,竞未发觉袁心怀称帝之意。1915年底,当得知袁世凯意欲复辟时,徐曾力劝他打消此念头。孰料这位老弟充耳不闻,一意孤行,徐只得辞去国务卿一职,暂隐田园。1916年1月26日,徐世昌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很耐人玩味:“世界上有三种有志之人:一为有志仙佛之人,一为有志圣贤之人,一为有志帝王之人。求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求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求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
想必此刻徐之内心当是万流奔涌,又恨又怕。恨的是袁世凯不听劝告,帝制自为;怕的是小老弟众叛亲离,不导善终。毕竟当初是自己甘作推手,亲手把袁世凯一步步送到了这万丈深渊的边缘。
孰料一语竟成谶。6月6日,当袁世凯于惊恐郁愤中撒手人寰的消息传来,徐写道:“数十年老友一旦怛化,为之痛哭!”
大概此时徐世昌的肠子都悔青了吧?呜呼!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