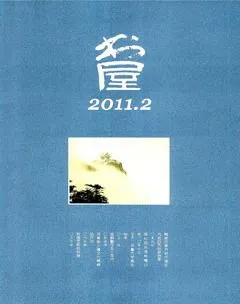神社招魂“靖国”难
2011-12-29赵刚
书屋 2011年2期
一
东京,1948年12月22日晚十一时,巢鸭监狱。
冬季的东京,细雨纷纷,气候潮湿阴冷。监狱外昏暗的路灯下,只有游弋的哨兵,看不出与平常有多大变化。但监狱内却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全副武装的美国宪兵,荷枪实弹紧张地守卫在各个牢门口。狱医正在给牢狱中的死囚做最后的检查,测呼吸、查脉搏、量血压……一丝不苟,如同往日。接着,监狱教诲师便与各个死囚进行了单独的交谈,让即将走上黄泉之路的囚犯,临终前认知和忏悔自己的罪孽。
按照东条英机临时提出的请求,监狱方为他安排了区别于以往法式面包与咖啡牛奶的和式饭菜。餐后,剃了光头,身穿灰色死囚服的东条留给监狱教诲师花山信胜博士一首和歌,权作绝命诗:“此一去,坐世高山从头越,弥勒佛边睡去处,何其乐;明日始,无人畏惧无物愁,弥勒佛边唯寐处,何其愁。”在此之前,他曾对花山信胜说过:自己也该死了,因为在狱中度过残生,倒不如死了好;知道死后可以超升到极乐世界,是可喜的。
十一时三十分,美国宪兵把将要执行死刑的囚犯分两批押进佛堂,要他们在各自执行绞刑的命令=B上签字,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武藤章陆续签名。
十一时五十分,在美军将领基南和韦伯的陪同下,负责监刑的美国代表西波尔德博士、中国代表商震上将、英国代表巴特斯克中将、苏联代表迪利比扬格中将等进入刑场。典狱长阿尼斯少校陪同他们在监刑席就座,一切准备就绪。
23日零点,被判处绞刑的七人分两批走上绞架。
二
为防止日后军国主义者借尸招魂,按照当时占领军的规定,对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尸体的处理是焚尸扬灰,火化后,骨灰将被美军飞机直接在天平洋上空抛洒。获得了这一消息的战犯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兴禅寺住持市川伊雄、军人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趁美军一时疏忽,将一部分骨灰偷偷从火葬场带出来。最初,他们将七名战犯的骨灰分别放在七个坛子里,在火葬场一角烧香祭拜。不料,这般鬼鬼祟祟的行径引起了美军的警觉,将骨灰坛没收,放回到后院的“供养蟓”。但三文字正平等人贼心不死,又趁圣诞节前夕美军戒备松懈之机,悄悄潜入火葬场,从“供养塚”中偷出骨灰坛。
这次,他们接受了教训,把骨灰直接送到被绞死的松井石根的老家,东京以南约五十英里外的热海伊豆山兴亚观音里,交给了一个叫做伊丹的农民,叫他们夫妇藏起来。直到1959年,三文字正平、飞田和市川才来到爱知县幡豆郡,在三根山腰买一块地,筑坟下葬,并且竖起一座高四米的“殉国七士”的石碑作为纪念,墓志由前陆相、甲级战犯荒木贞夫书写,并由当时的首相吉田茂题写了碑名。但好景不长,1971年12月,日本“赤军”打着“为东南亚死难者报仇”的口号,将这座“殉国七士”的石碑炸成了三截。
1978年10月17日,日本靖国神社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秋祭”时,把连同东条英机在内的十四名甲级战犯的亡灵偷偷摸摸地放进了靖国神社,或许是做贼心虚,干这样的事,连死者家属都没敢通知。直到1979年4月19日,此事被日本媒体揭露后,全世界为之震惊。
要说清这个问题,还需要从靖国神社本身说起。
靖国神社始建于1869年(明治二年),它坐落于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坂,总面积十多万平方米。靖国神社原名“东京招魂社”,是为祭祀自明治维新以来历次战争中的战死者而建的。1879年6月改名为靖国神社。“靖国”一词出自《左氏春秋》,在日文解释中有“安国”、“护国”之意。
自明治维新后,日本最终确立了近代天皇专制制度,并且迅速发展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走上对外侵2ae4de28b5d4bf79e65f47265139e7180fe3089aed40f9721021eb740324fc1e略扩张的道路。按照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处于国家权力中心,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集行政、立法、司法、外交权、军事统帅权于一身,换句话说,天皇是日本这部战争机器的最终操纵者。在这种集权专制统治下,日本国民的精神生活也得到了严密控制,通过对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以及学术自由的压制与禁锢,并通过各种宗教仪式及祭祀典礼对天皇进行百般神化,把天皇吹捧为集天地人神于一身的人间神物。正像英国著名学者、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英国研究院研究员埃里·凯杜利在《民族主义》中分析,自十九世纪以来,在大多数民族国家政府的资助和不断指导下,形成一个大众的公共教育体系,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制造忠诚,同质化民族成员。日本明治维新的先驱吉田松阴在其《士规七则》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五伦,而君臣父子为最大;生于日本皇国,就必须君臣一体、忠孝一致。历年来,通过不断地强化和灌输这一理论,在明治维新后,崇拜天皇、效忠天皇,为天皇效死,成为了日本朝野上下的共识,在蒙蔽日本人民充当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战争炮灰的欺骗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在二战期间,就在日本投降前一年,1944年4月1日,日本《基督教新报》曾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靖国的英灵》,文中鼓吹:“只有按照日本的传统,把英灵奉祀为神,才能体现血的崇高。在其他国家,为国家奉献的鲜血同样也受到尊崇。人们建造纪念碑,行人过往时向纪念碑脱帽,向死者致以诚挚的敬意。但是,唯有日本,将为国捐躯者奉赞为神,赋予血以崇高的意义。”可以说,靖国神社的信仰是与“战争”和“血”分不开的,其核心思想表达了作为岛国的日本,妄图实现“八纮一宇”即由“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完成“征服全世界,统治全世界”的野心。
要想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就需要把成千上万的士兵送上海外开疆拓土的战场,就需要把淳朴善良的百姓变成嗜血成性的杀人机器,侵略战争从来都是驱赶无辜的国民为当权者卖命的国家行为,每一个浴血征战的士兵都难以逃脱战死沙场的厄运。
从1874年侵占中国台湾起,半个多世纪,日本连续发动了九次侵略战争,平均每隔五年就要对外大举兴兵一次,不仅在亚洲,甚至在全世界都堪称是最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对此,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曾在1959年大言不惭地说:“如果吹吹牛的话,日本曾经威胁过太平洋一带,西起印度,东至美国,南至澳大利亚,北至苏联……其结果虽然失败了,但总之曾经在这个广阔的地区横行一时。在世界史上,迄今有过这样的伟大的丰功伟绩吗?”吉田茂这番话,确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的心理。
在靖国神社中,把战死者奉为“英灵”进行祭祀,而且无论生前军衔等级高低如何,出身多么低微,甚至人格道德方面有怎样的缺陷,只要是为天皇献身,死后就能够摆脱身份等级制度,不咎既往,成为万民瞩目参拜祭祀的“神”,这的的确确迷惑、欺骗许许多多的善良的日本人民。
在当时,由日本军方组织战争遗属到靖国神社参拜自己成了“神”的儿子、或是丈夫、或是兄弟的仪式活动,成为了日本人追求和向往的盛典,而“靖国遗孤”、“靖国之妻”、“九段母亲”成了时髦的流行词汇。但问题的要害是,国家之所以要彰显阵亡者,并非是出于人道,出于对参战而亡的将士们的哀悼与悲痛,而是为了准备下一场战争,动员人们像战死的士兵一样,“以为国捐躯为荣”,自愿为天皇牺牲自己的性命。
所谓靖国神社的精髓,不外乎三个方面:强调日本国民无条件地效忠天皇;要求“士魂商才”,即武士之魂、经商之才全要“忠君爱国”;崇拜战死,歌颂“玉碎”,号召把靖国神社当做国民的最终归宿。在这种所谓“靖国精神”的裹挟下,二战期间,日本国民全都被捆绑在天皇法西斯的战车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日本人对天皇的信赖感是靖国神社的基础,而靖国神社的思想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据靖国神社的资料统计,从十九世纪以来,日军阵亡的人数总计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七百八十一人。在这些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送命的亡魂。特别需指出的是在靖国神社中被祭祀而引起公愤的,是二战结束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的十四名甲级战犯以及约两千多名乙、丙级战犯。
三
作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及战败国的德国与日本,在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的反省和态度,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
通观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在八百一十五个字中根本就看不见“投降”二字,也没有承认过日本“战败”。对于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诏书中也是百般狡辩,说什么战争是为了日本的“自存”和东亚的“安宁”,日本仍旧以反抗欧洲白人统治、“解放东亚”的救世主自居。并且,裕仁在诏书中所说的战争是指自1941年开始的“已阅四载”的与英、美之间的战争,对侵略中国的行径根本就不置一词,对世界各国反抗日本法西斯的行为甚至用了“频杀无辜,残害所及”的字眼儿。
1945年8月14日,日本各大媒体都是在午夜接到裕仁的《终战诏书》的。第二天,几乎是不约而同各报都将“投降”说成“终战”。《每日新闻》的标题是“圣断:大东亚战争终结;颁布收拾时局诏书”:《读卖报知》则更加厚颜无耻,竟然以“为万世开太平”为题,声称“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自卫自存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东亚的解放和十亿民众的福祉”。
通过这个细节,不难看出,不仅仅是日本政府,就是日本社会主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仍旧摆出一副暧昧的姿态,缺乏深刻地反省、不愿诚恳地忏悔、只打算利用别人的宽容和好意推卸历史和现实责任。
正如二战期间的日本老兵东史郎所言:“当今日本,‘圣战’思想仍在盛行,‘不是侵略,而是从白人手中解放亚细亚’的怪论愈演愈烈,对历史毫无反省之心。日本军队在中国进行长达十五年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大批生灵涂炭,家破人亡。战争结束时,斯大林曾主张将日本一分为三+是蒋介石力排众议,保全了日本的完整;同样是蒋介石提出了‘以德报怨,不要复仇’的主张,使在华的两百多万日本士兵得以迅速回国,更不要一分钱赔偿。继而提出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的口号并实行的也是心胸宽广的中国人民。”
对过去这段全世界众所周知的不光彩历史,为什么日本会屡屡发生“暧昧的遗忘”?这种“集体的失忆症”究竟又是如何产生的?
多年来,对日本国民性的认识,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总以为历史上日本对外发动战争,仅仅是日本最高统治者天皇和一小撮战争狂人所酿造的悲剧,与广大日本人民毫无干系。充其量,日本老百姓只是受了蒙蔽。但是,如果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稍作分析,便不难看出这种看法的片面与幼稚。
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长、加腾清上侵略朝鲜,妄图迁都北京爆发的战争;公元1894年日本出兵侵占朝鲜,偷袭中国海陆军发动的“甲午战争”;公元1904年日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中国境内挑起的“日俄战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这些历史上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有哪一场没有得到过日本国民狂热支持和拥护?若没有多数日本国民的亢奋高涨的积极响应,这些战争能如此大规模地开展吗?
据历史资料表明:二战期间日本各党派对战争议案表决时,甚至连日本共产党也投过赞成票。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军向日本本土发起最后的攻击,在冲绳战役中,日本方面伤亡二十四万余人,其中正规的军人仅六万余人,将近十八万人则是普通的老百姓,这些老百姓为了效忠天皇所进行的“大东亚圣战”,宁愿自杀身亡,也坚决不投降。在英国人大卫·巴迪所写的《日本帝国的兴衰》中,记述了一个真实却令人恐怖的故事:二战后期,塞班岛之战,日军惨败。战役结束前,美军先遣部队发现,在岛的北端有几百名日本平民被困在海边的悬崖边,任凭日语翻译怎样劝说,他们拒不接受,要么跳崖自杀,要么拉响手榴弹自杀。一位日本妇女甚至将自己怀中的婴儿抛下悬崖,随后跳崖投海。美军攻打太平洋其他日本占领的地区时,都遇见过这样被称之为“玉碎”的集体自杀。
战后,日本政府追查战争责任,当时的首相东久迩曾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日本共产党也提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主张日本全体国民共同忏悔,但这种提法并没有得到多数日本人的认同。当西方记者对市民采访问及日本为什么被打败时,多数老百姓竟然回答,“日本还没有准备好”。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日本舆论在进行民意调查时仍发现,认识到过去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者不足百分之五十,而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进行者占了百分之五十;同意这场战争是“反抗欧美压迫,解放亚洲诸国”者竟然占了百分之四十五,而对此持不同意见者仅有百分之二十五。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一部电影在亚洲各国引起极大争议,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自尊》。影片描写的是二战被处决的战犯东条英机,它把这个罪行累累的战犯塑造成一位爱国者,但却遭到了同盟国不公正的审判。为了突出东条英机的正面形象,影片还把他描绘成在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中,直到被处死的一刻,都保持着自己和国家的尊严。对于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影片借东条英机之口竟然说:“所有的证据只是听来的证据,不能称之为证据,而且夸大其词。谁会相信他们(日本士兵)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甚至随意杀害妇女和儿童。”就是这样一部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歌颂杀人犯的电影,在日本竟然得到热捧,在放映的头一年就获得一点六九亿美元的票房收入。
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也提出了所谓的“纪念终战六十周年”。日本电影界煞费苦心,选择了在二战中被美军击沉的日本战舰“大和号”作为题材,不惜投放二十五亿日元巨资,并且动用了大批日本海上“自卫队”参加拍摄。同年12月17日正式推出了电影《男人们的“大和号”》,影片一放映,立即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据日本媒体报道,这部电影放映当日,全日本有三百二十四家电影院同时上映,有十二万多人观看。有些年轻人深夜排队等候入场,有的地方座位不够,一些观众就站着看。在影片放映过程中,“观众鸦雀无声,惟一的声响是一些人低沉的啜泣”。放映结束后,不少观众特别是“中老年妇女在离开座位时,脸上依然挂着明显的泪痕”。不少日本人为影片中那一幕幕血腥的战争场面激动不已,为“大和号”上的日本海军将士拼死战斗而挥洒热泪。日本各大报纸更是竭力渲染,电视屏幕上充斥着相关广告,该影片的票房收入高达四十三亿日元。
而反映历史真相的电影《南京大屠杀》在日本上演时,却只有少数屈指可数的电影院敢于播映。这与歌颂和鼓吹日本军国主义的电影《自尊》、《男人们的“大和号”》,形成了巨大而鲜明的对照。在东京,一些右翼分子甚至冲进一家播放《南京大屠杀》的影院,割烂了银幕,阻止电影放映。
据日本《读卖新闻》1982年的舆论调查,将侵华战争看作是侵略战争者不到十分之一。许多日本中小学生在看了《山丹之塔》、《听,冤魂的呼声》这类反战题材的影片时,不但不从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角度来欣赏,反而情不自禁地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打胜下一场战争!”“此仇必报!”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水均益也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他在日本进行采访时搭乘过一辆出租汽车,他希望能对出租司机进行现场采访。然而,无论水均益怎样问,这位司机总是摇头,不做任何回答。无奈之下,水均益和摄影师只好下车。下车前,水均益在递给司机车钱时,他这才开口嘟囔了几句日文。当天晚上,水均益让从大阪来的朋友观看这段录像。谁知,这位朋友看过录像后,破口大骂:“我操他妈!”
原来,摄像机所摄录下日本司机的原话竟然是:“这两个来采访的中国记者真讨厌!为什么当年大日本皇军不把这些中国人都杀光了!”
四
日本之所以掩盖侵略、逃避历史、拒绝反省、缺乏忏悔,绝非只是少数统治者所为,而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需要指出,日本的文化传统,在这方面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巨大的影响作用。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在十七世纪就曾对日本的文化特征做过总结:他们“顽固、任性、刚毅、古怪”,同时又“不把一切危险和灾难放在眼里”。孟德斯鸠认为,日本的立法精神是残暴的,他们相信只有更严厉的残暴才能驾驭残暴。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的《菊花与剑:日本文化模式》一书中也曾分析到:“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的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迥然不同。”“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这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日本民族对内可以表现出菊花般的风情,人与人之间讲究和谐、尊重。然而对外,他们则表现了剑与火的风格,霸道十足且充满攻击性,毫不顾忌世俗的道德和法律标准,所追求的目标只是进攻与征服。
若进一步分析,造成日本国民的这种近乎于偏执和狂热的民族情绪,其实是日本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在国家意志下被扭曲的结果。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资源贫乏的岛国,险恶、封闭、孤立的自然环境就需要有一个信仰或宗教使全民族团结起来。自明治利代,日本政府便煞费苦心地将原本属于民间,并无统一神祗的“神道”改造成为“万世一系、神圣皇国”的国家意识,天皇成为“神国”最高的象征和至上的荣誉。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在各个地区普遍设立崇奉皇室祖灵的神社,并且通过专门的礼仪、周全的祭祀,将参拜活动制度化,其结果,这种原始的宗教崇拜,通过国家意志演绎成主流文化深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成为了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至今仍在发挥着影响作用。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武士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和非常独到的作用。在武士文化中,忠君是最重要的精髓,真正的武士要勇于为国捐躯,为君殉死。只有这样死才能够体现其荣誉和价值,并被后人供奉为“护国英灵”,否则就是“犬死”(在日语中的含义就是死无代价)。明治维新之后,武士文化便通过国家意志,逐步演化堕落为替天皇尽忠、为军国主义卖命的武士道精神。
早在1911年,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河上肇就曾在《日本独特的国家主义》一文中揭露:“现代日本没有宗教上的烦恼(尽管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本应产生许多宗教上的烦闷),绝大多数人是坚定不移的国家宗教的信徒。对他们来说,国家就是人生的目的,为国家而生、为国家而死是他们的理想……国家主义已经成为日本人的宗教。所以,看呀,为国家主义而牺牲的人,死后都被当作神来祭祀。靖国神社便是如此。”当杀戮所带来的暴戾和残忍化成了士兵的忠勇,屠杀所带来的斑斑血迹化成了妖艳的樱花之美时,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以砍掉平民百姓的脑袋为乐趣的“百人斩”比赛,那些在太平洋战争中,以“自杀式攻击”为荣的神风特攻队的变态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正因为日本是一个特别强调爱国心与民族主义的国家,二战战败的历史在许多日本人心中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日本所谓的“神道文化”本质上就是“耻感文化”,它将失败与公开认罪视为一种耻辱,主张拼死保全面子。因此,对于中国人所强调的“有错知改,善莫大焉;只有分清是非,才能修复关系”的原则,日本人就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思想家本居宜长就主张“淡化人与人之间的是非判断,因为是非判断会阻碍人际关系的修复。况且是非是说不清的东西,没有绝对的是和绝对的非”,他的这一主张可以说是日本人普遍接受的是非观。持有这样的是非观会认为,坚持分清是非,必定会把一方推向“非”的境地,而日本人是绝不能把别人或自己推到那个境地上去的。因为,错是无法悔改的;断定别人做错了,就等于把人推到那个称之于“非”的万劫不复的境地。一旦落入这样的境地,是不容任何争辩,也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所以也就不存在任何可以被宽恕和原谅的情由。自我救赎的唯一出路就是切腹自杀。所以,在真正的错误面前,日本人不能认错,也不能代表别人认错。于是乎,回避是非判断就变得至关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日本政府道歉问题迟迟未能真正解决的文化根源所在。
可以说,日本国民对于战争罪责的认识,有着漫长而曲折的历程,至今仍旧未能有全面而深刻的自我反省。早在1952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判决不久,日本就爆发了规模浩大的请愿活动,要求赦免战犯;在日本律师联合会提交给政府的“战犯赦免意见书”上,竟然有高达四千五百万人的签名。1957年底之前,按照日本众议院通过的决议案,将甲、乙、丙全部战犯释放。耐人寻味的是,最先得到释放的竟然是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1963年,日本国会通过《对战争伤残病者特殊援助法案》,把东条英机等已经处死的战犯确定为“公务死亡”(即中国人所讲的“因公殉职”),并向他们的遗族发放抚恤金。
在释放战犯的同时,日本国内对靖国神社参拜也逐步升温。从东京审判后,对靖国神社参拜的日本首相有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方、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小泉纯一郎。至于自民党党魁、日本国会议员参拜者更是如过江之鲫。
据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所著的《靖国问题》这本书中记述,在日本国民的心目中,靖国神社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精神象征,同时也是作为记载大和民族在天皇的感召和激励下,开疆拓土,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的历史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日本在军事上遭受到惨重的失败,但是以“神道”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并未被根本触及。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被扭曲的文化传统下培养出来的日本人,还能够客观地看待历史吗,还能够冷静地对自己的过失与罪责进行深刻地反省和诚恳地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