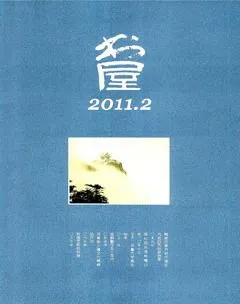诸教同理 力行证道
2011-12-29柯倩婷
书屋 2011年2期
“咸同中兴”名臣曾国藩功业与学问显赫,治家、教子也常为人称道,其家族克勤克俭、爱敬如仪,不信僧道,尊奉儒家之仁义道德。然其子辈、曾孙辈却一反家传信仰,或佛、耶同礼,或崇拜基督,是时代使然,抑或心性所向、机缘巧合,还是承续“三教同源”理路而别有新解,颇值玩味。辛亥革命那年的圣诞节,其曾孙女曾宝荪在杭州圣公会受洗,成为基督徒,这是曾氏家族的一个“异数”。时年十八岁的曾宝荪作此选择,给她日后的思想、职业与人生选择涂上浓重的宗教色彩。她于1912年到英国留学,成为第一位获得伦敦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的中国女性;1918年起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蓄志献身教育事业,传播基督精义,品德与操守犹然有其曾祖遗风,成为现代女胜的佼佼者。
一
在进入女校读书之前,曾宝荪在祖母郭筠的主持下学习。有家塾先生的耳提面命,她研读背诵《千字文》、《诗经》、《论语》、《左传》等典籍,兼修国文、史地、绘画、作文、日文等课程,她在封闭的环境里读书,基督教对她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倒是湘乡富厚堂独一无二的大书房,让她可以饱览小说方技之书,佛学与道学也有所涉猎:
麻衣柳庄等相法书,命学津梁,渊海子平
等算命的书,甚至如《遵生八笺》以及讲修炼
的书,都一一翻阅……咒偈也学会几个,用来
辟邪祛鬼。乡下人极迷信,从我房到书房要经
过一段长廊黑巷,我夜晚走过,总要念《心经》
偈语,这也许是我宗教观念的起头吧。
年少时读道家和佛家的书,未必有深刻的领悟,但宝荪富于实践精神,坐言起行,她从小就显示领导才能,与同辈读书之余,“教他们练气打坐,并虔祀帝君,颇多神道思想”。这一段儿时生活,一生支持她办教育的其弟曾约农津津有味地回忆道:
光绪二十八年,姊至南京,余及威谋,奉
为领袖。姊乃倡神仙修炼之法,谓龟寿千龄,
其诀在息。果能龟息,则不独祛病延年,且神
仙可企。于是我辈,每于背人处,闭目凝神,从
事龟息,谋以耳目皮肤为呼吸之道……吾姊
既娴八卦五行之说,吾辈复大奇之。…
为了显示龟息的奇迹,宝荪说服约农拿出练武的宝剑,杀一鸡,埋于香蕉树下,请龟息之神为之超度。第二日,土堆开裂,鸡已失踪,众人相信鸡已得道成仙,其实是饥饿的童仆挖起来打牙祭了。曾约农感慨道,宝荪的巫法与日后做教师,一脉相承。
曾宝荪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她信基督教的过程,其中两个发生在杭州冯氏女校的故事,已为人所熟知。其一,宝荪办“竹头木屑”小报批评学校,巴路义校长并未责难她,而是跟她一起下跪祷告。其二,司徒女士全家被乱民所杀,她也被刺伤致残,但她在宗教大会上受圣灵感动,以爱化解仇恨,继续在中国教英语。两位老师的真诚爱心,是感化与榜样之力。但基督教如何契合她内在的精神需要?她杭州读书时:“有一日游西湖、到了岳坟,不觉感到人世的不公平;看到苏堤、白堤,苏小墓等,又感人生的短促,到底人生在世有何意义?古人说:‘生为尧舜,死为枯骨;生为盗跖,死为枯骨。’那‘人’又何必做好呢?……又回顾我国国势的衰弱,更加不知所以。”
曾宝荪无法解答这些关于社会公正、国家民族存亡、人生价值的大问题,她回去向巴路义校长倾诉,亦未能得到满意的解答。但巴师真诚地理解她的困惑,与她一同查经、祷告,让她感到了切实的温暖。曾宝荪游西湖,竟有如此深沉的感动,触发“人生为何”之感慨,足见大自然与历史人文景观也能引发宗教体验。
曾宝荪是世家子,幼年时随父母住在北京,戊戌政变后返同湖南,后又随家人到过湖北、南京各处居住,本应见多识广。但她家庭管教甚严,游山玩水是绝无之事。后来,她到上海读书,也如《子夜》之吴老太爷,感受到现代城市的强烈冲击。“我们真是初出茅庐的土包子,加之我家世代俭朴,所穿的衣服都简陋非常,到此十里洋场,实在自惭极了”。乡村与城市、中国与西方、国学与西学、儒释道与基督教、改良与革命,那代人普遍感受过的文化冲突,曾宝荪一一迎面碰上。
细读她回忆富厚堂风俗的章节,她是置身其外的。曾家虽然让女子读书,但风俗惯例是男女有别,亦需严守。春节后,家塾开学前一日请先生吃酒席,由男主人及男学生陪,女学生不陪先生吃饭。盛大的祭祖和祭灶由男性主持,中秋拜月是女界的事,所谓“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清明扫墓,也是男孩们的事,女性的生活主要是在家中。家族中的男人妻妾成群,宝荪的父亲玩遍花街柳巷,娶了五房妻室。不少女性因生育而死亡。她感慨道:“在这样的家庭里,旧礼教之深,旧风俗之重要,要一个女子来摆脱,是很不容易的。”
曾宝荪在上海务本女校读书时,也接触到革命思想。师姐张昭汉(后改名张默君)读师范二年级,她已于1906年成为同盟会会员,小十岁的曾宝荪与这位湖南同乡十分投契,乃至后来到了杭州女师读书,依然受其影响,然而,曾宝荪选择了与张默君、秋瑾等革命志士不同的路。多年以后,曾宝荪与张默君于1946年国大代表竞选中较量,有学者解读为乡绅势力战胜了富于政治经验的实力派张默君;也有学者解读为曾宝荪并未远离政治。曾宝荪的回忆录则只有一言解释:“那时张默君原定不竞选国大代表,竞选立法委员。”不过,她亦不讳言,她能胜出,乡绅出力至大。这里还想说的是,秋瑾于1907年身殉革命,她的女儿王灿芝后来在艺芳女校读书,宝荪对她管教甚严,但灿芝秉承母志,性格刚烈,志向与宝荪格格不入。
曾氏家风温良,几代人之间其乐也融融,曾宝荪在情感与物质上均无大匮乏、大冲突,她精神上得到父亲(曾广钧)的支持,不缠足、不定亲、准许人基督教和出洋留学;学业上得到七叔父(曾季融)的帮助,到上海及杭州接受新式教育;经济上得到三表叔(聂云台)的资助,留学的部分费用由他支付;事业上有二弟曾约农和恩师巴路义等人忠诚追随、无私支持,她不像“五四”时期的那一代人,无需背叛家族来确认新的身份。
二
1912年4月至1917年10月,曾宝荪在英国求学,这是她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当时女留学生非常少,最早一批女留学生金雅妹、许金訇、康爱德和石美玉,倒是与宝荪有共同之处,由传教士带出国门,婚姻失败或不婚,没有子嗣,为工作与宗教事业奉献一生。官派女留学生方面,1905年,端方派出了中国第一批二十名留日女学生;1908年,他派出了第一批留美女生。当时,也有女学生到英国留学,但选择理科并获得伦敦大学学位的,曾宝荪是第一位。
曾宝荪抱定的志向是“为我国谋发展谋幸福而读书”。科学救国是当时知识界最普遍的信仰,曾宝荪也一样,她大学主修了生物学,辅修数学。五年游学,曾宝荪参与了各种宗教活动,“深深感到社会改良,非有基督教的精神不可”。她相信科学与宗教均是救国之重要途径,两者同等重要。正如孙尚扬所言,“在这些归信基督教的曾氏后裔的心目中,西学与西教的结合才可以救中国,换言之,他们赋予基督教以拯救中国的功能角色”。
曾宝荪笃信基督教,是深受巴路义老师的爱心感动。巴师为了陪伴她读书而放弃了圣公会的教职与退休金,又随宝荪回国办学,在艺芳担任教师,直至生命终结。宝荪与巴师的友谊很深,情同母女,然而,在践行教义方面,她并不完全遵循巴师的路径。据曾约农描述,巴师“信教极笃,为新教之守旧派”。曾宝荪则乐于接受开明的宗教思想,“我们为人行事模仿耶稣,就是基督徒了”,冯莉维女士的这句话,让她茅塞顿开,也为她后来探索“基督教中国化”开启了新思路。
曾宝荪在英国拜访并结识很多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践行教义的方式各有精彩。在那些她仰慕的女性中,有多位坚持独身的,如巴克女士照顾母亲到一百岁,获女皇奖贺;巴路义和冯莉维女士全身心投入社会工作和传教事业,费尔士博士的三位姑姑都不嫁。曾宝荪的独身主义,应是以她们为榜样的。她的同辈中,曾约农、曾昭桦、曾宝菡、曾昭燏都不婚嫁,曾宝荪的带头作用至巨。曾昭炳于1935年写信报告她选择了考古专业,并谈到:“妹在此遇三姐之前后同学数人,皆盛言三姐之天才并问近状,妹一一告之,妹常自念,以三姐之学问才能十倍于妹,为艺芳终身牺牲,妹何以不能。”㈣曾昭熵为考古事业奉献终身,亦不婚。
曾宝荪初到英国时,英语尚不通畅,待到一年后入读大学,已经陆续可以传道,在学校又被推举参加演讲。她以“科学对人生的贡献”为题,演讲相当成功,并由此获得校长的赏识,支持她回国办教育。她想要办一间纯粹中国人主持的基督教学校,理由是:“教会学校不是不好,但我想基督教若不纯粹中国化,则中国人总不能接受它,使它成为自己的宗教,如佛教一样。”
曾宝荪萌生此志,并决意践行,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关于基督教徒是否应该反战,宗教界有深入的辩论,曾宝荪亦由此思考宗教与战争、宗教与世界的关系,结论是:反对战争是符合耶稣精神的。同时,基督徒为国运祈祷之虔诚、理性与有序,让宝荪看到了希望——如果中国人能接受基督,注入理性、身体力行、爱人如己之精神,应有助于文化之改良。
那年寒假守岁,她与约农相约,“立志贡献自己为国家、为世界致用”,这志向就是办基督教学校。她赢得了伦敦大学西田书院校长及其友人的帮助,募集资金,聘请教师。她也通过书信与中国的同学、亲友联系,寻求帮助。她曾致信表姐萧孝徽:“再二三年,荪将返国办教育,姊幸助一臂为要。”足见宝荪筹划甚早。回国后,她拒绝表叔聂云台的建议去接管上海的启秀女子中学,皆因其志已明,当不旁骛。
三
1918年9月,艺芳女校开学,一办就是三十年,其中经历三次被毁、三次复校的艰难坎坷。艺芳崇奉基督,但不隶属于任何教会,保持了它的独立性。宝荪认为,很多教会学校无法引起学生对宗教的兴趣,办学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是与中国风俗人情相隔离,跟传统的文化精神找不到契合点,从而不能融入到中国社会中去。与教会学校严格的仪式不同,艺芳不勉强学生去礼拜堂,周末学生可以回家住。在课程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西方科技文化知识结合起来。
艺芳女校践行基督教的精神,救人济世。遇到自然灾害,艺芳学生用各种办法筹款,据《艺芳》校刊的新闻报道,施衣、募捐是学校经常办的活动。五四运动时,艺芳学生成立十人团,抵制日货,严格执行,一以贯之,坚持到抗战才结束。艺芳反抗日本的侵华政策,但相信民众是善良的,只是受了政府宣传之蒙骗,1923年日本东京地震,艺芳也为灾民捐款。
曾宝荪从信奉基督教到办基督教学校,她特别关切的议题是“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在艺芳,她倡导学生自主和自治,希望学生“能欣赏中国文化,又能具科学精神”,能“崇信基督,又不忘记孔孟之道”。1935年9月,她受上海青年会的邀请,到全国十二个城市的中学与大学巡回演讲,主讲“文化教育与宗教的关系”,历时三个月。所到城市,均有当地的教育官员、校长或知名教授接待,可见此次演讲很受重视,颇有影响力。
曾宝荪是教育家,亦称得上是宗教活动家。在英国读书时,她参加学生自献运动、贵格会的会议、在小型的宗教聚会中传道。1928年,她到耶路撒冷参加世界宣教会会议。1938年,她第二次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会议,会议设在印度的马德拉斯基督教大学,会议结束后,她随即到英国布道,并在各地演讲。她与上海青年会联系密切,积极参与演讲、翻译教材、出席慈善活动等。1951年到台湾后,她加入中华妇女祈祷会,每月开例会一次,每年开年会一次,讨论及安排全年工作、聘请传道人等。同时,她经常受邀到宗教团体和学校演讲。1970年台湾教育文化局编印了其演讲集《妇女对文化的贡献》。
传道要深入人心,需要解决宗教道德与世俗道德之间冲突的问题。曾宝荪直面这些现实的冲突,并对宗教道德保持反省的姿态。她早年认为,基督教应反对战争与杀戮,然而,八年抗战让她明白:为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而杀戮,是合乎道德的;如果以基督教反战精神为借口而逃避,是懦弱的表现。基督教珍视婚姻、家庭与传统文化,她听说英国的亿东贵族学校一半学生的父母离异,看到很多在国外的中国人任由子女弃学汉语及中国文化,她都非常疼惜,严加批评。也因秉持着这样的道德观念,她在1919年拒绝了哲学家罗素到艺芳女校演讲,理由是已婚的罗素与同行的勃拉克女士婚外同居。后来,她到英国,罗素不念旧怨,支持她申请庚子赔款,宝荪亦赞扬他是有修养的大学者,她不以僵化的宗教道德衡量人。
曾宝荪出席两次世界基督教大会,感触最深的是“只要有耶稣的爱,不分国界、人种、语系,全世界可以如兄弟姊妹一样的相亲相爱”。而宗教最重要的两个目标是:“一个是物质文明不能离开宗教道德;第二是以前传教的都不免看异教为大敌,近来印(印度)看出极端的唯物哲学才是宗教的大敌。”极端的唯物沦把物质置于绝对第一位,否定唯心论以及超验的宗教体验,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所以是大敌。
基督教是一神教,很多传教者视别的宗教为大敌。曾宝荪不持此论,她在《实验宗教学教程》中提出,诸教同理,宗教的经验是相通的,天、神、人一理,都是追求“天人合一”。
在英国时,她参加贵格会的聚会,有时是长时间默坐,静候圣灵的指导。习惯读经、讲经、祷告的同学,对此时有讽刺。宝荪却从中获益良多,感悟到的是天人合一,并由此想到“朱夫子也主张静坐,佛教更是提倡静默,甚至闭关多日”。
曾宝荪在山西演讲时,曾拜访过虔诚的佛教徒赵戴文先生,一起探讨佛教与基督教相似之处:“耶教由信称义,是自诚明;佛教是由大智启信,是自明诚,所以两者相通。”简言之,佛与耶都是让世人明道,明事理。在她家族中,有佛、耶同拜的前辈,她的祖姑母曾纪芬于1915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来又参加聂家每周一次的佛学会,亦佛亦耶,取的是两种教义都倡导博爱、俭朴和施与。
曾宝荪认为,基督教要发展,一定要与不同的文化融合。她这一思想的形成,也深受著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影响。李氏曾在中国传教,任山西大学校长。他赞美中国文化,并对如何沟通中西文化有独到见解。宝荪在英国时多次拜访李氏,非常推崇他“天下一家”的思想,盛赞他在《中国的四百兆人》提出的各国合作的方法,它竟与后来的联合国的理念不谋而合。有趣的是,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并不支持李提摩太的布道与赈灾工作。但李氏并未向宝荪提及那些过节,只说“同时赈过灾荒”。
曾国藩以反基督教而闻名天下,曾氏家族素以儒教持家立业。但曾宝荪并不认为信基督教是背叛家族。对她来说,恪守温良恭俭让,就是曾家的孝子贤孙,爱国爱民就是合格的中国人。她深信,诸教同理,其教义都是引人向善;得了开悟,就应努力践行,以力行来证道,利民救世。纵观她的思想与人生,事业上有过大挫折,思想上却没有大危机,许是得益于她对自己身份的确信。1926年的“四八”事件给她带来深刻创伤,“身负土豪、劣绅、地主、封建余孽、帝国主义走狗……等等罪名”,成为众矢之的,也没有改变她的志趣与信仰。
四
1934年,曾宝荪编译、出版了《实验宗教学教程》,这本书是上海青年会主持出版的“青年丛书”第九种。她的任务是翻译,最后却对原文进行了大量增删,原因是:“一,因为书上的引证,纯是外国的诗文事实。二,它整个的背景,都是西洋基督教的国家与文化。有了这两个困难,我便不惜割爱,把它的引证事实,能改的都改成中国的。同时也用儒释的精神来陪衬,使全书不致完全没有中国的背景。”
此书的英文版是由美国芝加哥圣经学校出版,但中文版已难见原著面目,也未提及原著的八位作者,算是一本编译之作。这本小书,再版两次,1948年出第三版,可见不乏读者。据序言介绍,有些教会学校的查经班以此为教材。
《实验宗教学教程》分八章,每章有三个部分:“准备”、“例证”和“讨论”。八章分别探讨由“自然”、“美丽”、“挣扎或奋斗”、“忠心于一种事业或主义”、“打破难关”、“愉悦”、“天人合一”、“团契或教会”中得来的宗教经验。
以第一章“由自然得来的宗教经验”为例,“准备”部分提出了十一个问题,以启发读者回顾面对大自然时的体验与思索。“例证”部分先阐述中国上古的神话及神明观念:
中国邃古时代的民族,看见山川的伟大浩瀚,因而生出神明的思想,到处致祭……古人起誓,必定要指山川河岳日月等物,例如晋公子重耳指河为誓,说“有如白水”;《诗经》上说:“谓予不信,有如撽日”,都是隐藏着大自然是神道,不毁不灭的思想。
作者继而摘录王维与苏轼的诗句,阐明诗人如何透过对大自然的描摹,来表达“万物有灵”、“人与神接”的宗教体验。
“研讨”部分针对宗教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其一是科学家的宗教体验,书中列举西方科学家为例证。科学家多以研究物质世界来探玄寻理,但他们普遍认为,只有更大的神明的精巧创造,才能解释他们所发明之规律或原理。其二,人类对神明的理解也逐渐变化、进步,早期人们认为神明也跟人类一样会有偏私,后来逐渐明白,神明是普遍存在的。曾宝荪援引了《史记·秦始皇本纪》、《晋书’苻坚载记》、伏琛的《齐地记》中的故事来阐明,中国古人认为神如人形,丑神也羞见帝皇。
《实验宗教学教程》引述了大量文献,以中国的历史、神话、诗歌、哲学等典籍来诠释宗教经验,贴切有理、分析精当,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实践之一。
第七章“从天人合一得来的宗教经验”要在此作特别介绍。曾宝荪在多个场合用“天人合一”这一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概念来描述宗教经验,是她融通中西文化的典型例子。在此章的“例证”部分,她详细讨论了儒释道如何理解“天”、“神”与“一”。她列举了《尚书·大禹谟》、《中庸》、《论语》、《诗经》、《孟子》、《二程集》等儒家典籍,以阐明“法天”、“与天合德”、“与道配义”的道理。试举二例如下: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道心怎样“惟一”?由这“惟一”上面,便知宇宙问必有一种大和谐,必不许有根本矛盾。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心是与道心相合的。
《文王之什》又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信孚。”郑笺云:“天之道,难知也,耳不闻声,鼻不闻香臭。仪法文王之事,则天下咸信而顺之也。”这明明是认定文王一举一动,都合乎天道,所以不能效法无声无臭的天者,可以效法文王,可见文王在诗人的眼光中,已与天合德。在《诗经》中,这样的证据多得很。
在曾宝荪看来,儒家把“天”看做是最高的德行、义理、道的代表,这也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近乎宗教的体验。儒家的“天”与基督的“神”是一理,对于人与天、人与神的关系,各门各派诠释不同,但其理相通。接着曾宝荪论及道家与佛家,《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强调“一”与“道”的重要性,这与基督教的一神论是相通的,都相信微妙的宇宙世界必有一最终的主宰;佛教认为“万有由我一心所造,万象唯心,万法唯识”,也是“天人合一”之理。实际上,宝荪借用基督教义来回应“三教同源”的古制,并在中国文化的老树上开出新枝,别开局面。
至宝荪信教之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已数百年,却一直没有真正融入中国的文化。面对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教义与文化,曾宝荪通过办基督教女校、演讲、宗教活动和编写教程等活动来普及,工作的重心是本土化、中国化。她自始至终认为,基督教应中国化,才可能感化中国人,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实验宗教学教程》只谈及儒释道与耶教共同之处,强调诸教同理,而对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没有着墨,但对于一部旨在供查经班使用的教材而言,已是难能可贵。当今,西方理论大量译介到中国,生吞活剥者有之,不求甚解者有之,面对西方文化的殖民,很多学者也深感愤怒与忧虑。曾宝荪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融汇西方文化的做法,时人可为镜鉴。
(曾宝荪:《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
注释:
[1][4]曾约农:《回味录》,载《艺芳》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收录于《民国珍稀短刊断刊》湖南卷三十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15101页。
[2]潘崇:《端方与清未女子留学教育》,《文史知识》2010年第3期。
[3]孙尚扬:《曾国藩家族与基督教》,《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5]曾昭燏:《曾君昭燏由英国来信》(8月30日发),《艺芳》校刊,第三卷第1期,收录于《民国珍稀短刊断刊》湖南卷三十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15060页、
[6]萧孝徽:《有志者事竟成》,《艺芳》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收录于《民国珍稀短刊断刊》湖南卷三十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15104页。
[7]曾宝荪在回忆录中记载这次巡回演讲是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但对照《艺芳》校刊的新闻,是1935年,撰稿者是高一的张成智,所列十二个城市与回忆录所述完全吻合。鉴于新闻不会记述未发生之事,应是曾宝荪记忆有误。
[8][9][10][11]曾宝荪:《实验宗教学教程》,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初版,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三版,第1、3、7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