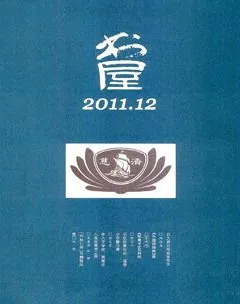《外国诗辞典》序
2011-12-29彭燕郊
书屋 2011年12期
诗歌在人类文化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历史学家早已发现,人类在蒙昧时期就自觉地用诗的灵感来证实自己的智慧、尊严和文明进程。每个民族都以诗歌艺术的发达表示精神素质的优越,表示他们绝不迟钝、粗野。诗不但是文学的元素,而且是所有艺术创造物的元素,是最困难的、同时又是作者最多的一门艺术,几乎没有一个人一生中从来没有过“诗兴”,在生活中最激动、最难忘的日子里,有谁不曾为诗的谜样的魅力所陶醉,不曾像个诗人般地吟哦过呢?诗歌文化从来就是人类的骄傲和共同财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交流的增进,兴起于五四运动、始终处于世界诗歌大潮流中的我国新诗,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诗歌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人们从更加广阔的视野里了解各国诗歌的历史现状的要求,更加迫切了,这是十分自然的。一方面,作为诗歌古国的我国对人类诗歌文化曾经有过辉煌的贡献,对其他民族的尊重历来是我们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多年封闭之后,我们发现我国诗歌文化和当今世界诗歌文化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发现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用好我们的才能,跻身于当代诗歌先进行列的紧迫感,和由此而产生日益旺盛的求知欲,正是我国诗歌文化腾飞的征兆,这是使人兴奋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编撰了这部《外国诗辞典》。
我们认为,作为一部专业性辞典《外国诗辞典》,它和一般文学辞典的不同之处应该是:尽可能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以外的世界诗歌文化过去和现在不断积累起来的、本领域知识中读者最需要掌握的重要和精粹部分,以详尽的但经过严格选择的词条,通过尽可能简明扼要的释文,将人类诗歌文化广泛的、丰富多彩的现象,经过浓缩提供给读者,为读者在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尽可能准确的答案或可靠的线索。我们的愿望是使它成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要,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咨询工具书,不但适用于诗歌创作者、文学和诗歌研究者,也适用于文学和诗歌爱好者。
我们认为,我们的设想应该首先体现在这部辞典内容的广泛性、它的收录范围上。它应该包括诗人、名著名篇、重要事件、重要出版物,诗歌团体、流派、诗歌奖等,尽力做到不遗漏、不重复。从地域上说,它的覆盖面应该遍及中国以外所有地区。我们唯一的取舍标准是:凡属有价值、有意义的诗歌文化现象都应该收录。不论大国、小国,不论其诗歌文化积累情况有多大不同,它们都曾经和正在以各自的独特成就丰富了人类精神宝库,因而都应该受到重视,不应该以这个国家的情况要求另一个国家。从语种上说,不应该只注意英、法、西等大语种,而忽视其它语种。我们还注意到对世界各地华文诗歌的介绍。我们认为,各国华籍、华裔诗人用华文创作的华语文学应该和诸如英国以外的英语文学、法国以外的法语文学、西班牙以外的西语文学那样受到同等重视,虽然目前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它还处于开创阶段。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中国文化的飞速发达,世界华文文学地位的日益提高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我们还认为,不能以世界性大诗人为标准要求所有的诗人,凡是在各国家和地区得到承认、有一定影响和成就的诗人都应该收录,事实上我们需要了解的往往不只是人所共知的大诗人。人类某一历史时期诗歌文化全貌也不可能由某一位诗人来代表,虽然他的成就显示了诗歌史上某一时期的高峰。我们的认识基点是:世界诗歌所体现的首先是全人类对诗的本性和素质的共同认识,共同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诗的把握并通过诗的艺术创造实现的、对现实认识的深化和人自身品格的提高,达到推进现实发展的共同愿望。其次是由于各自不同的现实社会和精神生活发展历程形成的、不同的现实和爱美经验形成的不同的把握现实生活中的诗,并加以艺术创造的特长。世界性是实质性的,地域性是派生性的,因此,以某个地域为中心或以某个语种文化为中心都是不可取的,非科学的。
这部辞典的辞条以诗人为主,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离开诗歌文化的直接创造者,就很难具体、深入了解丰富多彩的诗歌文化现象。其他辞条也同样与诗人密切关连,名著名篇是诗人写出来的,诗歌史上旳大小事项都与诗人有关。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不把这部辞典编撰成单调的诗人人名录,我们希望它能成为或接近于成为一部“横向”的诗歌史,世界诗歌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丰富成果和经验在这里应该从众多角度得到反映。在辞条设置上,我们遵循的主要是这些原则。
在详尽程度上,我们既重视古代诗歌,也重视现当代诗歌。古代诗歌有过光辉的成就,上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现代诗歌的发展更加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时限上我们尽可能延伸到当代,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速度是这样快,诗歌领域的新思潮、新流派不断出现,一部鲜为人知的作品很可能突然震动世界,一个默默无闻的诗人很可能一下子誉滿全球。我们的愿望是尽可能迅速地反映新的现实和现实提出的新的问题,不致于让人觉得这是五年、十年前出版的过时的出版物。我们对东方(阿拉伯世界、印度、南亚次大陆、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给予更多的注意,我们在文化上和他们有着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而我们对他们却往往了解不够。我们对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也同样给予较多的注意,上世纪以来他们的崛起给予我们的启示和鼓舞是十分可珍贵的,我们不应该对他们依旧生疏。
我们也希望这部辞典能够达到比较符合要求的学术水平。它不应该让人觉得虽然也还算提供了一些资料,但似乎仍然不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和学习伴侶。这里首先牵涉到的当然是我们的学力、工作态度和方法、工作条件问题。学力不可强求,工作态度和方法却应该从严要求,工作条件应该努力去创造。一部辞典的学术水平主要指内容的科学性,作为专业性诗歌辞典,应该对诗歌文化現象所显示的历史内容和文化素质作出客观的反映,而不应该仅仅冷漠地、流水账式地抄录人物履历表、年代记、图书目录;避免匆忙地以赶浪头的方式对两种以上不同观点产生以及对人和事的不同评价作所谓的“表态”;对争论中的、未有定论、定评的人和事和与其相关联的正、反面问题要尽可能公正地、冷静地作无偏见的介绍,在引用权威性评论的同时,也应相信读者能够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可靠和有用的资料和信息,我们不可能像写诗歌史、诗歌评论那样地写词条释文。
我们认为,重视科学性和重视可读性并不矛盾。在要求表达的明白准确,避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同时,应该注意避免行文的枯燥干涩。辞典的词条释文有它自己的文体,发表议论和进行想象式的描写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注意到了避免用大同小异的陈辞滥调作过分的赞许,也避免用苛刻的语言作过分的挑剔。
好的愿望的实现必须经过努力,努力的效果决定于我们的能力。我们知道,我们编纂的这部辞典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安心的是我们曾经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因此它可能多少接近我们的愿望,我们希望它能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达到完善。
1992年3月
这是燕郊为安徽文艺出版社《诗歌大辞典》(罗洛主编,他主编《外国卷》部份)中《外国卷》所作的序言。从1988年底开始组稿,集四十多位专家,撰写辞条约两百万字,于1992年交齐稿。1994年该社作最后校对,并称已列入省“八五”出版计划,但迄未出版。
在陈稿中发现他的“序”,为他当时的一片苦心和期望,也为凝聚了众多专家的辛勤劳动而遭遇如此,深感遗憾!年前,我曾经多次和该社领导、编辑联系,据对方称:事隔多年,原件已难追寻,无法退稿,云云。
兰欣谨识 201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