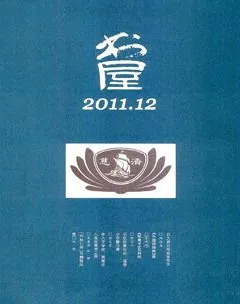庸臣焉知亡国痛
2011-12-29王学斌
书屋 2011年12期
当下中国,每逢应酬聚会,人们时常借讲段子以助酒兴、添谈资。段子之妙,大致有三:一来段子种类多样,有荤有素,如同菜单,适合各类人群之需;二来段子皆言他人之事,与在座诸位无关,博君一笑,不伤感情;三来有些段子涉及其他,既能满足人们某种好奇心,又能“借他人之酒,浇自己之块垒”,自然引来众人口耳相传,乐此不疲。其实,讲段子之风自古有之,并非仅兴于今日。晚清以降,掌故之学盛极一时,政治类段子可谓占得近代掌故之半壁江山,其中不少的戏谑对象即清朝闻人。有这么两则,专言清末重臣那桐饭量之巨:
那体肥硕,面团团而白皙,都人戏呼为天官脸儿。其一日三餐,每餐例食馒头首十枚、红燉猪肉或牛羊肉一碗,自谓食量宏为永年之征。
那桐善饭,非佳肴不适口,每食必具参翅等数簋,啖之立尽。其庖人月领菜费至六七百金之多。
如此形象之描述,给人感觉,那桐不啻为“饭桶”。不过,段子毕竟非信史,且经与众手,传于众口,自然烙上浓厚的娱乐色彩。身为清末中枢要员,那桐究系何等人物?半年来,笔者细阅近百万字的《那桐日记》,得以略窥其端倪之一二。
一
说起那桐(1856—1925),想必不少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都知道他是清末政坛显赫一时的要角,但对其生平事略尤其是发迹史却知之甚少。那桐是如何步步升迁、位极人臣的呢?此中颇有玄机。
那桐是叶赫那拉氏,内务府镶黄旗人,于是,不少人就猜测其能在清末火速上位,定是依靠慈禧的特殊关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与太后老佛爷同族,但那桐却是从基层做起,于户部郎曹蹭蹬浮沉长达二十余年。
仕途并不如意,但那桐依然勤勉工作,终于盼来了人生的伯乐——翁同龢。翁当时既是帝师,又是军机大臣,最为关键的在于他还兼任户部尚书,是那桐的顶头上司。那平日里经常赴翁府“回事”、“画稿”,其工作能力,翁自然尽收眼底,故那日后与端方、荣庆并称“旗下三才子”,绝非浪得虚名。
光绪二十二年(1896),朝廷拟定银库郎中人选,那排名第二,本无希望。此时翁力荐那桐,甚至不惜与军机首辅李鸿藻闹僵,终于让那获得银库郎中这个肥缺,可见那深得翁之青睐。那亦对翁终生感激,“凡此逾格恩施,皆翁、张两堂素昔之拔植也”。戊戌维新前夕,翁因内部矛盾横遭罢黜,遣送回籍。那听闻此事,犹如晴空霹雳,日记里写满了不舍之情:
申初归,今日上谕:翁中堂开缺回籍,朝廷去此柱石之臣,可叹,可忧。
四月卅日,到翁师处长谈时许,别泪纵横,不可道矣。
五月初二日,未刻到翁师处送程仪千金,辞不收,谈许久。
五月十二日,卯刻到翁师宅送行,明日南旋也。
五月十三日,卯刻,到永定门外马家堡火车站送翁师南旋也,送者数十人。卯正一刻,翁师揖拜登车,同有别离之感。
感慨翁、那师生情谊绵厚之余,笔者不禁好奇那桐出手之阔绰。此时仅为银库郎中的他,若按常规官薪,岂能“送程仪千金”?所以其收入有来源不明之嫌。据《清宫遗闻》载:“户部各差,以银库郎中为最优。三年一任,任满贪者可余二十万,至廉者亦能余十万。”可见那氏于此岗位上下手颇勤,获利甚丰。
恩师虽已返乡,但仕途还要继续。要想于宦海屹立不倒,背后须有大树庇佑。那桐自然深谙此道,开始物色新的靠山。经过一番选择,那发现荣禄最靠谱。
清末之官场,官员若能迅速升迁,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出身是否高贵,二是跑官能力是否一流。前已言及,那桐虽与慈禧同族,却很不受待见,所以他只能靠自己。恰逢戊戌之后,荣禄深得慈禧垂青,出任军机大臣,成为满人权贵之翘楚。荣虽为人极为精明,城府甚深,但却有致命缺陷——贪财。那桐正是瞅准其嗜好,每逢荣禄生日,必定登门送礼。有一回,那升任京堂,向原来的上司行感谢礼,“以千金拜荣仲华相国(前户部)受,四十金拜崇文山尚书(前户部)受,四十金拜徐荫轩相国受……”。按照常规,京堂送礼,四十两为准,而那唯独下血本塞给荣禄一千两,可见其明显乃有意讨好,一来二往,荣便把那视为亲信,重点栽培,不久便将其扶上礼部右侍郎的位置。1899年,那桐极力逢迎朝廷己亥建储之举,颇得慈禧、荣禄欢心。次年5月14日,那从“四品京堂候补”被破格擢升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便是由荣禄一手操办。当日获悉任命后,那立即“谒荣相”,表示“桐受恩深重,感激弥甚,惟心竭尽血,诚力图报称而已”。
孰料,荣禄于1903年便一命呜呼。那桐此时虽已为重臣,但仍需寻找政治后盾。转了一圈,他找到了庆亲王奕劻。奕劻是清末最著名的贪官,其“自当国以来,政以贿行,官以私进”。此等货色,但凡略有良知之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而那桐却甘愿与之同流合污。一次,清政府发行公债,号召全国大小官吏,必须先行声明认购若干,其标准同其家产挂钩,多买有赏,少买必罚,实际上是变相的征收财产税。奕劻、那桐二人身为重臣,且富可敌国,自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让他们二人花钱买一堆废纸,无疑是剜其心头之肉。于是,二人私下商议,想出了一个规避之策,以出卖各自财物来掩人耳目,奕劻卖掉自己的车马,那桐则更狠,卖掉自己的房屋,并且二人在报纸上大肆登广告,做宣传,表示自己为了替国家分忧,宁愿变卖家产,以博取世人同情。有一天,二人一同上朝,那桐埋怨奕劻不应该拿一批不值钱的车马出售,致使他人怀疑,自诩卖屋既能显示出自己的爱国之心,又可获得圣上的怜悯与信任,实在是万全之谋。奕劻竟恬不知耻的讲:“上若强迫承认,虽宣言卖身,亦复无益也。”说罢,二人击掌狂笑,真可谓臭味相投!
当然,在那桐看来,无论荣禄,还是奕劻,虽堪称大树参天,但皆不能庇荫自己一生平安。唯有博得老佛爷慈禧之信任,才至为关键。庚子之变后,那桐奉命留京处理善后事宜,不辞辛劳,格外卖力,其精明能干终引起了远在西安的慈禧之关注。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那桐收到好友桂月亭密函,“云皇太后因桐在京办事得力,特颁赏银六百两”,并要求那桐“不必具折谢恩,不令宣露”。果不其然,三个月后,那桐收到慈禧的六百两“私房钱”,“祗领心感无似”。慈禧偷偷赏钱给大臣,这在晚清堪称异数。显然,慈禧已将那桐视为心腹,但碍于同为叶赫那拉氏,故不便公开赏赐。待两宫返京,那桐迅即获得要位,出掌外务部。
此后,慈禧对那更是恩宠有加。1905年6月初一,那桐照例赴仁寿殿汇报工作。此时垂垂老矣的慈禧,对于政事已颇显倦怠,十分反常地对那桐说道:“尔近来办事甚历练,将来朝廷大事全依仗你了。”这句“全依仗你了”,对于那桐而言,既是条托孤令,更是颗定心丸,意味着自己在清廷的地位已无可撼动。
经过多年摸爬滚打、苦心经营,那桐内有慈禧当靠山,外有奕劻为同党,可谓打通了天地线,迎来了其官宦生涯的“美好时代”。
二
官运亨通,那桐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一手抓权,一手捞钱,两手都要硬。检阅其日记,里面大量篇幅记述了其敛财细节,颇令人触目惊心。要而言之,那氏聚敛之道,无外乎二条:卖官鬻爵与开设当铺。
前已述及,那桐从底层爬上高层,除却能力过人,更多的是凭借财神开路。等到那桐位居中枢,一切仿佛又进入了新的轮回,重复着他年轻时的故事。一茬又一茬的下层官员登门拜师,求取官位,银两自是络绎不绝。那每日接见访客,都将来者背景、谈吐写于日记中,以作备忘,如: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早特用吉林直隶州程德全来拜,号雪楼,四川人,在黑龙江有年,人能干有吏才。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早南非洲总领事官刘道玉麟来拜门,汪伯堂介绍也。刘为广东香山人,美国学生,在外洋廿年,现年四十岁上下,号宝森,人极明白能干,办交涉上等人物也。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今早江苏补用道虞和德,号洽卿,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年三十九岁,上海荷兰行买办,梅尔思、子言介绍持贽来拜门,人精明,甚明商情,惜有市井气也。
至于具体索贿过程,那桐并不参与,而是交与下人操办。一次,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冒鹤亭以候补道待分发。经人引介谒见那桐。几句寒暄后,那便吩咐门下书办作东,邀冒前往一僻静处吃饭。席间,书办道:“冒大人蒙中堂赏识,不久外放道台实缺,可是个美差!”当时政以贿成,每个官职价码不同,谙于此道者除写立字据按时报效外,还答应酌予那府书办们若干好处。冒鹤亭一介书生,懵然不知书办作东,意在交易,只是连连举杯称谢“那中堂恩典”而已。书办见话不投机,撞了木钟,懊丧的说一声“怠慢”,即掉首而去。过了几日,冒鹤亭经友人点拨,弄清其中底细,再度赴那府请谒,竟被拒之门外。
那桐积聚财富的另一手段便是开设当铺。那桐任职户部多年,深知当铺一本万利,乃快速致富之捷径。自从掌管银库,那赚得人生第一桶金,从而正式进军当铺业。《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记道:
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丽堂为总管,田诗园为掌柜,于八月初一日接替,开市大吉。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余于今日约孟总管到铺,上香祭神,书立合同。
之后,那先后收购了灯市口等繁华地段的当铺,生意蒸蒸日上。比如“天佑斋田二送来翠搬(扳)指一个,压京松银一千两,每月六厘行息,四个月归还取赎。如到期不还,银物两冲”。按那所记,一个小小的玉扳指,当存四个月,即可净赚二百四十两。当铺收益之丰着实令人咋舌。
那桐既做官又经商,在官不光言官,在商不忘揽权,最终弄得官场如商场,商场似官场,鼓了自己的腰包,亏了朝廷的国库。“自古召乱之道,莫甚于罔利”,信夫!
三
除去攀缘上级领导,聚敛巨额财富,那桐还不忘在同僚中开发资源,寻找盟友,他与袁世凯结盟便是典型案例。
那、袁之相识,始于小站练兵时期。当时袁主动登门拜见那桐,“直隶臬司袁慰亭世凯来拜,年甫三十九岁,局面扩大,谈吐朴直,诚大器也”。那时任职户部,掌管银库印钥。袁之目的,明显同审批练兵军饷有关,自然给了那不少好处。通过接触,袁发觉那桐富有学识,且行事谨慎,更重要的是其深受帝师翁同龢倚重,不啻为一支升值空间极大的“政坛潜力股”。故袁千万百计地腐蚀这位国家干部,与之深相结纳。翻看《那桐日记》,我们不禁惊叹袁世凯用心之巧,出手之大,手段之高,花样之多。为了“搞定”那桐,袁但逢节庆便派人送上厚礼,力求用金钱将其喂饱,不过这仅是常规手段。一次,那桐赴日本参加完博览会,归国之际,袁世凯不惜高接远迎,破格接待,“舟行平稳,未正抵大沽,慰亭制军遣小火轮来迎,易乘进口。酉初抵塘沽,换火车,戌初抵天津车站,袁宫保及阖郡文武来迎”。这哪里还是接待朝廷中层领导,完全是遵照迎送外国贵宾或元首时的标准。
那桐好听戏,亦喜唱戏,是个十足的票友。早在发迹前,便时常出没于京城各大梨园。比如一回那赴庆和堂给同僚志小岩做寿,“呼林桂生、小金弹琵琶唱玉堂春,苏曲绝佳。小金复唱教子,老生亦好”。可知那对于戏剧,颇为内行。袁世凯于是投其所好,施以猛药,不时作东邀请那桐听名角名戏。另外,每逢那桐之母亲生日,袁就一掷千金,出资将京城有名的戏班子请到那府演出,如: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袁宫保送洪奎班戏一天以为祝寿,请客二桌。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廿七日,袁宫保送同庆班戏一天,请客一百余人,夜寅初散。
同时,袁还从那身边亲属下手,对他们倍加关照。如袁曾授意徐世昌,让其接近那桐之弟那晋,并与之换帖,结拜为异性兄弟,然后袁顺水推舟,提拔那晋,“锡侯弟经袁制台、铁侍郎奏充襄理京旗常备军营务”。如此细致周到的“关怀”,自然使那桐感激不尽,从而甘心与袁互为奥援,形成政治联盟。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八,那桐“与徐菊人制军订兰谱”。自此,袁世凯、徐世昌与那桐三人,同坐一条船,同吃一碗饭。
四
清朝末年,袁世凯蛰伏洹上,端方蒙冤革职,善耆难获重用,铁良屈就闲差……朝堂之上,满眼望去,净是尸位素餐的庸臣们,亲贵见用,贤才见弃。一旦有变,朝廷自然遭遇无人能信、无人可用之尴尬。
那桐身处此危局中,除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外,便是与徐世昌谋划袁世凯出山事宜。1911年5月8日,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徐、那二人同被授为协理大臣。二人接旨后,皆上书请辞。徐于日记写道:“蒙恩授为内阁协理大臣,时艰任重,拟具疏恳辞。”那亦然,“具折恳辞内阁协理大臣差事”。二人步调如此一致,岂是偶然?关于其中内幕,民国掌故大家费行简曾有披露:
(辛亥四月)世昌告桐曰:此席予居不称,唯慰亭才足胜任。而以朋党嫌疑,不便论列,奈何?桐曰:是何难!我言之可耳。乃具疏以疎庸辞职,荐袁世凯、端方自代。当世凯罢后,有称颂其人者,载沣皆严斥之,其时褫逐之赵秉钧、陈璧,胥袁党也。自世昌再赞密勿世凯谋起用甚力,亲贵咸赖为疏通,至是桐疏虽未报可,而亦不加以申斥。
费氏之论虽未必俱符史实,但确也说明在起用袁世凯这一点上,那、徐二人已形成高度共识。
10月10日晚,武昌首义爆发。次日中午,那桐“接到各处来电,知武昌新军变乱,据城戕官,鄂都避往汉口,提督张彪被害”,其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当访菊人”,而不是向载沣或者奕劻汇报。午后,那桐、盛宣怀来拜访徐,接着徐、那二人又去庆王府同奕劻密议,三人“久谈”,至于内容,那、徐二人在日记中皆只字未提。他们身居高位,心机重重,安全起见,自然不留痕迹。不过当时掌管军咨府的载涛因接近核心层,洞悉内情,认为“革命爆发,那、徐协谋,推动奕劻,趁着载沣仓皇失措之时,极力主张起用袁世凯。袁在彰德,包藏祸心,待时而动……载沣本不愿意将这个大对头请出,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他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的勇气,只有任听摆布,忍泪屈从”。可见那桐于此事件中不遗余力,广造舆论,终于左右了载沣之决断。不久,那桐又请辞协理大臣一职,为袁氏入主内阁铺路。11月13日,朝廷降旨,批准那桐辞职,并委任其为弼德院顾问大臣。那氏于当天日记中居然写道:“邀此天命,感激涕零”,实在假得让人忍俊不禁。
待袁世凯甫一回京,那桐当天便迫不及待前往拜见,“袁总理今日酉刻到京,寓锡拉胡同,戌刻往拜,稍谈即归”。此后,袁、徐二人与那桐之来往便愈加密切,这在《那桐日记》中颇有体现:
九月廿六日袁总理组织内阁成立,由袁总理召见,署名矣。
十月初四日午后徐相来谈。
初五日午后未出门,翰卿、菊人、鑫吾来谈。
初六日(11月26日)因昨日感寒,手足麻木作烧舌痛,宣誓太庙典礼未能恭往陪祀……夜袁慰廷、徐菊人来谈。
三人私下里过从如此频繁,定当有要事相商,恐多半与清帝逊位一事有关。更堪玩味的是,自从11月26日夜里与袁、徐二人密谈后,那桐便称病不出。起初只是请假十日、十五日,后来干脆续假二十日,化身“宅男”,闭户谢客,直到清廷覆亡。同时,期间袁世凯“派卫兵二十六人来家常川守护”,可知那桐此举实乃与袁、徐密议之结果,其告病养疴是假,免责避祸是真。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那桐于日记里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江山鼎革,王朝倾覆,那桐非但没有痛心疾首,愤恨萦怀,反而满怀喜悦,相机而变。可见在那氏心中,唯有个人利益最为重要,所谓江山社稷,犹如天边浮云尔。
《那桐日记》之卷首,撰有这么一段话:
尝见吾叔父逐日书写笔记,垂三十年不辍,身心功夫与年俱进,历历可考;且偶遇往事,随意披阅,如在目前。吾甚羡之。自今伊始愿效所为,既承家法兼可自励。
光绪十六年庚寅元旦琴轩氏自记
时年三十有四
或许当年之那桐,曾真心打算以日记自醒,励志做一个国家栋梁。可惜岁月催人变,笔者通览这百万余言,体会到的却是一部鲜活而惊心的“庸臣成长史”。读罢整部日记,再翻至开篇,回看这一段,我顿觉啼笑皆非,好似被这个叶赫那拉氏“黑色幽默”了一把……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下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