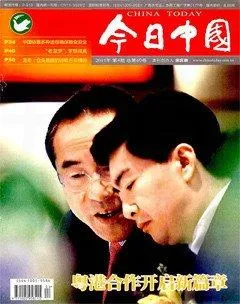“门外”谈鲁迅
2011-12-29张涛
今日中国·中文版 2011年4期
陈丹青回国已经十年有余。在画家身份之外,十年中,他的各种文字、言论常见诸于报端。这些文字或谈绘画美术,或议论当下教育体制,或触及公共言论空间,或遥想民国当年。在他的诸多言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其谈论民国文人与“民国范儿”。在那些民国文人与“民国范儿”中,鲁迅是陈丹青最喜欢的,也是其谈得最多的。
众所周知,“鲁迅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在成为显学之前,在鲁迅生前,就已有同时代的人谈论鲁迅了,在这些言论中,有朋友的,有论敌的,也有政党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自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就曾断言鲁迅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从“逆子贰臣”发展到革命战士。在鲁迅身后,最具影响力的论说应当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那段“鲁迅论”,他用“三家”、“五hmrWy9Gn9gIZCf6ypkrrmQ==最”将鲁迅认定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影响了当代中国鲁迅研究数十年。大约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当代学人逐渐地开始从启蒙的立场谈论鲁迅,开始了对鲁迅的“心灵探寻”,在更为深入、复杂的心灵、精神层面试图“与鲁迅相遇”。到了新世纪,在“告别革命”的声浪中,鲁迅成为了“是胡适,还是鲁迅”这一思想选择中的被遗弃者。无论在生前,还是在身后,关于鲁迅的论说从未休止过,尤其是在鲁迅“远行之后”的日子里,他只能任凭后世之人评说他的是非功过。
鲁迅早已被那些汗牛充栋的论说、文字给层层包裹住了,“我们活在教科书中太久了,而鲁迅先生死在教科书中已七十年,他总是被我们摁在是非的一端。”如何穿越这重重的言说壁障,尽可能地走进鲁迅的时代,走进鲁迅的生活,最终“走近”鲁迅?我以为,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走近”鲁迅的道路。
陈丹青毕竟是画家,他谈论鲁迅,最先就是给鲁迅“画像”。在他看来,鲁迅是最好看的:矮小瘦弱,但倔强有力,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鲁迅“既非洋派,也不老派”,在陈丹青看来,这副摸样与鲁迅正合身,与他的文字搭极了。鲁迅的好看在于,在他的那张脸上永远都是一副体面的书生本色。
“鲁迅之死”也是鲁迅身后的一桩谜题与公案。从怀疑是日本军医所害,到通过分析当年存留下的CT片,认为鲁迅死于肺病。其中还可能有诸多的迷障,但陈丹青谈鲁迅与死亡的关系,不拘泥于这样的“事实”,他更看重鲁迅如何看待死亡、书写死亡。在鲁迅的“死亡叙说”中,他看到了鲁迅的大慈悲、大情怀。鲁迅在身后尽管受到了各种“殊荣”,但却未有人像他对待死亡那样,去对待他的死。“人是向死而生的”,最终还是死神给了鲁迅一个宽待,“死神宽待鲁迅,给他好好的死,也总算送走了中国地面上这位纠缠死亡的人,死神了解鲁迅,一如鲁迅了解死神”。
在我看来,陈丹青谈鲁迅时常把鲁迅与同时代的民国文人联系起来。他把鲁迅与这些人横比竖看,试图还原、重建鲁迅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试看,鲁迅的同代人以及追随鲁迅的左翼青年在日后的命运结局,就可见陈丹青的努力与用心。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可见陈丹青身上浓重的“民国情结”。
寥寥数语实在说不尽《笑谈大先生》中涉及的诸多议题。我以为,陈丹青谈鲁迅之所以精彩,一在于他是“门外谈”——鲁迅也爱“门外谈”——这样没有“历史的负担”与“专业的压力”,可以最大程度上呈现“私人性”的鲁迅;二在于陈丹青对于鲁迅一直心存“敬意”。虽存敬意,但不顶礼膜拜,“敬”但不远之。“笑谈”是与鲁迅“面对面”,姿态上“平起平坐”。但内心里有大敬重。总之,我以为,陈丹青站在“门外”,以鲁迅般“无所谓的样子”,“笑谈大先生”,最终谈到“门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