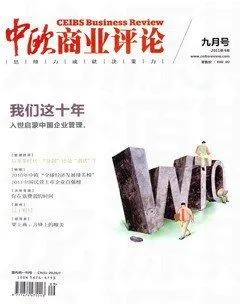我们这十年入世启蒙中国企业管理
2011-12-29杨微薰
中欧商业评论 2011年9期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莱斯特·瑟罗(Lester C.Thurow)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曾这样谈到全球性经济问题。中国入世,更进一步地融入了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市场,大量外来商品涌入国门,而世界上许多产品都已经是“Made in China”。
大时代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和成长空间,财富在全球版图上越来越平滑地流转并分享,由此推动中国从一个“世界工厂”逐步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带动中国的工商业从稚嫩走向成熟,成为全球市场上一股特殊的力量。
千百年来,中国的工商业从作坊形态和农耕思想中蹒跚起步,在坚船利炮的打击中被迫“图志”,并于上个世纪短暂汇流进全球市场和产业链,但很快被中断。1986年,中国重启复关谈判,并于15年后成功入世,由此终于走完了自1793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正式出访中国提出“自由通商,协定关税”主张后的200多年曲折的旅程。
“加入”是一种结束,结束的是以我为尊、自给自足、拒绝变化的封闭思想,“加入”也是一种开始,开始用国际的价值观和准则去获得利益、承担责任与发展自我。这种结束与开始,绝不会只是一个时间点的概念,不是一步跨进一个门槛后,就会天地大变的迅速改观。曾经以具有“巨大同化能力”为标榜的中华文明,这次面对的是一个比自己先进和大出许多倍的庞然大物,一种不对等但又各自顽强的张力将持续导演未来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各类剧目。
这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大环境与大趋势。入世十年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大批企业的生产力迅猛释放,一开始他们攫取利益的方式是原始而初级的,其能力是草莽而粗放的,就像一个路人突然发现了一条大道,路边掉满了皮夹子;但是,这样的状态很快就会结束,阵痛与压力持续变换它们的面目,以各种方式施加到哪怕只是蹲守在家门口的企业身上。
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学习和进步。中国企业群体在这十年里,从产品国际化,到经营国际化,到资本国际化,一步步爬坡迈槛,一步步建树自身的能力,使企业的运营和发展一步步正常化、现代化。这就如同中国的经济自身一样,机会发现型正在成为历史,市场创造型正在成为主流。而这,希望将越来越落在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上。
中国人很善于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是中国人也最不善于学习,因为我们的思想根深蒂固,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将一切——哪怕是理念与信仰——都工具化,这或许将是羁绊中国企业提升管理能力的最大障碍。
本期专题中,我们试图对这十年来中国企业的管理进化进行简要梳理,从管理理念变迁、全球资源的配置应用、企业法务建设、本土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到外企在中国的本土化成长等各个方面,去还原企业成长的足迹与脉络,并从中结晶经验与教训,相信这个工作,能为中国企业持续学习并建构未来长远竞争力带来裨益。
西学东渐,以人为本
早期中国企业学习西方管理有点像刚学开车的新手,只顾单一操作;随着时间变化会成长为老练的司机,注意细节观测与宏观视野的统一。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会出现“水土不服”,比如平衡计分卡的应用、核心竞争力的含义、学习型组织的理解,都在中国的商业、政治和文化土壤上产生了新的特点和含义,内涵也被改造。
正如刘文瑞先生所言,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学习是一种创造——外在的西式制度框架,创造性地容纳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十年来,中国对西方管理的学习日益扎实,不再满足于“西方先进”的宏大叙事,也不再局限于零敲碎打的局部模仿,而是试图从体系上把握西方管理的本质,在充分消化的基础上为我所用。(见《穿西装的“国货”——管理“西学东渐”十年》)
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东西融合的初始尝试,在形貌上器用上实施拿来主义,在内心深处的价值取向上还是实用主义。不过,国外企业对于人本价值的日益尊崇,也开始对中国企业产生影响。由此,就如西方企业管理的重点经历了“工具——制度——人”的转变一样,中国企业的学习,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历程。
西方企业中,将人本主义贯彻于管理实践的不乏其例,如星巴克集团的CEO霍华德·舒尔茨认为,只有当企业有良好价值观,秉持“员工第一、顾客第二、股东第三”的信念,才能通过员工的服务为顾客创造一流的消费体验,最终为股东带来丰厚的利润。这样的思想也在影响着中国企业。中国人多,也就廉价,往往对于人的价值是轻视与忽略的。但尤其近几年来,包括海底捞、大润发、德胜洋楼等一批企业,正在扭转这样的价值观。
从“世界工厂”到全球资本运作
面对全球的市场和竞争,中国企业也需要逐步去整合并利用好全球资源。
从中国企业资源利用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产品国际化。企业依靠敏锐的商机嗅觉、以及海外人才的初步应用,使得中国“世界工厂”的产品,可以放到全球各地的货架上,这成就了许多外向型的生产和贸易企业,也成就了如阿里巴巴一类的平台型企业。
第二是经营国际化。许多企业到国外开工厂、设终端,并购公司,和西方合作伙伴逐步磨合,也渐渐引入现代管理和公司治理结构,提升经营管理,华为、联想、吉利都是其中的代表,也不乏TCL这样在国际化中巨亏却也借此实现了企业再造、升级的“再变形记”。
第三是资本国际化。企业引入国际资本运作、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进而实现更大的转变,百度、盛大、携程可为此列中的佼佼者,这类企业对国外资本市场的规则与文化更需要深度的理解和融入,有各自的一番独特经历及体验,过程中也难免遭遇挫折,如近期的“中国概念股”风波就给人多重启示,而今后也还有更广阔的提升空间,更好地建树作为一个市场型企业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从总体来看,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和WTO准则下,中国企业的全球资源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是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的产业价值链的下游和末端,其手段还是相对单一而被动的,未来依然可能严重受制于下游挤压。那么如何走出新的全球资源整合之路?
通过统计过去十年间中国企业参与全球资源整合的案例,有学者总结出五种基本模式,从中看清全球化发展趋势、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与竞争实质。有一点需要注意:过于主体化的全球扩张意识可能最终伤害自己。资源整合并不意味着实际上获得资源,目的和根本落脚点毕竟还是不断提升公司利润模式的价值水平,确保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可考虑从产业价值链角度重构公司利润模式,从而形成围绕公司增长潜能形成的内生性资源整合能力,这要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管理与创新(见《亢龙出海一中国企业全球资源整合》)。
法律提升企业管理
入世意味着规则的接轨,这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法律法规的清理工作,涉及3000多个法律法规,企业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十年来,涉外案件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三大类:一是知识产权(如商标专利),二是反倾销,三是在国外遇到的劳动纠纷。而企业最大的变化,一是逐渐开始强调自有知识产权的研发和保护,二是非常重视在跨国经营中的整体法律风险控制。“走出去”的企业,还要懂得规则的竞争。中国企业出去得少,差别意识弱,容易把国内的习气带到国外去。这个现象很正常但必须马上改变,不然会付出很大代价。(见《一个涉外律师的十年体验》)
在涉外法务工作中要善用业务精熟的律师和中介机构,然而,律师无法对企业有真正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而企业内部的法律顾问的优势正是在于对企业的知根知底,所以应结合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并用好律师的专业知识,独立作出判断,想一想:律师说的话企业能做得到吗?要兼顾企业实际和法律规定,最后才可能制订出最优方案,真正解决问题。
更深一层看,法务应起到的作用不仅限于工具层面,还应让法律的理念更深地融合到公司治理中去,而且在整个管理体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形成“以法治企”的文化和能力。宝钢集团参与过三十多起钢铁产品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案件的申诉和应诉,应诉成功率为75%,远高于同期国内企业。集团法务部副部长陆俊勇感觉,反倾销的工作需要公司高层的重视,因为涉及的部门和子公司众多,工作量大、时间紧,而且需要与销售部门密切联动,还可以注意分散销售——宝钢的出口总量不小,但出口目的地却较为分散,可以减少贸易摩擦。很多企业往往觉得反倾销事件只是跟贸易有关,参加钢铁协会的会议时,往往也是具体到各个产品门类的销售人员,常常更换;宝钢则是从第一个案子开始就明确了这是一个法律问题,由法务部牵头,销售、贸易部门协作,十五六年一以贯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法律管理往往碰到难题,即商务部门更关心业绩而对法律往往不够重视,会存在心理抵触。负责法律风险控制的部门如何与商务部门做好沟通协作,兼顾效率与效果,宝钢集团在这方面的许多探索颇有助益。
“中国制造”升级与外资本土化
入世之后,中国“世界工厂”的定位日益明晰,然而这也把大量企业挤到了一条险峻的道路上,诸多中国企业都沉在国际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层,同质化、低附加值的密集竞争,成了无数制造企业的心头之痛。而在转型经济中的一些“特殊因素”逐渐消退之时,以往的比较优势日益捉襟见肘。这时,参照几家在转型升级方面的佼佼者,将不无启迪。
好孩子集团就是一例,集团领导者深知,要参与全球竞争,本质上要有价值,另一方面,不能只靠偶然的成功,还要有持续性的、不断创新的能力,保持优秀的品质。对于很多头脑中形成了固化的“OEM思维”的中国企业,值得反思自身。为了迎战全球市场,好孩子集团甚至在公司内部发动了一场把中国思维转化为西方思维的运动,同时注意把握行业标准,投资4.5亿元建设全球最大的婴幼儿用品研发中心,其背后有着“中国造”崛起的长远眼光(见《好孩子:用价值征服西方人》)。类似的例子还有浪莎袜业,入世后出口订单增多,它得以享受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而后又加速了自主国际化的步伐,成功进行了自身的升级。
正如硬币的两面,入世不止意味着中国企业面临更广阔的海外市场,还意味着更多的外资企业会踏进国门一并逐鹿。本土化、市场扩张、政策变化……外企在中国有着一系列的经历,它们中间,有受惠于广阔中国市场、深度融入的成功者如肯德基,也有水土不服败走麦城的百思买。
“一家外企进入中国需要大致7年的发展周期才能达到稳定状态。”迪卡侬大中华区总裁孟东是一名越野自行车赛的爱好者,他以亲身经历为证,慨叹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是一个爬坡的历程,如果只是一味的加速度,极有可能陷入泥潭,无法笑到最后。例如,迪卡侬进入中国的第一步并未选择在法国本土“自购自建”的运营模式,而是结合中国国情,租赁场地,并且引入了动态和静态体验相结合的营销模式。此外,员工的信心和凝聚力尤为重要,需要构建“中国式企业文化”。为此,迪卡侬大中华区还争取到了母公司的配合,文化整合效果显而易见。(见《我和迪卡侬在中国的爬坡岁月》)。
过去十年,伴随入世,许多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巨变,这自然就波及到企业内部的管理技术、组织结构和制度理念。全球化和信息化正在引发一场世界范围的革命,其规模与影响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如哈罗德·罗森堡所说,“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中国企业还任重道远。
刘文瑞先生提醒:“外观同西方非常相似的企业治理结构,在运行中表现出的全是‘国货’。国企不论名称和结构如何,实质总是同国家体制类似;民企不管大小和经营范围,实质总是同民情习惯吻合。这一点,非常需要引起重视。”企业管理变革和升级之路,到底怎么走,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实践的命题,但是毫无疑问,它也受制于我们的心智与思维。
“一个物种能够生存下来不是因为它更强壮或机智,而是因为它更能适应环境。”达尔文的这句话大家已经很熟悉,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真的已经深刻理解并淳熟使用。未来的长路,还有待于更多商业研究者、实践者孜孜不倦的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