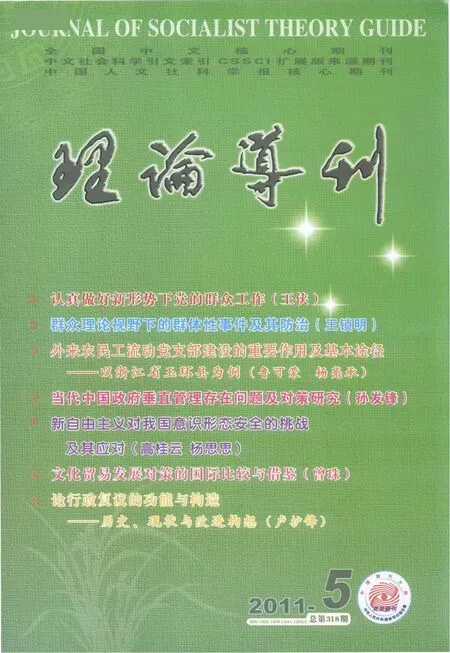政策网络模式研究的现状及分析
2011-12-24李琦
李琦
(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四平136000)
政策网络模式研究的现状及分析
李琦
(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四平136000)
政策网络模式作为当代公共政策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对其已有多年的研究,在中国也已被不断地引介和论证。美欧学者关于政策网络模式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大学派,聚焦于五个方面。政策网络已经成为解释政策过程复杂关系的一种有益路径,值得深入探讨。
政策网络;模式;辨识;公共政策理论
所谓政策网络(policynetworks),是指一群互赖行动者之间建立的某种稳定的社会关系形态,旨在促成政策问题或方案的形成与解决。而政策网络模式则是基于政策网络的现实,抽离出政策网络中参与者相互依赖、互动、自组织等特质,进而转化为一种分析政策现实的有效路径。政策网络模式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模式被引入公共政策领域,肇始于美国,经过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学者的不懈研究,流行于整个欧洲,乃至我国。政策网络正逐步成为公共政策学界的主流话语之一,它将公共政策过程视为多元利益群体复杂的互动博弈过程,弥补了基于国家与社会分野的宏观分析和基于组织与个体理性的微观分析的裂痕。
一、美欧学者对于政策网络模式研究的派别划分
美欧学者对于政策网络模式的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零星研究,到九十年代中期的锋芒展露,再到现今的百家争鸣,可以说已从“乱序”转为“有序”,但“分流”尚未“合流”。关于政策网络模式的研究,中国学者大多认可“三大学派”之划分:
2.英国学派。英国学者多把政策网络模式定位于中观层次。政策网络被视为一种利益中介模式,将政策网络中的参与者主要界定为行政官员与政策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重点研究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利益集团之间在政策过程中的结构关系对于政策后果的影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理查德森(J.Richardson)与乔丹(A.G.Jordan)指出在英国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几乎是在利益团体与政府协商中产生,而非以理性的方式形成;威尔克斯(S. Wilks)与赖特(M.Wright)采用社会中心途径,提出GIR(governm ent-industry relations)模型来解释政府与产业界之间的关系,强调是政策网络中的人际互动关系而非结构关系;罗兹(R.A.W.Rhodes)认为在不同政策领域中拥有不同的组织,这些不同的组织组成网络,这种网络也可以被看作是结合而成的一种联盟或利益共同体,并提出IGR(in tergovernm ental relations)模型,以政策网络概念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府际关系;史密斯(M.J.Smith)认为政策网络是一种“政府—团体”关系的分类方法,政策网络的产生之际,就是团体与政府之间达成资源交换且获得政府认可之时。
3.欧陆学派。以德国、荷兰学者为主,其多把政策网络模式定位于宏观层次。通过考察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将政策网络视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方式,主张政策网络的公、私行动者在政策过程中的非科层互动模式。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基克特(W.J.Kickert)、克利金(E.H. Klijn)与科彭扬(J.F.M.Koppenjan)认为政策网络是指介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之相互依赖参与者的关系形态,而“相互依赖”是网络途径的核心特征,信息、目标、资源等要素在不断地互动过程中得以交换,这些互动经常重复,于是产生制度化的过程,发展出特有的参与形态、互动规则与共同资源分享。
二、美欧学者对于政策网络模式研究的辨识焦点
考察美欧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政策网络模式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五个焦点:
1.政策网络界定:分析工具还是现实状态。由于政策网络进入人们视野的时间还很短暂,研究还很不成熟,至今学者对其涵义的界定还远未达成一致。但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其基本理论体系和观点大致可以做出两类划定:把政策网络作为客观存在的、影响政策过程的社会权力分配现象和把政策网络作为一种分析政策过程的模式与工具。前者认为伴随着社会事务的日趋复杂、公民社会崛起,政府单独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利益团体、市民理性参与政策的能力日趋增强,社会权力日益分散于各种团体之中,整个政策过程充满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并且多元的政策参与者越来越能够影响政策的制定;后者认为政策网络是一种分析途径或者是一种有用的政策工具,政策网络可以清晰地分析政策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反复博弈和平衡。布耶塞尔(H.A.Bressers)在《政策网络中的政策工具选择》(The Choice of Policy Instruments in Policy Networks)中认为:“政策网络在政策工具选择和政策执行过程起关键作用。”[1]还有学者认为,政策网络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社会体系,在其中,政策活动者发展了一套具有相对持久性的相互作用和信息沟通的模式,目的在于集体地解决公共问题或政策项目”。[2]
2.政府的角色:主导还是放任。无论是把政策网络界定为一种分析模式,还是把它定义为某种现实状态,政府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关于政策网络(工具/现状),在其形成阶段,是由于政府给予有效支持还是由于社会变迁产生了政策网络?在其发展阶段,政府是否试图主导政策网络的发展,还是政府对于政策网络的发展做肯定的认可、默许或支持其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判定,直接决定了政策网络现在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政府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孤立于政策网络之外的,也是政策网络中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被忽视的力量;这也决定了政策网络(工具/现状)的分析焦点是置于整个政策领域还是仅仅关注某些特定领域、特定团体的特定利益。因此在政策网络(工具/现状)分析过程中,除了强调网络中各个团体对政策结果的影响,亦应检视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对政策网络的影响进而对政策结果的影响。
3.政策网络与科层、市场:平行发展还是替代选择。学者们普遍认为,无论是韦伯意义的“科层”还是屡屡创造奇迹的市场神话,本身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政策网络的出现是继科层和市场之后的最佳替代选择——是第三种道路。但同时有些学者也认为,虽然科层与市场的缺陷无法自身克服,但是其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也是无法消逝的,政策网络的出现只不过是恰好弥补了二者的缺陷。治理理论颇为赞成这种观点。罗兹认为,“治理作为自我组织的网络不同于市场与科层的治理结构,政府的重大挑战在于使网络能够并且寻找出合作的新形式。”[3]
4.政策网络层次定位:整合还是断裂。前述政策网络研究分为三个主要派别,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次著书立说系统阐释政策网络,但是,这三个层次是可以整合为一个整体还是三个层次之间是断裂的?如果是整合在一起的,是什么使三个层次的政策网络连接在一起,如果是断裂的,政策网络在哪一个层面上更具有解释力,微观、中观还是宏观?这三个层次之间会不会发生相互影响,在各自界定之下所共有的特征因子如何加以区分,会不会构成某种语义学上的混乱,直接影响人们对于政策网络的认识呢?因此,三个层次有机整合也好,断裂分立也罢,总要有一个有意义的结论。笔者认为,断裂式的研究会导致忽略整体网络的局面,毕竟网络是要强调纵横、微妙的联系的,而整合式的研究则可以从全局的角度审视网络,使细节式的研究得以更好地延伸。
5.政策网络与政策后果:随机关系还是因果关系。目前学者对政策网络质疑的最主要的焦点就在于,政策网络之于政策后果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学者道丁指出,“传统对于政策网络的分类似乎难以超越单纯的描述,仅能作为描述政策结果的隐喻”。[4]学者拉布也指出,“在政策网络与政策后果的因果关系解释上存在薄弱之处”。[5]学者彼得森(J.Peterson)亦指出,“传统的政策网络途径所能做的,仅是对一政策过程当中所有的行动者间的连结情形做一静态的描述,但对于形成此种网络样态的原因,或是限制此种网络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单单以目前政策网络的研究途径似乎不足以解答这些问题”。[6]因此,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政策网络只不过是政策过程中一种非正式的、水平式的互动关系,政策的结果具有自发性,不具有某种必然性,没有任何一个主导者或引导者可以达到准确无误的有意图的结果。另外,政策制定的过程往往是动态的权力互动过程,而非如某些政策网络学者所认为的会形成稳定的网络关系,政策网络的分析中缺乏对权力的有效解释。
三、政策网络模式研究的现状分析
在经过了近30多年的研究之后,美欧学者对于政策网络模式的研究已经由萌生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观点繁杂、成果颇丰;最近几年,政策网络也逐渐被国人所认识,引介居多。但是从总体而言,中外学者之于政策网络的研究还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1.总体研究呈现片段式,缺乏普遍认可的系统论述。政策网络研究从总体而言,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个案分析,美欧学者的研究都具有领先地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总体还处在引进阶段,尚未完全消化,更谈不上创新发展;欧美学者已经有十数本专著,而大陆学者还没有专著,只是在与公共政策相关的书中有章节性的体现,台湾学者似乎比大陆学者先行一步,政策网络应用于具体政策领域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比大陆学者成熟一些,[7]但是其引介性内容也占有很大比例。
2.政策网络模式应用的范围尚未界定。对于美欧而言,无论是现有的理论还是个案分析都尚未具备普遍的解释力。成熟的理论应该具有普适性,而政策网络模式产生的背景根植于西方发达国家,学者对于其引介固然是好事,但重要的是应该考虑其对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价值。所以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政策网络模式的研究如果采用完全的“拿来主义”,忽视其应用性,则极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政策网络模式中存在的基本问题还没有清晰而合理的解释。上述研究焦点展示了政策网络研究的现实图景,政策网络之中还有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等待人们去解决,诸如“政策网络的定义至今尚未获得共识,理论的定位也不清楚”。[8]笔者认为,关于政策网络的界定,不可能把它仅仅作为一种工具,因为工具和现实是密不可分的,况且工具的目的性太强,有时则会过分强调工具的应用性而忽略现实;关于政府的角色是放任或者主导的判断,需要综合考量各种影响因素,不仅取决于政治制度,也取决于公民素质、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关于政策网络与科层、市场的关系,不可能把政策网络看作是独立的体系,它不可能替代科层与市场,因为正是科层与市场的缺陷才使政策网络的生存成为可能,在丧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府治理的前提下,政策网络不具有任何意义;关于政策网络的层次定位,完全的整合和彻底的断裂都是两个极端,在整合的意义上谈其千丝万缕的联系似乎是更有价值的;关于政策网络与政策后果,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下去具体考察,单一的案例或实证都不能对其做以肯定的结论。
四、政策网络模式研究的意义
关于政策网络,有的学者认为它开启了政策研究的新阶段。政策网络模式的研究具有如下现实意义:
1.有助于弥补政策研究方法的不足。目前公共政策研究主要以周期论或者阶段论研究方法为主导,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途径为主要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视角狭隘。因而,亟须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政策解释路径。重视行动者行为与结构的政策网络分析方法的引介与研究,可以弥补政策理论研究的不足。
2.有助于推进政策网络模式研究的本土化。现代意义上的政策科学本是舶来品,政策理论大多也是“拿来主义”,政策研究的跟进与政策研究的创新,必须根植于学习主体的自我消化;理论存在生命力与否必须考量其普适性与应用价值。因此,对于中国研究者而言,在对政策网络模式引介的同时,需要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消化与吸收。
3.有助于比较美欧国家现实的政策背景。现实的公共政策研究大都将注意力放到对美欧学界最新成果的引介上,以使中国研究者争取到与其平等交流的学术话语权。但现实是,我们的学术话语权基本丧失了。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套用他们的理论解释自己的问题不精准、解释他们的问题又不精彩。对于政策网络模式的出现,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其诞生地的社会背景,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可能会出现“橘生淮北则为枳”的风险。因此,需要清晰地研究美欧国家现实的社会与政策背景,如社会结构、权力划分、文化传统等等,这是以政策网络模式分析中国实际的应用前提。
总之,政策网络已经成为解释政策过程复杂关系的一种有益路径,虽然其研究中还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政策网络模式才更加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通过考察政策网络模式的研究现状,进一步为政策网络模式的系统研究提供一种梳理,为政策网络模式的焦点范围厘清一点界限,为政策网络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添增一些有益的解释。
[1]吕志奎.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角[J].太平洋学报,2006,(5).
[2]PETERS.B, VAN NISPEN K.M.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s[M]. Edward Elgar,1 998:86.
[3]RHODES.R.A.W. 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 out Government [J]. Political Studies, 1 996,(44).
[4]DOWDING.K. Model or Metaphor?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Policy Network Approach[J]. Political Studies,1 995,(43).
[5]RABB.C.D. Understanding Policy Networks: a Comment on Marsh and Smith. Political Studies,2001 ,(49).
[6]PETERSON.J. Policy Network [EB/OL].ht t p://www.ihs.ac.At /publications /pol/pw_90.pdf.:1 2.
[7]玉华.政策网络理论之研究[M].台北:瑞兴图书公司,2002.
[8]于常有.政策网络:概念、类型及发展前景[J].行政论坛, 2008,(1).
D035-01
A
1002-7408(2011)05-0081-03
李琦(1981-),男,吉林双辽人,吉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
[责任编辑:孙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