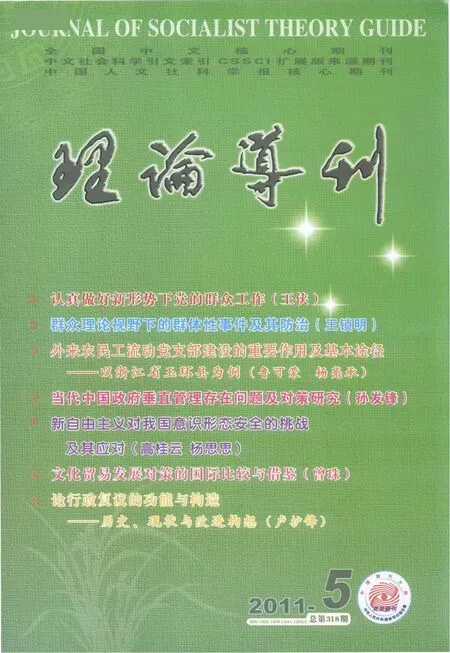略论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
2011-12-24李维意
李维意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略论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
李维意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两个和解”即人与自然的和解及人同其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把实践理解为人与自然同一性的基础,从生产和交往相互作用的角度,系统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必然性,论证了通过自由联合共同占有物质生活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两个和解”的真正实现。
“两个和解”;实践;必然;实现;系统分析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分裂,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对立和冲突,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了“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1]603把实现“两个和解”概括为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最为迫切的现实重大课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吸纳了恩格斯的“两个和解”思想并且把它与共产主义的理想诉求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2]12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沿着“两个和解”的实现即共产主义这一思路,立足实践主体立场,从生命的生产出发,系统分析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这一核心命题,论证了“两个和解”的实现既是一种价值理想,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两个和解”的实践基础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的批判的’活动的意义”。[3]3那么,马克思革命的实践之“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它的意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实践是理解“事物、现实、感性”,尤其是理解人与社会本质的基础。“事物、现实、感性”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而生成的,它们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是一种属人的存在。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更是一种现实的能动的社会存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5第二,实践是理解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基础。一方面,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基础是实践,“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3]3另一方面,宗教世界的基础在于世俗,“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3]4第三,实践是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从分裂到统一的基础,人与环境的关系主要是指人与自然和人同本身的关系。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4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并把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功能解释为“改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共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3]48他们从实践能够“改变世界”的角度,分析了人对自然的作用和人对人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4]38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进一步分析了“人与人的关系”,论证了实践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从分裂到统一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加深了马克思对劳动实践的认识,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劳动实践的理解实现了由抽象化到具体化的转变,把劳动实践具体化为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并由此生成了双重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诠释“两个和解”的基本维度:一是从生产实践出发,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23-24“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前提,自然史是人类史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就必须把生产实践作为人与自然关系存在与发展的中介。“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3]33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生产实践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同样也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二是从交往实践出发,进一步诠释“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交往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交往的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3]33同时,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前提下,人类的交往将冲破狭隘的地域限制,实现交往的普遍化。“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5]88当然,生产与交往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发展。
二、“两个和解”的历史必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实践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全部现存世界的基础。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劳动出发,阐述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主要是指“人化自然”即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这里的“自然”作为人类生产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人发生了现实的物质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天然自然”的存在及其先在性,但是,这种“天然自然”如果脱离了人类的生产劳动,相当于“无”。因此,自然(人化自然)的意义只能从人类生产劳动的立场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只有从生产劳动的立场来解释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是从人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的改造出发的。他们批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3]48由此可见,人的生产活动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这种对象性的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属人的对象性关系是“自然”所内涵的深刻本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能动地对待“自然客体”是直观地对待“自然客体”的基础,“自然”是人的生产实践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本质的确证和表现,是人本身的表现,因此,“自然”主要的应该理解为“人化自然”,“人化自然”使自然成为人的无机身体。从本体论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本源与派生关系。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唯物主义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从实践论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具有属人关系的改造和被改造的相互作用关系,即人类通过生产实践不断地使自然和自身得到双重的改造,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唯物主义所达到的理论高度。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考察,贯穿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的一致”的思想。在“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念上,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马克思恩格斯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揭示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自然基础,而且更在于揭示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本质是工业和社会状况即人的生产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最基本的生产实践出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和规律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人与自然的分裂和对立,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生产的落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也有赖于人类生产的大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6]525
生产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但是,生产离不开交往。交往实践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同时受生产实践的制约。在生产与交往的关系中,生产具有逻辑在先的意蕴。因为,物质生产是有生命的个人生存的前提,对人类具有本然的意义。“一当人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24然而,生产与交往又是密不可分的,生产是交往的基础,交往又是生产的前提。没有生产,人类便是一种动物性的存在,无所谓交往。交往实践是以人的现实存在为前提的,人类“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3]24生产决定了交往所采取的方式和组织形式。同样,没有交往,人类便无法从事生产。因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3]24生产与交往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生产与交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演进的历史。生产与交往是人改造自然和人改造人的过程,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演进的历史。
三、“两个和解”的实现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83只有使人从生产和狭隘的交往中解放出来,让人们通过自由的联合,完全占有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即人化自然),才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在这里,从人与自然即人与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看,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的劳动对象化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确证和表现,人只有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即占有自己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才能做到自由自主的活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解。而人对物质生活条件的占有,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就是通过人们自觉自愿的联合,通过“真实的集体”来占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才是人与人的和解。
实现“两个和解”,人类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3]79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产生以前,“个人之间进行交往的条件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对于他们说来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它们是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只能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3]80在这样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个人在孤立的范围内片面地发展着,因为他们进行生产和交往的条件是同他们现实的局限状态和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些不同的条件,后来变成了个人自主活动的桎梏。从而,使“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3]81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3]84任何现实人的存在,都是某种集体中的存在。过去的集体只是冒充的虚假的共同体,在“虚假的集体”中,个人是作为阶级的人而存在的,而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虚假的集体”是一种新的“牢笼”,这时,“物的力量”则是束缚被统治阶级自由自觉活动的“枷锁”。个人要想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只有通过“真实的集体”才能实现。“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3]84“真实的集体”就是各个个人“自己的联合”,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联合体。这种联合,不是出于某种外力强制的联合。而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联合,因此,每个个人都能够从这种自由的联合中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也就是通过自由人的联合体共同占有物质生活条件,才能为“两个和解”的实现开辟无限广阔的空间。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A81
A
1002-7408(2011)05-0052-03
2010年度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研究”(HB10AMK022)的成果之一。
李维意(1963-),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