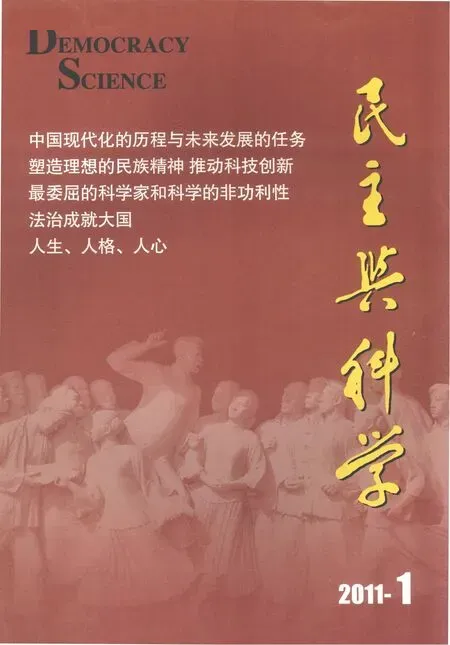理性与迷信
2011-12-24吴长青
■吴长青
理性与迷信
■吴长青
我们大多数人使用“理性”一词是非常随意的。它的本意是指人类认识能力的三个环节之一,即感性、知性到理性。而我们广泛应用“理性”一词似乎是指那些遇事冷静,不作过激反应,所谓能做到唾面自干的人的表现;我们还习惯将理性同科学精神等同,那些臆想、狂妄的言行,我们叫它非理性;“理性”一词称谓虽同,但在不同的情景下却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只有相对的意义;更有甚者,我们早就将理性归入了值得追求的价值范畴。
迷信则可以顾名思义。在科学史上,迷信和巫术及科学曾经混杂不分,但很快就被视为科学的绊脚石,说它一直企图阻碍科学的进步,但终究不能得逞;在社会生活领域,近百年来我们差不多一直在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好像迷信一定是科学的大敌。故此,迷信不是个好东西。
当牛顿面临万有引力成因及对宇宙秩序进行解释时,他给出了上帝第一次推动的答案;当爱因斯坦质疑后进发明的量子力学理论时,他坚信“上帝是不会掷骰子的。”这两位知识的富有及思想的能力绝对达到了人类的最高水平,而最终却拜倒在上帝的脚下。如果可以将有神论者归入迷信之列,那绝大多数的人,或者是理性的无神论者,或者是非理性的有神论者,或者非理性的无神论者,像牛顿、爱因斯坦一类的理性的有神论者只能是少数。大多数人其实是没法分辨理性和迷信的。
我经常听到十几岁的中学生们一本正经地讨论着如果地球爆炸,我们人类将会怎么办的问题,最鼓舞人心的答案就是,我们早就移民到其他星球上了。其实,这个答案只是霍金某次演讲中一句戏谑性玩笑,但孩子们当了真,因为那是顶级科学家说的话。
我也听到过一群城市边缘的老太太们每逢初一、十五到庙里去烧香时的闲谈:“我要去烧香不过(及)了,感冒得一塌糊涂。”烧香可以治感冒,这恐怕不是个别人的想法,特别是在农村。
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觉得以上中学生们讲的是科学,而批评老太太们信迷信,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是看标签指物认事的。但假如要认起真来,恐怕后者比前者还要显得有把握一些,因为也就两个礼拜就可以看到结果。我记得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中说过一个意思,伤风感冒,打针吃药两礼拜,不理不睬十五天(痊愈)。她烧了香是事实,感冒好了也是事实,并且一前一后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到此,似乎烧香治感冒是个真题。问题出在哪里,归因有误。前者认为科学家说的就是真的,后者则是分不清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两者认知的第二环节——知性都没达到,更别说理性了。
我们每一个人经常要遇到归因问题,即为一个结果找出原因。比如油箱里没油了,汽车熄火,这是因果关系;秋天到了,枫叶红了,这只是相关关系。当然,我们经常面临的问题比这要复杂得多,比如社会问题。
撇开哲学概念,借用经济学的观念,理性就是算帐。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有理性的人要“系统而有目的地做可以达到其目的的最好的事”。(曼昆)这里的关键是达到目的(个人的)、又是最好(至少是不能妨害别人),这是理性的价值所在。迷信呢?迷信就是“轴”、“拧巴”,不算帐,只认准心中的目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当然,迷信如果不借助于体制,不借助于公权力,纯属个体所衷,危害有限,如晚年牛顿所为,也就是让几个假币贩子上了断头台;甚至还会成为一种美德,成就伟大的事业,如特雷莎修女,如纳尔逊·曼德拉。
好像没有人把理性的品质归于集体,是不是隐含着理性一定是针对个体而言的,或者是,指望一个集体表现出理性是困难的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坚信,理性若不经设计良好的法律的驯化,也可能弄出危险来。我们只是说“集体无意识”,无意识显然就是非理性。当然,我们有时也大谈集体智慧,那就是集体算计了。理性既然涉及到算计,就难免只看到自己而看不到别人,特别是集体内掺入的私欲,我们的《刑法》里面设立有集体(法人)犯罪的条款,就是我们认为集体也可能犯罪的明证。以集体面目出现的理性算计不是说完全不考虑别人的利益,而只是将各种利益排序,分出先后和延迟兑现而不想平等协商,并且给出一个非常崇高的理由希望你服从。
理性人有时候可能会作恶,这一句话好像不符合经济学家对于他的定义,其实不然。实际的社会中,当一个结果不明朗,或者对结果的解读受到信仰、利益影响的时候,理性就会走上迷途。有人会说,这就是非理性了,当然是,问题是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康德说过:“理性的唯一正当行使就是用于道德目的。”显然,他是担心理性可能作恶的。比如,那些信奉“科学主义”的人,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这不正是以理性武装起来的非理性么?环境问题属于典型的理性的灾难,正是由那些使得人类生活更美好也更丰富的科学技术进步而导致的。又比如今天争议不断的转基因生物的利用,怎么评判支持者和反对者谁理性谁非理性,科学理性本身能化解纷争吗?难。倒是社会学家们给出了意见:“如果对新开端可能蕴含的风险有充分的怀疑,那么最好是坚持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所谓预防原则。这个意见显然是符合康德理性使用判据的。在我看来,为了满足康德判据,戴维·罗斯在《正当与善》说的一段话:“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什么行为会在长远的眼光看来对我们有利。然而不确定的是,如果我们竭尽全力地评估我们的行为在这方面的趋势,而不是随意而行,我们一般而言更有可能获得好处。”似可作为行动指南。
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表面上把科学的地位抬得很高,让迷信没有藏身之地,但稍作反思就会发现,内里则刚好相反,除了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得到发展以外,科学的精神却生长艰难。我们今天看到台湾五都选举前马英九带领一帮人到庙里烧香,祈求国民党胜选,已经不认为是迷信了,只是觉得有点搞笑,但比起当年红卫兵砸庙宇毁菩萨哪个更可笑?当然,我们现在又开始了重建庙宇、重塑偶像、搜寻并供奉圣(神)迹,领导剪彩、大师开光、甚至国家公祭,好不热闹,迷信(信仰?)似乎卷土重来。
信仰也好,迷信也罢,其实并不可怕,只要不和公权力搭界。这一点,我们似乎一时不能做到。某古城前几年举办了一个“迎关公归故里”的盛大活动,本埠报纸显目的标题称关公为“某市第一任市长”,这显然不是迷信,而是算计。
理性的历史上也有污点,而迷信也不总是意味着愚昧和落后,并且“信奉宗教信条也是符合理性的。”对这个结论,英国当代基督教分析哲学家斯温伯恩当然有他严格的论证,这似乎为我们重新审视理性与迷信指明了思路。观察我们的社会,体认我们的心理,理性和迷信绝不是泾渭分明的。而迷信在我们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被用来管住道德的,甚至就把它当成理性,所谓“以理杀人”,正是几千年的历史。前几年,发起过一阵子讨论“人类应不应该敬畏大自然”,其实在我看来,借用大自然说事,是因为它的确强大无比,而每个人又无法逃离开它,因此,人类应该管好自己的道德,不要轻易向它发起挑战。有敬畏之心,必不敢胡作非为。历史来到今天,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出于非现实功利的敬畏之心存在?
在展望人类关于宇宙起源及命运的大统一理论之后,霍金只是认为,人类理性的终极胜利也只是终于知道了上帝的精神。那你说他是理性还是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