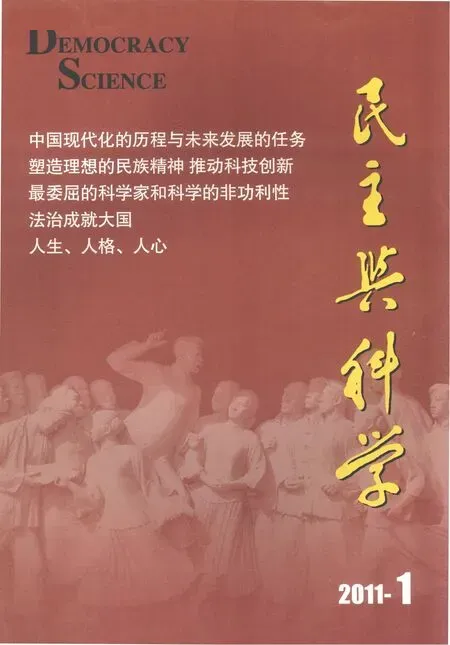2010年中国法治的进步与局限
2011-12-24张千帆
■张千帆
2010年中国法治的进步与局限
■张千帆
2010年,中国制定了《社会保险法》和《人民调解法》,修改了《保密法》、《国家赔偿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同时出台了不少规章和规定。总的来说,这些法律规定的主要亮点在于技术细节方面的完善,其程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以新制定的《社会保险法》为例,这部法律的一大进步是实现了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异地漫游”;对于跨统筹地区就业的个人,其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这一规定为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全国联网提供了法律基础,也为劳动者跨地区工作清除了不必要的障碍。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建立这样的全国联网系统显然不是一件难事。但同时不能不看到的是,技术进步并没有解决这部法律解决不了的实体困难,那就是养老和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有限、保障程度过低。目前大多数人都不可能靠养老金过活,医疗保险也只管小病,大病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仍然是灭顶之灾。要让《社会保险法》真正发挥作用,国家今后还得投入比现在多得多的财政,增加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和力度。
《保密法》修改的主要亮点也在于技术细节,譬如以往中国只注重保密,而不知道解密的重要性;如果已经超过保密时效的事项仍然被保密,人民的知情权自然就遭到剥夺。因此,此次修改规定了两种解密制度:一是自动解密制度,保密期限已满的国家秘密自动解密;二是主动审查制度,要求有关单位“定期审核”所确定的国家秘密,不需要继续保密的应当及时解密。更重要的是,修改后的《保密法》有限度地上收了定密权。以前由于有权定密的政府单位过多,定密程序十分随意,造成“国家秘密满天飞”的现象,严重限制了公民知情权。现在县级以下的单位不再拥有定密权,而且规定了定密责任人制度:单位负责人及其指定的人员为定密责任人,负责本机关、本单位的国家秘密确定、变更和解除。新法对定密主体的限定和程序的完善有助于纠正国家秘密范围过宽的现状,但这种改善是有限的。严格来说,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资格确定国家秘密,因为国家秘密应严格限定于国防、军事以及某些敏感的特殊外交事务等专属中央政府的事项,其余都属于必须向社会公开的政府信息,因而只有中央有关部门才有权决定什么是“国家秘密”,地方政府仅有权执行中央规定。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的治国理念——既然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内部治理,有什么地方事务是不能或不应该向老百姓公开的呢?即便是公安侦破等当时不宜公开的信息,也属于信息公开的例外,而非严格意义的“国家秘密”,而我们一直将两者混为一谈,从而极大扩张了“国家秘密”的范围。现在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都有权确定国家秘密,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秘密满天飞”。今后需要进一步上收定密权,将其严格限于中央有关部门,并使之接受全国人大有关专业委员会的监督。
《村委会组织法》的修改经过激烈争议,最后顶住各级官员的普遍压力,保留了任期三年的规定,有利于村民自治不受上级干预,因而这种不修改也未尝不是一种“进步”。新法进一步规范了委托投票,有助于治理选举舞弊。另一方面,新法没有对选举细节进行适当规定,例如没有规定当场记票制度,从而为选举舞弊留下空间。对于作用越来越重要的村民代表会议,新法也没有实质性地规范其选举和组成,成为今后村民自治的一大隐患。总的来说,新法对技术细节的改良不足以在整体上改善村委会选举质量,而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有所强化。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村民自治的前景面临诸多变数。
《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施行后,由于赔偿范围小、标准低、程序复杂而备受诟病,甚至被戏称为“国家不赔偿法”。这次修改除了赔偿程序有所改进、赔偿时间有所限定之外,还扩大了赔偿范围,明确规定了获得精神赔偿的权利以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赔偿责任,将监管人员虐待或放纵他人实施殴打、虐待等行为纳入赔偿范围。这类明显违法行为在许多国家被界定为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国家并不承担直接责任,国家替代个人赔偿被认为有纵容个人犯法之嫌,甚至被认为是慷纳税人之慨以弥补政府管教不力的过失。从受害人权利保障出发,由于肇事者很可能赔偿能力有限,国家确有必要保证赔偿;但是从政府法治、责罚分明、提升威慑的角度来看,国家有必要在赔偿之后对明显的个人过错加大追偿力度。不可忽视的是,目前掌握公权力的某些人之所以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权利,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正是因为法律责任太小;对于那些无法无天的公职人员,倾家荡产的罚款或许是最有效的震慑,而国家赔偿的目的显然不是为肇事者提供“保护伞”,而是为受害人提供充分救济。由于新法关于追偿力度和精神赔偿幅度的规定存在极大弹性,今后的司法实践有必要适当把握,在为受害人提供充分救济的同时适当追究肇事者的个人责任。
调解本来可以是解决纠纷的有效机制,只不过这套民间机制不太适合法院,反而容易混淆司法职能并加剧司法政治化。《人民调解法》明确规定了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有助于将民间调解机制规范化和制度化,进而有望厘清调解和司法职能的分界。调解应该在法庭外进行,调解不成的案件进入庭内诉讼;对于调解达成的协议,法院的主要职能限于协议的解释和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将属于司法的(诉讼)还给司法,属于民间的(调解)还给民间。
最后,程序性规定的作用当然未必仅限于形式,而是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国家安监总局出台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将领导带班下井制扩展到所有矿山,要求每个班次至少有1名领导在井下现场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另外,矿山“领导”明确为矿山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领导班子成员和副总工程师。如果矿山企业没有领导带班下井,从业人员有权拒绝下井作业;如果从业人员发现并确认带班下井领导无故提前升井,经向班组长或者队长说明后有权提前升井。虽然这些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打折扣,但是让矿山领导“陪死”确实有助于促使他们重视矿山安全,从珍爱自己的生命出发加强矿山安全保障,从而让广大矿工也能搭上安全保障的“便车”。和所有其它规定一样,这条规定的关键也重在落实。让领导和矿工“同生死”当然好,而目前将监督实施主要交给矿工自己,但是矿工是否敢坚持要求领导下矿?矿工自己是否有意识坚持这条要求?如果缺乏具体的监督措施,只有等到矿难发生后才发现领导没有下井,那么任何处罚都为时已晚。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