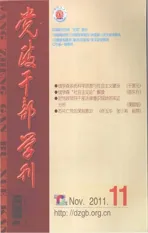钱学森“社会主义论”解读
2011-12-24苗东升
苗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钱学森“社会主义论”解读
苗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本文回顾了科学家钱学森在学术研究中如何提出“社会主义论”这一理论课题,略述了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环境的再认识,强调他的再认识是以坚持共产主义方向为指导原则的。
钱学森;社会主义论;再认识
钱学森不仅是科学家,而且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科学家。翻阅《钱学森书信》就会读到“我们搞学术研究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走向共产主义”[1],“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2],这样的话比比皆是。但钱学森毕竟是科学家和学问家,他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主要体现在学术理论思考上。“现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有那么多问题等待哲学社会科学界去解决,真使人有‘危机感’了。”[3]危机感使晚年钱学森把很大精力投放于研究社会科学,努力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锻造新的科学理论。以钱翁的用语讲,这种理论探索可以统称为“社会主义论”。
一、导言:论题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身处变革大潮,开始研究社会科学而又极具历史感的钱学森,已经感觉到时代变迁的脉搏跳动,领悟到历史对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呼唤。他决心跟上时代步伐,投身于这种理论探索中。
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潮流,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一个快速变化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科学理论。钱学森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自觉运用了系统科学的整体观、过程观、环境观、非线性观、动态观等等,颇具理论深度和新鲜感。当然,他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1984年7月5日钱学森致信中央党校的吴健提出:“现在世界上的确出了许多新事物、新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代没有,轮到我们来总结、概括。”[4]同年年底又致信吴健:“列宁写了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您何不写一本新的什么阶段?”[5]这表明,钱翁意识到世界历史发生了时代性改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给诸多标志新时代的新事物、新情况以新的理论概括,写出新时代的著作。“轮到我们来总结、概括”,这自信而豪迈的言词表明,钱翁认定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学人的重大责任。至于新书和新时代的主题和名称是什么,他尚未想清楚,只能猜想类似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大致上是“新的什么阶段”。而新书的作者,钱翁认为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家,他自己则是点火者、推动者。
1985年5月9日他致信国家体改委的唐明峰说:“总之,世界在前进,我们要研究新事物。我也想:列宁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1916年,快七十年了,该有一部新著作了。谁来写?”[6]钱翁想的、说的还是同一件事,其急切的心情跃然纸上。
1986年3月10日他又致信吴健:“我祝您在未来十年中写出 《资本论》的续篇”。[7]此信有两点重要新意。其一,新著作在内容上是对新时代经济和政治的基本态势和走向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论述,称得上《资本论》的续篇。其二,这样的著作所用方法也应该称得上《资本论》的续篇,那就“一定要用数量经济学和系统科学的方法”。(同上)但新书的主题仍然不够清楚,还不能拟定具体的书名。
1986年8月12日他再次致信吴健指出:“那时列宁还没有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迫切要回答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所提出的问题,真是心急如星火!”[8]钱学森这时的认识有了重要新进展,明确了列宁时代与当前时代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同需求。列宁面对的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尚未列入日程上来,他的书没有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数十年的摸索和实践,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新时代的主题明确了,新书的主题应是回答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所提出的问题。此意在后来给朱光亚的信中说得更明白:需要的“是探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书。”[9]但新书书名仍未想清楚,表明此时钱翁思考的理论深度尚不到位。
1989至 1991年国内外发生的事件是规定和表现新时代到来的历史事件。它激起社会主义者钱学森的高昂斗志,喊出这样的时代呼声:“在今日社会主义事业遇到暂时困难之际,我们是否应该再次宣传伟大的共产主义?我看要结合100年来的事实,加以宣传。”[10]这些事件更激发了钱学森的理论悟性,把近十年来思考的理论问题完全想清楚了。在1991年7月15日致中国社科院孙凯飞的信中说:“您和于景元同志在撰写的大文章是一篇重要文章,它实际是讲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将来可以继续努力,写成一本书,是继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之后的《社会主义论》。”[11]这段话言简意赅,标志着大约十年来钱翁魂牵梦绕的一个认识过程完成了。
这段话体现了钱学森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一种宏观把握,其基础性背景则是对世界历史的时代性演进的宏观把握。从系统科学原理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一个非线性动力学过程,存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要矛盾,规定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同历史任务,每一阶段都需要并且能够产生自己标志性的理论著作,而后一阶段的著作必须是前一阶段著作的续篇。马克思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写出反映那个时代的理论著作《资本论》。列宁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写出反映那个时代的理论著作《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处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代,写出反映那个时代的理论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世界现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需要写出《社会主义论》这一标志新时代的著作。四个时代的前行后续构成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历史演进的序列,四个“论”则构成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序列。
实际情况是,至今没有人起而响应钱学森的呼吁着手写这样一本书,他自己也没有写。但深入解读他的著述可以明确地感觉到,晚年钱学森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91年以后钱翁关注的中心,已经从系统学等具体科学问题转向探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在这方面虽然没有专著,却留下大量分散的言论,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问题论及社会主义,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题、科学猜想,实际上为这部大作勾勒出一个粗框。
准确地说,这样的《社会主义论》也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多卷本系列著作,不同卷由不同时代的作者撰写。社会主义建设既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包括前行后续的多个历史阶段,它的指导理论就不会是某个阶段的某个人能够全部完全创立的,只能是一个接力跑的过程。事实上,列宁和斯大林做过有其特色的探索,留下他们的理论思考;毛泽东做过有其特色的探索,留下他的理论思考;邓小平做过有其特色的探索,留下他的理论思考。今后还会有这样的人物及其著作,不是张三,就是李四,历史会作出选择的。
二、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对冤家,前者在娘胎里就已包含着后者的因素;而社会主义,不论理解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是理解为横亘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一种社会形态,只要它还没有建成,自身就仍然包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完全消亡之时,也是社会主义消亡之日,因为那时人类已进入共产主义了。所以,认识资本主义需要研究社会主义,认识社会主义也需要研究资本主义。
人类社会无疑是一种非线性动力系统,而且具有自然科学考察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所没有的复杂性,钱学森称之为特殊复杂巨系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就是这类特殊复杂巨系统,有着曲折复杂的演化过程,在它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形成前行后续而显著不同的多个时代。这种特殊复杂性必然带来两个重要的认识后果。一是每个时代总有些本质特征是当代人看不清楚的,需要以后面的时代为参照系回头看才能看清楚,即所谓“当代人看不清当代事”。二是非线性的演化过程总会使系统在每个时代都产生出前一时代无法预测的新特征、新规律,不能简单移用上一时代的认识,需要新时代的人重新研究,把握系统在新时代涌现的新特征。这两方面都要求随着时代变迁对系统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反复进行再认识。事实上,《资本论》是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没有认识清楚的资本主义进行的再认识,《帝国主义论》是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再认识,《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代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另一半——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进行的再认识,构成一个不断再认识的系列运动。到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全面融入资本主义仍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系统中,时代又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不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你就不知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
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过程中,钱学森明确提出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问题。他说:今天的“资本主义也早不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了 (当然也不是列宁时代或毛泽东时代的资本主义——引者),以后有第四次产业革命和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一切在变化呵,不进行再认识能行吗?”[12]钱翁在这里提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课题,但人们不能苛求他本人对此问题给出系统的回答。钱翁没有系统地论述过资本主义如何变化,亦即如何对它再认识,他留下的是一些只言片语。但这些只言片语却极富启发性,深邃而精准。更重要的是,他在对资本主义再认识中所秉持的态度和运用的科学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钱学森认为,我们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的目的是研究今天的资本主义,回答“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13],从中引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来。针对中国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词的混乱状况,他提出两点主张。一是把今天的资本主义放在资本主义作为系统的历史演变全过程中观察,跟过去的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把握变化。二是“还得从根本原理出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反馈作用。”(同上)第一点显示出一种系统思维,强调用整体观、演化观和历史观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第二点是确保这种再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是《资本论》的续书。说具体点,钱学森是从产业革命的角度提出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他的分析可以用下表给以简要说明:
钱学森对资本主义再认识不是简单地贴标签,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在系统科学中,钱学森基本上搞的是他组织理论和相关的技术。但他又是把自组织理论引进中国的主要推动者,熟悉普利高津等人倡导的自组织演化理论,并把它应用于学术研究中。用这一理论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复杂生命系统,具有一定的适应环境、自我调整、自我改进能力,即在环境压力这种他组织作用下进行自组织的能力。我们面对的现代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资本主义经过一个半世纪反复的自我调整和被迫调整的结果。系统科学家钱学森当然懂得这一点,尽管他没有明确使用自组织理论的语言,系统自组织演化的观点清晰而准确地体现在他有关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言论中。需要指出,发达资本主义是新闻用语,科学的概念应该是金融资本主义,一种更高级、更有欺骗性,因而更腐朽的资本主义。
就经济方面说,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是没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一味发动自发性而否定国家的宏观管理,造成经济领域的极度无序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对此给以理论的批判。但一系列经济危机以及由之引发的社会动乱迫使资本主义进行自我整顿,对市场经济加以某种宏观管理,在市场经济中逐步引入有序性。所以,“现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早已不是完全无序的了,有国家干预、调节”。[14]
就政治方面看,资本主义在环境压力下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调整,钱翁也从政治方面深入思考过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问题。“资本主义对社会形态中的政治文明是有贡献的,认识到要重视人民主动性,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要发挥人民的潜在能力。”[15]如此评价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
对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钱学森也作出再认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系的出现,是不是也是一次产业革命?列宁在他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讲了生产组织的变化,金融资本的出现等等。列宁在书中着重从政治上批判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性,但也讲了整个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这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一个工场主的生产体系是很不一样的”。[16]又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就进入到现代科学技术的时代,工作方式从个体劳动变为集体劳动,科学技术工作社会化了。”[17]列宁重点讲的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揭露“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反动性。但这一历史性变化也有积极的一面,资本主义从一个个工场主的生产体系进化到出现整个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导致一次新的产业革命,科学技术进入到现代科学技术的时代,都是历史的重要进步。经济活动进一步社会化,人类活动各方面的社会化,实际上是为社会主义做准备。
但钱学森绝不一味美化现代资本主义,在肯定它的成绩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指出它仍然具有无法摆脱的局限性。在肯定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国家干预、调节后,钱学森立即指出:这“不过只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已”。[18]在肯定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进步后,他也立即指出:“但又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资本家的利益,所以到底有局限性,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又有不文明的地方。”[19]在肯定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积极意义之后,他又立即指出:“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劳动的集体化和社会化是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根本矛盾的。”总之,“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在制度内部无法解决”[20];“不管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怎么发达,它有治不了的病,这病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而且“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越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内部矛盾就越解决不了。”对资本主义自我调节之阶级本质作如此明晰的揭示,是现在的许多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做不到的。
今天讲再认识中心是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即所谓发达资本主义。“我们必须搞清楚:第五次产业革命是什么?它是怎样改变或重组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的?”[21]钱翁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大问题,可惜至今未见到令人满意的理论分析。
三、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社会主义事业也是一种特殊复杂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需要反复进行自我调整、适应、改进,经历一个长期、曲折、复杂的过程。只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来构建社会主义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 (特别是错误和失败的教训)来建立。早期社会主义建设是一种试错式的实践过程,要允许试错式的探索,更要及时地、科学地、反复地总结经验教训。这也就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及时的、科学的、反复的再认识。如钱学森所说:“我们对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和对所有客观世界,包括人自己在内,都是在经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认识、不断发现的过程。”[22]从上世纪 80年代起,钱翁就自觉地开始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得出这样一个总结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复杂巨系统,我们(国内外的社会主义者)“都曾经头脑简单过,曾经想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但结果不行,碰了钉子。”[23]他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可以分为苏联和中国两部分。首先看他对苏式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又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从哲学上进行再认识。“我现在想: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思想水平不算高,所以在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后继无人,苏联哲学家屡犯错误。”[24]苏联哲学界用机械唯物论对待科学创新,动辄扣上唯心主义大帽子,批摩尔根遗传学,批分子结构共振论,批控制论,等等,钱学森把它概括为“以哲学反对科学”。结论是:“可见苏联在列宁之后,直到现在,犯了大错误,丢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25]
二是从科学技术上进行再认识。苏联在科学技术上曾有过重大创新,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也有严重错误,不仅表现在以哲学反对科学,而且 “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中不提倡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研究及解决问题!”[26]晚年钱学森大声疾呼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技术,一再告诫科技工作者警惕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论,就是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结果。朗道是享誉世界的苏联物理学家,钱翁在阅读朗道传记后发现“全书不见马克思主义哲学”[27]。郎道“成长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本应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物理研究的指导;而此书对此极为重要的思想,未置一辞!”这当然不仅是朗道和传记作者的错误,而主要是“斯大林的失误,他背离了列宁主义,忘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们千万不要再犯这个错误!”[28]特别是,苏联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思想,未能解决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此乃苏联在与美国竞争中最终落败的重要原因。
三是从政治经济学上进行再认识。西方世界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是世界系统形态演化史上一件大事。列宁站在时代制高点,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揭露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基本结论至今仍然正确。但对于组织管理大生产和发展大科学、大技术、大工程,垄断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性的一次质的提高。从历史大尺度看,这是为社会主义做组织文化上的准备,因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是高度组织起来的复杂巨系统,大工业、大农业、大科技、大民主等,都必须按照科学技术来经营管理。列宁对此认识不足是一种片面性,直接影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钱学森说:“回顾我在50年代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很受教育和鼓舞,对当时的苏联模式充满了信心!”[29]这并非说那时的钱学森对苏联模式毫无疑虑。他曾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后来五院成立,我到南苑一院工厂去看,发现就在这么一个小厂,五脏肝胆俱全,连螺钉螺帽也自己有车间生产。这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工厂单干,没有协作,生产效率极低。到苏联去参观访问,才知道这是苏联模式!我心中有点想不通,这样干效率太低呵!”[30]“想不通”就是对苏联模式有疑问,发现苏联模式效率低就是一种再认识。但总体上看,此时的钱学森相信苏联模式就是社会主义模式,没有看出问题的本质所在。这在当时属于主流社会的共识,是一种难以避开的历史局限性。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的解体,终于使他改变了认识:“直到党中央决定要在我们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引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组织模式,搞公司集团,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垄断大公司’。这才明白‘垄断’是高效生产组织模式,资本家用它,我们也要用它。 ”[31]
钱学森更重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再认识。从思想层面看,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再认识。今天回头看去,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再认识。一种势力借此再认识之机完全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试图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钱学森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趋势,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我们也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受苏联老大哥影响,新中国也存在“以哲学反对科学”的事。钱学森批评苏联哲学界,也是在批评中国哲学界,揭露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存在以哲学反对科学的教条主义,纠正这种错误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走向另一极端,“现在的情况是有的人在坚持马列主义,而有些人则走偏了路,反对马列主义哲学,这就更不对了”[32],“现在诚然是哲学的贫困,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了”。[33]钱学森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倾向。在他看来,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才能正确认识今天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现在和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钱翁晚年努力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11个哲学分论,强调通过它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些努力都涉及到从哲学方面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思考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提出“科学技术是我们的时代精神”[34]这个重大理论命题(钱学森命题)。对现时代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必须站在这个理论高度、联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际。实事求是地说,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都重视科学技术,新中国头30年的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但科学技术本身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是历史地改变着的。不必说马克思时代,就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期,科学技术还没有成为规定时代精神的决定性因素。从世界范围看,这一变化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即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世界前沿,中国人当时不可能首先意识到这一重大变化。这就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际上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变化。跟踪世界科学技术前沿发展的习惯,对科学论的长期思考,“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使钱学森迅速接受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并给以科学的阐释。钱学森命题和邓小平命题一起开拓了一个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全新视角,钱翁在这方面有大量论述。
科学技术能够成为规定时代精神的因素,原因之一是它在20世纪中后期基本上实现了体系化,初步形成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其直接后果有二:一是由于有了完备的分系统划分,不同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大大加快了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二是层次结构的完整化大大加快了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导致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加速进步。但这种变化首先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却落在后面,此乃导致它解体的深层原因之一。新中国也落后了,我们的许多失误与此密切相关。幸运的是中国出了个钱学森,他适时地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概念,初步建立起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你要认识今天的社会主义,就必须自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整体地把握现代科技的发展。细读钱学森后30年的著述就会发现,他努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从不同方面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在科技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钱学森针对不同具体情况发表的意见都包含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如批评 “科技人员身后都有部门线条牵着,没有真正的合作共事的工作条件”,指出这是背离社会主义的表现。他赞同社会主义要树立大科学的观念,进而提出“应该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研生产关系”的问题。[35]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在经济建设方面,以往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需要并且能够引进市场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在1987年,钱学森就开始用系统科学观点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我觉得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用微观管理的办法将指令下达到每一个企业,但是问题在于企业的状态不可能每一个瞬间都知道,实际上最后下的指令是糊涂指令。”[36]这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的呼唤。又说:“看看我们中国,因为长期在封建制度的控制下,又有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生产没有发展起来。我认为其重要原因就是生产、社会管理上的问题,也就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问题。从前习惯了的一套管理叫微观管理,计划经济已经管到每一个工厂里去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很落后的管理方法,完全的微观管理。而今天,这么复杂的经济体制,再用微观管理的办法,是不行的,领导人再聪明也管不了。所以,一定要从微观管理转到宏观管理,微观上要搞活,宏观上来控制、调节。”[37]这些论述体现了自组织与他组织辩证关系的系统思想。所谓“微观搞活”就是充分发挥经济活动中的自组织作用,“宏观调控”则是充分发挥经济活动中的他组织作用,两者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这种认识,当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后,钱学森很快就接受过来,并依据系统科学从多方面给以论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上的新事物。市场固有的自发性总是在滋生资本主义,要使市场经济接受社会主义的监督和管理,需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机制。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包围中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相当艰巨复杂的过程,搞不好有可能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化。这是中国面临的一道难题,钱学森没有正面提到过。但在讨论社会建设的不同具体问题时,钱翁总要提醒人们要明确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为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富人服务。例如,他明确提出建筑哲学“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38]。我猜想他思考过市场经济的阶级属性问题,只是尚未形成可以发表的观点。
钱学森要求学界搞清楚第五次产业革命如何改变或重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目的是借鉴它们的经验来改造和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他认为:“第五次产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是有矛盾的;而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是协调的。”[39]并预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21世纪,第五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结合起来,将引发一次社会革命,新的一次社会革命。”[40]基于这一判断,钱翁主张要“按照第五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的内涵来规划设计现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41]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碰到的新问题,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即对新的产业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变革的认识。只有科学地认识了新产业革命将赋予社会主义什么样的新内涵,才能正确地规划和设计现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
四、对社会主义的环境——世界系统的再认识
系统与其环境是互塑共生的关系,系统的结构和质性,组分的取舍、演变、新陈代谢,都与环境密切相关。科学社会主义是在世界系统化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随着这种系统化不断深入发展而演变到今天。要认识不断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必须对它所处的不断演变的世界环境进行再认识,通过认识变化了的世界来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演变。这是钱学森社会主义论的重要内容。他说:“今天我们的国家所处的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到下个世纪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这将是一个高速变化的世界”。[42]钱翁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高速变化的世界”。
第一,战争问题。新中国的前30年,我们是在新的世界大战难以避免这一判断下认识和部署社会主义建设的,这在当时是正确而且必要的。但战争也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到上世纪80年代就需要新的认识。在1987年的一次报告中,钱学森向听众发问:“请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世界跟过去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特别是“有没有在关键问题上不一样的?”他的回答是:“大家要注意战争问题”。[43]钱学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战争演变的历史,分析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判定人类战争这个非线性动力学系统随着武器破坏力急剧增大,已经“大到一个临界点”,“就是核武器的破坏力,核武器作用的距离都是全球性的”[44],大的核战争是全球性的,没有胜利者。20世纪战争趋势还要继续下去,但真正打大的核战争,谁也不敢打。“战争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现象,正在走下坡路,只有小的冲突,局部战争不断”。[45]以新中国建立100周年为限,钱翁判定:“如果我们搞得很好,可能世界大战打不起来”[46]。在这样一个世界环境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论的重大课题之一。钱翁从人才与智力、科技发展、国家的整体功能、改革的整体性、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等方面作了论述。
第二,世界的一体化发展。资本主义兴起开启了地球人类系统化的进程,并于 19世纪末完成,人类从此成为一个巨系统,即世界系统,一种特殊的社会系统。这个巨系统有两个基本结构特征,一是以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霸权,两者决定了世界系统最初的社会形态。一百多年来,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俄国、中国等国内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等,世界系统已发生了重要变化:到20世纪末,出现所谓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钱学森十分重视这一历史趋势,判定“世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大社会了,哪个国家也不能闭关自守,闭关自守只会落后。世界一体化,经济、文化交往频繁。 ”[47]又说:“21世纪的世界,是整个集体化了的世界”[48],并判定这一变化标志着人类 “历史的新阶段”。[49]由此得出结论:“世界很可能不发生大的战争,如果照这样发展,世界的一体化就更表现出来了。”[50]这是钱翁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世界环境的基本判断,亦即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来论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钱学森还援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概念来分析世界系统的演变,提出“世界社会形态”概念。他对此概念的具体表述未必准确,需要学界商榷,但其思想是深刻的。世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既是一种挑战,更是历史机遇。“我们的任务是研究现阶段的世界社会这一社会形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内容。”[51]中国如何适应这一趋势改变自己,如何在世界系统现在的社会形态中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际中是极具研究价值的。
五、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技术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不仅是理解的唯物主义者,更应当做实践的唯物主义者。[52]作为学者的钱学森是从工程技术走向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我思考问题,一方面在理论上要站得住,另一方面在工程上还要有可操作性。”[53]作为终身从事科学技术创新的学者,钱翁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其长处和中心不在于上述深层次理论问题,而在于如何把现代科学技术全面地引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或者说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确立全面的科学技术基础。钱翁岳丈、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有句名言: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54]钱学森在这方面的全部努力,就是让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方面都做到工程跟着理论走。他的理论思考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十点:1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思考,2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考,3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4关于社会主义地理建设的思考,5关于社会主义人民体质建设的思考,6关于社会主义国防建设的思考,7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学说的思考,8关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思考,9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组织文化的思考,10关于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的思考。鉴于这些论述比较具体,有大量文献资料,加上篇幅有限,本文就不再展开论述了。
六、坚持共产主义目标
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形形色色。就目前的中国看,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谢韬等人讲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宣称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中国应该且能够追求的目标是建设北欧 (实质是美国)那样的社会。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讲的、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所以,仅仅说钱学森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不够的,还必须弄清他讲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钱学森曾经这样说:“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理想境界……这种共产主义的最高文明形态仍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人类解放,特别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应该追求的崇高理想。”[55]这段掷地有声的话明确地回答了上面的问题,连讲四个“真正的”,真正的人性,真正的人道主义,真正的追求人类解放,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要跟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对于共产主义,钱学森不止有上述政治表态,还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理论思考,提出新见解,都是有关共产主义学说的重大问题。
一是思考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第四节讲到钱学森关于世界一体化和世界社会形态的言论,其用意在于论述如何从现在的世界向将来的共产主义过渡。钱翁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世界一体化的政治的社会形态”,而现在的世界“国家制度不同:有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有资本主义制度以前的国家,但又有社会主义的中国等,国家又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即‘南’与‘北’之分。是世界一体,又多极分割,矛盾斗争激烈。这是过渡到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必经阶段。”[56]钱翁讲的世界社会形态究竟指什么?他回答说:“这将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一种过渡的世界社会形态。”[57]钱翁又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大同,不是一国一国自理。怎么从一国一国过渡到世界大同?这是个未回答的问题。”[58]钱翁期望中国理论界来回答这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二是思考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问题。视共产主义为乌托邦的人有一个自鸣得意的论点,就是认定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终极目标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他们的观点才符合辩证法。这是在反对形而上学的名义下搞真正的形而上学。绝对的终极目标当然不存在,但相对的即阶段性的终极目标是存在的,须知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不等于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人类社会是多维度系统,在每个维度上都有前行后续的多个阶段,最后阶段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该维度上的终极目标,但到达它并非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社会是多维系统,迄今人们关注的是财产维 (所有制维),在此维度上共产主义社会确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一旦进入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在财产维上就走到尽头,不会再有新的进步。但其他维度的作用将凸显出来,人类社会作为系统将在另一个维度上展开不同社会形态的演化。同样,在那个维度上系统也会存在终极目标,一旦实现那个终极态,系统将沿着新的维度继续演化,直到人类在宇宙中消失。钱学森思考此问题的视角略有不同,他的观点是:“到了大约200年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世界大同,最终消灭了战争,国家没有了,国界没有了,全世界一体化。这就开始了人类社会的第二大阶段,人们完全自觉地利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创造历史”,然后还有第三大阶段、第四大阶段等等。[59]
三是估计何时可能到达共产主义。上一段引文已包含钱学森对此问题的答案,即200年后。钱翁通过分析21世纪将相继发生的三次(第五、六、七次)产业革命,由它们引发的中国第三次社会革命,以及世界社会形态的发展,估计人类社会到23世纪就可能进入共产主义。这当然也需要深入细致的论证,但不能要求耄耋之年的钱翁承担此项任务,可贵的是他给出了大思路。
最后需回答的问题是:你说钱学森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但他具有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感情基础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就他的社会影响、广泛的人脉和超常的能力而论,晚年钱学森完全可以借市场化之机成为大富翁。但事实表明,他姓钱不爱钱。曹雪芹给史湘云的判词是:“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我们有充分的根据下这样的判词:钱学森“从未将升官发财,略萦心上”。这就是他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思想基础。中共中央组织部把他同雷锋、王进喜等“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使他“心情激动极了”[60],则是钱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感情基础。只有愿意置身于普通劳动者行列的人,才具有共产主义者的感情基础。自然,对于把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准则的人来说,这是不可理喻的。
[1][2][3][4][5][6][7][8][9][10][11][12][13][14][15][18][19][21][22][24][25][26][27][28][29][30][31][33][34][35][39][40][41][49][51][58][59]钱学森.钱学森书信 [M].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5-391,7-385,3-318,1-480,2-110,2-282,3-091,3-231,5-063,6-091,6-063,4-264,5-009,4-264,4-409,4-264,4-409,5-010,8-331,5-3485-349,5-348,5-349,5-346,9-054,9-054,9-055,5-349,5-359,9-492,6-112,8-006,8-288,7-268,7-121,7-120,6-092.
[16]钱学森.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33.
[17]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 (增订本)[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518,518,519,520.
[20][23][36][37][42][43][44][45]
[46][47][48][50][53][55][56][57]钱学森.创建系统学(新世纪版)[M].上海交通大学 出 版 社 ,2007:33,68,27,21,25,22,22,184,24,184,132,23,215,79,185,208.
[32]钱学森.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M].杭州出版社,2001:294.
[38]鲍世行,顾孟潮.钱学森建筑科学思想探微[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513.
[5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人民出版社,1961:38.
[54]王文华.钱学森实录[M].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31.
[60]钱学森.创建系统学[M].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254.
责任编辑 姚黎君
B0
A
1672-2426(2011)11-0009-06
苗东升(1937-),男,山西榆社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系统科学、系统思想、复杂性科学及其应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