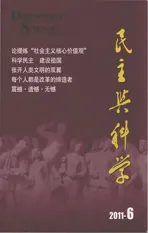南科大之困:循规律还是循国情
2011-12-23王长乐
■王长乐
由“南科大内忧”引发的舆论浪潮,估计在“南科大决定面向国内外招聘200多名教师和工作人员”、“南科大成立理事会”、“南科大聘任一位副校长”等一系列举措的影响下,将会很快地归于沉寂。而导致南科大“内忧”的一些问题,也将在南科大内外力量的积极努力下很快化解,然而,经历过“成立党委会、理事会”(成员一半是政府官员、另一半中的一半是现任或往任著名大学领导人——没有真正的教育理论家、没有教师和学生的代表——显现的是“官本位”特征),以及朱清时校长“市长任南科大理事长是现实下必要选择”的表态,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此南科大已非彼南科大了,其感觉正如某学者所言:“‘另类’的南科大已经彻底被官方‘招安’了,走向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学的不归路。”
这虽然是一些“梦想南科大能够引领中国高教改革未来之路的人士”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但在作者看来,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奇怪,它是南科大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南科大模式无法避免的社会形态。而作者其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南科大“内忧”风波虽然停息了,但导致“内忧”的大学体制和教育问题还依然存在,“内忧”的矛盾还在发酵和继续,它不仅会影响南科大的道路和前景,而且会为中国大学的整体性发展提供负向的提示和警戒,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为南科大、以及中国大学的整体性发展提供理论启示。
一
审视南科大“内忧”的争论,可见其基本观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所谓的“规律论”,一个是所谓的“国情论”。其中,朱清时校长的主张被归结为“国情论”,他认为南科大应该立足中国国情来办学,因而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利用一些有利时机,大胆地采取“改革性”行动,来破除阻碍大学体制进步的“坚冰”,以便为南科大赢得发展的空间。比如: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以“既成事实”倒推大学体制改革。而香港科技大学三位教授的主张则被称为“规律论”,他们主张南科大应该与现体制保持平衡,在现体制的框架下立足教育规律来办学。具体的思路是应该认真规划好办学思路和教学制度,然后根据规划和制度按部就班地办学。比如:他们不主张“仓促招生”和“盲目上课”,认为这种做法有违教育规律。综观双方的主张和分歧,作者以为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在规律论者而言,所讲规律无疑应该是全面意义上的规律,而不能只是某一种层次上的规律。而香港科技大学三位教授所讲的“先制定大学发展规划、大学章程、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然后根据大学发展需要,有的放矢地聘任教师和设置课程”的规律,在大学发展中的确很重要,但立足中国大学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立足像南科大这样意欲“要为中国大学改革创路”的大学的实际情况,这样的“规律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一是这样的“按教育规律办学”思路,既不是南科大“创校”的初衷,也无法显现南科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南科大“创校”的目的,就是要在传统的大学中创出来一条新路,就是要反传统大学的潮流,若“循规蹈矩”的办学,南科大就失去了创办的意义。二是这样的规律并不是大学教育中的上位规律,而是中位或下位规律,对其遵循是需要在上位规律实现后才应该考虑的事情。而对南科大、以及中国所有大学而言的上位规律,就是根据世界大学通例,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肯定、确认或授予。也就是说,大学要有完全的办学自主权。
作者这种看法的依据是,大学的自主权对大学而言,是大学能够成为真正大学的最基本的思想和制度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大学的思想就会由于受到外界力量的禁锢和束缚,而失去大学的精神和灵魂,变得残缺不全或萎靡不振;大学的制度就会因外界力量的干扰,而背离教育本性,变得左支右绌、自相矛盾;大学的文化就会因为抵御不住强权威慑和利益引诱,而陷入奴性和欲望的泥沼,变得腐败、堕落、投机、势利、庸俗。而朱校长在办学过程中的“当机立断”(自主招生)和“虚与委蛇”(设立党委会、由市委组织部选聘副校长、成立理事会等),可以说都与这个规律的内容缺失有关。否则,若南科大与外国大学一样,天生就拥有大学的自治权,那朱校长就不用去纠结于是否要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由组织部选聘副校长这些事了,他完全可以专心致志地考虑“如何选教师,如何筹集经费”这些国外大学校长们所从事的工作。因为在世界大学的制度和活动逻辑中,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作者以为,要讲教育规律,就应该首先讲这个上位规律,而不是在回避了上位规律的情况下,去讲处于中位或下位的规律。因为在没有上位规律保证的情况下,讲中位或下位的规律是没有意义的。而在大学活动上位规律的问题上,有两方面的内容需要特别注意:
其一,根据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世界上最早时期的大学自治权的授予或获得,都是需要仰赖当时的国王、教皇或诸侯的理智和开明的。大学虽然需要进行争取自主权的努力,但这些努力似乎并不是大学能够获得自治权的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还是要看能否遇到开明、理智的统治者。就我国大学和教育体制而言,由体制外力量来纠正体制内错误的想法还不太现实,因而对体制性缺陷的改正办法,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还是“体制内的自我纠错”,也就是由体制内的卡理斯玛人物,亦即理智、开明者来为大学的体制“破冰”——为大学下放自治权。这种方式从表面看起来似乎与世界性的民主潮流不符,但可能是我国大学制度进步思路中的最合理的选择,也是中国大学体制改革中的真问题。
其二,由私立大学为主形成的大学自治的文化和制度传统,是现代大学形成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公立大学消除自身缺陷(容易被行政权力控制)的重要条件。因为由私立大学所坚持和彰显的大学自由、独立传统及思想,形成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思想和文化标准,引导着现代大学制度和文化的发展趋向,限制了公立大学、教会大学的自我性利益趋向(行政的、教会的),使他们不敢背离大学的本质和规律太远,只能规规矩矩地按照大学的规则活动。如果这些大学囿于举办者的自身利益,背离教育本性和社会公义,就会面临被同行蔑视和唾弃、以及大学内部人基于教育本性而反对的压力,从而使公立大学不敢在大学本质方面走得太远。这就是大学行业规则、或者说大学文化生态的作用,也就是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公立大学虽然很多,但都基本上恪守由私立大学创立的三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学术自治)的原因,也是大学这个世界性组织能够跨越时空、跨越地域而长期存在的原因。正是这种传统和文化的力量,才使许多国家的公立大学,不敢坚持“谁创办、谁控制”的方式,而是选择“支持(出资)而不控制”的模式。亦即国家虽然出资创办或资助大学,但并不控制大学,而是理解和支持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制度。也可以说正是这个传统和文化的作用,所以才使许多以移植为特征的国家的大学,一开始就因为移植的原因而享有自治权,省略了他们为争取大学自治权的艰难、代价和痛苦。也使许多国家的公立大学,无法在国内形成垄断同盟,必须自觉地按照世界大学(也就是私立大学)的模式来设置自己的制度、组织自己的活动。试想我国香港地区的大学,若没有英国大学的传统和文化做后盾,他们能够像现在这样,毫不顾虑政府的行政干预吗?可以放心大胆地实行教授治校制度吗?当然,这样的文化生态在我国目前还是空白(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其形成也需要时间,但我们起码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应该懂得尊重大学活动的客观规律。
二
对于大学活动上位规律第一方面的内容,作者以为,我国大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我国大学的发展显然是无法脱离世界大学的发展规律的,也是无法超越世界大学的发展规律的。而世界大学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基本步骤,甚至有些问题的解决方式,我们可能都无法省略和回避,而需要认真地学习甚至模仿。在大学自治权的获得方面,世界大学的历史经验是,由当时的教皇、国王、诸候及市政当局授予和赋予。比如:巴黎大学是从教皇手中获得“自治”许可证的(1215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是从国王(亨利三世)手中获得“自治”许可证的(1209年),萨来诺大学(意大利)是从国王(腓特烈二世)手中获得“自治”许可证的(1231年)。那么,由谁来给我国的大学颁发自治许可证呢?
审视我国大学目前的外部环境,可以说与欧洲中世纪时期大学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被“绝对权力”形成的森严戒律禁锢着。这种戒律的表现方式,就是政教合一、与政治同质同构的大学制度。在这种大学制度中,大学对外不是一个享有独立自主权利的教育和学术机构,而是各级政府的下属,是政府以及政治实现自己各种目的的工具。对内不是以学术、学问规则为基础运行的学术共同体,而是被官本位原则控制和覆盖了的准行政机构,大学中活动的基础逻辑是权本位、官本位的意识,大学师生在大学中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他们只能按照“上级”的指示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其身份只能被定位为“凡事被决定”的大学成员。从历史上看,这种制度的打破方式一般只能有两种,一是由“绝对权力”自己打破,让大学回归自己的本性。一是由“改朝换代”的革命打破,一切从头再来。我们现在并不希望有什么革命,那可能的方式就只能是由卡理斯玛式人物主导的“自我打破”了。而由卡理斯玛式人物主导的大学制度改革,在目前来说可能是一种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只是这样的活动一般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要有“卡理斯玛”式的领袖人物,以及他们推动教育进步的意愿和决心。当然,他们的意愿和决心,不能是那种得过且过、顺水推舟式的敷衍了事行为,而应该是一种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其决心和魄力的实实在在的行动,像邓小平当年决策“恢复高考制度”时那样,当机立断、斩钉截铁、立竿见影。一是要改变国家的大学认识,转变国家的大学观念,亦即在国家的层次上,要改变对大学的传统观念,承认大学是研究学问和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而不能是社会政治或者经济的工具。承认大学教师是大学中天经地义的主体和主人,承认大学需要通过自治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对社会的责任,应该由教育家按照教育规律来独立办学。强调改变国家大学认识的原因在于,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没有先进的认识,就不可能有先进的行动。而“卡理斯玛”们的努力,是需要明确的认识和信念支撑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卡理斯玛式人物主导下放大学的自治权,是世界大学的历史经验,也是后发展国家促进本国大学进步的理智的、必须的举措。由于在世界大学发展早期,卡理斯玛式人物主导赋予大学自治权的行为,与大学人对大学自治权要求的意愿是一致的,因而这些自治权一旦下放到大学,就能够很快地在大学中“生根发芽,并长成大树”——形成大学及社会中稳固的制度、文化和传统,使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而对于大学制度改革的外部阻力,大学人当然也需要努力,需要通过争取大学自治权的斗争,对统治者施加影响。但客观地说,一方面,他们努力的力量是微弱的,是无法在大学与社会关系、尤其是大学与政府关系的调整中起主导作用的,而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统治者的自觉和明智。另一方面,大学人争取大学自治权斗争的方式,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间接的、和平的、理性的,比如通过大学“迁徙”来对当地教育、文化、经济造成影响等。亦即是通过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对卡理斯玛们进行呼吁和要求,催促他们采取下放大学自治权的行动。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对权力的软约束,其效应全在于统治者的反应和态度。这也是世界大学发展历史其所以曲折、甚至经常反复的原因。
从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上看,这是一种常见的方式,也是政治人物对大学进步所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当然也是他们名留青史的历史机会。然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一些特定的统治者下放给一些具体大学中的自治权,转变成世界大学中普遍性的传统和文化(蔡元培先生强调的“世界大学通例”),以及社会中大学与权力机构关系规则的原因,是接受自治权的大学本身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学术共同体”,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是学术性而非行政性的,大学内部具备了使自治权“生根发芽,并长成大树”的思想和制度条件。而反观我国目前的大学,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我们的大学在本质上还是行政性的,大学教师和学生在大学中还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基本的表达权和参与权,由“上级”下放给大学的自治权,极容易变成领导者们的“集体或私人权力”,因而我国大学获得自治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改造现实的大学内部领导和管理体制。而这于我国大学而言,显然是一个十分艰巨的难题。应该说,香港科技大学几位教授的想法很自然,那是因为他们长期在香港或国外大学中工作,根本不存在大学没有自主权方面的困扰,因而所想的只是怎样实际地组织教学活动。
三
在国情论者而言,一是对国情的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国情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性问题,其中既有绝对性的一面,也有相对性的一面;既有客观性的一面,也有主观性的一面。比如,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上世纪70年代末期,人心思变、渴望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国情,而“两个凡是”、“按既定方针办”也可以说是国情,人们应该以哪一种国情为准呢?再比如,在高考改革问题上,社会诚信资源贫乏、权力腐败,使高校完全自主招生难以推行可以说是国情,中小学教育应试化、学生个性被抑制、创造性意识和能力难以培养也可以说是国情,人们又该以哪一种国情为准呢?而在南科大的办学问题上,不囿陈规,大胆创新,为中国大学改革探路可以说是国情;而周密规划,稳妥推进,与现体制保持平衡,对所招学生负责也可以说是国情,办学者应该顺应哪一种国情呢?所以,国情虽然是一种客观现象,但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国情时,却包含有主观的成分,很容易将自己主观性的认识说成是客观性的结论。另外,国情也不是一种唯一的状态,而是一种多样化的状态。人们在解释国情时以什么样的国情为依据,取决于其认识水平和精神境界,而朱校长在强调立足国情时,则极可能使南科大的理想变形,因为真正的大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于自己理想的坚持和固守,不因为社会的变化而随波逐流。而南科大新成立的理事会人员结构,从外观上看,就是对大学“学术共同体”本质的挑战。显而易见,这样的“顺应国情”于南科大以后的发展是有精神障碍的。
二是应该全面理解国情与教育的关系。一是国情决定着教育,有什么样的国情,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二是教育也在决定着国情,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情。另外,国情与教育还是互相包容的,一是国情中包含了教育,国情的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教育的形态。二是教育中也包含了国情,教育的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情的形态。而国情与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提示我们,一方面,对教育与国情的关系不能进行机械性的理解,亦即只认为国情决定着教育,而忽视了教育对国情有反作用的性质。想当年,由邓小平果断作出的“恢复高考制度”决策,就不仅解决了高校招生中的质量和公平性问题,而且推动了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气的形成,也就是改变了当时的国情。另一方面,应该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待国情与教育的关系,亦即二者的关系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有机的而非机械的。具体到南科大的问题上,就是南科大建校的灵魂是什么?是追求真理?是追求普遍知识?是建立一所真正的大学?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进行怎样的制度和文化建设?勿庸置疑,朱校长坚持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举措,是符合世界大学活动规律的,人们无须因其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而怀疑或动摇。但朱校长对自己办学信念的坚持,是应该做怎样的选择呢?应该说,朱校长的选择可以是多样的,既可以是蔡元培校长“我绝不做这不自由的大学校长”的选择,也可以是梅贻琦校长“我就是戴王帽的”、“我从众”的长期坚守、以柔克钢的选择,还可以是罗家伦校长“被清华师生赶出校园”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选择。而这些,于中国大学而言,可以说都是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是后人可以对照的镜子。
三是南科大的“内忧”风波显示,南科大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南科大的校名本身,就预设了办学者的技术性价值趋向。而办科技大学,其教育指向明显就是要培养深圳发展需要的技术性、应用性人才。这样的想法或许并没有错,但其办学的精神意蕴却是与真正大学的理念隔膜的。因为真正的大学的目标是人的精神和人格的健全发展,而不是仅仅为了人的技术能力。而从南科大的专业设置、教师类型、学校发展前景预设来看,都具有国内科技大学重工轻文的特征,这与南科大设想的为中国大学改革探路的目标可以说相去甚远。因为如果立足人的发展,立足学生的健全人格培养,就必须遵崇学问——好的人是要以学问为基础、并由学问来熏陶的,尤其是要遵崇具有文明精神的价值性、文化性、社会性学问,而这显然是南科大在设计上缺乏的。二是许多世界著名大学的经验都表明,任何一所真正的大学,都是要以体现人类文明精神的人文知识和品格为基础的,没有人文精神和意蕴的大学,可以说都不是真正的大学,最多只能是高级技术知识的培训中心。而南科大在既对人文精神没有充分认识(没有材料表明南科大崇尚人文精神)、又不设置人文专业、不打算聘任人文学科教师的情况下,就期望办成“一流大学”,这显然是一种天真的幻想,表明了主事者对大学基本精神的陌生,也埋下了“反复”、甚至“沉没”的隐患。三是南科大的主办者曾多次强调“要在世界范围内招聘一流学者或大师”,似乎这样就可以使南科大很快成为“一流大学”,作者以为这是一种“大师崇拜症”,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因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固然有一流学者,但有一流学者就未必能够办成一流大学。在师资方面,关键是合理、恰当,是各得其所,各扬其长。而大学的关键是灵魂,是对一种高贵理想和精神的维护和坚守。比如:哈佛的“与真理为伍”,普林斯顿的“追求普遍性知识”,哥伦比亚的“教授就是大学”,牛津的“牛”——“我们教授的决定是首相也不能改变的”。而南科大在这方面似乎还不够坚定,也难以坚定。当然,这不是南科大的独有问题,而是中国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的普遍和共同问题,是需要整个社会来思考和努力的。
南科大不是朱校长个人的,也不仅是深圳市政府的,它是中国的,促其成功,不仅是朱校长的责任,也不仅是深圳市政府的责任,应该是中国社会共同的责任,尤其是中国当代政治人物的责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应该走出“为尊者讳”、“习惯于诠释体制意图”、“照搬国外教育理论”的“鸵鸟”传统,大胆的直面大学的真问题,呼吁和督促下放大学的自治权,呼吁和督促大学内部的行政化体制改革,让大学真正成为能够为国家文明和进步提供思想、理论、人才、方法的教育和学术机构,真正成为国家和民族文明、理性精神的源泉和摇篮,真正令人尊敬和向往的文化和精神圣地。而若如此,国家幸,民族幸,学生幸,教师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