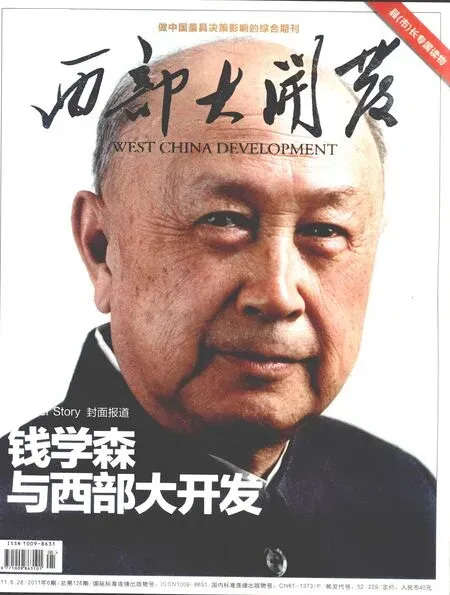“动态稳定才是常态”
——何增科谈社会管理
2011-12-23李静睿章文
◎ 文/李静睿 章文
社会稳定、社会秩序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由此获得一种安全感,但如果社会稳定以牺牲公民的自由、尊严和幸福为代价,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
进入“十二五”开局之年,社会管理受到了全社会的空前关注。“十二五”规划纲要设立专篇,提出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社会管理创新”,也首次以重要篇幅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成为2011年的重要工作之一。此前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5月23日,长期研究公民社会以及社会治理的知名学者、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教授,接受记者专访时,针对近日社会上关于公民社会的争论,颇有感慨,“市场经济这个词在很长时间内也是异端邪说。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究竟是互补合作的良性关系,还是彼此敌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国家如何对待公民社会”。
记者:据你所知,关于社会管理,目前社会上有几派观点?
何增科:目前关于社会管理有两派,一是民生派,一是秩序派。前者侧重于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后者强调通过维护社会秩序,给人们提供基本生存和发展的安全感,更加强调从社会秩序的角度理解社会管理。但是我认为,社会秩序是一个基础,只是一种底线要求,绝不是最高要求。
记者:那你认为社会管理更高的要求是什么?
何增科:社会稳定有两种方式,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静态稳定是指单纯地以僵硬的方式压制矛盾,而动态的稳定,则是指让各种意见和利益诉求得到充分的表达,使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来,这有利于更好地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
我们认为,动态稳定才是常态,因为对一个开放复杂的社会进行管理,更多应该采用疏导的方式,包括对网络等公共空间舆论的引导,让各种言论交锋,使极端的观点得到稀释中和,而不是简单封杀。
记者:在将来的社会管理中,中央更可能采取的是哪一种思路?
何增科:中央层面还没有明晰思路,但是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一种架构,即由政法委书记兼任社会管理领导小组组长,把社会管理导入了维稳的思路。当然各个地方做法不一,比如北京专门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但这种做法也有困境,本来是要超越职权,但它还是要争具体的职权,比如把民政部门的职权抢过去了。所以我们学者很为难,担心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怕变成一个超级部门。中国最不缺的是职能部门。另外,中央层面也有人提议超越部门,设置一个领导小组之类的机构,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记者:对于公民社会的争议,你怎么看?
何增科:市场经济这个词在很长时间内也是异端邪说。到底认为公民社会是人为“陷阱”,还是一个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家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这是一个基本的理论判断。
我认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互补合作的良性关系,还是彼此敌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国家如何对待公民社会。一味地控制限制压制,必然会产生一个反抗的对手,造成一个对抗性的公民社会。但是如果国家对公民社会采取包容的态度,允许自治自律,同时对公民参与提供一种合法的制度化的渠道,在社会管理中允许公民社会发挥合作伙伴的作用,那么换回来的是一个强大、活跃、合作型的公民社会。
记者:有人说,发达国家并非都是“小政府、大社会”,不少大国都是“大政府”,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
何增科:西方国家的确经历了从最低限度的政府,即“守夜人”国家变成福利国家的阶段,这个阶段中确实存在政府规模扩大的问题,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西方社会自治的空间,也有一个不断增大的过程。如果只强调一个方面,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在政府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培育一个强大的社会。
我们希望的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双强,注意这是强,而不是大的概念,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大而没有能力,大而很弱,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如果政府的成长以挤压社会的成长空间为代价,则社会的反抗会使政府大而不强,形成一种脆弱的和易于裂解的政府。反之,如果政府在增强自身能力的同时,为社会的成长提供空间、资源和权利保障,社会也会更多地支持政府并与政府互相合作。
记者:你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和公正,这是否也是社会管理的主要目的?
何增科: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条件,自由对于人来说,就像空气一样。社会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公民的社会权利,使全体公民生活得更加自由、幸福和有尊严。社会稳定、社会秩序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由此获得一种安全感,但如果社会稳定以牺牲公民的自由、尊严和幸福为代价,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
记者:如果以此为目的,社会管理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何增科:社会管理有其边界,就是不能侵犯挤压个人的自由私密空间,社会管理要划清“群己权界”(严复用这一词语翻译密尔的《论自由》),公权不能随便进入私权的空间。
如果政府对社会管理一味追求网络化、全覆盖、无缝隙,政府将重回全能国家的老路,政府对社会自治自律能力的不信任,必将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强控制的反感和不信任,改革开放后涌现的社会自治自律能力和创造活力都将会得而复失。
记者:不少人把创新社会管理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你的看法呢?
何增科:不管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创新社会管理,都要遵循善治的基本原则,一些精神价值是相同的,比如参与的原则,法治的原则,透明的原则。社会管理改革如果改得好,的确是会增加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和政治改革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从不同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