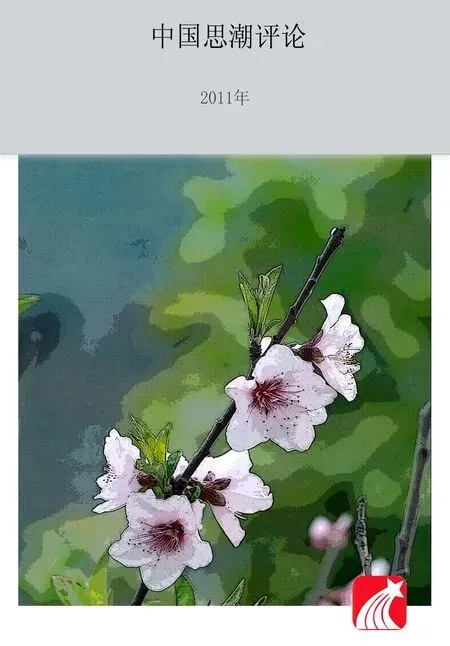“旧瓶装新酒”
——兼论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方法
2011-12-17刘梁剑
刘梁剑
或许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中国哲学日益自觉的时代:中国哲学日益感到有必要以自己的独特面貌担当更多的文化责任。然而,当代中国哲学的运思离不开现代汉语哲学语汇。因此,当我们试图以所谓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姿态参与中国哲学的自觉的时候,首先可能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用于哲学运思的现代汉语哲学语汇是怎样一种状况?为此,有必要对基本的现代汉语哲学语汇进行系统梳理,查清其来龙去脉。这将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本文试图通过对重要思想家严复的个案考察,探讨其中一个基本语汇——科学,看看是否能够增进对它的理解。同时,我们的探讨将展开于对以往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方法的反思之中。
一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便开始了迄今为止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运动。在此过程中,中国现代思想发生了。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思想?中国现代思想可能开展出怎样的价值与意义?这两个问题敦促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思想史。与此同时,我们在这样的反思中理解未来,筹划未来。因此,反思同时又是前思。反思必须是前思。反思只有在同时成为前思之时才成其为真正有意义、有力量的反思。
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思想?在这里,“如何”所带入的,不仅有追问的对象(问之所问),而且有追问的方式(问之如何问)与追问的旨趣(问之所以问)。而且,不是三者的简单并列,而是相互制约、相互渗透所形成的整体。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项研究中,列文森发问:中国近代早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出现是否表明,“即使没有西方工业主义的催化作用,这个看上去平稳的、传统的中国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也将迈入一个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吗”?[注]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这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列文森追问的是儒家传统的现代价值(问之所以问)。儒家传统的价值由专业化、科学等现代价值标准加以衡量(问之如何问)。成为反思对象的,是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命运,而不是专业化、科学等现代价值(问之所问)。列文森的如上反思基于以下前思: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儒教传统?因此,在列文森那里,反思的结果——儒教中国和它的古代价值业已成为博物馆的陈列物——与其说是一个实然判断,倒不如说是一个应然之则。对于历史与传统我们纵然有难以割舍的牵挂,理智的选择只能是悲壮的,“不得不对自己的历史作一番清算,用一条新的绳索将它牢牢拴住,而同时朝着和它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注]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所谓传统与现代、情感与价值的两难同样主导了列文森的其他著作如《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理智上,我们也许都不太能接受列文森的看法。按照他的逻辑,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逐渐由现实退入历史,它们对于中国现代思想的生成基本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建设性的价值。这无疑忽视了中国现代思想发生过程中“古今中西”于冲突中融通创获这一基本实情。有一种情形颇值得玩味:即使在那些看似激烈反传统、看似主要依靠移植的思想观念中——比如科学——仍然以某种方式依靠中国古代传统并且保留了中国古代传统。在此,我们领略到人类熔铸新的思想观念的奇观:一边是西方传统,一边是中国古代传统,两相交际,产生了“科学”、“民主”等中国现代思想观念。以科学为例,它既不是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又不是现代西方的science或Wissenschaft,但同时却又继承了各自的某些特点。对于这样一种思想现象,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基本评价。比如,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格致思想为science这一西方观念的引入提供了有力的依托。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格致思想(再加上中国现代历史过程的现实要求)导致了西方外来的science观念的变形——但无论如何,西方传统的主导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基于同西方思想脉络中science观念的关联,我们才能把“科学”界定为现代观念,并进而厘定这一现代观念中的现代内涵。无论是对“变形”过程的具体考察,还是对“依托”过程的思想史研究,其研究的旨趣首先都是从关切“中国”本身出发,理解不言而喻的西方现代思想在中国的流传。这样的研究工作,无论其细节如何引人入胜,但最终似乎永远只是为以下观点提供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印证:现代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展示了中西思想交流融合的复杂形态。在此视域之下,中国现代思想无论如何生机洋溢、丰富多彩,它的意义似乎仅限于中国文化本身的现代转变。在此视域之下,我们很难看到中国现代思想对于人类思想的独特贡献,因为它充其量不过是已有的西方现代思想不精确的翻版;我们同样很难看到中国现代思想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因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学习西方思想而功课不太理想的学生。[注]墨子刻在评价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一书时说到,这部著作改变了严复的历史形象,严复不再是“一位学习西方政治理论而功课不太理想的学生”。参见墨子刻为该书所作的序。不过,黄著所探讨的问题是:严复——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调适取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什么没有完全接受西方弥尔式的自由主义?作者的回答包括:严复对弥尔自由思想的误解主要在于严复对弥尔自由思想之所以然的误解,后者可以进一步归结于严复对弥尔的悲观主义认识论缺乏领会与接受。在这里,西方弥尔式的自由主义显然被设定为严复所当学会而未能学会的东西。在此意义上,严复仍然是“一位学习西方政治理论而功课不太理想的学生”。
二
在此背景之下,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颇值得我们注意。这部名著的意义,远远不限于严复研究。即使不同意作者在具体问题上的观点,[注]比如,李泽厚作于1977年的《论严复》一文认为,在进化论问题上,严复的立场是折中赫胥黎和斯宾塞,这“似乎是矛盾,实际却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创造’”。因此,他评论说,“史华慈只讲严复用斯宾塞批评赫胥黎,说严完全站在斯的一方,似片面”。(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册,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97页。)我们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它展现了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思想的另一种可能性。史华慈问,“把西方假设为已知量”是否成立?这一质疑开始松动中国现代思想研究习见范式的基本出发点。西方现代思想传统开始可能成为反思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通过中国现代思想反思西方现代思想传统。与此相应,中国现代思想家的角色由西方现代思想的学习者转变为西方思想的“外国观察家”。作为“外国观察家”的中国现代思想家,比如严复,其迷人之处在于看到了西方文化中为西方人自己所忽视的东西。路易斯·哈茨在评论《寻求富强》时概括史华慈的发现: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力量”这一主题。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外国评论家的本事在于能够揭示出所研究国家的社会生活中蕴含着的思想方面的东西。因为这些评论家往往通过母国文化提供的对照,使异国社会生活中蕴含着的思想显得清晰可见”。[注]史华慈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序言”。如果我们转变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家的角色期待,也许可以找到不少有洞见的西方文化观察家与评论家,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西方现代思想中原本被遮蔽、被忽视甚至被误解的东西,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由此,中国现代思想展现出另一重价值:作为返观西方现代思想的镜像。
进一步看,我们甚至有可能在中国现代思想家本身没有清楚“看到”的地方找到审视西方思想的有利观察点。这时,我们不是通过中国现代思想家的观察,而是通过对他们的观察的观察返观西方现代思想。就科学观而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科学观的某些特征或许可以启发人们(西方学者及中国学者)反思对西方科学观的通常理解。参照西方思想的脉络,严复的科学观可以归于实证主义名下。他将科学方法概括为考订、贯通、试验“三际”。[注]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3页。考订,以观察或演验(实验)之法即物实测;贯通,以内籀(归纳)之法得出一般的因果公例,“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注]斯宾塞著,严复译:《群学肄言》,严译名著丛刊之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ⅹ页译者注。试验,对公例加以印证。但是,严复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把得出公例的过程理解为“道通为一”的过程。通过这样的修辞,基于经验材料而来的具体公例似乎就很顺当地过渡到作为世界第一原理的“道”。实际上,在严复那里,我们不难看到对于两者的平行叙事:一方面,公例既立,“必无往而不融涣消释”;[注]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71页。另一方面,道无不在,“苟得其术,虽近取诸,岂有穷哉?而行彻五洲,学穷千古,亦将但见其会通而统于一而已矣”。[注]同上,第1096页。而在严复的另一些叙述中,科学公例与形而上学原理有时混杂不清:“穷理致知之事,其公例皆会通之词,无专指者。唯其所会通愈广,则其例亦愈尊。理如水木然,由条寻枝,循枝赴干,汇归万派,萃于一源;至于一源,大道乃见。道通为一,此之谓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42页。有时则直接等同:自然公例,“即道家所谓道,先儒所谓理,《易》之太极,释子所谓不二法门”。[注]同上,第1051页。如何理解严复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形上之维?它的意义何在?一种可能的思路:严复科学观的形上之维意味着实证论在现代中国的一种变异,思想史研究的任务之一便是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及中国近代社会的实情考察,揭示这种变异产生的历史过程及理论机制。[注]可参见杨国荣:《从严复到金岳霖:实证论与中国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及《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无疑,这一思路从如下前提出发:西方实证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反形上学。换言之,西方实证论科学观的反形上学特征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能否这么想:恰恰是严复科学观的形上之维启发我们思考:科学与形上学之间是否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这种关联在严复那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而这种较为充分的体现进而启发我们反思西方实证论科学观在反形上学表象之下的形上学特征?[注]实际上,史华慈已经多处提到斯宾塞实证主义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例如,“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深一层’的抽象的宇宙论方面,斯宾塞对于天地万物的想象与中国某些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非常明显地相吻合。在斯宾塞的含糊的、泛神论的、自然主义的、内在论的一元论中,各种现实现象都‘脱胎’于唯心论的‘绝对实在’,并通过空间、物质、时间、运动、力这些饶有趣味的范畴发生联系”。(史华慈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46页)实证主义将对现象之后的本质或本体的追问作为形上学加以拒斥。但吊诡的是,这种拒斥恰恰是基于一种隐蔽的形上学立场。当然,重要的不仅在于指出实证论科学观的形上学特征,更在于具体揭示实证论科学观的形上学基础。海德格尔曾在反思形上学的脉络中展开对科学的深刻反思。他指出,实证主义——我们几十年以来并且现在前所未有地置身于实证主义潮流中——“认为光有事实或者别的和新的事实就足够了”。基于此,现代科学以事实科学、实验科学和测量科学自居。这里有一种特殊的与物打交道、规定物之物性的“形而上学筹划”。[注]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47—850页。
以中国现代思想为镜像返观西方,这是试图通过现代中国重新审视西方。当我们进行这样的反思工作之际,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超越了“中国”立场而获得了某种似乎可称之为“世界学者”的抱负。鉴于西方思想在当今世界的渗透性力量,重新审视西方意味着非西方文化的文化自觉,意味着人类思想试图超越某种特定文化,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中探测自身的限度,开辟新的可能空间。
三
《庄子》的“道通为一”帮助严复的科学观完成了从经验到玄学的跳跃。传统的力量无处不在。传统可以提供引入西方观念的契合点,传统帮助中国现代思想家成为西方文化深刻的观察者,传统的在场使得中国现代思想有可能成为返观西方现代思想的镜像。这些多多少少印证了前面提及的一个说法:即使在那些看似激烈反传统、看似主要依靠移植的思想观念中(比如科学)仍然以某种方式依靠中国古代传统并且保留了中国古代传统。然而,“看似”仍然暗示着,在最直接的、未加反思的层面上,我们显然把科学等观念理解为主要依靠移植的外来观念。即使“看似”意味着假象(Schein),但假象在现象层面亦是真实的。“看似”在这里揭示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一种实情与危机:现代汉语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往往是作为译名得到思考与理解。以现代汉语翻译西方近代思想的情形,乃是输入一种强势的文化。现代汉语思想的基本范畴、甚至现代汉语的基本结构都包含了未思的西方近代因素。与此相应,现代汉语/思想呈现出因移植而产生的无根性。[注]参见拙文:《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困境》,《人文杂志》,2007年9月,第27—31页。对于这样一种现代汉语/思想的实情与危机,我们应该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因为这是我们开始下一步工作的前提:如何克服现代汉语/思想的无根性?也许一个可能的途径在于,透过“看似”的假象,通过诠释开显出中国现代思想观念产生之际本有的传统根源。
我们不妨考察严复如何吸纳“看似”主要依靠移植的思想观念“科学”。严复曾说,斯宾塞的群学“约其所论,其节目支条,与吾《大学》所谓诚正修齐治平之事有不期而合者,第《大学》引而未发,语焉不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页。但实际上,《大学》亦为严复的科学观提供了重要的形式框架,从而使得严复的科学观呈现出“旧瓶装新酒”的面貌。《大学》八条目始于格致。朱熹《大学章句》补传又以即物穷理释格致。严复即用格致或即物穷理安顿“实测内籀”的科学方法。虽然“吾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词文字而已,求其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西人所谓学于自然者,不多遘也”,[注]同上,第237页。但是,朱熹的即物穷理之说本来包含了研读自然无字之书的要求。“夫朱子以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读书穷理言之,风斯在下矣”。[注]同上,第29页。进而言之,由即物而穷理的程序隐含了内籀之法。“内籀西名Inductive……唯能此术,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期。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宋儒朱子以读书穷理解格物致知,察其语意,于内外籀原未偏废。盖读书是求多闻。多闻者,多得古人所流传公例也。穷理是求新知,新知必即物求之。故补传云:在即物以穷其理,至于豁然贯通。既贯通,自然新知以出,新例以立”。[注]耶方斯著,严复译:《名学浅说》,严译名著丛刊之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4页。

另一方面,格物致知最终指向齐、治、平,与此相应,科学的价值在于为富国保种奠基。[注]史华慈:“斯宾塞的书所以最使人激奋,还因为此书显示了西方科学的方法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史华慈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31页)“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注]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页。汪晖曾说,“科学概念在20世纪中国的广泛使用远不像表面看来的那样简单。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思想家对于科学本身就是目的,即科学就是为认识而认识的理想主义科学观不感兴趣;正如培根时代的科学观一样,‘功用’和‘进步’是中国思想家的科学观中的两个关键字眼。”[注]汪晖:《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载汪晖:《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8页。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于19世纪末期的严复。他曾说:“今之科学,自是以诚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荒。”[注]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1页。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引发最迫切、最震撼人心的、生死攸关的问题:中国何以积弱不振?同时,它成为最有待解释的问题。反过来,对此问题具有解释力的学说将由此获得最有力的合法性支持。按照严复的观察,西学命脉之一便是科学。“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注]同上,第2页。进一步,科学所提供的进化论不仅解释了中国为什么积弱不振,而且指出了走出困境的出路:从根本上放弃中国文化优越感,颠覆中国文化的价值本位,对中国文化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换言之,作为科学理论的进化论为社会变革与反传统提供了合法性依据。科学经由进化论开始了逐渐上升为世界观与意识形态的行程。
严复以“进化”(evolution)为“天演”,这里的修辞策略颇值得玩味。严复曾分疏汉语中“天”的多重含义:“中国所谓天字,乃名学所谓歧义之名,最病思理而起争端。以神理言之上帝,以形下言之苍昊。至于无所为作而有因果之形气,虽有因果而不可得言之,适偶西文各有异字,而中国常语皆谓之天……天演,天字则第三义也。”[注]斯宾塞著,严复译:《群学肄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99页,译者注。然而,天字的多重含义恐怕并不像严复所说的那样“皆绝不相谋,必不可混者也”。由于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天字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总是带有某种独特的形上意味与准宗教情感。天字似乎本身就意味着作为最终价值源泉和最高行动准则的天理。因此,以进化为天演的修辞,不经意中将进化提升到了天理的地位。或者说,“天演”的叙事暗暗利用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天理观,赋予进化以根本原理的地位——虽然进化论本身似乎以颠覆天理观为己任。[注]汪晖认为,在严复那里,“科学既是实证精神的表现和结果,同时又是‘天演’这一普遍原理和第一推动力的显现。作为普遍原理,它不仅揭示了世界变迁的图像和前景,而且规定了人们行动的准则和价值取向。‘天演’是自然现象,又是道德命令。”(汪晖《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载汪晖:《汪晖自选集》,第234页)
严复借助于天演引入进化的叙事策略同培根在神学的基本框架下引入科学的方式之间有相通之处。比如,近代科学观以征服自然为基本特征。然而,征服自然的合法性在培根那里却是诉诸《圣经》。他说,“人类在一堕落时就同时失去他们的天真状态和对于自然万物的统治权。但是这两宗损失就是在此生中也是能够得到某种部分的补救的:前者要靠宗教和信仰,后者则靠技术和科学。须知自然万物并未经那被诅咒者做成一个绝对的、永远的叛逆,它在‘就着你脸上的汗来吃你的面包’这样一个宪条的作用之下,现在终于被各种各样的劳动(当然不是被一些空口争论或一些无聊的幻术仪式,而是被各种各样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征服到来供给人类以面包,那就是说,被征服到来对人类生活效用了。”[注]培根著,许宝骙译:《新工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1页。
四
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意义,不在于创建了一个试图接近于西方现代又“走样”的中国现代思想,而在于:在一场规模宏大的“思想实验”运动中产生了一些有别于西方现代的另一种可能的新世界观的“萌芽”。中国现代思想传统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它区别于中国古代,更在于它区别于西方现代;在人类思想史上,这一传统的意义首先不在于它跟西方的同,而在于它跟西方的异。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任务之一,便是揭示这些萌芽,并阐明它们如何发生的具体历史过程与运行机制。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提供一幅与已有研究不尽相同的思想史图景。在此新图景中,问题意识、思想主题、思想发展的关节点与整体线索都可能是新的。
进一步,中国现代思想传统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现成性,而在于它对于我们面向当下全球性的问题本身时的生成性与启发意义。在这一层面上,中国现代思想实验过程中生成的新世界观的“萌芽”,其意义将从元哲学的思考中得到评判。当然,中国现代思想在这一层面的作用或许有其限度。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就思想家而言,“由于现实经历着剧烈变革,思想家们一生变化较大,往往来不及形成严密的哲学体系”;[注]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00页。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思潮尽管有其丰富性,“但就某思潮个案而言,则大多发育不够充分,理论建设较为薄弱,其代表人物常常又是政治人物,难以成就真正有原创性系统性的学说”。[注]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因此,中国现代思想对于我们的启发意义、解蔽意义或许大于提供现成的系统或深入思考。中国现代思想的某些洞见——它们将引导我们对现代性的前思,另一方面,洞见的发现及其意义的开显有赖于我们对现代性的前思——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思想起点。当然,思想起点不是完整的思想历程,甚至也不可能是在思想历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思想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