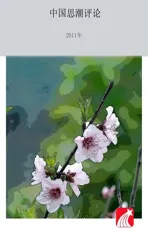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关系简论
2011-02-18李维武
李维武
在我们对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研究进行反思的时候,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社会思潮史研究,实为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自觉区分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以来,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不同,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原来的那种思想史研究,包括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难以明确区分的状况,已经由此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冯契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总序中指出:“收入本丛书的著作与一般的近代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将有很大的不同,它常常需要跨越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乃至俗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从而反映出社会思潮自身的广度与深度。在方法上,本丛书注重研究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思想如何传入并影响中国,而中国古代传统又如何被发掘、继承及转化,从而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思潮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富于民族特点。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社会思潮是在西方同类思潮的传播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为了要把握它们的近代民族特点,又需要通过中西比较的途径。”[注]冯契:《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丛书总序第3页。在他看来,社会思想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具有不同的特点,是一个比哲学史研究更为广阔、更为复杂、更为生动的研究领域。
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再来反思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关系,我们认为还可以作更深入更细致的清理,发现其中更为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于:这两种研究除了具有各自的特点外,实有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关联,即两者一方面有着内在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是联系中的区别,而不是非联系的区别。也就是说,今天仅仅一般地谈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不同是不够了,而需要进一步从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联系中来说明这种不同。
为什么说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有着联系呢?就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史和20世纪中国哲学史看,这种联系不仅在于不同的哲学思想与社会思潮在各自的开展中会有相通、影响、交叉、重合之处,更在于一个能够产生持久有力影响的社会思潮往往具有哲学内核,这个哲学内核在社会思潮的开展中有着自己生成、辐射与更新的过程。与作为观念形态的哲学思想相比,社会思潮都是针对并为解决某种重大社会问题而出现的,与实际生活、社会实践、下层民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吸引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响应与参与,甚至演变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只是少数哲学家的学问,不只是局限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但就这些社会思潮最核心的内容看,往往仍然是以哲学家思想家的思想创造为其主体,而非仅为群体性的心理认同和心理表达。特别是一些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具有鲜明奋斗目标的社会思潮,其间都存在着经过哲学家的自觉创造而形成的哲学内核。这是因为,哲学总是思考、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题,总是提出希望,建构理想,解构过时的价值观念,形成新的价值观念,以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只有具有了自己的哲学内核,一个社会思潮才能形成自己思想的原创性的活水源头,才能较长久较有力地保持自己思想的活力与激情,才能在理论上说服人、在思想上吸引人,从而形成自己掌握群众、动员群众、激励群众的理论力量。当年,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就说过:“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马克思在这里就已自觉地揭示了社会思潮中哲学内核的意义,他所要创立的哲学也绝不是那种局限于书斋中和书本里的学问,而是要造成一个伟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思潮来说,能否形成自己的哲学内核,能否使这个哲学内核坚强有力,能否使这种哲学内核适时更新,是这个社会思潮能否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关键。在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中,那些曾在长时间中产生过很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往往都有自己的哲学家思想家对哲学内核作出思考、建构和解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哲学内核,并程度不同地对哲学内核作出适时更新。如科学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思潮,它们之所以能在较长时间中在中国思想世界保持很大影响,原因当然不止一端,但具有自己的哲学内核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这就使得哲学内核在社会思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在开展社会思潮史研究时,一定要对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作深入的发掘与把握,把探讨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生成、辐射与更新,探讨哲学内核在社会思潮中的影响、作用与位置,作为社会思潮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在社会思潮史研究中少不了哲学史研究的功夫。这就成为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内在联系之所在。
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除了有着这种内在的联系外,又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是就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相区别而言的,而且是指对于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研究,还有着与一般哲学史研究不同的要求。这种不同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和探讨哲学内核的哲学内容,还需要关注和探讨一些不完全属于哲学内核的哲学内容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一)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传播;(二)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普及;(三)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制度保障;(四)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实践转化。在一般哲学史研究中,这些问题并非重要问题,往往不为哲学史家所重视和探讨,但在社会思潮史研究中,这些问题却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当为社会思潮史研究者所重视和探讨。
首先,关于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传播。对于一般哲学史研究来说,哲学思想的传播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有的哲学经典著作由于各方面原因的限制,传播十分困难,影响极为有限,阅读者很少,能读懂者更少,但我们仍然可以给予这些著作以重要的哲学史位置,如金岳霖的《知识论》、张岱年的《天人五论》就是这样的例子。但作为社会思潮史研究来说,哲学内核的传播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大问题。这是因为,一个哲学思想要成为一个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要真正起到它对于这个社会思潮的作用,就必须有一个积极传播的过程,使其向社会作广泛的辐射和深入的渗透,影响社会人心,进行社会动员,掌握广大民众,成为社会运动的思想旗帜。在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的传播,就其方式、载体和手段来说,是与中国现代化运动分不开的。在这一运动中出现的现代出版业、现代报刊、现代大学哲学教育,成为了传播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的重要方式、载体和手段。20世纪80年代电视在中国的普及,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的出现,更为这种传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载体和手段。这些传播的方式、载体和手段,都是以往前近代中国社会所未曾有过的。在这里,现代报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中国思想世界中有改良主义思潮、反清革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等不同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而这些思潮之所以能影响一时,造势一方,轰轰烈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思潮都有自己的报刊来传播自己的政治哲学:改良主义思潮有《新民丛报》,反清革命思潮有《民报》,无政府主义思潮有《天义报》。而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如狂飙崛起,呼啸奋进,陈独秀所创办和主持的《新青年》功莫大焉。正是这个刊物,把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民主”与科学主义所主张的“科学”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使之成为深受中国人欢迎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当时中国思想世界的两面旗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是与上述这些刊物联系在一起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在《民报》上,刘师培在《天义报》上,都发表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连续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向中国人作了初步系统介绍,从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大社会思潮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直至今日。即使是带有较多传统色彩的20世纪佛教思潮,也自觉地运用现代报刊作为传播佛教哲学观念的手段,出现了《海潮音》、《佛教日报》等现代佛教报刊。近来出版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和《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就集中地展现了20世纪佛教思潮的这一传播特点。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现代报刊作为传播的方式、载体和手段,这些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要在一个短时间内产生广泛而有力的影响,无疑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来看一些20世纪中国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出版、办刊活动,尽管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活动,但却对一些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对这些社会思潮的开展意义不可低估。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在1920年主编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本理论刊物———《共产党》,在1921年创办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1922年主持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在1956年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他的这些活动就可作如此看待。这些活动,未必会引起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者的关注和兴趣,但值得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史研究者予以重视与研究。
其次,关于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普及。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要向社会作广泛的辐射和深入的渗透,影响社会人心,进行社会动员,掌握广大民众,特别是影响、动员、掌握广大下层民众,还需要有与之相联系的普及工作。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普及工作,既与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传播有联系,又并非与这种传播所相同。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传播,所涉及的内容当然既有普及性的思想内容,也有专门性的思想内容。如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尽管以《新青年》为载体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但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性宣传。在哲学史研究中,我们在衡论评价一个哲学家思想的价值和地位时,这个哲学家的思想有无得到普及往往并不重要。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一些有影响的哲学家的思想就未曾得到过普及,熊十力、金岳霖、贺麟都是如此,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位置。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来说,普及工作则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环节。一个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之所以能够吸引广大的下层群众,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造成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不仅在于积极的传播工作,还在于强有力的普及工作。在20世纪中国诸社会思潮的激烈竞争中,有力有效的普及工作,对于一个社会思潮争取民众、赢得民众,进而争取胜利、赢得胜利,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种普及工作,在20世纪中国诸社会思潮的开展中,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如用白话文写作,进行群众性讲演,出版通俗性书籍与刊物,编制政论性电视片,举办电视人文讲座,等等。通过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使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由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走向生活,走向大众,为非专业人士,特别是为一般知识青年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所接受、所认同、所掌握。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工作的典范。在“大众哲学”这普普通通的四个字里面,实蕴含着艾思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方向的一种创造性的思考,这就是在中国这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方农业大国里,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更多的没有哲学基础的普通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这一点,艾思奇在《大众哲学》第四版代序中说得很清楚:“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就没有想到要它走到大学校的课堂里去。……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定要到尊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这样的大饼,在吃草根树皮的广大中国灾民,虽然已经没有能力享受,但形式粗俗,没有修饰剪裁,更不加香料和蜜糖,‘埋头’在学院式的读物里的阔少们,自然是要觉得不够味的。”[注]艾思奇:《大众哲学》,《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284页。《大众哲学》从初版到1949年12月共印行32版,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引导许多进步青年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从“大众哲学”中引发出的“大众化”这一概念,亦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理论自觉。党的“十七大”即明确提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注]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因此,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必须关注和探讨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普及工作,关注和探讨这种哲学内核是如何通过普及工作而影响、动员、掌握广大下层民众的。
再次,关于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制度保障。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思想,都是哲学家们个性化的自由思考、自由创造的产物,其传播、普及也非一定与制度有关。即使与制度有关,如儒家哲学与制度化儒学的联系,佛教哲学与佛教宗派的联系,也往往不是这些哲学思想开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哲学史研究往往只把哲学与制度的联系作为背景来考察,而不作为哲学史的主要内容来探讨。但是在社会思潮的开展中,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传播与普及,则往往与制度有直接的关联,依靠制度作为一种有力的保障。特别是把一种哲学思想,转化为一个社会思潮及社会运动的思想旗帜,其间就必须依靠制度的保障作用。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史中可以举出许多例子。特别是一些代表某种社会思潮、并对其中的哲学内核作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家思想家,很重视制度对哲学内核的保障作用。三民主义的开创者孙中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建国方略》、《三民主义》等著作中,他为三民主义建构了系统的哲学内核。为了保持这一哲学内核的长久作用,他于逝世前在遗嘱中专门作了强调:“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注]孙中山:《遗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4页。他力图以政治遗嘱这种特殊的制度形式,来规范和约束国民党人,保障他所确立并重新加以解释的三民主义及其哲学内核。孙中山的这种用心和努力是有其作用和效果的。后来成为新儒学大师的徐复观,在回忆中就谈到他在1926参加北伐军后,正是通过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接触到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他说:“我之开始和政治思想发生关涉,是民国十五年十二月陶子钦先生当旅长,驻军黄陂,我在一个营部当书记的时候。他问我看过《孙文学说》、《三民主义》没有?我说不曾;他当时觉得很奇怪,便随手送我一部《三民主义》,要我看,这才与政治思想结了缘……从民国十六年起,开始由孙中山先生而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论等等。”[注]徐复观:《我的读书生活》,《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113—114页。从徐复观的这段回忆中可以清楚看出,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即《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三民主义》确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人、革命军官的必读书籍。在这方面,当然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如开设统一的哲学课程,编写统一的哲学教科书,在特殊时期创办特殊的学校进行哲学教育,发动以保持或更新哲学内核为目的的大规模哲学论争或哲学运动,等等。这些与制度相联系的哲学内容,一般来说没有浓厚的哲学味,更缺乏深刻的思辨性,往往不好纳入到哲学史研究中进行专门的研究,但却是社会思潮史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内容。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从1956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编书到1961年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出版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本身没有多少哲学创新可言,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来说并不重要,但这一过程却典型地体现了用制度保障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史研究来说确是很有意义的。又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群众运动,当然在哲学理论上没有什么新创见,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很难占有位置,但却是一种在制度保障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核所作的大普及,在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史研究中值得重视和探讨。
最后,关于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实践转化。在哲学史上,一些具有实践性格的哲学思想,往往有一个思想转化为实践的问题。但这种哲学思想向实践转化,由于已超出了哲学的自身范围,在哲学史研究中往往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对哲学史研究来说,更主要的是考察和总结历史上哲学家在思想上、理论上的贡献。但对于社会思潮史研究来说则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向实践的转化,应当而且必须作为重要内容来加以研究。很明显,如果缺乏这种转化,哲学思想即使再系统、再精纯、再完美,也难以起到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作用,难以由此而影响社会人心,进行社会动员,掌握广大民众,造成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对于这一点,不少哲学家思想家已有明确的认识。特别是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里,这种自觉性就更为明确和强烈。1939年,李达在为《社会学大纲》第四版作序中,即用一段富有激情的文字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注]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在他看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传播,也就是为了帮助先进的中国人掌握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有效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决不能离开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来谈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对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多有启发。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创立了自己的文化儒学后,即以很大精力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力求使自己的哲学思想转化为社会实践,以造成一种旨在改造中国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当年梁漱溟在谈到这一点时,就认为自己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他说:“当我看出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已属崩溃时,便在比较中西社会组织构造之不同中,一方面寻求西洋社会的组织构造,如何从历史之背景演变而来,我们何以不能成那样的社会。总之,过去是那样,现在当然另是一个样子,将来又是一个样子。于是我先前所用之心思,所有的思想,已随即落实而不是流入于空洞之处,我的主张便更坚决不疑。在这些地方,得益于马克思和共产党各方面之启发不少;我的主张虽不相同于马克思和共产党,正因为不相同而思想上获得许多帮助也。先前喜欢比较的研究东西文化,现在更上下沟通成为一体。……在这样看透了通体整个之后,我一方面很快慰的认清过去对于东西文化所研究,一方面更成熟了我今日乡治的主张。”[注]梁漱溟:《自述》,《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9页。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他的这种努力对文化保守主义却是有示范性的。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再度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就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实践形式,特别是进入到教育活动领域,开展从倡导儿童读经、创办书院讲学到推动建立大学国学班、国学院、国学专业等多种教育活动。这一向下的开展,立基于现实生活的开展,使得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直接切入到中国人当下最为关注的人生、教育、家庭诸问题,与社会生活、与广大民众有了直接的联系,从而促成和推动了时下的读经热、儒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产生了比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保守主义要大得多的影响。仅从儿童读经运动看,在近年中,“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深圳等地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万儿童先后投身其中,受其影响的成年人超过六百万人,武汉、南京等地甚至一度出现青少年读经热”。[注]《读经运动:重寻古典智慧———王财贵博士访谈录》,《读经:启蒙还是蒙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因此,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的实践转化,对于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作用的发挥,对于社会思潮的开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把它们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史的重要内容予以研究,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说,这是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又一个很大的不同。
从上述四个问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环绕着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除了有着联系外,又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社会思潮史研究在这里除了包含哲学史研究的内容外,还更多地包含非哲学史研究的内容,前者更多的是“思”的内容,后者更多的是“史”的内容。与之相应,在研究的方法上,社会思潮史研究亦与哲学史研究有着明确的区分。对于社会思想史研究来说,除了吸取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外,更要重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还需要引入社会调查、数据统计、案例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这里入手,我们大概能够发现社会思潮史研究的自身特点和自身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