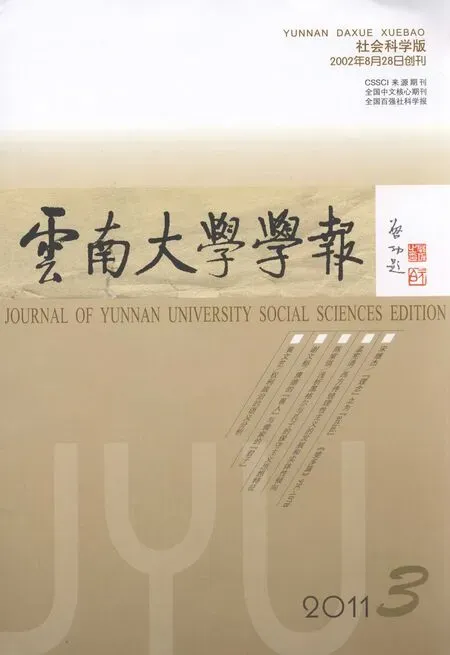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和实体性倾向*
2011-12-08孟宪清
孟宪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和实体性倾向*
孟宪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理性主义;实体性
西方传统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哲学。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理性主义、近代理性主义。西方古代理性,特别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理性,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客观理性。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代的客观理性逐步演变成主观理性,如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而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相对理性主义或实践理性主义又实现了客观理性。但无论是绝对主义的主观理性还是相对主义的客观理性,都具有实体性的特点,并存在着理性高于非理性以及二者的二元对立倾向。
按照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的观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理性主义、近代理性主义两个基本时期。但他并没有对这个历史过程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
哲学是从原始社会的巫祝世界观中产生的。古代宗教世界观是古代理性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人们通常把哲学的本质看作是“爱智慧”。但是,对这个“爱智慧”的含义的理解却经历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中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直到后世的转变。据有的学者考察,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认为“爱智慧”即哲学是人的生活所具有的内容。它不是存在于人之外的客观的东西。“爱智慧”是人的最高生活形式或最高追求。“爱智慧”的“爱”是包括人在内的事物间的和谐一致,是人与事物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所谓“智慧”,是指所有存在的东西 (存在者)都在存在之中,都属于存在,都集合于存在之中。[1](P4)根据海德格尔的考察,在希腊文中,所谓“存在”就是“聚集”、“集合”的意思。所谓“爱智慧”,就是一切存在的东西或存在者都聚集在作为整体的“存在”之中。古希腊人强调按照自然的方式去生活,就是指在洞见到人与自然一体的情况下,在尊重人的天性和自然特性的基础上,通过理性来认识、建构自我和世界,而不是简单地去适应自然。古希腊人没有后世所谓的主体观念。他们所谓的主体,是指事物的基质或基础。按照当时哲学的眼光,整个世界的存在者的主体即基质或基础,就是作为整体的“一”的“存在性”,即“去存在”。如黑格尔所说,古希腊人“同时也有一个前提,就是精神的东西与自然的东西的合一的方式的实体性”,“希腊人以自然与精神的东西的实体性合一作为基础,作为他们的本质。”[2](P160)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后文中海德格尔和福柯等人的论述中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
但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时期就存在着理论理性的传统。按照胡塞尔的观点,哲学存在着“理论-科学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神话-实践的态度”。“神话-实践的态度”居于“理论-科学的态度”之先,并普遍存在于古老的东方社会中。“理论-科学的态度”脱胎于“神话-实践的态度”,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地位。因为在“神话-实践的态度”中,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主宰,在这个世界中没有突出人的自由。而在“理论-科学的态度”中,人通过理性,逐步破除了这种巫祝世界观,认识到人和世界的本质,并通过这种理性来建构人自身和整个世界:社会的道德、法律秩序和整个物质生活。
包括古希腊哲学在内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理性的根本特点在于:它把理论看作是高于实践的东西,产生于实践中的经验只是一种“意见”,是非本质的杂乱而模糊的东西,只有通过理性的洞见所把握到事物的本质,才是一种“知识”,才是一种清楚明白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另外,古希腊人还存在着另一种思想倾向,认为哲学思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真理性的知识本身。胡塞尔说:“对于古希腊罗马人来说,什么是根本性的呢?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肯定,它无非是‘哲学的’人生存在形式:根据纯粹的理性,即根据哲学,自由地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塑造他们的法律。理论哲学居于第一位。对世界的明智观察应摆脱各种神话的和整个传统的束缚,应绝对毫无先入之见地去认识普遍的世界和人,并最终在世界本身之中认识它的内在理性和神学,以及它的绝对原则:上帝。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不依从于一切研究者,它独立于任何一个受哲学教育的人。实践的自主性紧跟着这种理论的自主性。按照文艺复兴的主导思想,古人是自己明智地在自由理性中塑造自己的人。对于更新了的柏拉图主义来说,这意味着,不仅在人的伦理方面,而且整个人的周围世界、人的政治和社会的存在,都需要从自由的理性出发,从一种普遍的哲学观点出发加以重新塑造。”[3](P983~984)
对哲学的“爱智慧”的认识,我们也可以从古希腊时期的物我一体,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阐释,变成了客观化和主客体二元对立这一转变过程中得到理解。那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的思想家,把哲学的“爱智慧”的“爱”,看作是一种主观的追求,把“智慧”看作是一种脱离于人的生活而存在的纯粹客观性的东西:“(在希腊哲学看来,)人被观察与认识世界的热情勾住了。这种热情由一切实践的兴趣转向它自己认识活动的封闭圈子,在那个时代专门从事这种研究,建设并且只希望建设纯粹的理论。换句话说,人成了世界的公平的旁观者与监护者,他成了一个哲学家。”[3](P959)例如,柏拉图就明确地把哲学的目的看作是对真理的追求,而真理就是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性,从此真正开启了从古希腊早期实践哲学向后世理性哲学转变的先河。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哲学的智慧,就是对作为普遍原理的原因的知识的把握。求知就是人的本质,是人最大的乐趣和幸福,而且人的求知活动的目的就是知识本身,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哲学就是以智慧的方式去探讨神的知识。这种智慧既区别于感性经验,也区别于神话的幻想意识,同时又区别于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因为哲学的智慧所追求的是对自然的合乎理性的实在的和真正的知识,不是模糊和虚幻的意识,同时哲学的智慧又是对作为事物的基本原理的原因的认识,而不是如实用知识和技能所追求的是对具体事物的原因的认识:“原理与原因是最可知的;明白了原理与原因,其他一切由此可得明白。”[4](P3~4)他也认为,从事哲学的目的就是获取真理。但是,这里的真理,已不是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希腊早期思想家所强调的存在者向存在的聚集、存在性对人的绽放和显露,而是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的符合一致,是与真实情况的符合一致,真理即是真实。
有的学者认为,古希腊罗马哲学在关于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的论述中,似乎存在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如赫拉克里特和巴门尼德关于“存在”和“存在者”的关系的思想。他们认为,认识到万物一体是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令人惊异的最高成果。他们把“存在”或“是”看作是“存在者”之源,人和自然都是“存在者”,都是“存在”的创作物,人与其他存在者都统一于“存在”或“是”,并按照自然的方式去生活。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是在生活中、特别是在道德实践中,通过体悟即想象和体验,去认识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一致,从而达到一种高远的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这种人生境界,具有理性思辨能力的哲人、圣人可以达到,而没有这种理性思辨能力的普通人也可以达到。它强调的首先是在生活实践中对作为世界存在实体的“道”的本质的体悟,其次才是对“道”的本质的抽象分析。而古希腊罗马哲学强调的,是通过人的自由理性的逻辑分析或洞见,去认识人和自然的本质上的统一性,即人和自然都源于“去存在”或“去是”本身。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哲学的智慧就在于通过人的理性而认识到事物的原因,而认识的根本途径,就是运用理性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
我们发现,西方传统哲学经历了从古代社会的理性到近代社会的理性的逐步抽象化和主观化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归根结底是在于人的主体化和自然、社会的客体化。理性从客观性或社会性的存在,经过人的主体化而成为人的精神世界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具有理性,人首先是理性的动物,其次才是语言和劳动的动物,人的语言和劳动的性质和特点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上的。
在西方古代社会,特别是古希腊社会,具体地说首先是“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上的理性,主要是一种“客观理性”,其次是一种主观理性。这种“客观理性”,如“努斯”、“理念”,等等,主要表现为纯粹精神性的神,以及客观化和社会化的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精神。这种“客观理性”或“客观精神”又被称之为客观性的“善”。在超验的实体性方面,它基本上相当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道”:它是创造世界的根本因素和力量,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行为,是社会制度和人的行为合理性的最重要的标准。与这种“客观理性”相对应的是人的主观理性。它是指存在于人的主观精神中的理智和反思精神。在古希腊人看来,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在人的具体行为中是一体性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是理性动物,受到理性 (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的支配;另一方面,人是社会实践的动物,人的实践是在人的理性指导下的实践。当然,人的实践,特别是自由人的实践,主要是指社会性的道德行为、语言交往和沉思性的精神活动。生产劳动不是一种真正的实践,而是“非人的人”即奴隶所从事的非自由的工具-目的性活动。所以,在古希腊哲学那里,理论和实践基本上是一体性的,而不是后来的截然对立的。
这种“客观理性”虽然体现了西方古代人民对世界和人的认识的积极成果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古代先民的浓重的巫祝世界观,但是,这种以“客观理性”为主体的世界观仍然是不成熟的,在某些方面是不合理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是建立在以实体性为主的哲学存在论的基础上,世界存在的超验性使这种世界观呈现出一种神秘性。这是人的理性不够高度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人对世界存在的建构主要是一种语言的建构,是感性直观的建构,甚至是猜测和臆想。
另外,西方古代哲学,包括“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还存在着理智理性和实践理性、实践活动的工具-目的合理性和反思-价值合理性的二元对立。这一思想被柏拉图发展为一种系统性的理念论,即理念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成为一种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有支配地位的思想体系。按照美国人怀特海的观点,柏拉图的理念论是西方思想史的底本,在他之后的哲学都是对理念论的注脚。柏拉图认为,理念是纯粹精神性、形式性的东西,因而也是纯粹主动性的东西;而物质是一种质料,一种纯粹被动性的东西;最高的形式是神,最低的物质是自然;而人一方面具有精神、理性,因而具有神性,另一方面,人又有肉体、欲望,因而具有物质性。所以,人是介于神和自然之间的东西。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四因说”,即认为推动世界运动的力量或构成世界存在的因素有四种,其中最根本的是“形式因”和“质料因”。人的实践活动就是纯粹主动性的“形式因”与纯粹被动性的物质质料的结合。同时,他认为,人的道德实践活动是一种纯粹自由的活动,活动本身就是目的,而技艺则是一种非自由的活动,因为活动的目的只存在于活动的结果,活动的过程只是实现活动目的的手段。
“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的文化理念对西方理性主观化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例如,基督教的创世观念一方面发展了人的精神的实践性,即哲学存在论的建构性。因为创造性是人的行为的本质,上帝的精神创造性是人的创造性的一种表达形式。另一方面,它又强化了理性与感性现实的二元对立,造成了古希腊时期的“客观理性”的淡化和作为个体的主观理性的强化:古代先民的巫祝世界观中具有丰富个性化的诸神的精神世界,变成了一神教中上帝的纯粹理智性的精神世界;古代社会中由“客观的善”、诸神、城邦、个人等交叉形成的多元世界,变成了尘世和天国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由社会政治、道德交往活动所决定的合理和幸福的生活理念,转变为个人努力得到的上帝的救赎的生活理想;肉体不再是个人幸福生活的基础,而是应该鄙弃的纯粹惰性的物质。因此,物质和精神、社会和个体、理论和实践等二元因素的对立又进一步加深了。
在近代工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的推动下,西方理性的主观化及其二元对立又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所谓理性的主观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古希腊时期超验的、客观化的理性进一步被淡化和消除,理性逐渐成为人的主观存在,人日益成为一种与客观的自然和社会相对立的主体。二是西方哲学发生了一种“认识论转型”,成为一种认识论哲学。哲学不再以人的道德实践和社会历史为研究重点,哲学不再以存在论为主要任务,而是以研究人的认识为主要目的:以自然科学的理念及其方法论为标准,以人的理性为主要根据,去认识和把握包括人的认识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本质和规律。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的理论-科学态度也发展到了极致,人成为自然和社会的完全的认识和观察者,一个冷漠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建构者。如胡塞尔所说:“在始于笛卡尔的、勇敢的甚至过于激昂的提高普遍性的意义过程中,新哲学所追求的无非是,在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用一种严格的科学方式,即用一种进行逐一证明的清楚明白的方法,在一个无限的但具有合理秩序的研究过程中,包容一切有意义的问题。人们世世代代无穷尽的扩建最终在理论上联结一切真理的大厦,这样它可望解决一切可以设想到的问题——事实问题和理性问题,暂时的问题和永恒的问题。”[3](P984)
近代西方哲学虽然是一种认识论哲学,但它的哲学存在论仍然是存在的,是潜在于它的思想的前提之中的。其存在论主要是沿袭了古代西方哲学的存在论,只是这些“存在”的超验性进一步淡化,建构性进一步强化,而且进一步简化为二元实体,如物质和精神、经验和理性,等等。近代哲学的存在论的实体性表现为:这些存在实体本身,如物质、自然、上帝、天赋观念等,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因而是超验的。其建构性即人的理性建构、经验建构。
启蒙运动实质上是一种理性运动。相对于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和思想专制来说,它是一种通过复活古希腊的人文理性精神而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即理性复活运动。但它所复活的不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客观理性,而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主观化和科学化的理性:“启蒙运动奠基于四个理论支点之上:理论万能论——理性是通向知识的万无一失的向导;宇宙机械论——宇宙是独立于人的有其自身严格规律的机器;道德自律论——人只要按照理性的要求生活,其未来就充满希望;人无原罪论——人天生并不堕落,只是教士和暴君迫使人们堕落。这其中理性崇拜是核心。”[5](P58)
学界通常认为,笛卡尔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先河。他的哲学具有近代理性哲学的鲜明特征。首先,在他那里,世界被明确地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实体:物质和精神。物质指自然的物质和人自身的物质,即人的身体。它是纯粹客观的惰性的东西。它只有空间而无时间。相反,人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理性化的主体,具有绝对的认识能力和创造力量。人的精神只有时间而无空间。虽然笛卡尔之后的西方近代哲学各自具有这样那样的特点,但是都明显地受到了他的深刻影响,不但包括他的理性哲学的理念,而且包括他的以近代自然科学试验为榜样的方法论,如按照近代数学方法去从事认识论研究。这种观念和方法直接影响了17、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甚至影响到康德哲学。按照卢卡奇的观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一个是17、18世纪英法等国的“绝对理性主义”,另一个是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相对理性主义”或“实践理性主义”。
“绝对理性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它强调人的认识来源于人的感性直观,来源于人的理性对这些感觉材料的归纳和总结。它注重的是理性的归纳推理。二是唯心主义的唯理论。它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人的先验或天赋观念。这些先验或天赋观念就是存在于人的主观精神中的理性观念、形式。它注重的是理性的演绎推理。无论是经验论或是唯理论,都承认,认识的本质和决定力量是人的理性,认识基于人的理性分析或综合。
“绝对理性主义”的特点:一是受到了数学方法的深刻影响。这种理性,不是指反思辩证理性,而是指人的理智,即抽象化、形式化的逻辑思维。二是存在着经验和理性的二元对立:理性本身是实体性的,先天存在于人的认识之前,与人的行为活动无关,不是人的感性经验内化的结果。三是这种抽象化、形式化的逻辑思维主要限于纯粹认识领域,缺乏社会历史内容。例如,培根的经验论的归纳方法,莱布尼茨的先验分析方法,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的体系结构和方法,等等,都明显地带有数学理念和方法的痕迹。即使是后来的康德,也把牛顿和笛卡尔的数学体系的清楚明白和严密性,作为自己哲学的楷模,并且认为,哲学的目标就是通过理性的沉思和分析,把握人的认识: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实践理性各自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就是“通过追问理性认识能力,探索自身的理念、知识构成的界限”。康德的目的就是把理念的明晰与体系的构建相结合,使理性成为建构哲学体系的基础:“理性的纯然自行发展,宛如一本源的胚种”,“每一体系结构与理念相结合,此体系又有机地连结在‘人类知识之体系’中”,进而构成“人类总知识之建筑”。[6](P567)在康德那里,经验的东西包含着先验的理性形式,但是,先验的东西是与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经验的东西相互割裂的,也就是说,先验理性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不受人的经验内容影响的一成不变的东西。
可以说,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相对理性主义”或“实践理性主义”,是相对于17、18世纪的英法等国的“绝对理性主义”的“后现代哲学”,即对后者的解构和建构。它的特点可归纳如下:一是它以“实践理性”和“历史理性”为基础。实践理性不只存在于人的认识领域,而且也存在于人的社会历史领域,如道德、法律、宗教、艺术等领域。它不只是一种理智的、对认识的理论前提的反思批判,而且特别强调对人的行为、对社会历史合理性的反思批判性。与自然科学理念和数学方法论对“绝对理性主义”的影响相比,“实践理性主义”深受当时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二是它强调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实现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对立统一。如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指在认识论领域中,在“批判理性”的基础上,把经验论和唯理论结合起来。费希特强调,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自我”不但建构自身和“非我”,而且能够实现二者的统一。和康德一样,谢林力求在历史的过程中,在审美领域中,实现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和谐统一。黑格尔则称历史的主体也是实体,作为总体性和超验性的民族精神的“绝对理念”,把人即历史主体作为自己的工具和发展环节,通过主体实践的外化和内化的双重过程,实现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等等二元因素的对立统一。相对于17、18世纪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来说,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实现了从认识论向历史哲学的转变,以及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变。它强调历史主体对历史客体的建构性的思想是比较突出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首先是实践理性活动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性的个人改造现实世界的感性活动”,而是人的抽象化的精神性活动,是封闭的甚至是神秘的活动。其次,它沿袭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一种基本观念,即理性是纯粹主动性的东西,而物质、自然是纯粹被动性的东西,认为人是纯粹的主体,是纯粹主动的、创造性的,而自然和社会存在物是纯粹的客体,是纯粹被动的和被创造的;而没有像马克思那样,认为“人化自然”是人的社会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实现人的精神的对象化和自然对人的精神的内化的统一,是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统一体。它虽然承认主体精神的外化和内化这种人的活动的二重性,但是,它认为,现实存在物的价值和意义完全来源于人的主观精神,即人的理性及其对象化,而自然本身是没有原初意义和价值的,其意义和价值来源于人的精神对象化即对物质的“赋形”行为。
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缺陷是多方面的。接下来我们仅从它的实体性的角度进行简要分析。
这里的实体性是指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超验性和不变性;理性的实体性,就是把理性看作不是为人的实践活动所建构的,因而是自足不变的。我们说,古代哲学,无论是西方古代哲学还是中国古代哲学,由于它们都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所以,都具有实体性的特征。如中国的“道”、 “太极”与西方的“理念”、 “原子”,等等,都具有明显的超验性和自足不变性。就理性的实体性方面,西方古代哲学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它不是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内化的结果,而是上帝赋予的或自然形成的,因而是自足的、固定不变的。而且它认为,人的非理性不但对人的理性没有积极的建构作用,而且具有消极的影响,如欲望是人的肉体的机能和表现,会败坏人的灵魂,使人失去理性,做出有违人的本质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抑制甚至消除非理性,坚持和彰显理性。由于西方古代社会是以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并重的,而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的,所以,它们的哲学存在的实体性又具有一定的差异,简单地说,就是西方古代哲学的实体更呈现出无生命的“宇宙之砖”的性质,而中国古代哲学的实体更呈现出生命有机体的种胎性质。二者的差异直接决定了理性的差异。例如,中国古代哲学的理性强调对实体的整体性的理性直观和体悟,而忽视了对实体的局部的逻辑分析,而西方古代哲学则恰恰相反;中国古代哲学的理性强调理性和非理性、天道和人性的融合统一,而西方古代哲学的理性强调理性高于非理性、主体高于客体,甚至是二者的对立。
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是建立在西方近代工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它一方面是对西方古代理性主义的实体性的某种克服,强调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如经验、意志)对知识和历史的建构。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强调理性、精神的对象化和理性的自我发展过程,强调以理性为主体的实践,形成了一种历史理性或实践理性的哲学形态。如黑格尔认为绝对理念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世界的历史就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创造的历史。在“苦恼意识”中,黑格尔甚至意识到劳动对精神、理念的建构作用,在“市民社会”理论中他意识到经济活动在历史中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德国古典哲学又继承了西方古代理性主义的实体化、形式化的思想。其实体性主要表现为:一、它强调精神的对象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神的内化,即人的活动及其成果对人的精神的建构作用,特别是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明确地认识到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人化自然等对人精神、理性的建构和决定作用。二、在它那里,人的精神的对象化活动是非常抽象的,是以理性为本质的人的抽象活动,甚至是黑格尔的无主体的精神活动,而不是现实的人创造世界的社会历史性活动。其形式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按照当代西方哲学家的观点,近代以来的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其理性都是抽象的,缺乏生活内容。近代哲学把理性看作是世界存在和人的认识的主体和根本力量,而忽视了人的生活、生命活动对理性的建构和决定作用。二、西方近代社会的理性主要是一种“科学理性”,即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中的理性受到了自然科学理念、方法的深刻影响,使整个理性走向一种形式化、逻辑化、客观化的狭隘道路。他们认为,虽然黑格尔哲学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但同时也是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在近代的集大成者。当代西方哲学家正是在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理性主义及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过程中重建实践哲学及其理性观的。
但是,西方当代哲学家对其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其主要表现为:一、他们强调实践高于理论、非理性高于理性,强调生活实践对理性的建构和决定作用。但是,他们的这种实践主要是一种抽象化的生命活动,特别是语言活动,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强调实践是一种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活动。在整个实践活动中,马克思首先强调生产劳动对包括精神、理性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如劳动工具的抽象性和丰富性决定了理性、思维方式的抽象性和丰富性,劳动的需要和性质决定了精神、理性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特征。而当代西方的一些哲学家只注意到近代科学对理性的巨大影响,而没有进一步明确认识到生产方式和经济力量对科学、理性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还指出,现代社会中理性的抽象性和片面性还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即现代资本的存在方式的抽象性和片面性,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就是这种抽象性和片面性的理性观的具体表现。二、一些当代的西方哲学家,如一些“后现代”哲学家,过分强调非理性的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否定了理性的作用,从而走向另一种绝对化和片面化的道路,这也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批判的。
[1]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黑格尔.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1).
[3]胡塞尔.胡塞尔选集[M].倪梁康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季国清.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临界点上[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B089
A
1671-7511(2011)03-0035-07
2010-10-21
孟宪清,男,哲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课题“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意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张瑞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