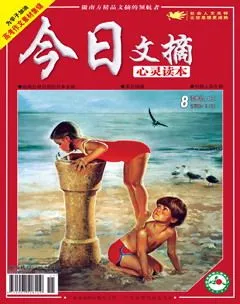纳税人 众生相
2011-12-04□李超
今日文摘 2011年15期
如果你是大老板,开公司、开商店,肯定避不开各种商品税,例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等,也避免不了各种所得税,例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如果你只是一名普通的工薪族,月收入超过2000元,同样需要纳税;如果你业余写作获得了一笔稿费,转让了一笔知识产权,或是买卖了一套房子、汽车,甚至是幸运地中了一笔超过1万元的彩票大奖,还是要纳税;也许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无产者,工资不高、没有额外的收入,根本不够纳税的资格,但只要你的银行存款产生了一分钱的利息,依然需要纳税。
从广义税收的角度来说,任何人都逃不掉纳税的命运,只要你还依赖社会链条生存,还在吃饭、穿衣、住房,你就是一个“纳税人”。
“沉默”的纳税人
美国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潦倒的克里斯因为没有按时缴纳税务局寄给他的税务账单,被政府强制从银行账户里划走了所有积蓄,克里斯给税务局打了一通满腹牢骚的电话,平静而无奈地接受了破产现实。“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情不可避免,死亡和纳税”,西方社会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这个论断已经在不同阶层中形成共识。
李媛艾一直赞同富兰克林的这段话,但她从来没仔细考虑过纳税对自己究竟会有多大影响。去年春天,参加完十几轮校园招聘,北京一家传媒公司给了她一份月薪6000元的工作,李媛艾粗略算了笔账:公司附近租间房子每月1500元,伙食费每月1000元,水电、交通和日常杂费每月1000元,平时逛逛街、人际应酬平均每月1000元,再加上其他一些开销、扣下一点税,算下来,攒不了钱,6000元的收入在北京生活也勉强够用。尽管拿着一纸名校硕士文凭,但不大景气的就业形势让她最后接受了这份工作,毕竟月薪6000元听起来还不太寒碜。
头3个月,因为还没毕业,李媛艾以试用的名义像公司其他员工一样上班,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福利,公司付给她80%的工资,这笔钱没有经过正式员工的工资系统,也不用交税。
7月份,李媛艾转正,让她始料未及的是,第四个月的薪水仅比试用工资高了两百多元,财务发给她的工资清单上:基本工资从5000元变成了6000元,同时增加了1000元左右的代扣费用,包含了各种保险、住房公积金,最多的是个人所得税,将近500元。表面上月入6000元,实际收入居然相差这么大,李媛艾开始重新计划自己的预算。对于纳税,她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缴纳了将近500元的个人所得税,还有衣食住行里隐藏着的消费税,税负对于她来说不再只是一笔可以忽略的开支。
与克里斯相比,税务上的误差并没严重到让李媛艾“破产”,她也没有收到过政府寄来的账单,绝大多数普通的中低收入者和她一样,尽管时时刻刻上缴着赋税,却很少关心自己的收入被谁拿走、拿走多少、用于何处。对于“纳税人”的身份,李媛艾既熟悉,又感到陌生。
和李媛艾一样。2007年,杨玲参加一个交流活动,到美国加州勤工俭学。她在一家小镇餐馆打工3个月,向美国政府纳完税后赚了两千美金,期间去周边城市玩过几趟。回国后没多久,杨玲收到了一封美国发来的电子邮件,因为是境外短期务工人员,没有向美国政府纳税的义务,税务部门要退还她在美国居留期间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总共有两百多美金,按照当时汇率,将近1600元人民币。
杨玲从来都没有保留税务凭证的习惯,退税手续需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证明材料,但杨玲在美国时习惯性地忽略了税务方面的考虑,根本没有想过退税的事,连印有商品税务额的购物小票都没有保留。与美国方面用电子邮件交涉了一个多月后,她决定放弃这次退税机会。与她同去的朋友当中,只有少数人成功拿到了这笔“意外之财”。
“痛苦”的纳税人
一个普通中国人一生究竟要负担多少税?余刚在一家跨国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对税收问题比同阶层的其他人更加敏感,但让他回答自己一生要纳多少税时,余刚也犯了难,繁杂的税种和税收政策很难建立起一个标准的模型,很多时候他都只能说:“具体要看个人从事的行业、收入水平和消费行为。”
毕业时,吴昊放弃一份地产公司的工作,南下广州当上了公务员。与在地产公司做白领相比,公务员工资并不优厚,第一个月,他的各项收入相加勉强达到4000元。不过4000元中,他所处行政级别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只有700元,没有达到个税起征点,其余大部分收入属于各种福利待遇,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也有专门的体系,总共加起来,需要缴纳的个税不到50元。除此之外,单位食堂和宿舍拥有国家财政补贴,相对于市场价格便宜将近一半,吴昊形容单位食堂“5元钱什么都可以吃到”,从税务角度看,他又免去了一笔消费税。
距离广州150多公里的深圳,程明在一家台资企业从事心理咨询师工作,他和吴昊是高中同学。程明的基本工资每月3000元,如果愿意加班最多可以有500元加班费。去年11月份,程明拿到了3500元的月工资,扣除各种保险和150多元的个人所得税,大概可以领到3100元。最近一段时期,长三角的私企用工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单位给程明安排了双人宿舍,为了降低员工伙食开销,公司食堂没有承包给外人,都是自主营业,程明形容“5元钱可以和一般的学校食堂吃得差不多”。
吴昊和程明都有对生活感到不忿的时候,区别在于,前者选择接受,后者寄望改变。
“精明”的纳税人
王莹是国内一家地产公司的职员,公司有个规定:员工每年有1.9万元的薪金收入需要用交通费和通讯费报销抵扣,平均下来,每月大概1600元。王莹有些为难,这个规定带来了很多麻烦,自己得拼命积攒发票,唯一的好处是,不用交税。
用人单位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减少员工的纳税额,通常是像上面提到的那样将一些需要纳税的项目,通过报销等免税方式发到职工手中。合理利用“平滑工资波动”也是一种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常见方式,因为工资薪金是累进税率,同样一笔钱,例如12万元,一次性发的话将适用45%的税率,但如果分成12个月发,每月1万,适用的税率为20%,总共可以节税6000元。国家税法还规定了年终一次性奖金将按照除以12之后所得金额适用的税率征收,将一部分收入并入年终奖里发放,也可以部分节税。
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动力去冒这些税务风险和麻烦为员工积极做税务筹划。在会计师事务所中,余刚的工作是为各种各样的企业筹划税务,和许多专门提供税务咨询服务的公司一样,只有寥寥无几的客户专门为个人所得税寻求帮助。税务筹划基本都是为企业制定减轻甚至免除税负的计划,提供避税方案。
不久前,余刚为一家广告公司做了份营业税筹划方案。按照税法的规定,这家公司的经营活动需要全额缴纳5%的营业税和3%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如果从广告客户那里获得了100万元代理费,两项税费分别要缴纳5万元和3万元。但同时税法还有另外两款条文:“从事广告代理业务的,以其全部收入减去支付给其他广告公司或广告发布者的广告发布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和“向广告发布单位支付的全部广告发布费可以从其从事广告代理业务取得的全部收入中减除”。
3个条文加一起,意味着只要这家公司能够提供支付过广告发布费的有效证明,就可以减少营业税的数额。假设同样从客户那里获得了100万元代理费,只要能够提供50万元广告业专用发票证明其支付了相应的广告发布费,两项税费分别减少为2.5万元和1.5万元。
唐慧从事资产评估工作,在她看来,利用法律条文自圆其说以达到减少税收成本的目的,是避税方法中比较高端和“常规”的一种,这种“常规”筹划涉及到很多法律法规和税务程序,前期还要耗费相当的时间和货币成本。一般的中小型企业更偏向于简单快速的“非常规”手法。
“非常规”手法的惯用思路是冒充高新技术企业、冒充小型微利企业、冒充经济开发区企业、冒充经济特区企业,这些类型的企业都享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唐慧接触到的冒牌企业当中,“假外资”最多:内地人通过在境外注册公司A,然后持股内地公司B,B就成了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不用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等,企业所得税税率也更低,除此之外,外资企业进口符合条件的设备免税,购买国产设备可以抵税,用分得的利润继续投资可以退税。
从2008年开始,国税总局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逐步取消了内外资的税收差异,又在2009年曝光了一批“避税天堂”国家名单,国际上正在合作抵制这种行为,流行一时的“假外资”在中国的生存意义越来越微弱。
唐慧说,相对于企业和高收入人群的避税效益,中下等收入者的避税完全是杯水车薪。
她用自己所从事的股权转让税务筹划举了个例子,如果A企业的一名股东想把自己在公司的1000万注册资本和1000万未分配利润转让出去,未分配的1000万元利润按照净资产转让的话,需要缴纳25%的资产税250万元,但是先分配完1000万元的利润,只将1000万注册资本转让,未分配的1000万元利润所得就只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200万元,调换一下利润分配的先后顺序,马上节约了50万元的税赋。
避税究竟合不合法?起码在法律法规内的避税是合理的,当安迪用自己的税务知识为同伴讨得一瓶啤酒时,没有人会责怪他。
(杨千川荐自《南方人物周刊》)
责编:小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