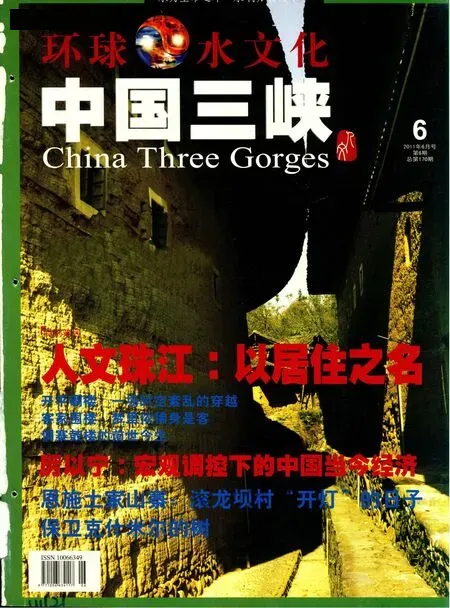记忆里西陵峡的三个小地方
2011-11-21编辑柳向阳
文/杜 鸿 编辑/柳向阳

西陵初雪。摄影/黎明

乐天溪莲沱大桥。摄影/黎明
乐天溪
乐天溪是白居易未写出来的一首诗。但这首诗永远署着他的名。
白居易是在华灯初上时分登上镇的。即使是大唐的扁舟,次第从南津关、灯影峡、莲沱三漩上来,留给大诗人的精神惊惧,仍然不亚于为他拉纤的纤夫。可以说,那些惊涛骇浪闪失了他胸中的诗意。这或许是为他在乐天溪重新让诗意附体打下的伏笔。
掌灯时分,他拖着晕船和惊吓留下的半条命,一脚踏上石岸,胸中的诗情立马开始死灰复燃。一瞬间,诗情在这位古人心中开始燃烧起来。他的诗情最初始于脚下的石阶。即使这些石阶很一般,只是简单的黛色,但是,作为首次来到峡江的诗人,在这里的每一个举动,都是他进入峡江的第一站,第一脚,所以他衣袖生风,石阶一下子排解了江水带给他的漂泊感。江水带给他的眩晕依然在眉目之间徘徊,可是,他非常分明地感觉到了乐天溪土地的坚实、石阶的坚硬。此时,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坚硬。
江风从东向西吹,自然吹动着他的衣衫后摆。江风让他的脑子里有了足够的氧,让他胸腔的血液喷张了,让他上台阶的脚步轻便了。诗意就驻进了他的心里。诗意让他很快来到了街面上。纤夫就留在船上过夜,他们即使现在进入了油画,可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他们始终没有在诗人的印象里停泊。
入了镇口,也许会有几位像“青滩姐儿”一样的女人向诗人流盼。他也没让她入心。他的眼睛全部落到那些房舍上,那些马灯油灯之下街道的朦胧,那些窗棂门楣上的招牌,那些可以撞到额头的幌子,那些卵石铺成的街巷,也许他每走一步就感觉到走在自然的图腾之上,那些夹杂着峡江与川江官话的五马横腔,以及那些夜色和那些在夜色里安然栖息的人们,一切的一切,都勾引着诗人心魂,都让他沉醉,让他魂不守舍。

太平溪望家祠堂。摄影/黎明
在彷徨中,他和随行找了一家客店住下。然后他们来到一家吊脚楼酒店。他并非因为饥饿而这样做,是这儿催生了他想占有什么的欲望,而现行最直接的东西,就是这儿的食物,一座小而古的镇上的食物。
在诗人而言,此时此地,前后观望到的风景,左顾右盼到的人物,没有一样不是诗,不有诗意。
可以这么说,作为诗人的白居易,从他一脚踏上乐天溪开始,心里就开始有诗了。那串又急又陡的石阶,涌着诗意的温暖,通过脚传达到他心里,然后变成印象停驻下来,成了一首似水墨画的诗。那位流盼的徐娘,以一种动画般的情态附到他的印象上,成了风情的诗。那些门楣、街石、幌子、酒店,包括酒店里面的楼梯,以及上楼时引路嫂娘浑圆的臀,还有下梯时的昏黄,都在诗人的印象里,成了一首首可圈可点的诗。

太平溪望家祠堂一角。摄影/杜鸿
可是这些还不够。诗人还需要更灵动更深刻的诗。他的诗意需要一步步走得更远、更深,即使消失到街巷最深处,也不惜。只有这样,他才会得到更大的沉醉。他需要在印象里面,建筑起一座关于乐天溪更宏大更立体的诗意。于是他需要吃。
于是,在酒店里,他获得了更新的诗意。在油灯的昏黄里,从第一道菜上到竹桌上,从第一杯酒出壶、进杯、入口,从酒店妹子执壶的手指与动态,从火锅里升腾起的香气,从窗外闪过的人影和声音,从脚下面溪与江温存的光影,诗意一片一片落进诗人的心田,落进那部隐秘而且是最大最全的《白居易诗全集》。
然后,他合上了诗书之页,因为他微醺了,甚至他有些把持不住了。他朝着随行挥手,随行连忙上来扶他。他推开了随行,沽酒的妹子上来把他扶住了。在她的扶摇之下,他们摇晃着走向客店,走向诗意的最深处。
第二天,店家的嫂娘去叫醒客人。房子里人去楼空,只有一些足够付店钱的碎银放在睡桌上,碎银下面还有一张宣纸。纸上面写满了鬼画桃符的字,嫂娘打开,见上面写道:
真正的诗,就是这样的夜晚,这样的小镇,这样的饭食,这样的女人。白居易。
太平溪
小镇口上,那两棵大柳树下的老木屋,手牵着镇1980年以前的古代和1980年至2000年的中生代。我见过镇的古代,至少童年时我的赤脚穿越过它。在镇处在中生代时,我在那里生活了三年时间。
老木屋的板壁是那种黛色。时间在上面呈现出黑色的霸道。房子正墙用的木板又宽又厚,板与板之间绝没有缝隙,正墙有三米高,上到墙眉时,往外放了一米宽的斜面,向两棵大柳树的方向斜着,构成飞檐的景象。镇里的房子都讲究平整,即使是高档轻便的原木,也没有孔府那些飞檐勾心斗角的机巧。
屋顶上盖的是黛瓦。瓦上因为时间经年,长出了一根根叫不出名字的植物。还有许多苔藓,顺着瓦脊生长,一点也不影响防水或流水。
屋脊上有三幅瓦雕,脊中一个,脊端各一个。样子也朴实,不是龙头,就是虎牙,脊中间往往是梅花图案,是镇上的老窑烧出来的物件。老木屋是镇上房子的标本,镇内任何一间木板房,几乎和它一模一样。

小镇太平溪。摄影/杜鸿
老木屋留给我最后的记忆,是八十年代。新生的泥土将它的屋脚淹住了不少。它像花丛里的老太太,独立存在于镇口。早先的镇,比它的位置低,低多少记不住了。按照葛洲坝建成之后镇抬升的高度,至少有十米以上。门口有树丛,还有许多芭芒之类的草。相对镇而言,它真是个桃源之所。在它面前三五米处,是一条板车小道。板车道上有一条从江边一直穿过镇口、然后再直达镇中心的绞索。一条叫坦平溪的溪与板车道同向插入长江。绞索是镇上搬运队用以节省力气的动力。将板车的挂钩挂到索上面,索在柴油机的动力下,拉着板车,板车载着船上下来的货物,让赤着上身的搬运工人撑着,一路悠闲地走。搬运工肩上挂着板车拉带,一手撑车,一手用汗巾在额上和胸上擦汗,一日一日把身体擦成和镇一样的古铜色,擦成一眼就能看得见的力量。
沿着绞索望去,老街临溪一面的东街,全是镇上的居民住宅。房子全是板壁屋。街道全是卵石铺成。石头与石头之间全是黄泥。无论天晴下雨,都灵干得很。西街就复杂一些,西街的地基比东街要高出三五米。进西街那些房子里去,必须爬石头台阶。西街的房子或是土木结合的石屋,或是板壁老屋,或是半截土干打垒加上半截板壁砌成的老屋,或是以灰石加木板建成混合型老屋,稍显杂乱,可总体仍然呼应着小镇黛色的境界。那个时代,那种颜色,任何一幢房子都无法逃脱这种风格的控制。
西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饭店。在那儿,凭二两粮票和五分钱就可以买到香喷喷的馒头。即使买不起馒头,只需走到它门口,就能闻到馒头飘香。再就是染坊,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从屋里到屋外,直至街面上,全是那些靛蓝敷衍的颜色。甚至有一种只要一走近就会被染成蓝皮人的感觉。而且,那些蓝颜色还散出一种靛蓝的气味。我一直觉得,那种靛蓝色的气味就是死亡的气味。只要闻过一次,一辈子就不会忘记。
再往镇里走,就是茶站,是区公所,是人武部。它们的颜色是红的。红色板壁将它们与周围黛色的民居区分开来。再往后依次是邮政所、银行、卫生所和一些公事机构,还有一家归属街道的小型诊所。我在那个诊所里购过消食片。至于花圈店,寿衣棺材店,镇上肯定是有的,只是我没有印象了。
有糖出卖的供销社在东街上。也是红板壁屋,长长的,足有五十米,里面卖的任何一样东西,在现在而言都是文物。印象最深的是火纸、麻糖和把把糖。啤酒和汽水乃至冰棒是八十年代以后引进的新名词,那个时候,供销社里面没有这些。那时能吃上一粒一分钱一颗的糖,就算奢侈。
除了小镇的黛色印象之外,还有一个印象,就是那时的老太太特别多。她们多坐在东街西街的老房子的门口,晒着阳光,无嘴无口,默默享受时光。她们什么时间来到这个镇上,什么时间离开这个镇上,我一律没有印象,永远的印象只是她们在阳光下无语地坐着。以至那时我就想,等我老了,也要像她们那样,坐在安静的阳光里晒太阳。那幅景象,即使到了现在,我依旧会那样想,惟独不同的是,我希望那时身边有一位我深爱的姑娘。
白马大峡谷
白马大峡谷就在西陵峡口的南津关。
白马大峡谷是三峡从根部直接生长出来的一根树枝,是那条进入了三苏诗里的下牢溪生长出来的一段隐秘的生命,是大自然对人类最后最真诚的宽容。
在初春里一个阳光很足的日子,我走进大峡谷,一直走到大峡谷的深处。阳光照在腊梅峡的山梁上。
山高草黄,一切都是以一种纯朴自然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壁立的石岩,风中轻轻摇动的植物。那座巨大的石屋,像一户农家,显得落寞而沉寂。石屋后面的山上有一道瀑泉,瀑泉飞流直下,形成一泓深潭。在阳光里,那潭是一面明镜。石屋过处,是一个漫水洞。洞里,水在这里化成响彻时空的音符,高高地从洞顶落下来,把置身其中的旅人带到从没进入过的静谧境地。

白马大峡谷。摄影/黎明

南津关大峡谷。摄影/黎明
腊梅峡,就是因这里野生的腊梅而得名。
每逢冬季,在峡谷的两岸,满山遍野的梅花,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一些美好的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西陵峡谷折寒梅,争劝行人把一杯”。让人觉得白马大峡谷的梅有一种妩媚,一直媚进了人的骨子。在腊梅峡的深处,有一棵五百年树龄的古柏,静静地站在峡谷中一处宽阔地带上。它枝繁叶茂,如日中天,显现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很显然,它是在向我们证明,它就是一棵活着的历史。
到了龙口。它那八十多米的身架,横亘在峡谷的关口上,像一只历史的大眼睛,注视着我们一步一步向更原始、更隐秘的地带迈进。芭芒疯长,山溪响动。水清见底,溪床上,无论岸上,还是水里,全长满了黄色的青苔。溪岸上,布满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溶洞。洞里的石头长相各异,有着如同钟乳石一样生动的神情,却是一幅自然本色的面孔。朴实、原始,又不乏美丽生命一般的涌动。这些美妙的景象,加上峡谷里的小瀑,溪水里圆圆的石头,水流动的声音,小溪如弦,弹奏出如灌珍珠的声音,构成了一幅绝妙的高山流水图。山涧溪水的声音弥漫了峡谷的整个空间。那些石壁和树木,被这种自然纯朴的声音过滤得纯净而空灵。
在一处宽谷的溪里,有一块狰狞的大石头。它像一位面目狰狞的人正在沉思。它在沉思着什么,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沉思的模样,让人想到雅典城最杰出的雕像。似乎所有的大峡谷都有宽谷。宽谷是一种姿态。宽谷里的一切,显得那么舒缓、烂熳、随意而安然。
腊梅峡的尽头出现了一处原始的村舍。风蚀雨浸的土墙草舍,百年飘摇的老屋,让每一位曾经生活其中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老家,想到故乡,产生强烈的怀旧感。这老屋是峡谷里唯一可以窥见的人烟。站在这老屋旁,放眼向峡谷的峰望去,在那天色的逆光里,呈现出一派千军万马驰骋奔腾的景象。随着山谷溪水的轰鸣,真似金戈铁马,刀枪相向,一片狼烟四起的古战场。
闻香峡是人类文明的痕迹。
从这里的遗迹,依稀可以看出,不知是哪朝哪代,我们的先祖,曾经在这里播撒过他们以劳动这种最朴素的形式,所展示出的智慧。就是这种满山遍野的香草,撩动了这些先民的心智。他们就地取材,就地造坊,建起了大概是人类最古老的手工作坊香厂。现代人完全可以想象,水车冲动着石碾,石碾碾压着芳香四溢的香草,刚刚从原始人身体里蜕出的先民们,正在埋头劳作。他们的每一个动作,石磨的每一次碾压,都把巴楚文明碾得滋滋有声,都把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原始作坊生产出来的香柱,一方面被先民用于维护他们生命进程中所必须的信仰,完成那种虔诚的宗教祭祀活动;一方面,他们把它们非常功利地运用到生活中去,灭蚊杀菌,驱虫除臭。就是在这种大量的生产实践里,闻香峡得以有名,而且伴随着香这种特殊产品的外销,闻香峡很自然就成为了白马大峡谷家喻户晓的所在。
即使是抵达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遗迹,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这种抵达必须无畏地翻越一道高近百米的难关。它的名字叫三道关。攀爬着这险象环生的三道关,每上升一步,都要付出毕生最艰辛的努力,都要经历人生最险峻的考验。
上了三道关,是一种柳暗花明。
绿树,古藤,老洞,鸟鸣,构成了闻香峡最自然最本色的千姿百态,让人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溪水成了人们常说的真正秀色。厚厚的青苔,把水拥得那么文静,安宁,从容。杂木树林里,树姿相亲相拥,似人一般地流露着温情。树根在这里就显得更神奇。大概是洪水让它们得以显山露水,这盘根错节的树根大写意,简直就是古商州的甲骨文,让人想到人的来路和文明的起源。
山空鸟鸣,抬眼望去,那石壁是一重又一重的洞天,千层的石岩,一层一层的,大概就是这峡谷里每一座山峰的年轮,加上石壁上洪水留下的痕迹,它们又是一部部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编年史。洞中打坐的大佛,一点也不比乐山那种人工雕凿逊色。天然的岩屋,是千锤百炼的凿痕拼起来的艺术杰作。
春还很浅,草木已经很深。伴随着人类文明的退却,这里的自然又还原成为一种人迹罕至的领地。人自发地为大自然腾出了一种如同神话般的空间。得以让这里的植被显现出最原始的风貌,得以让这里的物种生长出最丰富的层面。
进入马肝峡,就真正进入了白马大峡谷的深部。自然与原始的神情,在这里被浓墨重彩地抒写到极致。
在平常人们看来最普通的石头,到了这里也成了世上最奇妙、最富变化的东西。它们有的是一枝独秀的钟乳石;有的组成成群的溶洞,展示出一种被时间风化着的面貌;有的呈现出一种奋力拼斗的姿势,幻化成类似人类的残酷的角斗;有的就是那千手佛像,既千姿百态,又佛心林立。
这里动物的待遇,是世上最温厚的。在它们最本能的词典里,找不到恐惧,找不到伤害,更没有欺骗这些只有人类才有的词语。鱼儿游得多安静。它们是多么旁若无人,无忧无虑。它们成群结对地游动着,安详地嬉戏着,让人心生无限的感动。在这种大峡谷里,面对伸手可捉的鱼儿,人们的心灵也变得无限宽容,无限纯净。

西陵峡早霞。摄影/黄正平
走得累了,一阵热闹的水响就起来了。隔潭展现在我们眼前。
潭里大大小小的石头上,布满的青苔比以往的任何一处都厚,都重,它们绿得发黄,水清见底,水底每一颗石头,都被青苔包着。一簇簇紫色的兰草,顺着潭的来路泻下来,形成罕见的紫瀑,或叫兰草瀑。潭里的水静得有一种潺潺的声音在水的内部涌动。直到它们随着潭水流到潭的出口处,在一刹那间,这种宁静的潺潺声得到爆发,发出哗哗的声音。潭的峡谷里, 百年的古藤在空中摇荡。野兰草独立在潭边迎和着它们,不停地摇曳。植物陈腐的尸体横呈在潭的周围。站在人工扎成的筏子上,放开声音喊一嗓子,声音刚一出口,就被峡谷的嶙峋峭石,撞得七零八落,纷纷落进这绿汪汪的潭里。
过了隔潭,峡谷就变窄了。每进一步,就生一份窄逼。抬眼望去,那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线天”。走近一线天,发现它实际上更像从峡谷里生长出的一棵参天大树。与普通的树不同的是,它的树干枝叶全部是天空。
蝴蝶是爱美的精灵,它们在峡谷的动物、植物、甚至水的生命里飞舞,在这些沁人心肺的芬芳里飞舞。
来到牛肝马肺面前,才明白为什么把它作为这段峡谷名字的原因。在这儿,比起三峡里的那个马肺峡,它离我们要近得多,以至于让人感到大自然那种深切的人情味。也许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同的是,一个置身三峡,出尽了人生的风头;而另一个被隐身在这里,独享着人生的寂寞。其实,人与大自然也是一对孪生兄弟。看那一丛一丛的心肺,披沥着如同人生所经历的风雨飘摇,一个个都显得泪湿肝胆,让人想到高山流水,想到春江秋月,想到岁月流逝的忧伤。
峡风在斜阳里起了。壁立的石寨,紫藤垂帘,轻溪伴奏。一线天拽出的仍然是一汪潭水。潭顶是一座高山,山脚是一处水洞。潭就是白马大峡谷行程的尽头,到了这里,我们在峡谷不知不觉行进了二十多公里。当地的老人说,峡谷一直连绵到神农架。面对这堵险峻的山,有人说从洞里可以过去,有人说,可以翻山过去。而最能翻越它的是传说中的七仙女,她们在这个潭里洗浴之后,很轻易地就飞上天去。
走在这人迹罕至的原始领地,心里体味着这些生命样本的野趣,体味着人生终极和隐秘的意味,体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探险乐趣,我们的生命也在这种行程中,一片一片地散成这里的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