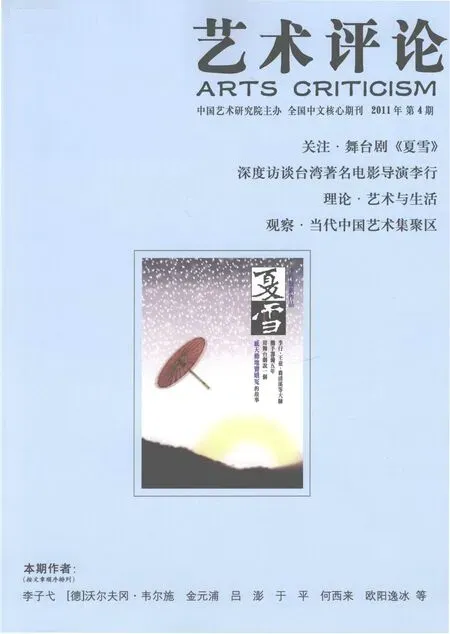呼唤大美术史观
2011-11-21张景鸿
张景鸿 杨 晴
呼唤大美术史观
张景鸿 杨 晴
专业化的观念伴随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及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为追求生产效率出现社会分工而日渐强化。专业化的技术理性精神随着现代性的推进而蔓延全球,从而渗透于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教育方面,这种“知识爆炸”时代的专业化意识将原有的古典人文学科分裂到至微至小,以致巨细铺陈,这便是“学科壁垒”式的专业化。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仅仅旨在培养专业性的各行业技术人员为目标,各种不同的学科系统先后被确立,也就“由此开始了古典教育解体的历史过程,它包括从古代贵族精英培养下移为社会教育、从伦理中心向科学知识与技术能力的教育目标推移、科目的多重性质分化为单一性质专科等一系列改变。”[1]
专业化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能依靠学科的某些优势有效的挖掘学术资源,保障研究深度的实现,使某一方向上的研究达到“术业有专攻”。在西方,美术史(艺术史)学科建立于19世纪中期的德国,之后便出现了温克尔曼、沃尔夫林、里格尔、贡布里希等有深远影响的艺术史家。问题是,在专业化技术层不断模式化和操作化的同时,学科本质主义的倾向也日趋严重,而当这种意识形态与学术外在的条件结合,学者往往为稳固自身的既得利益而背弃学术发展规律的要求、学术资源垄断等现象就会相继出现。对人文科学而言,如果说学科专业化的积极作用是能配合社会化经济生产的分工,并在一定意义上使研究具有纵向的深度,那么其消极作用就不只是工具理性对学科学术研究的畸形引导,更重要的是使人局限于“专业知识”,失去把握的高度而迷失在算计的深渊。
早在20世纪中叶,贡布里希就对美术史学科中的学术工业现象提出警告:“……由于兴起了那种我们只能称之为“学术工业”(academic industry)的东西,已经横竖变得朝不保夕了。这是一种要求“研究”的工业,不是出自对真理的渴望,而是公开地为晋级升等提供证书。……”[2]
与学科专业化道路相伴而来的,是跨学科又称交叉学科的产生。没有学科专业化过程就不会有跨学科研究的需要,恰似一把双刃剑。跨学科的概念是基于人文科学精神的整体性原则,跨学科研究是学科专业化背景下的策略对治与观念调控的力量。
在人文学科的跨学科探讨中,一些其他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对美术史学科而言颇具有参考意义。在经济学家的讨论中,他们认为:
(一)“跨学科”行动消解了专业“范式”的意义。[3]“跨学科”和专业“范式”是对立的范畴,前者意味着与学科外建立联系,后者则是学科内部封闭式研究的必然结果。贡布里希对美术史的研究“范式”亦有讨论,他认为一种学术的专业范式如果被作为一种方法工具滥用,则其范式本身所具有的学术权威性就会导致研究者屈从于投机取巧,远离创新的意识。他将这种范式称之为“智力风气”或时尚。尤其这种风气与它所批评的“学术工业”相依附,就阻碍了“面向真理的学术研究”。
(二)在跨学科视域内,经济学家们认为学科的兴盛与衰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方法论之争的必然产物。[4]这一点确乎可以看作是对美术史方法论研究意义的肯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术史与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紧张关系。美术考古学的方法论,是运用考古发现的一些出土文物,主要是图像制品,通过对其做考古学鉴定来进行史料意义的研究。文化人类学提出的“第四重证据法”亦是对出土的图像文物进行比较图像学分析,来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跨文化资料,使传统用来收藏赏鉴的图像变成史学的“第四重佐证”。美术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本身就是跨学科的结晶,与美术史发生联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联系被一些美术史家解读为“入侵”,对于那些认为美术史学科是以艺术作品的风格、鉴赏和图像学分析为主要任务的研究者来说,这种入侵导致他们不得不提出两种急切的质疑:美术史作为独立的学科将要被取代了吗?美术史研究只是为美术实践提供理论总结吗?美术史只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图像史料吗?质疑的过程似乎使美术史家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关键在于美术史方法论的研究。这虽然看上去与经济学家们的结论如出一辙,可是具体的研究意识毕竟有很大区别。经济学们的方法论是考量一种方法在社会科学整体中能否担当一种整合意义的建构作用,所以他们可以明晰结构主义与韦伯的理想型各自在哪种情况下更为适切。而美术史家们习惯和认定的方法论切入点并未总览人文科学的全视野,而是局限于寻找美术史学科的立身之法,然后或将之深化,或将其他学科的成果取为己用。
近年来,中国美术史界存在两种主要趋势,一是以艺术发展自身规律为主线,同时吸收文化史、考古学成果为己用。二是善于采用考证方式澄清美术史中一些有待争议、未确定的疑难问题。但是后者存在着被考古学吞并的可能性。……艺术史最值得关注的部分就是艺术家性格及其所掌握的技法。[5]
今天艺术史有时似乎更像一个各种理论和方法论相互冲突争夺的荷马式战场,各种观念形态和人物都在谋划争夺艺术史领域内的发言权和控制权。……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或女权主义等理论标签下结成了各自的联盟。[6]
因此,美术史研究者这种对方法论与学科关系的理解并非是在人文科学整体内的跨学科性理解,而是依从学科本位出发来考虑方法论问题。下面这段话对美术史研究者同样适用:
今天似乎不太有人对方法论的比较和争论感兴趣了。这也许正是学科分割,大家相安无事、没有竞争力的结果。……各个学科的专家都在“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但我们却很难判断,其中到底有多少专家是因为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严肃反思,多少专家不过是为了维护被经济学刺痛了的学科虚荣心和危及的既得利益。[7]
在字面意义上,跨学科研究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多学科间的比较研究,在使用材料上以本学科为主,兼容其他学科的材料来辅助本学科研究,例如前述对美术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解,由此产生了美术史只能为其提供材料的疑问。在研究方法上理解为跟随学术时尚尤其以追随西方学术思潮运动来进行应用性创新研究,于是就出现了打着各种理论、主义、方法论的“荷马式战场”。以上两种看法都是对跨学科理解的偏见。人文科学中的跨学科研究既作为方法论又作为一种研究行动。它的确是在学科间才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它还具有一种主旨精神,即这种研究并不是形式上的杂糅,不是“一种随意鼓励任何一类学科间综合对话的呆板主张,而是指在跨学科互动中更适切地重组研究计划中的问题系列和方法组合。”[8]这一点也是使超越部门学科的人文科学得以向前推进的动力。
在美术史的跨学科研究中,对一种外在方法的介入存在质疑是审慎的思维逻辑,这有利于防止学术时尚肤浅而无益的复制性操作,使有限的学术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和利用。这种审慎不同于基于学科本质主义立场的排外。形成这种审慎的思想根源大概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美术史研究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其二是美术史家自身的知识结构。专业性和技术性是每一个学科所特有的,例如美术史的风格分析和图像分析,经过学术训练后对作品的风格、真伪、背景的鉴定才能更接近史实,材料的真实性得到确证。
由于布莱森等“新艺术史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图像读解训练,他们力所能及的是用既定的符号学理论套用到图像解释上去,或搜寻可以运用他们的理论解释的图像,而他们的大胆推测,虽有时给专业艺术史家带来某些理论上的启示,但就理解艺术史本身而言,经常显得比较幼稚。[9]
这是美术史家对专业性和技术性最彻底的回护,也是看上去最为有力的排外。曹先生的治学是提倡跨学科研究的,然而他对跨学科的理解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偏见之一。对符号学的不肯释怀最根本的原因是认定布列逊这些非美术史出身的研究者对美术史专业技术的生疏。这种审慎不免与学科本质主义趋于一致。方法之为方法,正是在于其既定和可操作的程式,寻找合适的图像不仅是其中之意,更是其有效性的体现。至于布列逊的研究是否为生吞活剥的套用,则需要另外的研究。
美术史家自身的知识结构也对理解跨学科研究有重大影响。跨学科研究不仅是方法,更是行动,是一种人文精神。这是由人文精神自身的整体性决定的。它要求研究必须超越学科局限,有效拓展自身的知识结构。这并非是要学富五车和触类旁通,而是培养对所从事研究的目的、意义与价值做人文精神的整体关照,将学科位置放在各部门学科相互联系的网中。这样的跨学科才可能产生交流与对话。
“跨学科”不是指各领域对象材料的融通。跨学科方法论指的是各理论方法之间的对比和会通。例如,只有当你的西哲知识实质上影响了你的中史撰述时才会发生理论性的会通,只有当西方理论实质上影响了你对中国小说的评论方式后才会发生跨文化的理论会通。[10]
由此可以看出一些后现代主义的狡黠。例如“艺术终结”说,伴随诸如极少主义、大地主义、观念艺术、人体艺术等后现代艺术思潮的广泛传播,传统艺术确乎已经濒于终结。“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已然成为现代性的宣言,视觉文化以一种比美术史涵括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姿态出现,以“视觉”作为后现代文化标识。虽然视觉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不可否认,然而问题却并未得到解决,反而愈加严重:以视觉图像切入仅仅是文化研究的一个角度,这与文化人类学的第四重图像佐证殊途同归。将文化平面化为视觉图像,即文化视觉图像化,那么这绝不是所谓的文化的图像转向,这恰恰是文化被工商技术异化的商业化。因为,“图像转向”在深度上与“语言学转向”不可同日而语。
文字文本的理解和解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和与非文字的“文化文本”(culture as text)的概念及其解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图像作为非文字文本所特有的认知意义,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关注和重视。那绝不是什么关于“读图时代”到来的判断就能够说明的。[11]
这种即时消费的图像文化不仅导致了美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而且对人文精神是一次荒漠化的重创。因此,美术史学科以其所诞生的古典人文传统为依托,不仅与全球化的抹平一切相对抗,与后现代读图消费相对抗,与商业化操纵下的非理性艺术行为相对抗,更与其他人文学科诸部门一起肩负着重建人类理性精神的重任。在这个意义上,对美术史跨学科研究更应该具有人文科学的整体精神,同时希冀通过对跨学科方法理解误区的有效厘正,呼唤这个时代的一个全方位、大视野、大背景、整体性、立体性,共享性的大美术史观的到来。
注释:
[1]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2]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范景中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
[3][4][7]汪丁丁、罗卫东、叶航:《跨学科的范式》,《社会科学战线》,2004。
[5]宋玉成:《美术史学辩》,《美苑》,2002。
[6]普莱茨奥斯:《当代艺术史学科的危机》,常宁生译,《世界美术》,1999。
[8][10]李幼蒸:《历史符号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9]曹意强:《图像与语言的转向——后形式主义、图像学与符号学》,《新美术》,2005。
[11]叶舒宪:《第四重证据:比较图像学的视觉说服力——以猫头鹰象征的跨文化解读为例》,《文学评论》,2006。
责任编辑:唐宏峰
张景鸿: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杨 晴: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