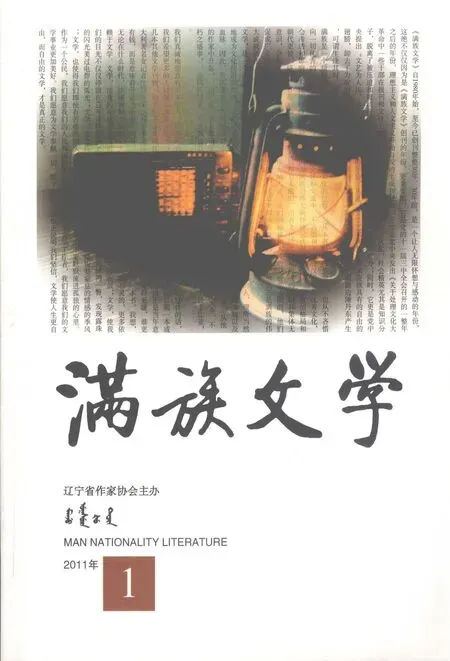巫面
2011-11-21陈然
陈然
巫面
陈然
陈然,男,1968年生,江西湖口人。发表中短篇小说200多万字。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轮子》,长篇小说《2003年的日常生活》、《精神病院》等。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并入选多种年选。现供职于江西省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之前,我一直弄不明白,比如说“年”是一种猛兽,可人们在过年时为啥要敲锣打鼓欢天喜地?是庆祝自己再次被送到了猛兽的嘴边,还是庆祝“年”这只猛兽又增了岁月体格又大了一倍?还有,我们这里有一种叫“傩”的凶猛面具,我们小时候谁看了都害怕,大人还以此来吓唬我们,可后来我才知道,它是我们村里的吉祥物。每年,大人都要戴着它来表演戏曲,外面的人都拿着照像机摄像机来看稀奇。
他们说,我们村保留的这种东西,非常难得。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每年省里搞相关的文化活动,都要派专车来把我们村的傩面借去,用后又恭恭敬敬送回来。这时,村里管事的人便在村口大放鞭炮迎接。
我家的事情,想必很多人已经从电视里看到了。那个曾做过我姐夫的家伙,和我姐姐谈了整整五年的恋爱,才结了婚。然后又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害死了我哥哥,又害死了我姐姐。
我还记得,姐姐第一次把那个男人带回家时的情景。姐姐初中毕业后,没再上学,在县里一家新开的工厂找到了事做。那几年,我们县的经济发展很快,不断地有外面的大老板来投资。奇怪,本地人办厂都办不成,外面的人一来,就办成了。我姐高兴得像只麻雀似的在院子里蹦来蹦去。我爹以前是乡农机厂的采购员,但他在一次出差途中失踪。事情已经过去十八年了,也就是说,我已经十八岁了。他匆匆忙忙把我留在娘肚子里,就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我娘固执地认为我就是爹出差前的那晚留给她的。她不止一次罗罗嗦嗦地跟人家说起过。她说,我爹平时跟她睡觉,好像总提不起劲,但一准备出差,劲头就来了。因此,在完事后,她就像以往那样起身给我爹收拾行李。等她醒过来,爹和行李都不见了。大家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是跟别的女人私奔了还是被坏人给害死了。她对想象中私奔的那个女人由恨而爱,转而变成热切的渴望,她梦想有一天那个女人带着我爹忽然从天而降。即使这样,也比我爹彻底地杳无音信好。当她对这一点完全绝望,就只好重新沉浸在我爹当初给她的甜蜜里不肯自拔,直到我姐带着一个青年人走进家门。
那天晚上,我娘特别地想我爹。她一边在灶屋煮饭,一边抹眼泪。我看出来,她甚至有些嫉妒我姐。她比我姐更过分地跟男方套近乎,问他穿多少码的鞋子,平时吃得好不好。那时,他还没进那家公司,跟我姐在一个厂里做事。我注意到,娘的神情有些恍惚,好像在发愣。我姐是个马大哈,只顾和对方说笑,没心没肺的。有时候,对方的手还没碰到她,她就夸张地尖叫起来。像在我们面前炫耀。说实话,别说娘,我也不太喜欢他们这样。好像我们家的东西被别人沾了手。我甚至厌恶地皱了皱眉,觉得姐姐就是贱。女孩子就是贱。有了男人,就把家里人丢一边了。后来她跟我说话,我也故意爱理不理的。
此后,他们就经常歪歪倒倒地骑着一辆自行车到家里来。有时候他坐在后面,有时候我姐坐后面。反正不管谁坐后面,都能听到我姐那没头没脑的笑。好像自行车上驮着的是一袋红薯,袋口没扎紧,我姐的笑声就像结实的红薯那样的的笃笃滚落下来。我姐叫他小曲,我娘也叫他小曲,我和我哥也跟着叫小曲小曲。我姐呵斥我和我哥说,瞧你们没大没小的,你们应该叫他哥哥咧。我哥就低下头,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我却把脖子一挺,说,我偏要叫小曲,我偏要叫小曲,小曲小曲。
小曲倒不在乎。他跟我姐说,你这个弟弟挺调皮啊。
其实从内心里来说,我也觉得他这个人不错。除了比较小气。比如他叫我或我哥去帮他买烟时,总舍不得多给一块钱。买四块五毛钱的烟,他就给四块五毛钱。如果他钱包里没有零钱,就叫我姐给。好像他们已经成了一家人。这样,我家里不但没占到便宜,反而损失了四块五毛钱。我给他买了一两回烟,后来就不愿去了,都是我哥的事情了。他大我两岁,比我好说话。在背后,我跟娘抱怨,说小曲这个人太小气。娘扑哧笑了,说,男人小气一点也没什么坏处,精打细算会过日子。唉,我们家的人,都太好说话了。小曲看出来我比较排斥他,后来就有意跟我套近乎。
小曲说,他就喜欢我这种性格,有叛逆性。
他这句话果然赢得了我的好感。我虽然不去给他买烟,可还是乐于帮他赶赶自行车。周末,他和我姐一出现在廊口,我就把他们的自行车接过来,到村里的稻场上去骑几圈。骑着骑着,我就不那么排斥他了。看来我也是个见利忘义的家伙。
小曲说,别瞧不起他,他也是个有理想的人。总有一天,他要赚个几十万百八万的,到县城里去买房买车。他跟我说,如果他买了车,首先就教会我开。
那天晚上,他还真的像《荔枝蜜》里那样做了个梦。梦见小曲买了车,像个飞碟一样降落在我家院子里。他西装革履,像个外星人一样闪闪发亮地从里面踱了出来。
只是他和我姐一直谈恋爱不结婚,我娘很着急。尤其是,后来他睡到我姐房里去了,娘想阻拦我姐根本不听。她说娘啊,你老封建。娘说,封建有什么不好,封建不吃亏。到了晚上,我姐又像一袋红薯没扎紧。这时我娘就把床板拍得咚咚响,但呵斥的却是我和我哥,她说,你们还不睡觉,就不心疼电么?我娘当然不是觉悟高为国家节约能源。她是想节约袜子里的钱(她怕我和我哥偷她的钱,把钱藏在袜子里,可我敢说,我比她更了解她到底有多少钱)。见我和我哥打夜班做作业,她就烦躁不安,说日里光知道玩。我差点脱口而出:昨天卖鸡蛋不是又卖了几十块钱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姐搞得我们老不能集中精力做作业,我哥这年没考上高中。小曲把他介绍到县里的一家面包店做事去了。
这时,小曲已经参加了县保险公司的招聘考试,他被录用了。就在我娘大骂我姐傻,现在肯定要被小曲甩了时,他笑容满面地出现在门口,说妈,我要和雪桃结婚了。
我娘立即笑得像一张刚烙熟的烧饼。
小曲太急了。如果他慢条斯理一些,说不定任何破绽都不会露出来。
他和我姐结婚后不到半年,我哥就触电死了。我哥住在小曲和我姐租来的房子里。我去过几次,很宽敞。小曲说,等赚了钱,他也可以买这么大的房子。后来我记起来,他当时说的是“他”而不是“他们”。这说明他当时已经下意识地把我姐排除在他未来的幸福生活之外了。本来我哥不想住在那里。他跟我说,别看姐夫硬要我在他那里住,可他这个人还是很小气,看到对门的住户订了牛奶,总是说,牛奶有什么好喝的,味道腥。实际上,他有好几次看到小曲在店里买了牛奶自己喝,然后飞快地把空纸盒扔掉。
我哥死得很蹊跷。那天,他像往常一样用电饭煲煮饭。每天晚上,都是他先煮饭,然后我姐买菜回来了。等饭菜都弄熟了,小曲也下了班。中午他们各自对付。我姐打开门,闻到一股皮肉烧焦的味道,紧接着她看到我哥倒在那里。电饭煲摔在地上,电线还连在墙上。她把手里的东西扔了,惊叫起来。幸亏她懂得一些物理知识,没轻易碰那根电线。她把我哥抱起来。像有一颗炸弹在我哥手里爆炸了,他手心被炸出一个黑洞。过了一会儿,小曲也回来了。我猜想他的脚步很重,把楼道里的感应灯都震亮了。而平时,他的脚步是很轻的。我哥曾经说过,他的脚步轻得像猫一样。小曲似乎早有准备,一点都不慌张。我猜想,在他踏进屋门前,他的手就已经放在手机上了。不用说,他无非是做做样子,什么作用也不会有。我哥就这样被电饭煲电死了。糊涂就糊涂在我姐。她根本没怀疑什么。糊涂就糊涂在我娘,她除了说自己命苦,也根本没怀疑什么。糊涂就糊涂在我,我也根本没有多想。真的,如果不是以后的事情,谁也不会多想。这时我马上要中考,为了不影响我考试,老师还自作聪明地不告诉我,把这个消息一直隐瞒到我考完试。因为我是班里的尖子生,常常凭着一己之力提高全班的平均分,现在眼看着又可以提高升学率。在我们学校里,每一个考上重点高中的学生,可以给每个任课老师带来三十元的奖金。学校把此事告诉了县电视台的记者,于是从校长到班主任到我的任课老师都被宣传了一把。其实,考试那天,我还路过了我姐他们住的地方。我们在县城参加中考。那几天,我们住在学校早就租好的旅社里。似乎整个县城都是我们乡下来的考生。城里的灯火让我很惆怅,我差点就去我姐那里了。但想到小曲那不冷不热的样子,我又打消了念头。事后推算起来,我路过那里时,很可能我哥已经从面包店回到住处,正准备用电饭煲煮饭。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沉浸在自责之中,我想如果我当时去了,说不定我哥就不会出事了。我肯定会发现电饭煲被人做了手脚。我哥读书时物理很不好,他一看电路电流就头疼。我跟他完全相反。物理老师说我以后“很可能为电路事业做贡献”。他的这句话使我有了一个绰号“电路”。由于我个头矮,高个子同学总是摸着我的脑袋说,电路在哪里呢?女同学则挺崇拜地望着我,好像我的脑袋在发光。可我的“电路”脑袋为我带来了什么?首先就把我哥给电死了。这简直是报应啊!
事实上,我的自责并未维持多长时间。因为我姐接着出事了。当然,正如人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在她出事前,小曲先出了事。我哥死后不久,他就买了车。那天,他开着车带着我姐上我家里来。他出息了。几年前,他和我姐还是骑自行车呢。所以他的神态看上去有些得意也有些严肃。现在想来,应该还有些紧张。他开车很有悟性,没几天就运用自如。好像他早已在梦里就学会了。然而等他们吃完饭收拾东西回去,刚开出村口,就跟一辆卡车撞上了。小曲被卡在车里。等大家把他拉出来,他就站不起来。我姐倒是没事。交警来了,责任全在小曲自己。新车报废了,小曲也坐轮椅了。大家说小曲真倒霉。于是我姐每天除了到厂里上班,还要回来照顾小曲。这时我已经在县城读高中了。但我仍很少去他们那里。每次走到他们楼下,我都好像看到我哥站在什么转角的地方,想跟我说话,又说不出来。小曲似乎也不太欢迎我去。有一次,他推门进来,看到我在那里,吓了一跳,似乎转身要逃。我和我姐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说没什么,他担心楼下车门没关好。后来我明白过来了。进入高中后,我个子往上窜,都有我哥那么高了,那天我刚好穿着我哥穿过的一件衣服。我怀疑他刹那间产生了错觉,以为我哥又活过来了。现在他坐了轮椅,更不欢迎我去了。
我跟他说,你既然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怎么就忘了给自己买份保险呢?
他脸色很不自然,支吾半天,才说,是啊,大概就像裁缝,总忘了给自己做衣服吧。
还不到一星期,我姐又出事了。据小曲说,他第二天醒来,发现我姐躺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他报了警。如果我姐一下子死掉了,那小曲真的就成功了。但幸运的是,我姐在警察到来后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吸了一口气。警察把她送到医院。医生找不出我姐的毛病。一位好心的护士发现我姐头发乱,顺便用手摸了一下,这一摸,就摸出问题来了。他们把我姐的头发剃掉后,吓了一跳:我姐的脑袋上有一个孔,孔口还有血迹。他们报告了警察。通过X光检查,他们发现我姐的脑袋里插着一根七厘米长的铁钉。
铁钉是怎么跑到我姐的脑壳里去的呢?警察自然就开始调查小曲的相关资料,这一查不要紧,他们发现小曲瞒着我姐和我哥为他们买了意外伤亡保险单,而且已经在我哥触电死亡后领走了五十多万元的赔偿款,这些,我家里所有人都不知道。但他的车祸是怎么回事?虽然那次车祸也来得蹊跷。他总不会想把自己撞死吧。现在,他已经瘫痪了,又怎么可能把铁钉扎进我姐的脑袋呢?我姐身体健康,个子跟他差不多高,手臂比他还有力。她可以一口气把自行车从楼下搬到楼上。
在这关键时刻,小曲再次表现得沉不住气。或许,他对自己的聪明太自信了,居然没想到警察会暗中监视他。于是,有一次,警察发现坐在轮椅上的他,忽然离开了轮椅,忘乎所以地四处走动起来。
我姐的案子破了,小曲被抓了起来,检察院对其提起公诉。开庭。宣判。没多久,他就被执行死刑了。本来,他想借那次车祸杀死我姐,但阴差阳错的,他自己受伤了,我姐毫发未损。刚开始,他以为自己真的要坐轮椅了,不禁有些灰心,但他很快发现他很幸运,便索性假装下去。他给我姐下了安眠药,等她睡熟了,就拿起他早已准备好的锤子和钉子。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娘在我姐的病床边哭得一塌糊涂。可不管她怎么哭,我姐也没反应。她成了一颗树,一颗必须用很多钱养在医院里的树。
电视台的拍案惊奇节目对此事的报道到此为止。后面的事情却像陡峭的大山一样横在我和我娘面前。我们不知道怎么翻越过去。
我忽然记起小曲给我姐买了保险。我想,既然买了保险,现在找保险公司理赔,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想到这里,我对小曲的恨,小了一点点。我姐受的苦,多少也有了点补偿。有了钱,她就会一天天好起来,重新从一株植物变成动物的。只要她成了动物,哪怕傻一点也不要紧,反正还是我姐,可现在她躺在那里,一点也不像我姐。简直跟一块泡沫一块塑料差不多。小曲的车报废了,他用我哥的命换来的钱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反正他在临死之前任何东西也没给我们。为了交医药费,我娘四处借钱,以致熟人一看到她就远远躲开了,亲戚听说她上门就赶紧从后门溜出去。这时想起保险公司,真让人高兴。就好像在黑暗的隧道里忽然发现一道光。就好像在汪洋大海上抓到一根草。
可保险公司连这根草都不肯给我们。他们说,我姐的保险单是无效的,因为上面的签名是小曲的笔迹。按规定,一定要当事人的亲笔签名,即使别人代签,也要委托书。不然合同无效。
那个人说,小曲的字我一眼认得出来。
我说,那我哥的保单是谁签的名?小曲不是在我哥身上赚了五十多万么?
他说,那个,我不清楚,再说,它和这件事毫无关系。
我说,那我姐不白白吃苦了么?
他说,哎,你姐夫不是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了么?
我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他不是我姐夫!
他对我的愤怒似乎充满了理解和同情,说,是啊,是啊,他配不上哩。
我问我们学校一位懂法律的老师。他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法律专业的文凭,一直想当个律师。但不知怎么回事,一直没去考律师证。他说,保险公司明显是在抵赖,可他们的抵赖是有法律依据受法律保护的。你即使打官司,也打不赢。
我说,小曲买保单的时候,难道他们就没有发现吗?为什么现在倒搬出这个理由来?
他说,最终,法院会认定保单无效,你还是什么也得不到。
我说,可小曲是他们内部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保险公司也是凶手。我难道不能把保险公司也告上法庭吗?
他说,孩子,你的想法不错,但有些事情,就是谁也说不清楚。就好像一个单位的人打了你,如果打错了,他们会说那纯属个人行为,但如果你打了他,他们就可以说你殴打机关工作人员,冲撞政府机关,对吧?
我觉得胸口被堵住。我的眼泪出来了。
老师摸了摸我的头,说,孩子,有些事情靠个人的力量是没办法改变的。好好读书。这段时间我在看《潜伏》,明白了许多道理。你要改变一个东西,得首先打入它内部,不然你只能干着急。我现在很后悔没有去从政。当时我书生意气,可在他们眼里,我渺小得简直不值一提。你要想改变什么,得先掌握一定的权力。
然而我还是辜负了老师。我没能好好读书。坐在课堂上,我看不到黑板,我哥、我姐还有我娘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娘一看到我,就念叨钱。钱。钱。有一次,我忽然吼了起来。然而我自己也被吓住了。我想我怎么能这样呢?可我不这样又怎么办呢?我要发疯了。我恨小曲,没有一下子把我姐杀死。我踢了一脚操场上的小石子,说,你怎么不把她杀死呢?我把它当成了小曲。同时我也意识到,我没叫“我姐”,我用的是“她”。“她”字跟医院里的绷带和石膏之类一样,是冷冰冰的。我感到她离我越来越远了。她的热气正从我的记忆中一点点散去。的确,我每次去医院,总要在门口徘徊好一阵。如果我姐真的是块冰倒好了,那说明还有融化的一天。可她不会融化。她是石膏。是塑料泡沫。不,她还不如塑料泡沫,塑料泡沫也是有温度的。冬天到了,我无意中摸到它,发现它居然很温暖。于是我悄悄拿了一块放在桌子下取暖。
我姐终于死了。我长吁了一口气。我注意到,我娘脸上已经没有了悲伤。她如释重负地干嚎了几声。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她暗中做了什么手脚。有时,她看着那根输液的透明塑料管子发呆。不一会儿,她的手忽然颤抖起来。她肯定是想到了什么罪恶然后可以让我们得到解脱之举。不过即使这样,也应该原谅她。不然,我们家剩下的这两个人也迟早会被累死或逼死。医生宣布,我姐的确已经死亡。脑死亡。医生压抑着兴奋之情。因为再拖下去,他们就要赶我们出门。但这样做,他们又担心舆论压力。这么多人希望我姐死,说明她该死。这样一想,我的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想,以后还是不要这么爱流泪为好。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告诉娘,那就是,我差点跑掉了。如果我姐再晚一点死,我一定会跑掉的。跑得越远越好。所以,她死得很及时。她挽救了我的名声,不让我成为地方新闻的热点或被世人唾骂的对象。
期末考试,我的成绩一团糟。我已经对读书彻底丧失了信心。过年时,家里贴的依旧是大红的门神。姐已经嫁了人,就不是我家里人了,我们没必要为她守什么孝。她的骨灰,还是不得不跟小曲呆在一起,不然她只能成为孤魂野鬼。虽然曲家人并不愿意,然而我们就愿意么?听着别人家在不停地放爆竹,我和娘寒着身子,缩在火炉边。里面烧的是木柴,烟呛得娘不停地咳嗽。我望着鲜艳的门神,又产生了跟先前一样的疑问:那张牙舞爪的门神也好像戴着傩的面具,为什么给人们带来吉祥和安稳的心理保障的门神,面相是那样凶恶呢?按道理,他们应该像菩萨或传说中的帝王将相一样慈眉善目啊!
寒假过后,我没再上学。以往,娘总是催我,现在她也好像忘了这回事。其实,家里过年的肉和辣椒都是舅舅送来的。我不忍看娘故意装做不知道我该报名而局促不安的样子。我说,娘,我不读书了。她的手抖了一下,说,那你准备做什么?要不,跟你舅学手艺去?话一出口,娘意识到自己说急了。我装作没注意。我说,舅那手艺赚不了什么钱,我到外头打工去。
我找到班主任,托他帮我买一张高中毕业证。就这样,我提前从学校“毕业”了。
我先到了一家电子厂。我的“电路”的外号没有白叫,我的知识还真的派上了用场。但我很快明白,我不过是它电路板上一个小小的元件。如果我不另谋出路,迟早会被老板用旧然后随手抛弃。
有一天,跟我住电子厂宿舍上下铺的一个同事来了个老乡。是个女孩。请她吃饭时,同事把我也叫上了。她说她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问我们买不买保险,说很划得来的。我一下子来了劲,说我买一份。同事很高兴,因为他不想买,我买等于给他解了围。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个女孩子,我看了很亲切。到了晚上,我似乎才明白我真正地想干什么。
此后,我背着同事跟他老乡又见过几回。她说她的名字叫孔林,我差点笑了起来。她问我笑什么,我说你怎么取了个男孩子的名字。她说她喜欢这个有点像男孩子的名字。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没说,怕她不高兴。我想说,她的名字让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孔老二。我家墙上,还贴着一张几十年前的报纸,娘说,那是我爹的爹也就是我爷爷贴的,纸已黄透字迹依然清楚,上面有几个黑体大字“批林批孔”。我猜想,一个人的名字跟性格肯定有点关系,要不,她的名字像男孩子怎么性格也像男孩子呢?她简直比男孩子还开朗。她的嘴巴会说。眼睛也会说。有一天,她望着我,忽然说,你干脆到我们公司干得了,我们一起卖保险,好不好?
我说,好。
就这样,我也成了保险公司的一名员工。没想到这么容易。我以为,要千回百折呢。为此我作好了充分准备。可是都没用上。不过是交钱,填表,简单的培训,再交一笔押金,就可以上岗了。买一叠宣传单和保险单,自己到大街上去卖。我不禁有些失落。不过提成(我们称作佣金)挺高,有两三成。我和孔林每天在外面跑。找各种关系,老乡,同学,老乡的同学,同学的老乡,还有亲戚,亲戚的亲戚,亲戚的同学,亲戚的老乡。我惊喜地发现,按这种方法推理,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互相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前景广阔无限。难怪课本上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孔林说,公司里要的就是我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关系越多越好,等你关系用完了,就像螺丝用旧了,他们就要把你踢出去了,即使他们不踢,你自己也要滚出去,不然靠那点基本工资你根本活不下去。新来的每十个人里能留下来的顶多只有两三个。公司里几乎天天都炒人,也天天都在招人。所以我们先卖力地干,尽量多赚点钱然后自己走人。
她自尊心还挺强的。
可我发现,要做到她说的那些,我几乎天天要骗人。我不骗人他们不会买。他们不买我没提成。保单上的文字很动听,不仔细看很难发现里面的陷阱。比如一项理赔条款上说,如果你突发心脏病就如何如何,心脏病后加了个括号,里面写着心肌梗塞。卖的时候,公司教我们突出前面,而真正理赔的时候,他们就在括号里做文章。因为心肌梗塞不过是心脏病的一种嘛。公司还想出种种办法让大家互相嫉妒和竞争。于是我发现我绝对不是孔林的第一个男朋友。她找男朋友大概就像公司招业务员一样,她每换一个男朋友就会给她带来一大批社会关系。等关系用完了就跟他拜拜。所以我不急着把我的社会关系用完,并经常在她面前吹嘘我还有多少同学朋友亲戚。让她以为找到了一眼不停地冒石油的好井。
我没把跳槽的事告诉娘。难道我能说,我也像小曲那样,成了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有一次,我独自跑一个单子。刚上公交,发现旁边有个女人一直在朝我微笑。我有些奇怪,心想我是否在哪里见过她。一般来说,谁会在公交上跟陌生人说话呢?所以在公交上见到的永远是别人冷漠的脸孔。如果你主动跟人家说话,人家一定会认为你是骗子或流氓。不过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不但要习惯别人跟我说话,我还要主动跟别人说话。说不定可以让我多卖出一份保单呢。所以我也朝她笑了笑。她跟我没话找话,刚开始,我以为她神经有问题或有其他什么荒唐的要求。我听说有个富家女孩,吃饱了没事干,全世界找人亲她的嘴,还美其名曰让世界多一点爱。我想,让世界多一点爱也不是这么个多法。她要真的钱多了,可以捐给孤寡老人或失学儿童嘛。
后来我清楚这个女人的意图了,原来,她也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员,她想让我买保险。我们公司业务员太多了,又经常更换,互相不认识很正常。
这时我已经跟孔林同居。我很有信心把我现在的工作干好。我发现,在这方面,孔林其实远远不是我的对手。毕竟,我的大脑里满是“电路”嘛。我的业务在不断扩大。人的社会关系可以创造也可以改道,我不停地跑工厂,跑医院。我经常虚构出各种美妙的神话,说谁谁谁花了两百块钱买份保险,结果每年能报销差不多一万块钱的医药费。再比如,有些人已经有病在身,按道理他们不能投保,而又急于投保,我便帮他们隐瞒病情签下保单,他们还对我感恩戴德呢。孔林着急起来,说,万一客户来理赔怎么办?我笑了笑,说,你以为公司真的不知道啊,他们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客户来理赔,他们一端出条文,客户还是什么也得不到。对此,孔林也不得不佩服我。我猜想,现在她考虑的不是怎么炒掉我,而是怎样才能不被我炒掉。
我的业绩在公司上下越来越显眼。我多次得到口头表扬和各种实质性奖励。白天在外面奔波,到了夜晚,我把自己放在床上,长吁一口气,心想现在好了,不怕别人来害我了。然后像得到了某种保证似的安然睡去。
我又梦见了过年时贴的门神,村里的巫傩面具。我们村里有个人,老是受人欺负,说话都不敢大声。但一唱起傩戏来,就完全像换了个人,声若洪钟,穷凶极恶。他戴着巫面到处追我,喉咙里发出呼啸。
我从梦中惊醒,大汗淋漓。我拧亮台灯,打量着熟睡的孔林,忽然觉得她这时的模样特别的像一个人。像谁呢?我努力挖掘着我的记忆,终于发现:她这时特别地像我姐!
我怅然若失。我已很久没想起我姐了。我甚至都忘了有过这么一个人了。我和她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石膏。她的模样已经完全被石膏吸食掉了。就像恐怖片。有一段时间,一有空我就找地方看恐怖片。录像厅,网吧,老乡的出租房。我看得特别起劲。后来我也拉孔林去看。我喜欢听她的尖叫。
我把孔林抱得紧紧的。第二天一早,她醒来说,她好像在梦里听我叫她姐姐。
〔责任编辑 于晓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