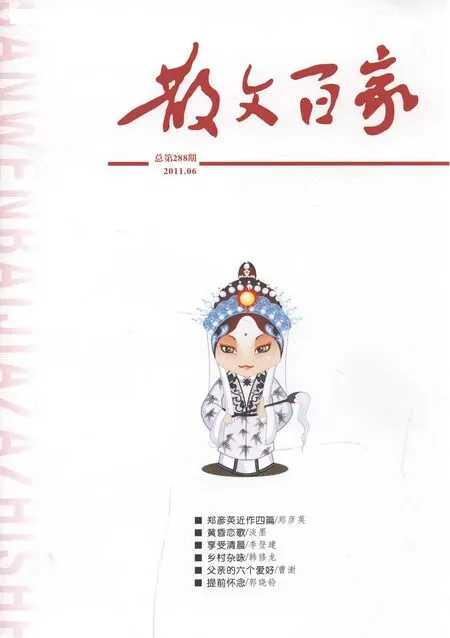舞者
2011-11-21田中美
●田中美
舞者
●田中美
小时候每逢集市,我总能见到那些黑暗中的舞者,他们舞睡了黄昏,舞亮了黎明,舞醒了早起的庄稼人。
上学的路上,我总能看到那些在黑暗中燃烧起来的火光,在集市的一角,天还未破晓,月牙儿还在天上巡逻时,他们便开了工,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但可以看到他们舞动的身影,在无边的黑暗中,只见他们双手抡捶,双臂上下用力地舞动,时而高高扬起铁锤,时而重重地敲打铁砧上的农具。黑暗中他们的影子犹如原始社会的人类在跳舞,舞蹈简单而重复,但却朴实而生动。
打铁的声音划破黎明,响彻小村的上空,缓慢时如舒伯特小夜曲,激昂处似贝多芬的交响乐,这样的曲子只能在乡村的集市才能听得到,犹如说书的,在乡村的集市,他们是最耀眼的明星。
打铁一般由两人或者三人合作,一个负责风箱,剩下的一人或两人负责抡锤,抡锤是力气活,一般人不能胜任。
那时候,我见的最多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有的是力气,男子人高马大,强健有力,女的个子虽矮些,但也很结实,黑暗中,他们配合默契,节奏协调,只有丁丁当当的音乐在夜空中为他们伴奏。火光闪烁中,他们幻化成一副力与美的舞者镜头。
事隔多年,当我再次回到故乡,却发现集市上的铁匠铺少了很多,仅剩下街头的那对夫妇,不过他们都已不再年轻,男的脸上写满沧桑和落魄,女的脸上画着憔悴和忧郁,那是经过岁月打磨后的一种真实。
那天是阴天,当我走到他们打铁的地方时,不自觉地停了下来。女的散漫地拉着风箱,呼呼的火苗欢快地跳跃着,男的将农具放进火中,当锄头等被烧得通红时,男的快速地将其用铁钳夹出,然后放在铁砧上,于是男人和女人便开始轮番敲打起来,一旦开始敲打,女人好像忽然来了劲,她的铁锤比男的要小一些,只见铁锤在她手里,仿佛长了翅膀,虎虎生风,额前的一缕头发随着双臂的摆动而上下起舞,犹如蝶儿在风中翻飞。她的目光中有一种坚定,那种坚定被锤锤击打在铁砧上,溅起星星点点的火花。每当锻打到一定时候,男的便把农具钳入石缸,焌水。农具于是发出“哧哧”的声音,气泡“咕嘟嘟”向上直冒。然后再继续锻打,直到打得农具脱尽了沧桑,焕发出尖锐与光彩。
不出几分钟,一件农具便被锻造成功。两人的脸上虽然挂满了汗珠,但掩映在汗水中的眼里却有了些许的笑意。他们笑着打量着锋利尖锐的农具,仿佛在欣赏一件艺术品。那种朴实而憨厚的笑在火光中是那样生动,犹如农民收获了殷实的庄稼,朴实中不乏骄傲与满足。
农具越来越锋利,他们却一天天老了起来。更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随着现代化农具的出现,来铁匠铺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他们始终坚信打铁的营生不能丢,虽然生意大不如前,虽然体力也已渐渐不支,但他们还是每到集市,便准时来到固定的地点,因为只要还有人需要,他们便不愿放弃这个干了大半辈子的古老行当,因为打铁早已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于是我想到了嵇康,嵇康为人光明磊落,坦荡如镜,他对那些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那些乌烟瘴气,尔虞我诈的官场仕途。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竖子们同流合污。他如痴如醉地追求着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那熊熊燃烧的炉火和刚劲的锤击,不正是这种境界绝妙的生动阐释吗?
与那些为了生活而泯灭人性的人相比,这对铁匠夫妇不也正向我们演绎着简单而真实的生命传奇吗?没有张扬与做作,亦无阿谀与奉承,与其说他们在锻造农具,不如说他们是在用一生来锻造生命,因为每一锤都是意志的定型,每一锤都是力与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