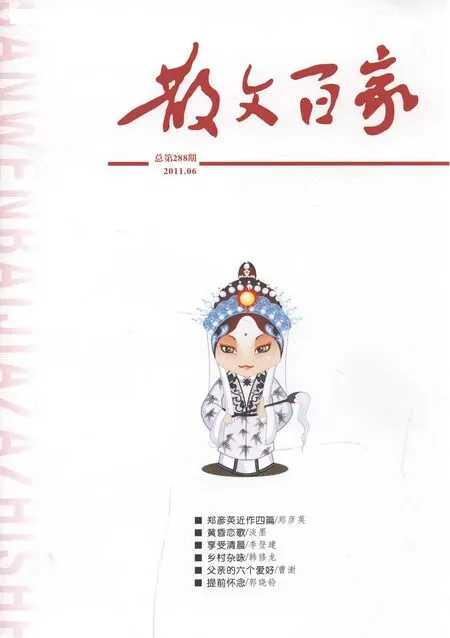“戏迷”父亲
2011-11-21靳天顺
●靳天顺
“戏迷”父亲
●靳天顺
我敢说,父亲如果有一副好嗓子,或者说有一副正常的嗓子,凭父亲对戏曲的执着热爱、凭父亲的聪敏好学、凭父亲惟妙惟肖的表演天赋,父亲一定会成为舞台上一位颇有建树的大腕人物。
但是,“挑担就怕没膀子,唱戏最怕没嗓子”,父亲虽然遍身戏曲细胞,可偏偏就缺了一副好嗓子。因为自小嗜烟如命,常年咳嗽,父亲的嗓子损坏到了几近沙哑,说话远听像山谷滚雷,近听似空屋捶鼓,音传二三里,不知何所云。因此,父亲每每观看戏曲,一旦遭遇了那些唱功、做功不怎么样的拙劣表演,常常顿足捶胸、气恨交加,怒骂其玷污祖宗传统、糟蹋宝贵艺术——愤懑至极点,双目瞪若铜铃,钟馗捉鬼般地怒视着手中的尺长烟袋,咬牙切齿,口吐戏曲韵白:可恨哪可恨!老夫一世朗朗前程,不想却毁在你这宵小贼子之手……
父亲虽然遗憾于舞台表演,但却拉得一手令人称绝的好板胡。
父亲一生为农,一双大手皮糙筋突。但父亲看似粗大、拙笨的手指,一旦触及板胡,即可化变得柔软光滑、灵巧异常。父亲的手指在板胡的丝弦子上按压移挪、上下翻飞,时而如蛟龙出水,时而似凤凰翻翅,一曲曲优美、动听的戏曲曲牌、唱腔过门或如小河流水,或似幽女悲歌,奔腾着、欢叫着、悲戚着、呜咽着在父亲的手指下倾泻而出……此时的父亲,全神贯注,左手把持板胡,右手挥甩弦弓,神态恰似众多舞台和电视荧屏上的艺术家一般,脑袋随着乐曲韵律的疾、缓、张、弛,上下左右有节奏地、剧烈地、夸张地摇摆着。那种幸福、自足和陶醉,完全脱却了一个农民的憨厚、木讷、内敛和谦卑,仿佛自己已经幻化为肋生双翅、身披雷电的鲲鹏,驭驾着美妙的天籁之音,翱翔在蓝天白云、浩渺无际的穹宇之间;也仿佛是长久孕育在土壤深处的种子萌芽,历经艰辛一旦拱破坚实的地表,即刻疯狂地喧嚣、张扬着生命和灵魂……数曲拉罢,颗颗豆大的汗珠,便会布满父亲消瘦、黝黑的脸庞和脖颈,少顷,又化作一道道闪闪作光的蚯蚓,挣扎着、蜿蜒着徐徐淌落,为父亲原本一丝不苟、满脸专注的神色平添些许的生动……
每每曲终人散,父亲便会长长地、缓缓地呼出一口气,然后便如雕塑般地口含烟袋,默不作声,长久地凝望着手中那把漆色油亮、会说会哭的板胡。此刻的父亲,满脸徜徉着的是慈祥、和善与亲切。眼神像两口汩汩喷涌的山泉,流淌的是意犹未尽的回味和与命运进行抗争后获胜的快感。良久,父亲轻轻地拍拍板胡,微微张口,仰头向天,仿佛在默默地唤回板胡远离躯体、依然留恋在音乐天堂的灵魂,也仿佛在倾听飘荡在云端、风头的一缕缕愈来愈远、愈远愈悠扬的乐音的脚步……
父亲虽然钟爱、娴熟板胡,但父亲却将在我们村业余剧团拉“头弦”的位置让给了同姓的一位远房长辈。
长辈是父亲的叔辈,小父亲十余岁,为人忠厚,性情木讷,年近三十,尚未婚娶。长辈每每听到父亲的板胡一响动,就会从隔壁的家中第一时间跑到父亲身旁,举止恭敬,满脸羡慕。这个长辈,庄稼人的春种秋收、二十四节气歌每每记不全,却天生乐感,父亲拉的戏曲曲牌只要听一两遍就能哼唱成调调。父亲有意为之,用了不到半年工夫,竟把长辈培养成了自己的接班人。长辈第一次登台坐在乐队本应属于父亲的位置上,即引来舞台下许多年轻漂亮女人葵花向阳般的注目和窃窃私语……
长辈结婚后,真诚地要把板胡送还给父亲。父亲却拒绝了,对长辈说:你离开了板胡,舞台上就没有了你的位置,生活就缺乏了乐趣。而我则不同,只要愿意,舞台上处处有我的容身之地。
父亲所言不虚。因为情有独钟,处处留心,父亲是我们村剧团公认的多面手,而且还有一个外号“戏偷”。
“戏偷”即偷戏的意思,学名叫做移植。我们乡是个“戏窝”,全乡村村有剧团,男女老少人人会哼哼。肩挑茅粪,臭味熏鼻,嘴里却美滋滋地哼唱着“李世民坐龙位万民称颂”;五黄六月,烈日如火,田间地头你一句我一句地接唱“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农人虽然常年不舍四季亲近土地,但骨子里却向往着读书人的风流倜傥、富贵者的衣食无忧,甚至于居官司者的大权在握、朝廷君臣的治国韬略。这种向往表现在形式上,即是在春节或农闲时节,于村中的古戏楼或村口临时搭建的简易舞台上,几十号有“嗓子”(会唱)、有身段(会表演)的男男女女“粉墨登场”,或扮生旦,或饰净丑,踩踏着“咚咚呛呛”的锣鼓点,伴随着琴笛笙弦的抑扬顿挫,或唱、或念、或做、或打,尽情地演绎着才子佳人的爱恨情仇、演绎着朝廷社稷的金戈铁马、忠奸纷争……一般观众看戏看的是热闹,父亲看戏看的却是门道。哪个村子来了外地剧团演出“生戏”(当地观众没看过的戏),父亲是风雨不误的最忠实观众。只要连看两场演出,父亲就能把一部戏的一应人物、剧情、唱词、唱腔、板式、对白、场景等记得完完全全,一丝不差,然后就在我们村剧团排演,搬上舞台。
有一年正月,一个河南“乱插班”剧团来我们乡演出。说实话,这个剧团的演出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但他们懂得扬长避短、夹缝生存,尽是演出一些“生戏”。父老乡亲天天面对“大米白面”,腻了,当然也想换换口味,尝尝山野菜的滋味。一连两天,观看外地剧团演出的观众人山人海,而其他各村舞台下的观众还没有舞台上的演员多。父亲急了,撇下来我们家走亲戚的舅舅、姑父、姨父一干人等,怀揣一个铅笔头、几页纸,也去看外地剧团演出了。不料,戏唱到一半,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舞台下数千观众除我父亲外,顷刻间作鸟兽散。剧团演戏的规矩是,只要舞台下还有一个观众,你就不能中途停演,否则就要被扣罚演出费。但二三十号演员给一个观众看,毕竟是没面子的事,演员自然提不起精神来,就开始以说代唱、删繁就简,玩起“偷工减料”的把戏,想草草收场。父亲火眼金睛,当即就跳上舞台和剧团团长理论起来。团长先是不屑,认为一个貌不惊人的山区农民,岂能懂得高雅、神圣的艺术,一定是地痞无赖借机生事、找茬闹场。不料唇枪舌剑中,父亲如数家珍,扳着指头从剧情发展、表演程式、唱腔板式、人物着装等,一二三四五,头头是道,把团长和一干演员“教训”得五体投地,佩服不已。团长是个江湖人,也是个虚心人,一看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遇到了“神人”,脸上立马生动起来,当即就搬出十多部父亲从未见过的剧本,又是递烟,又是端茶搬凳子,一口一个“师傅”,求父亲“休嫌我等无知,万望不吝赐教”。父亲受到尊重,得意起来,使出看家本领,认认真真给他们排演了一部戏。晚上一演出,观众好评如潮,赞不绝口。第二天上午,我们村剧团就开始排演父亲“移植”来的剧目,下午就在我村上演了,而且内容、语言、服饰更加符合我们当地观众的欣赏习惯,一下子,吸引各村观众犹如海水涨潮地一浪接一浪,滚滚涌向了我村。一连五天,父亲下午、晚上去看外地剧团演出,并帮助他们排演剧目,提高演出水平,次日上午再指导我村剧团排演新剧目,走马换枪,两不耽误。外地剧团演出结束后,对我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感谢,相识恨晚地走了,而我村剧团的演出剧目也实现了“鸟枪换炮”,全面以旧换新、升级换代。
每年过了正月初八,父亲都会带着我们村剧团前往一山之隔的山西省演出。山西靠近河北一带的农村百姓,酷爱戏曲,正月唱大戏、闹社火是各村百年不变的传统。父亲和剧团在山西走村串乡,如鱼得水,每到一村,受到的款待就像是腰缠巨资回乡投资的华侨一般。这种待遇与荣耀,一直要享受到春种农忙、脱掉冬装换春装,往往,还要把明年的演出预约签订得满满当当。一年之中,父亲最欢乐、最兴奋、最幸福的日子莫过于此,整日笑呵呵的,精神焕发,像是带着一帮兄弟姐妹们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戏曲汇演。锣鼓笙弦奏鸣声中,父亲既是一个总管,又是一个上下前后跑场的杂役,忙碌并痛快着、劳累并幸福着。在父亲眼里,并没有多少文化的兄弟姐妹们,能够在一席之地的舞台上“出将入相”,尽情地放肆着自己的精神,释放着自己对命运的挑战和不屈,袒露着自己遥不可及的心声和愿望,无疑是一个农民毕生最大的成就、最大的辉煌。这种精神层面的丰收,堪比甚至更胜于黄土地上的丰收。这种收获珍藏在心里。慢慢地发酵、慢慢地张扬,势必会成为充实人生的填充剂和人生幸福的润滑剂。
哦,父亲虽然缺了一副好嗓子,没有机会成为舞台上 “唱念做打” 的人物,但父亲并不遗憾,因为父亲不需要凭嗓子演出,父亲是在用心演出,演出的也不仅是戏曲、不仅是艺术、不仅是文化,而是自己丰富多彩、饱满充实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