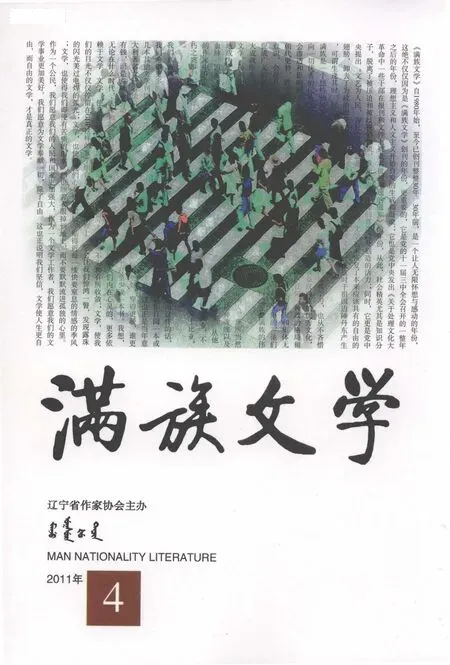由无数碎片缝缀起来的无限河山——解读李轻松及其诗集《无限河山》
2011-11-20
就在这个午夜的零点时分,我开始打开黑暗,让一种光穿进来,穿进我心,连同那些零零散散的诗,或者是李轻松用精神连缀起来的所有语言,蘸着铁一样的黑,我——阅读……
这个世界只有我和我们,以及我们一同穿越或者连接我们并使我们从容穿越的河山碎片,仿佛一块块文明的补丁,由我以及我们,由心灵以及我们的眼睛,或者说由花鸟鱼虫、草木树林,抑或是土砂石山等等连缀了一个唯美的无限河山。那里有我的语言,我们的母语,我们的诗歌,还有对生命的呐喊、探寻、抚摸、痛感,和一些已知的、预知的、未知的、求证的,甚至是无解的大量情结。诗人李轻松说,我们爱生命,爱生活,乃至爱家,爱国。
这是我的寻找。/总是与山水有关/江山大多是黯淡,/风也传情……
——引自李轻松的《琴·山水》
这是生命的世界,与色彩无关,与走向无关,与未来无关。既然出生就预知死亡,那么无论怎么计算,此时只能也只能是从今天开始。
要么是从生命开始,要么从创造生命开始,这一切无疑都选择了河流,选择了山,选择了最初的最初,最混沌的混沌,最原始的原始。不知道何时出现了铁,出现了打铁那个纯粹的生命意象,纷繁错乱,且杂乱无章。果真如此吗?生命沿着起初的孕育,从母体里成长,娩出,然后再破解,长成。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从发展的态势一直延续,直至到色彩开始出现。
于其中,我们可以看见完整的、不完整的、规则的、不规则的碎片和连接碎片的技巧。
从孕育中的成长个体之前,是虚无的,看不见的,触摸不到的,而在被种植之后的具象,没有病,没有杂质,没有隔膜,没有羁绊,指出了人之生命迹象的开始,人从今天孕育成长并长成开始。然而在此之前,在那些阴郁的、黑色的、诗意的情绪中,诗人李轻松制造了山、向阳的坡、麻、葵花地和棉花田,她的医巫闾山,她的河流,还有她未经世事15岁那年的街头。李轻松在无尽的表达中,快意而安然,从死尽之生始,从柳暗之花明,从虚无之实有,她淋漓尽致地抒发着她的情感,书写着种种的神秘开端和件件的真实开始,她与神通观世界,与魔共舞椽笔,可谓是梦魇生花,拈手成诗……
在她运用大量意象的同时,绝不忘记对情感的表述,具象与意象的相互统一,完整地描绘出了她因情绪纠缠的意境以及她创造的语境,在她生活或者是经历的一切影子中,她找到了总是与山水有关的一切因素,然后风也传情……她亮出了自己最原始的盘踞地,也就是她精神的出行地,那里是她曾经放飞记忆和童真憧憬的乐园,当然这也正是她“无限河山”的第一块碎片,或者还有很多……
我懂得那韵律,像熟知我自己的经典/那个抚琴人坐在水边/他的指法因为过于娴熟而衰落/一股腐朽之气吹向我——让我暮气沉沉。/我曾经山高水远……
——引自李轻松的《琴·山水》
隔着这茫茫世界,李轻松以一个诗人的身份,走着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她随时剥离着梦幻与现实,却又沉浸于梦幻和现实。在她所有创作的过程中,重新或者说是再次走进过往的境地绝非她刻意而为,但有些时候,抽身出来则需要她在思考的行走中,做出必要的调整或是及时的停顿,否则她将伤害她自己,从而陷入极端的痛苦。在破茧拔丝的理智梳理中,她的知与性,神与灵,心与虑,都将形成特定的态势,进入新一轮的意识里,并有所节制地探索与飞翔。
李轻松绝对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她剑走偏锋,抒发性灵情感;她又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她直指生存,关照生命。在浪漫与非浪漫,现实与非现实的行走中,她成就了自己特定诗人的属性,她是社会的,自然的,纯粹的,这让读过她作品的人,都能从其看似支离破碎的模糊思路中、忘乎所以的情感体验里,触摸到她的思想温度。
那一片片俯身生活、行走生命、思索人生遍拾的五彩碎片,都在努力地建构着丰富着她的精神家园,并使之尽善尽美,富庶而能担当任何一切。她从入冬以来,一直陷入迷茫,陷入青春时期的惨淡,她努力拔高,长成,甚至疯狂地幻想并追逐她想要的所有,以及她自认为伸手触及的理想,然而现实让她回归开始的起点或者重新启梦的开始。
尽管有着那种挣扎与反抗,或者可以说是能而不惧,但她的力气弱不禁风,她的骨骼挺而不坚,她的身躯高却不能,她不得不选择重新积聚重新积累,于是她拾捡了这个时期所有的梦和碎片,并做重新审视。她开始阅读,从自我开始,从心之内部开始,从梦之痕迹开始,她转过身,由“一只鸟看见一粒米里的天堂”思索,“以虚就虚,以实打实”,因此她找到了结症,找到了“病征”,找到了“生活的悖论”。那些“绕不过的枝蔓”连同“我双手上的宗教”,都让她进入“模糊年代”,她有了放飞的起点,有了积攒力量才能挑战的动力源。这样,她变迁着自己的过往,让“苹果落在地上”,甚至愿意醉酒,甚至品尝“煎鱼”,甚至沉迷于厨房里的“拼盘”和“一道汤”,而恰恰这些,都让她在有意无意中又一次地发现前行的曙光。
与此之中,她的精神碎片开始五颜六色,逐步丰富多彩,她寻觅的幸福已经催促她甩开枷锁和桎梏,去大地上触摸疼痛,她触觉的形成从而坚定了她的本性个性的使然,她要飞,飞出高远。
从此,李轻松练达地走出了这茫茫世界。
一个追寻的人,对古典的琴声抱有成见/一旦琴弦断裂,所有的爱都成了绝唱/……我只是倾听一刻,并从手法上情变/……
——引自李轻松的《琴·山水》
在破译审读的深度中,李轻松作为一个追寻的个体,她发出了沉重的如释重负的呐喊。她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了大地,投向了无限河山。她用她不再稚嫩的后青春嗓音,那种带有金属质地的声音乐律和G调和弦,挑战那些来自体内、来自状态、来自憧憬的自然,抑或是属于生命,属于生存,属于发展的种种痛感。
塞内加说,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李轻松的大视觉意识已然形成,她从自然河山的具象起笔,书写到意象的身体河山,再到无限河山的风雨雷电乃至阴晴圆缺,她钟情近乎于魔幻现实的种种现象和精神感悟,进而抒发出来,并予以深刻的悲悯和怜爱。一个智慧超群的诗人,一个精彩纷呈的诗人,一个兼济天下的诗人,构建了千姿百态,和谐了万紫千红,温暖了芸芸众生。
在抚摸疼痛中,诗人李轻松缘于山水,衔情行走,惯看天南海北,她在沉郁之中找寻自我,在顾盼之间找寻依托,在左右之后找寻灵魂,她说母性的、情人的、浪漫的,种种不一的情愫,不外乎地承载着一个厚重历史与现今文化的对接,连同碎裂。既有“风雨之中的安然”,也有“裂变之后不能容忍的悲伤”。此情此景,尽在内心,也在河山无限。
飘逸的,繁杂的,唯美的,性情的,交错的,立体的,藏而不露;引而不发的,呼之欲出的,无休无尽的,全都纠结成诗,含情而发。由此可说,李轻松不仅是一个大智者,更是一个大勇者。于不惊、不怒、不悲、不喜中,蕴藏波澜;于静态、动势、停顿、行走中,初现惊雷。
悠哉,我高山流水;忧哉,我伯牙子期。动静之中,山水之里,万般风情,无限河山。
大意境,大手笔,皆在起承转合间。
今天我不表达。我只听琴/且看风生水起处,最破败的一笔/或者是最惊艳的一瞥……
——引自李轻松的《琴·山水》
“我只爱自由的风,胜过今生的笑容……”在《无限河山》最后一辑,李轻松更是意象频出,异彩纷呈,她接续俗世神间的种种转瞬,在紧闭和疏放中染指“诗经”“大道”。
在最传统的转合中,李轻松——这个寻觅诗中“大道”的“探索家”,从“琴”开始,从“棋”的视觉,从“书”的内涵,从“画”的风格,破释最伟大的琴音。这种探索,纵情华贵,遣词丰满,入戏和顺,用典超然。矛与盾,雅与俗,是与非,真与假,明与暗,等等,悖论从容。
她的自发意识和自觉思索由弱到强,以悲悯大爱为中心,“我”、“祖母”、“姐姐”、“青衣”、“刀马旦”、“失语者”……在“锣鼓点”喧嚣的戏份里,在矛盾纠葛的生活中,演绎生死、悲欢、离合以及爱恨情仇和幽怨缠绵。一折一折的“江山美人”,一出一出的才子佳人,都不着痕迹,随心生发,于无声处听惊雷……
尽管左右张望,剑有所指,都没有脱离如画河山,“白浪河”、“牛河梁”,甚至是“夹竹桃”、“北普陀”、“积石冢”,不一而足,“都在山上听经”,都在起承解构的瞬间,沉入浮出。仿佛一只最弱小的蚂蚁,仔细地,一粒一粒地,咬开泥土,开辟出、搬运出一条属于自己抑或是宗族才能走上的“阳关大路”。尽管“独木桥”似的“路”幽暗曲折,却也畅通无阻,尽管身后的宫殿极其泥泞潮湿,却也韵雅别致富丽堂皇,那些等待废弃的、曾经的、模式的以及必须打碎的“桎梏传说”,必将成为先锋诗人和前卫探索家的战利品,不论收缴、馈赠抑或丢弃、焚毁,都无伤大雅。而那些辛苦建立的修筑的城堡居所,才是安身立命的家园。犹如“我们身边的仙境”、“街与道”或者“大苇荡”,都将在“箫声一种”的韵脚里,走出男人、女人,甚至还有妖魔鬼怪、眷侣神仙。故事的情节只是江湖中的那些“浅得发白”的“小日子”,在诗人细心经营下,努力地驻守流芳。
夫唯道,善始且善成。所以大道无形,优雅无像。李轻松在最后的章节这样说:“所以,我还在这儿——”她要继续找寻天人合一的、挥洒自如的、没有隔阂的“自家经法”,并沿着疾病和幸福的要义,“一只鸟,一粒米”的哲学,提前进入预定的“东八时区”,一任百鸟朝凤,并且和骨肉相连的祖国一起奠定永恒基业,那应该就是《无限河山》和无限河山的特指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