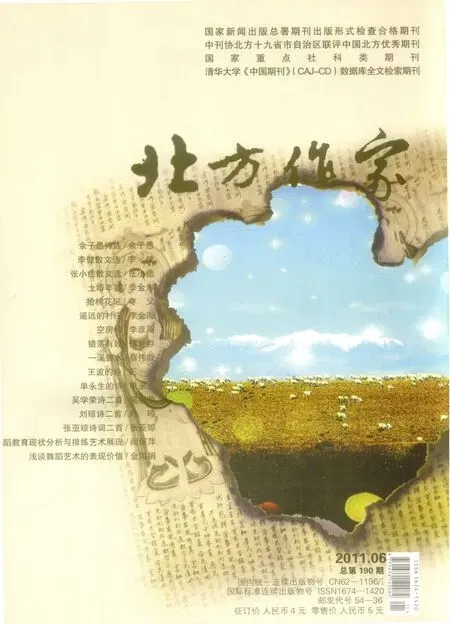李健散文选
2011-11-20李健
李 健
唱土地
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古梅山人信土地神。他们以为吃的是土地,用的也是土地,他们所有的苦难和幸福都是土地所赐。没有土地就没有他们的一切。于是,各村在田地密集的地方,建造土地庙,庙里香火供奉着土地菩萨,庙门上书写对联:“土里生万物,地内产黄金”。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一庙管一方地,保佑那一方平安。出门在外,就有同喝庙里的水之说,就是同乡。
梅山人就像树一样,不择贫瘠肥沃,靠土地喂养。出于对土地的感恩,对土地的敬畏,一到过年,就出来了唱土地的人,正月初一就开始走村串户。他们手持一面铜锣,边敲边唱,“铜锣敲得响绵绵,土地来到贵府前,我看你门庭多紫气,听我来帮你唱几声,祈你富贵高升年年有,年年月月在高升。屋里堆金积玉人吉祥,养个儿子坐中央……”唱者代表的是土地爷爷,是土地爷的使者。土地爷走到哪,就会给那里带来喜庆。唱得味道足了,主家笑容像花一样盛开,打发红包,有的两元,更有那大方的十元,几十元不等。如碰到穷困人家,唱的人也不嫌弃,选取一些激励词语,给人以希望,穷人也来精神,尽其所能打发一些米、糍粑等食物,以示感谢。一般可以唱到十五。也可以碰到路人即时唱。唱词都是即兴脱口,也就是见啥唱啥,而且唱得很流利。
儿时,我也送过“春牛”,唱过土地,并且大胆唱到村外的地方去了。每到过年,一见到唱土地的人来我家,我就来兴趣,千方百计拖延阻挠母亲打发红包的时间,以期能更多的听到一些唱词,学习经验。听得几回,居然就能单独操作了。背着家人,开始挨家挨户唱:铜锣敲得响绵绵,土地来到贵府前,护你人兴财旺万万年,子子孙孙点状元。也有点模样。可是,唱多了人家,我的唱词就缺了变化,有些显拙。大人是见什么唱什么,口齿伶俐,声音宏亮,圆熟,一点也不会打停。唱得活灵活现,看着主家那慰贴劲,我就羡慕,加紧学本事才行啦。
有一回,我单独到屋对门的晏家铺唱土地。晏家铺只居一户人家,单屋独向,与我家隔一座山。那家的屋子是我们村里最大,没有哪一家屋子有他家的屋宽敞。他家人多,土地也多,又勤俭,他家附近所有的荒坡草地均被他们翻过来了,种上庄稼。收入多,也正常。但我想,去他家唱土地,想必红包也大大的,我非常喜欢红包拿来的那种爽味。没想,他家喂了几条黄狗,在周围看守。一见我出现,就朝我呲牙咧嘴汪汪嚎叫。我就怯了胆子,站在不远处和狗们对峙。狗们可能看出了我的怯,一步步往我逼近,我吓得丢了铜锣,往回飞奔。狗们也真欺软怕硬,竟放腿追赶,一直赶过山脚下的小溪,才休停。我就奇怪,那唱土地的大人,为什么就不怕呢。他们回答,他们是土地神附了体的,当然就不怕了。狗也怕土地呢。从此,我再不敢唱土地了。
今年春节,我在母亲家过年,竟又见到了唱土地的人。我就由衷亲切,过去我和他们是同行呢。任何时候,无论时事如何变化,如若你淡漠了土地,土地也会淡漠你。那土地从乡村唱到城里来了。城里人也给唱得满屋欢笑,似乎这也可以给他们带来娱乐,说这传统民俗值得挖掘和保护。唱土地的人却不管这些,你保护也唱,不保护也唱。我行我素。
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远离了土地,却没想和土地还这般亲近,还这般喜欢。我的根在土地上,不论走得再远,也要被一根无形的线牵回这土地上来。因为这土地在,我的力量才在。
爹
至少晚上十二点了,我躺床上读《我的名字叫红》,枕边的手机猛然响起,我给怵了一下。是弟打过来的,说是爹怕不行了,他要求你赶紧回家,担心见不到最后一面。这个时节恐怕搞不到车票,不是说回就能回的。我说要爹接听电话,磨蹭一会,终于听到他老人家含混不清的声音,想来他没戴假牙,不关风。他说这一次怕是大限到了,冲不过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刚才突然跌倒在屋子里,两脚像棉花条子一样,站不起来,你现在回来,你们回来一起商量后事,一点二点三点,在电话里提出他牵心要解决的问题。他老人家思路还蛮清晰的呀,我寻思要死也不是今晚的事,我就把提起的心放落下来,安慰他,没事的,你攒起精神来,现在没车了,我明天清早回来看你。
这时候,我才想起,不知不觉,快两个月没回家了。
接到电话后,我再也无法看书,也无法安眠。第二天天没溅亮,我就坐车往家赶。推开家门,我就见到爹坐在沙发上和妈说话,埋怨责怪的口气,只听他说,这时候了还没见到影子,没用的家伙,亏还学过医,我这点毛病也诊不好,白送他的书……
我装着没听明白,说:爹,你在说哪个啊。
还能说哪个,还不是说你。一见到我,爹脸上就绽放出笑容。
没事啦,你爹是喝多点酒才至站不稳,害你辛苦大老远白跑一趟。妈笑着说。
我说:爹批评得对啊,是应当回家看你们了。
我没带礼物,给了爹票子,教他想吃什么就买,别省。像惯常一样,推辞一阵,他收了。我又要他把手伸出来,把了脉。脉象没见异常,我就彻底放落了心。高兴说:爹,你还活个几年没问题。
问题大呢,反正我感到不行了。爹说他背脊骨断了,肩膀也断了,兴许骨头都露出来了,你看看。爹患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加上风湿,那些痛处变形是真的,断就不可能了。医生要他戒酒戒逗风的菜。我就说医生开的药要吃,至于戒什么就没必要,一大把年纪,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爹常为这个与妈顶撞,听到我的话,他笑逐颜开,对呀,黄土埋上膝了,这不是活活要我的命么。
同时,我向他老人家汇报我的近况,尽捡好的说,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差处和缺点自是隐瞒不报了。这对我是很好的鞭策,对爹的病痛来说,未尝不是一剂治病良药。平时,他手发颤,碗筷都捉不住,一听起我说这些,手竟不见发颤了,瘦竹样的食指还在桌沿上击打起来,挺有节奏感。
爹好久都没下楼了。这么温暖的太阳,他不敢出去晒,只在阳台上坐一坐。有一回,他出去,找不到回家的路,是熟人送回来的。那以后,我写上家里的电话,把纸头放在他口袋里,嘱咐他万一不会回家,就掏出纸头请人打电话。爹,真的像风中的一支残烛,说不定某个时候就突然熄没了。
妈整了菜,有一道钝猪心还特意添加了人参粉。我陪爹喝酒。爹酒量并不大,喝一点就脸红,也没瘾,他只是想把自己喝得晕晕糊糊。这样可缓和风湿疼痛。喝着喝着,想起爹电话里和我说的话,我眼里就生起泪花。
边喝酒爹边做报告,就和他当书记在台桌上做报告一样,听众只有我一个人。他有几个问题:一是死后不做道场,只请人开条路唱唱歌就行;二是他怕死在县城火葬,要搬回老家去住;三是他的工资卡要结算……
爹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早有研究。归结起来关键是火葬和道场。我们老家新化乡下,还没兴火葬,但道场是一定要做的。爹嘴里说不做道场,其实他是想要,虽受党教育一辈子,他担心没道场在那边的世界不好过。我说入乡随俗,别人做多大道场我们就给你做多大道场,你放心。至于去乡下住,妈有点不情愿,要求暂时住县城。别的不讲,买菜都不方便啊。她说她会注意,万一爹真的不行了,她就通知我们,再动身搬乡里住。
通过商量,爹同意了。解决了这些问题,爹放下了包袱。他说一定要珍惜在生之年,争取多看几年太平盛世。
我的小学
我的小学是在一个叫石陇的地方完成的。
石陇叫大队。石陇大队下面分十三个小生产队,后来我们最后那三个小生产队摘出来,成立了农科站。农科站与石陇大队平起平坐。尽管分开了,但仍共用一个学校,就是石陇小学。石陇小学座落在一片略微隆起的茶园之中,单独的一幢二层楼房,长长的,扎在高低不平的山地上,非常醒目。学校全是石陇地方人一块砖一片瓦筹建起来的,对建学校他们很积极,有物出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各有分工,建筑工地真的可以说热火朝天,同心协力,不消一星期,房子就屹立起来了。
当然,我不是第一届。
那时候,我什么地方也没去过,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外婆家。外婆家位于新化县城和冷水江之间,两地均有铁路公路贯穿。冷水江那边多矿藏,经济活跃。外婆家地方人把我们地方叫吉庆山里,石陇属于吉庆,更是山里的山里。山里就是落后、闭塞的代名词。其实,在我眼里,外婆那地方照样有山有田地,连鸡犬叫声也是一样,没多大区别,也就相隔四五十里地,却叫我们山里。我就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先看到火车汽车,而我们那里什么也不产,就产花生和红薯,这就是他们叫山里的理由吧。
石陇地方出过两个稍有名气的人。一个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他带兵打仗是在外面,和石陇不相干,他自愧与人民为敌,解放后流亡在外,无脸回家,客死他乡做了游魂。另一个是黄铺军校的高材生,听说很标致的一个男生,只是不知为什么后来却当了石匠。他给我家砌过阶基、打过碑。我看到时,他浓眉大眼,却是个驼子,走起路来,背弓成直角,十足的驼子,兴许还近视,眼睛几乎低在路面。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如遗有书法作品,定可与当今一些所谓大师有得一比。只可惜没几年就死了,什么也没留下,唯一遗留下来的是他在外面读书谋职时带回石陇落脚的乖态婆娘,倍受满世界的孤寂。那女子生得细皮嫩肉,白白净净,并且终生没破身,真的是要几多乖态就有几多乖态。她说话几里咕噜,无人听得懂,一点也不为交流障碍而产生难过。她照样该吃就吃,该笑就笑,没看到有任何孤寂感和不满情绪。她还抽烟,我们那地方女子是不抽烟的,她在山地出进,自成一种风景。
就这样,我带着这些潆怀的童年记忆进入了石陇小学,开始启蒙。
我们一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姓刘的男老师。
刘老师很年轻,长条脸,是从三角塘那边交流过来的民办教师。第一堂课,我记得他教的是“上中下,人口手。”他说他的拼音学得不是很到位,先将就着,就如草鞋边打边像。我们以为他谦虚,没怎么在意。他教我们学会了好多规矩,比方立正、稍息;比如上课时间不准交头接耳讲小话、做小动作等等。他很负责,管我们特严,他在讲台上摆一条竹片,教授他的文化。上课我就盯着那竹片不放,生怕一不小心挨了竹片。但我终归还是没能躲过。原因是他指责我拼音没读准确。挨了打,我心里很不服,刘老师舌头笨拙,转抵不灵活,天知道他是不是教标准了。我舅舅的女儿我的表妹在他们那边也读一年级,课本一模一样,她读的音与我学到的好像不同。但我不敢提出异议,刘老师毕竟是上头派来的,没有不相信的理由。偶尔遇到一些生僻字,他教我们说不要紧,那就读一边,一般八九不离十。
新化土著人,古就不通王化,说话发音和北方语系本就相左。与人交流,我的塑料普通话常成为朋友们取乐的资本。他们甚至夸大其词说郁达夫是“油豆腐”,玫瑰是“麻蝈”。嘿嘿,有时自己想起也好笑。幸亏不是教师,不然就真的误人子弟。
读到二年级,刘老师换掉了,来的又是一位男老师。我们多么盼望来一名女老师啊。可是,石陇小学一至五年级,全是清一色的男老师。
小时候,我特别爱讲小话,就像麻雀开荤似的。老师常常家访,以此向我父亲告状,每回少不了挨一次打骂,搞得我非常烦恼。老师,一见到他们,就渐渐让我产生恶劣的抵触情绪。可能是那时候我把想说的话都透支了,统统说完了。现在和朋友们在一起,倾听的多,说的少。以至朋友们讲我惜言如金。
后来,发展成逃学。我不想到学校去了,就邀约几个童年好友去那条干枯的小溪捉螃蟹。螃蟹蠢笨,太好捉了。搬开一块石头,螃蟹就藏在下面,它想跑也无处可逃。有一回,正兴头上,朋友把一块石头撬起来,我伸手去石穴里掏螃蟹,没想我捞到螃蟹,手还没来得及退出来,朋友就松手将石头放下,结果把我的食指砸穿,血流满地,回家不敢跟父母说,只好自己到山上弄点草药敷了。至今,我的食指还残留着这些童年记印。
……
不知不觉,我的小学时光,一晃而过。跋涉在人生旅途上,我回想起来,那情景时常在记忆里冒出来,令人嘴嚼,青涩,久远。
清水塘古玩街市
周围全在下雪,只有长沙例外。但冷是格外地冷,冷得我赖在被窝里不想动弹。文键打来电话说别恋窝啦,我请你去一个小巷子里吃早点。我说不想动,还躺一会,我没吃早点的习惯。他却有些执着,那巷子馄饨真好吃呢,快起来,在你门口相会。
那巷子就在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隐在一些商铺后面,容易被忽略,我真还没去过。巷子坐满了食客,的确有点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味道。吃完馄饨,他说反正闲着没事,清水塘古玩街逛逛,老闷在家人都要长霉啦。已经出来了,即便回被窝也没了兴致,我想去就去吧。
清水塘古玩街就在展览馆对面,清水塘路,坐303到展览馆下就到,只三站路程。
溆浦的几位书画爱好者在展览馆展览厅集体搞书画展览,文键说不看白不看,我说这个上午交给你了,随你。文键喜欢书画,在这方面是行家,看着欣赏着,他品评得条条是道,自是有这资格的。我是外行,自然只有看和听的份,但感叹溆浦在艺术上的浓厚氛围。不错,艺术真的在民间,可又有几人真的走出来了呢。
横过马路,走进清水塘古玩街,我心里还在想着这些民间艺术家。工作之余,别人打麻将,声色犬马,他们却躲在寂寞一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管他春夏与秋冬。他们用自己的爱好默默丰富着这个浮躁的社会。
清水塘路,我有时偶尔路过,路边天天停满了各色豪车。他们在这里转悠,大多是来这里淘宝。而我跟文键到这里纯粹是玩,闲逛,没任何目的。
街道两旁,摆满各式各样古旧物品。石头、书籍、瓷器、手镯、刀剑等等,还有一些细碎的钱币之类。书籍中有的发黄,毛了边。我发现毛主席语录书最多,其次就是小人图书,连环画。一些铁器铜器上沾满泥土,像刚出土的样子,仿佛每一件物品都在诉说着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或许是有关战争,或许关乎爱情……说不准真有价值连城的宝物隐藏其中,要不,怎么会吸引这么多全省甚至全国各地客人来呢。我不懂,所以我不认识这些宝物,说不定某时我已与它擦肩而过。文键说见到了宝物,你弃之不顾,那真是大傻瓜。
宝物当然人人喜欢,我也是。但既然是宝物,并不是人人皆可获到的。如果人人得到了也就不成宝物了。我在它们之间穿行、流连,分明感到我喜欢它们古旧的颜色。我轻轻地抚摸它们,和它们对话。它们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古代、现在和将来。它们发出的声音,深奥,充满磁性,是那么的抚慰人心。好像在世间遭遇到的不平和浮浅,一时得到很好的安歇和慰藉。
我心变得愈加安静,不再纷乱。
看来,清水塘古玩街市,我庆幸没有白来。我有一种获到宝物的喜悦。一边也懊悔过去经过这里,却没有深入进去,失之交臂。
这时,文键的朋友打来电话,邀请去芙蓉路新长福那边中饭,我婉拒了。中午,一定不出去应酬,还是回家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吧。在那里,才会找到真正属于我的快乐。
冬天里的靖港
连续几日霜雪天气,御寒的冬装搞得人很雍肿。一下子太阳高照,气温回升到20度。街角有人在放氢气球。氢气球就像一大红灯笼悬在天空,如拧了螺丝钉固定了一样,纹纹不动。朋友说,没风,宜钓鱼。忙碌了几天,也该放松一会了。我不会钓鱼,选择去了靖港。
冬天里的靖港,田里除了干枯的禾根,看不到作物,原野有一种阔大的苍凉,到处是落叶的树梢,河流瘦得不能再瘦。瘦瘦的河流中静静搁着乌逢船,水不多,不流,船只是一个静物,像岸边的树一般静止。到时,红红的太阳好像羞怯的女子,半掩脸面,正顺着靖港的巷子向西边一寸一寸滑落。
街道上只偶尔出现几个游人。靖港正在修葺,张眼望去,两边店铺开门营业的不多。店铺大多是二层高的木板房,古旧。铺面装的全是一扇一扇的木板门,桐油漆就。早晨,老板将门一扇一扇取落,斜码在一边,晚上又把门一扇一扇按顺序装上。装门是有规矩的,门的背面号着一二三四的序号,如把序列弄错,门就合不拢。窗是木格窗,黑黑的,透着神秘的气息。窄窄的街道一路蜿蜒而去,明显地有别于凤凰,别有一番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
晚清青楼建筑“宏泰坊”就座落在街脚,那是古代才子佳人集聚的地方。
漫不经心,我在深深的街巷东游西荡。这个店里有糠油粑粑,那个作坊有现做花片、姜糠,买了边走边吃,高楼大厦之间的重压和沉闷,溜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却是什么也不用想的安适,仿佛我并不是一个旅人,一个过客,而是这深巷中闲散的居民。
我在街坊一个茶铺坐下来,喝豆子芝麻茶,还吃香干。一边用淡淡的眼神逆着时光看古朴的麻石街道。昔日,靖港是繁荣商埠,商贾云集,听说有小汉口之称,曾是人间的天堂。岁月沧桑,古街,古庙,老房,深巷还依然婉在。在安静的时光背面,我仿佛看到了着古装的爷爷,还有爷爷的爷爷。我并没见过他们,但我似清晰地看到了他们的模样。与这里有关又无关。这些让我想起故去的一些事物,追溯到明清或更久远的年代。
暮色四合的时候,我想我应当回家了,抬头望天,月亮已远远地爬上了靖港低矮的古木房上,幽暗的街灯已然亮了起来,让人突然生起某种期待。原来,靖港古镇的神秘和韵味全在这苍茫暮色里。
到南县看荷花
五月的某一天,我去了南县。
南县在八百里洞庭湖的边缘,河渠纵横,湖塘密布,风景独好。起身时还阳光匝地,没想进入南县境地就下起雨。雨是豪雨,齐刷刷的,像树一样在窗外站成一域宽阔的雨林。这个时候,我常喜欢闭目塞听,别人以为是瞌睡多,其实是我内心最精神的时候。我会想一些期待而又难以实现的一些事情,比方爱情,比方别的一些什么。想着想着,那些小人样的心机和嫉妒垃圾一样被水流冲走,不由然就会出现这样一帧画面,朔风吹拂的严冬,雨雪交合,茶馆,空调,一个女子爱情一样光顾。她一身的冰霜,仿佛在冰天雪地独行了一个世纪,但她的美丽笑得像荷花一般灿烂。我不知为什么在这酷热的夏天突然想起严冬季节,可的确是想了。一路想着,心里一路的沉静和清凉。
南县,我是奔着荷花而去的。笔直的大道,河港,树和房屋,还有船……我想像着蓝天、碧水、花海,这些意念组合一起,所形成的图案。“出浴亭亭媚,凌波步步妍”。
小时候读书,每当老师解释纯朴一词,我脑海中就会映出荷花亭立水中“起舞弄清影”的姿势。我就骄傲老师对这词理会没我透彻。荷花生在水中,有的也生在污泥里,但它出生、成长、成熟,在我眼里是最干净的。是世界上最纯洁最朴素的美物。
在我老家,新化吉庆的那个乡村,偶尔,我也看到一塘或一田的荷花。白的,粉的,粉红的,一朵朵鲜艳夺目。我摘一朵插在瓶子里,把叶子戴到头上,将它当成我生活中的一个饰物。
老家是山地,逼仄,南县毕竟是平原水乡,视域开阔,荷花生在那一望无畴的地方,必定如草原和大海一般壮观,那是荷花理想的归宿。
我对南县之行充满期待,料想与荷花不期而遇的场景。万没想到,朋友说你来早了,荷花要七月初才出,光复湖、明山等地的荷花,那个美呀,美得叫人心碎。
大老远跑过来看荷花,竟然没有。失落水一样濯洗着我。大爱无形,既然看不到就在心里存个念想吧,抱残守缺也是一种境界。普希金是个纯粹为爱而活着的人,他在诗中写道:“一切都会过去/而那些过去的/会成为美好的记忆……”
尽管在南县没看到荷花,但我已感到很美。
明天,就进入七月。荷花应出来了吧。荷花啊,我在久远的地方远远看到你,几多俊俏。
在易俗河上宵夜
花石是个小地方,却这么强烈地留下记忆,这是我压根没有想到的。
同学在花石开了一家药材公司,举办盛大的剪彩仪式,那是一定要去看看的。
易俗河像一个妩媚乖态的女人,风韵绰约,在花石扭腰而过。车过花石桥上的时候,我看到桥下不远处泊着几艘船,暮霭中隐约透出灯光,照见船上一溜排开的桌椅。我就想在这么静谧的河上宵夜必定会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当时,听到易俗河的名字,我就有点好奇。从字面上理解,易是容易,俗是世俗,加在一起不就是容易变俗么。是不是说外地来的人,遑论男女,到易俗河打一转就俗了?那这河流岂不成了一只大染缸。无形中,这个俗字好像穿上一层衣裳,衣服下面无端多出一些神秘的东西,让人突然生起期待,一窥究竟的期待。
我们算是迟到。到时,同学的朋友们已在推杯换盏,气氛很是热烈。他的那些朋友大多来自医药领域和文学艺术界,省内省外均有。我们一行在预留的一桌坐下,刚好一桌,很快加入战场。同学过来陪喝,潭州骚客还有美女罗诗人也来相陪,和他们吃喝过多次,见到他们,自是一顿乱侃,长途劳累在酒水中渐渐泡淡,淡到兴奋的勃起。
与同学打浑,我们这么大一支队伍,会把你吃垮。同学不善言辞那是出了名的,他含混不清回答,一时吃不垮。仿佛底气十足。
晚上谈业务的谈业务,逛街的逛街,唱歌的唱歌。我们这一拨子人自是选择唱歌。花石只是一个小镇,歌厅却不逊省城,音响特好。可见花石人是挺会享受。唱至十二点,歌厅要打烊了。镇上人家早熄灯进入梦乡。街道墨黑,鸡肠子一般,两旁高楼建筑现代气派,脚踏在水泥地上的声音清晰可闻。同学安排他公司的人带我们步行,往易俗河上的船舶进发。那感觉就像过去抗日战场上行进敌后的一支小分队,在小巷里穿插,嘴里还意犹末衰哼唱着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
竹垫板铺就的一条匝道将船和岸连接起来。踩在上面吱吱响。船上清一色的红地毯,桌椅安放在应放的位置,看着蛮养眼。河面不时有鱼虾之类的水族活动,它们搅起的波澜在昏黄的灯光下渺远。菜还没上来,大家伙吵嚷着先来冰啤酒。最吵的人数潭州骚客,潭州骚客头发长,现在女人都不蓄这样的长头发了,他坐在我们一堆人中,格外扎眼。我家乡有句俗话:头发长,见识短。他的识见可比他的头发长。人帅,文字也很性情,热烈而忧伤,和我们很对路。
一到花石,就喝酒没停,白酒,啤酒,一通乱喝。其间上了几次厕所,有个女同学说喝酒上厕所证明肾功能好,书上是这么说的。书上既然这么说自是肾功能好了。听到这话,我好像拥有了喝酒的本钱,自是开心,她就是会安抚人。只是喝酒上厕所把裤子拉链弄坏了,很不好意思。我出门喜欢赤条条去,赤条条回,没带备裤。一边喝酒,还必须一边藏着掖着,有些狼狈啊。心里老是寻思着明早买条裤子换了。没想这鸡毛蒜皮的小事竟会左右我的情绪,想盖也盖不了。
心里烦躁,一时听不到易俗河的流水声。可是,宵夜的热闹并不因我的烦躁而有所改变。
夜宵正酣,对虾把我们辣得汗流浃背。忽然听到“哧溜”一声,接着听到鱼的挣扎声。有人钓到了一尾大鱼,大家吵嚷着趁鲜煮了下酒。
我记得在长沙湘江边的船上,同是夏天夜晚,我们也去吃过河鱼。一大盆,均是赤膊上阵,很过瘾。可是,后来长沙禁止在河上经营餐饮,我们就再也没这么尽过兴了。我就犯疑,为什么长沙街头那么多餐馆不禁呢,也有潲水脏物污染环境的啊?为什么河流上有点污染就一棍子打死呢?如果负起责来加强管理,还方便于民,市井喧嚣中拥有这样一份情趣,应不是一件坏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