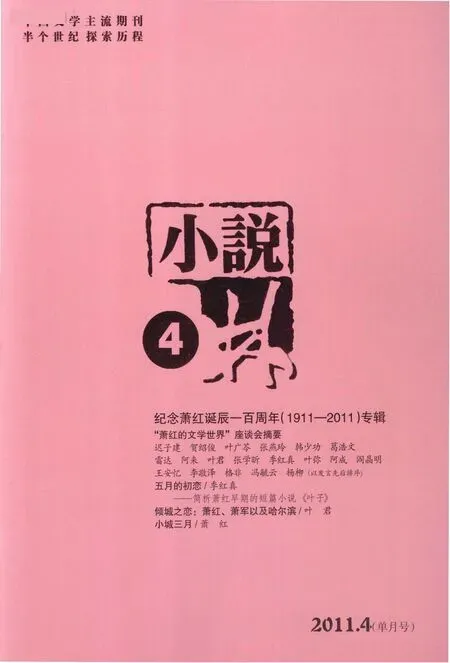老白——太平市逸闻之四
2011-11-20李松樟
■李松樟
老白瞄上她,是在三天前的晚上,十一点多,快半夜了,下着不大不小的雨。
老白没带伞。他也没有伞。他就让雨淋着,不紧不慢地往家走。偶尔遇到路边一棵有些枝叶的树,他就在下边站一下,用手抹一把脸上的雨水。看着有打伞的人从面前走过去,他就想:不知一把伞多少钱,明天要买一把。走着走着,又有一棵树,就又停下,站在树下,再抹一把脸上的雨水。又想:这雨哩哩啦啦下了三天三夜没停。明天要去买一把伞。
老白住在太平市北边的平乐区,离儿童公园很近,就在公园围墙的东边。有时聊天,别人问他家住哪里,他一般不说哪个区哪条街,而是说住儿童公园旁边,人们就知道了。围墙东边的那条路很窄,不是水泥路,是多年的土路,一下雨就坑坑洼洼,泥泞不堪。一边是高人一头的破旧的围墙,随时都会哗地倒下来一片;另一边是高低不等的住宅。有楼,有平房,都是二十年前的建筑。紧临住宅的那条土路,有一条不太宽的人行道,铺着红砖,比路面略高,很多砖都破碎或丢缺了。不下雨的时候,也让人稍不注意就会深一脚浅一脚的。
老白就走在这条深一脚浅一脚的红砖人行道上。
又碰见一棵树。老白本来不想停,前边不远就到家了。等要走过时,他看见树下站着一个人,是一个女人。阴着的天虽不见一丝亮光,但围墙对面的住宅窗子里有灯光照出来。借着这点灯光,他看见,树下站着一个女人。一犹豫,他就停下了。他又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自言自语地说:这雨下的!
说这句话时,他瞄了女人一眼,像是给自己找一个停下来的理由,意思是:我不是为你停下的,是因为雨。他还想传达一个信息给那女人:我不是坏人。我和你一样,也是避雨的。
女人本来背对着他,听见说话,转过身。老白看清了,她不是女人,准确地说,她是个女孩子,二十五六岁左右的模样。雨水把她脸上化的妆搞花了,尤其是那两道黑,是白天描的浓重的眼影流下的,像屋檐流下的脏污的雨水。太平市的女孩和女人都喜欢化浓妆。外地来太平市的人曾经开玩笑说,在太平市,女人的脸上,一年四季总是局部地区有霜冻”。也有人说,在太平市,乍眼一看分不清谁是良家女孩谁是小姐。这话有点刻毒,但仅从脸上的妆彩来说,确实如此。女孩也没带雨伞。她举着两只手遮着头顶,警惕而又略显狼狈地看了老白一眼。老白又说:这雨下的!
雨没有停止的意思。女孩犹豫着,走,还是不走。她不敢像老白那样用手去抹脸,她知道,要是一抹,自己的脸就更花了。
老白也犹豫着,走,还是不走。这时,一辆看不出颜色的轿车从他们面前的泥路上驶过去,一颠一颠的,两只车灯像是醉汉手里晃来晃去的手电筒。积水溅到老白身上。老白骂了一句。他不知泥水是不是也溅到了身边女孩的身上。他就偏了头去看。这一看,老白就看见了女孩的胸,看见了胸脯上那一对饱满坚挺的乳房。
雨水打湿了女孩身上浅灰色的T恤。胸前印有英文字母的T恤被雨水淋湿后,紧紧贴在了女孩身上。淋湿的地方变成了深灰色。女孩也像老白一样,将双手举过头顶,这样的动作,让那对乳房显得更加原形毕露,凸凹有致,异常性感。老白脑袋轰的一声,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虽然,当时天上根本没有闪电,也就没有打雷。这三天里,太平市下的是哑巴哭丧一样的闷雨。
老白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么饱满这么美丽的乳房。他先是觉得脚底生根,走不动了,脖子灌铅,僵死住,扭不过来了。继而,两条腿像感冒发烧四十度,控制不住地抖了起来。他梦一样飘飘悠悠地又说:这,这雨下的!
他觉得自己非要亲手去摸一下不可。不是隔着衣服和乳罩摸,而是要真真切切地摸在那对乳房上。当然,如果不能直接摸在乳房上,那就隔着衣服或乳罩摸一下也行。因为,就在他双腿发抖的那一刻,他心里跳出一个大大的疑问。他心里说:妈的,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在老白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采取行动的时候,对面儿童公园的墙轰地一声塌下来一大片。老白吓了一跳,脖子不由自主地扭过去朝塌墙的地方看。
塌下来的豁口里面,黑森森空荡荡的,露出围墙边几棵稀稀落落的树,枝叶在风雨中发出轻微的哗啦声,给雨夜增加了几分恐怖气氛。只几秒钟时间,老白再转回头,身边的女孩却不见了。老白的头皮就麻了一下,湿淋淋的头发也像通了电一样竖了起来。他揉揉眼睛,又抹了一把脸。淅淅沥沥的雨中,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突然,身后住宅窗子里的灯熄了。天黑得连他自己也看不见了。见鬼了!老白想。一定是鬼,不是鬼不会有那么让人神魂颠倒的乳房。长这么大也没见过,那么勾人!不是鬼,她也不会这么快就消失了,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对了,我刚才也没看见她的模样啊!只有鬼是不让人看清模样的。
……不对。老白又想,我看见了。她不是二十多岁吗?没看见她的模样我怎么知道她有二十多岁?老白拍拍脑袋。看见了,是看见了,因为她的乳房比脸好看,我才顾此失彼了。
塌倒的墙豁子,又有几块砖掉下来。看不见,只听哗啦一声,像一个人跨过时,脚被绊了一下。这时的路上没有任何人影。老白脑子里一个闪念:女孩是从刚塌的豁口跳到儿童公园里去了?这么晚,又下着雨,她到公园里干什么呢?不会。也可能是公园里面有人跳了出来?比如谁家的孩子白天玩得忘了回家,公园关门了,他就沿着围墙转圈,转了无数圈,一边转一边还哭着,正好这面墙就塌了,他就跳出来,像犯人终于逃出监狱。这样的话,那墙就是让孩子哭塌的。孟姜女能哭倒万里长城,小孩子就能哭倒儿童公园的墙。这是老白的想象。其实周围黑的啥都看不见。但这样的想象,在这样的夜晚,这样的时刻,是能够让一个成年人也像一个被关进黑屋子的胆小的孩子一样,吓破胆的。老白慌乱地转身,借着住宅楼犬牙一样交错的黑黢黢的影子,辨别一下方向,磕磕绊绊地往家走,没几步,就一脚踏进泥坑里了。
这是三天前的事。那天晚上老白一夜没睡,在老婆的鼾声里想着那个神秘女孩,想着女孩完美的乳房。想来想去的结果是,那女孩不是鬼,是自己心里有鬼。那对乳房是这世上唯一真实的东西,除了它,再没别的了。少年的时候,他看过很多遍电影《地雷战》,里边有一个情节是:日本鬼子被神出鬼没的地雷炸蒙了,恍惚中,连路边的石头也变成一颗巨大的地雷,而且越变越大。三天前那个无眠的夜晚,老白眼前荡悠着那个女孩浑圆的乳房,而且不断涨大,像汽球一样,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老白使劲闭上眼睛也不能阻止它,他怕听到爆炸时的那一声响,到处跑也避不开它。天亮时老婆叫他一声,他才发现,自己的腿紧张得快抽筋了,拳头也攥麻了,头上的汗把枕头浸湿一大片。
本来,老白早就彻底绝望了。他早就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真的东西。
老白绝望的原因很复杂,和他人生遭遇的三件事情有关。头一件,发生在老白三十四岁那年。那时的老白还没人叫他老白,他叫白文起。一天,被肝癌折磨了两年多,在医院的病床上已经形销骨立气若游丝的父亲,把他叫到跟前,断断续续地告诉他,说,文起呀,我这是要走啦,就是阎王爷不让我走,我也非走不可,我不想遭这份罪了。老白望着爸爸被化疗化没了头发的秃头,和死灰一样痛苦脱相的脸,心里一阵酸楚。他伸手递了一只刚刚削过皮的苹果给爸爸。爸爸摇摇头,说,我啥也吃不动啦。白文起就又把苹果放回到病床旁边的柜子上。削了皮的苹果渐渐地变得和爸爸的脸一样锈黑了。爸爸说,你成人了,也成家了,还有一份工作,比你大弟和二弟都强。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我不是你的亲爸,你妈在和我结婚前,就怀了你,我,我没嫌弃她,也没嫌弃你……
父亲的声音时断时续,时强时弱,白文起听的也不怎么专心,后边这句,让他老半天才反应过来。他以为爸爸不行了,说胡话了,惊慌地站起来,想去叫医生。爸爸抬一下手,示意他坐下。白文起的心快要从闭不拢的嘴里跳出来,掉到地上了。
爸爸咳了一声,接着说:……我把你当成亲儿子。说良心话,你大弟和二弟都是我亲生的,不假,可他们还不如你,知道我快不行了,到现在也不回来。要是早知道这样,我说啥也不会同意他们出去打工……
爸爸的力气快要用尽了,两颗混浊的眼泪从闭着的眼睛里瑟瑟缩缩地溢出来。
白文起想起三年前因车祸去世的妈妈。妈妈从没告诉过他的身世,也许是想有一个适当的时机再说,可没来得及,也许,这是她内心的痛与悔,她不想说。车祸当天,白文起和爸爸赶到现场时,妈妈的脑袋像一只破烂的血葫芦,已经看不出是她了。她把那个痛与悔像秘密一样带走了。
白文起犹豫半晌,声音涩涩地问,那……他是谁?
爸爸仍是闭着眼睛,轻轻地摇摇头。白文起觉得爸爸是不想说,也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就不再问了。他望着面前这个垂死的老实了一生的男人,这个不是爸爸的爸爸,忽然觉得狭窄的病房变得异常空旷,好像他一个人坐在冬天雪后旷野的一块石头上,冷的让他发抖。他感到非常的孤单!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的白文起,不到半个月就花白了头发。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人们都不再叫他的名字了,好像太平市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叫白文起的人,他本来就叫老白。
老白遭遇的第二件事,是去年的一个月末。厂里发完工资,他兴冲冲地到家附近的银行里存钱。填好存单,排队等了一会儿,轮到他了,他把钱从窗口递进去。办理业务的是一个不太熟练的小姑娘。她把钱放进验钞机上,哗啦哗啦一阵响,她又翻过来掉过去地过了两次,然后从十多张百元钞票里摘出两张,隔着玻璃晃了晃,说,这两张是假币。老白说,不可能。这是厂里发的工资,我都没动过,只是把零钱拿出来了,怎么会是假的?小姑娘把验钞机放到窗口跟前,说,不信你自己听。她就把那两张放上去,刚一过,验钞机里一个女人就断然宣布:这张是假币!这张是假币!
老白蒙了。说你这机器不好使,钱肯定是真的。他高声责怪小姑娘业务不熟练。小姑娘委屈地找来主任。主任是男的,拿起钱,很有经验地在手上摸摸,又摇了摇,很客气地和老白说,没错,这两张都是假币!根据有关规定,假币要没收,银行可以给你开具证明。老白急了。说,那不行,我要拿这假钱去找厂里,这可是他们给我发的工资!经理想了想,说好吧,可以给你拿回去。然后,分别在两张假币两面盖上作废的红章。老白从窗口接过那两张被判决的假币,气得白头发都快烧黑了。他想立刻赶回厂里找财务算账,可出了银行才想起,厂里早已经下班了。
这个晚上,也像一年后他在雨夜的路边看见那个女孩,看见那女孩的乳房一样,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老白第一个赶到厂里,在财务室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财务科长、出纳、会计才先后来到。他把两张假币给他们看,要求换成真的,可财务室的三个人,一女两男好像商量好了似的,一齐把枪口对准老白,轮番扫射。
一个说,昨天发工资的时候你为啥不看清了?每个月厂里发工资的钱,好几十万,都是从银行取回来的,成捆成捆的,没人打开过。你是不相信银行,还是不相信我们?
一个说,难道是我们三个把真钱换走了?再说了,全厂八十多个职工,咋没有别人碰到假币,这么多年,偏偏就你老白碰上了?
科长总结说,钱在你手里过夜了,厂里没办法负责。
老白听出了他们的弦外之音。当时有很多人围着看热闹,老白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也不知从何说起。
那两张假币还在看热闹的人们手上传来传去。传着看的同时,有人还不时地把不屑或怀疑的目光落到老白身上。老白觉得那些目光像唾沫一样。最后,老白也不争辩了。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有口难辩,什么叫孤立无援,什么叫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两百元对他来说很重要,但老白当时没想到钱的重要,他只觉得心里无比的委屈。他从看热闹的人们手上夺过那两张假币,跺着脚撕成几半扔在地上,还吐了口唾沫,一句话没说就去上班了。
差不多一个星期,老白没和任何人说话。他看什么都像是假的。吃饭没滋味。这是米吗?他看着碗里的饭发愣。喝酒也不香。这酒也是假的?他抡起酒瓶就往墙上扔,哗啦一声,立刻满屋子的酒气。
第三件事就更奇了。
老白有一个朋友,也是酒友,叫刘天。他和一个女人搞婚外情,其实也不算什么情,顶多就是个勾搭成奸。那女人比刘天大五岁,在街边开了一个小卖部,刘天常去光顾,买酒买烟,一来二去就搭上了。这事儿刘天不瞒老白,每回喝酒的时候,都是他们必说的话题。刘天爱炫耀,总是把他们在一起苟合的细节当下酒菜,说起来眉飞色舞,尤其说到那女人的一对奶子,捏酒盅的手就发颤,眼睛也眯成一条缝,夹了菜的筷子停在半空,常常忘了嘴在什么地方。刘天从不把乳房叫乳房,而是叫奶子。对此,老白纠正过他,说,你就不能说得正经点儿?刘天的理由是,说乳房就没什么感觉,就像说手啊腿啊什么的,可是,要是一说奶子,那就不一样了,心发痒牙发酸,甚至……老白知道他接着要说啥,赶紧打断他。行了行了,我看你是一辈子也断不了奶!臭德性。喝酒!有一次他们两个在路边小饭馆里喝酒,服务员的领口开的有点低,刘天怕直接看让服务员发现,就假装瞄菜单,斜着眼睛看,那副贪婪下作的样子,让老白很觉不齿。服务员走开后,老白糟践他:你哈喇子都淌出来了,像个下三烂。刘天却说,咳,男人都好这口,你就没看?老白一时语塞。心想,是啊,我不是也瞄了好几眼吗?老白赶紧举起茶杯,说喝酒喝酒!刘天反唇相讥,说你都把茶杯当酒杯了,心虚了吧?
说的是后来。那个小卖部的女人还真上心了,非要闹离婚再和刘天结婚。刘天想都没想过。两个人僵持了一段时间,刘天以为没事了,过去了。一天,那女人约刘天到城北的排水河公园见面,谈崩了。女人直接使出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第三招。她说你要是不同意,我就跳河。刘天下意识地看看周围,还好,当时近处没有什么人。他说,你就是跳河我也不同意。那女人毫不含糊,一扭身就冲着坡堤跑下去,到了水边,稍一犹豫还真跳下去了。看着女人顺着污水一起一伏地往下漂,刘天才觉得事情闹大了,鞋也没脱,在岸上追了一段,也纵身跳下去。当他把又哭又叫的女人拖到岸上时,在几个围观者当中正好有一个《太平晚报》记者。这个记者是男的,不是《自绝》里边写寥一兰跳楼的郑艳艳。他问刘天认不认识这个女人。刘天一边喘着粗气,吐着脏水,抖着身子,一边摇头。记者说,那你这是见义勇为呀,我一定要给你写篇报道!后来,那个记者还真写了,还发了刘天坐在水边落汤鸡一样的照片。刘天一夜间成街谈巷议的名人了。这事儿的真相只有老白知道。报纸出来的第二天,刘天请老白喝酒,求老白千万保守秘密。说,老白啊,你替我瞒了这件事,就是喝我血扒我皮砸我骨头,拿我的脑袋就酒喝都行。老白看着他不说话。刘天又说,要不,老白呀,好哥们儿,我请你喝一辈子酒行不?
那天,老白一声不吭地喝了一晚上闷酒。最后他醉了。他替刘天保守了这个秘密,但从此以后,他不再和刘天喝酒,也不再看任何报纸了。他几乎啥都不信了。啥都不信的日子里,老白觉得自己像一只鸟,一只孤单的只知道寻找食物填饱肚子,只知道寻找树枝歇脚瞌睡的鸟,飞在总是不太干净的天上,很自在,但非常无聊,没魂儿了一样。就像……怎么说呢,就像天天吃不放盐的菜,从里到外地寡淡!
一夜没睡的老白,被那神秘女孩的乳房折磨得神魂颠倒。他暗暗地骂自己:我他妈还不如刘天那个混蛋了。可是,当他觉得,这世上还有一样东西是真的,他就又觉得有点欣喜,好像天天不放盐的菜里突然有了咸的味道,那味道很遥远,很不清晰,但他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要亲口去尝一尝,哪怕为此坐牢掉脑袋也值。
从那天开始,老白以守株待兔的方式,每天晚上都在儿童公园那条昏暗的路上徘徊等待。
雨从第二天就不下了。老白也没去买伞,他早就把买伞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塌倒的墙豁子没人管,老白每次经过那里,都停下来往里边看上一会儿,想象着那个女孩会突然从墙里边跳出来。第三天,也是晚上十一点钟左右,老白几乎丧失信心了,疲惫地从街口拐进那条与围墙并行的土路,刚走不远,就看见前边有个女孩的身影。女孩前面不远处影影绰绰还有个人在匆匆地走着。老白紧走几步跟上去。还好,前边那个人很快就拐进左边一条胡同不见了。现在,这条坑坑洼洼、昏暗寂静的路上,只有他和那个女孩了。
老白离女孩越来越近。他感觉得到,她就是三天前的那个女孩。老白似乎闻到了女孩身后飘散的香气。他觉得很熟悉,很舒服,也很陶醉。这香气让他血脉奔流,跃跃欲试。他一刻也不想等了。老白在自己都还没搞明白的时候,就已经饿虎扑食一样地冲上前去,一把将女孩抱进怀里。
女孩本能地惊叫一声。老白压低声音说,不许叫,我有刀!其实,老白身上啥都没有,这也是他的一个本能反应。女孩听说他有刀,就不敢叫了,浑身抖着,开始哭。老白又压低声音说,不许哭,我有刀!女孩就不敢哭了。
老白觉得路上太危险,随时会有人或车过来,四处看看,这里正巧是塌倒的墙豁子对面,是他三天前遇见这女孩的地方。老白挟持着女孩,几乎是连拖带抱地横过马路,从墙豁子跨进儿童公园里边,隐到墙后面,就把女孩按倒在黑暗中的地上了。
围墙挡住了对面房舍透出来的几点昏黄的灯光,像一个天然的屏障。老白觉得安全了。
女孩抽泣着问:大叔,你是要钱吗?我包里有一百多块钱,还有手机,都给你!
老白镇定了一下,说,我不要钱,也不要手机。
女孩还在抽泣,并被老白压着,一口气没喘好,打了一个很响的嗝。老白闻到了从女孩嘴里喷出的酒气。女孩说,大叔,你要是想要我,我包里有安全套,你戴上。
老白一闻到那股酒气,憋了三天的渴望就已经减退了三分。他闷声说,我不戴那玩意儿,戴上硬不起来。我又没病。
女孩见老白没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也没像传说中的歹徒,掏出刀子架到她脖子上,就稍微松弛了些。她不哭了。她说,大叔,我没说你有病。我那是情趣安全套,戴上感觉好,舒服。
老白说,那我也不戴。你别蒙我。
女孩叹息了一声。大叔,那你就不怕我有病?
老白往起抬抬身子。这时,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墙下的黑暗。他看着女孩的脸。你不要叫我大叔。大叔大叔的,我还没那么老。我今天没想干那事儿,我只想摸摸你的乳房。
老白本想也像刘天一样,说我只想摸摸你的奶子,那样说可能更像一个歹徒,更能让对方害怕,但他就是说不出那两个字。
女孩像触了电一样,迅速抽出双手护住前胸。说话又带着哭腔了。大大大叔,不,大哥大哥,你动我全身哪儿都行,就是别动乳房,好不好?求你了大哥!
老白坚决地说,你全身我哪儿都不动,就要动你乳房。我等了你三天,为的就是摸摸你的乳房。说着,老白就去掰女孩的手。女孩用力地护着,咬着牙齿,誓死捍卫的样子,说,我就是不让你动!就是不让你动!
一辆汽车从墙后边的路上驶过。老白用一只手捂住女孩的嘴,怕她喊出声音来。汽车开过去之后,女孩僵直的身子突然就松懈了,护着胸脯的手也无力地滑下去。老白还以为自己太用力,把女孩捂没气了,晕过去了,赶紧把手松开。刚一松手,女孩的哭声就出来了。这回是真哭,哭的悲伤极了。老白有点慌,赶紧说,不许哭,我跟你说过我有刀!我杀了你!
女孩恐惧地尽力压低了声音,边哭边说,大哥呀,别人劫道,不是抢钱就是强奸。你干吗非摸我乳房啊。我跟你做爱还不行吗?你不愿意戴套,你就不戴,我也不怕你有病。我告诉你吧,我是做小姐的,就在太平娱乐城,你知不知道太平娱乐城?就在儿童公园正门斜对面。
老白没回答,但心里说,妈的,我知道,几年前那里是太平市的少年宫。
女孩讨好地咳了一声:你看我问的,大哥是太平市人,当然知道了。我是外地来的,才在那儿干了半个多月。大哥,我侍候你,让你舒服还不行吗?我会。我每天陪客人唱歌喝酒,还上床,我培训过,我啥都会,我侍候你还不行吗大哥!
老白动了恻隐之心。但却有些糊涂。顿了一会儿,他说:我就不明白了。你浑身哪都让我动,为啥就不让我摸摸乳房?难道乳房比你那……那啥还金贵?
女孩带着哭腔说:大哥,我看你也不像是个坏人。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的乳房……是假的。
老白听女孩说乳房是假的,像热身子上被泼了一盆冰凉的水,打个剧烈的激灵。你说啥?你说啥?
女孩说:大哥大哥你别生气,我说的是实话。从前我乳房又扁又小,别说做小姐没客人要,就是走在路上也没人看我一眼。在一起的姐妹给我出主意,让我去隆胸。我吃了好几种药也不顶用,干脆,用这两年进城攒下的两万块钱,还借了一万多,就做了隆胸手术。你要是给我摸坏了,我就干不了这行了,还不上借姐妹们的钱不说,也就不能挣钱给家里寄了。我爸有病瘫在炕上不能动,我妈身子也不好,还有……
不让摸乳房你做小姐,你骗我吧!老白有点被耍弄的感觉。他不高兴了。
女孩说,我不骗你大哥,骗你我不是人大哥。
不让摸乳房你做小姐,你咋做小姐!老白强调着。
女孩说,我只让他们看,不让他们摸。我这是三万多块钱换来的,当然比啥都金贵。实在不行,我就和他们做爱,做爱总比摸乳房好啊,是不是大哥。
别说了!妈的!老白翻身从女孩身上下来,颓丧地坐在地上半天没说话。女孩也不敢说话。公园里漆黑一片,一点声音也没有。女孩听到老白心脏咚咚咚地像敲鼓一样。妈的!老白长出一口气。你他妈毁了我。我今天要是真带了刀子,我就宰了你!说完,老白趔趄着站起来,像醉了酒一样,跨过墙豁子,朝他家相反方向的街口走去。
老白的心里又空又乱。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见路边有一个烤羊肉串的摊子。半夜没人,炭火都快灭了。看不出年纪的摊主正打着哈欠。老白走过去问,有酒吗?摊主一下来了精神,有,有,要白的还是要啤的?老白在塑料凳子上坐下,说,要白的,红星二锅头。
摊主把一瓶红星二锅头递给老白,老白说,要两个!摊主就又从地上的口袋里摸出一瓶,笑着说,真巧,就剩两瓶了。然后他开始拨弄炭火,很快,炭火就燃起来了。当摊主将先烤好的十几只羊肉串递给老白时,老白已经空着嘴喝完了一瓶,正在拧开第二瓶的盖子。
两瓶酒喝完了,羊肉串也吃完了。老白还要酒。摊主说没有了,就这两瓶了。老白口齿不清地问,羊肉,还有酒……是真的吧?摊主赔着笑脸,错不了,大哥,你就放心吧,我天天在这儿,要是假的,你就砸了我的摊子。
老白付了钱,趔趄着站起来,说,酒好,羊肉……也好。摊主把找的零钱塞到老白手里。走出去几步,老白又像想起什么,折回来,拉着摊主的胳膊问,你肯定是……是真的?
摊主看他喝多了,惹不起,也想赶紧收摊回家,又点头又赔笑脸。大哥,咱可不做亏心事。有空你再来,我多给你预备几瓶好酒,你真有量!
老白还是不大相信似的,摇摇头,摆摆手,还用手指了一下摊主,但没说出话来,晃了晃,站稳了,朝前边走去。
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的哪条路,等老白稍微清醒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当年刘天跳河救那个要和他结婚的女人,演出了一场荒唐的英勇救人事迹的排水河边。他闻到了河水臭哄哄的气味。他自言自语着,他妈的,全是假的,全是假的!到底还有啥是真的?啊?妈的,没有,没有!他走上了那座横跨排水河的破旧的水泥桥。后半夜了,河两边的太平市睡得连个呼噜都没有,真是安静啊。
老白在桥栏上靠了一会儿,他想,要是有根烟抽就好了。但是没有。他身上啥都没有。真是扫兴。缓缓流过的河水,在夜色里闪着混浊而灰白的光。突然,老白在河水里看见了他妈的脸,不是活着时候的,而是他在车祸现场看见的那张破碎的血肉模糊的脸。一会儿,那张脸就让河水洗干净了,变得异常苍白。妈妈的脸隐在水波下面,五官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没有任何表情。水往前流走,但那张脸却原地不动,好像留恋着什么,和他对望着,却又像并没有看见他。老白哽咽着说,妈,妈呀,你……你可是我的真妈!你听我说,妈……
老白手脚不大灵便地想要跨过桥栏去和妈妈说话,去抚摸妈妈的脸,但一条腿刚跨过去,失去平衡的身子就倒栽着掉了下去。
一只可能是早起也可能是找不到归巢的夜鸟,从坠下去的老白身边刹然掠过,翅膀刮了老白的衣服。它惊得嘶叫一声,从桥洞下面穿过去,逃向子夜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