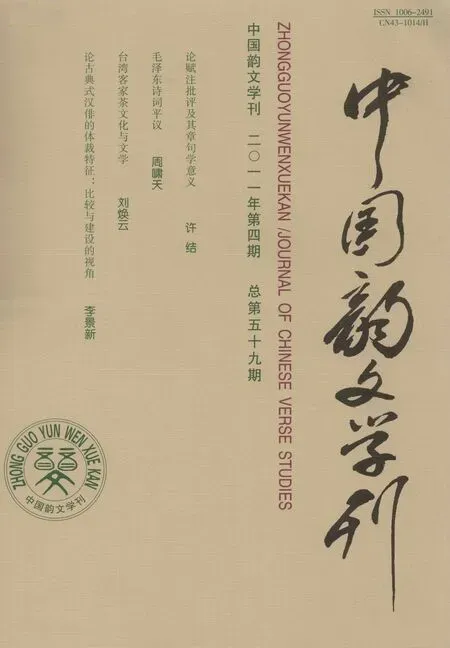摇落深知宋玉悲——新中国文学史宋玉评介简议
2011-11-20毛庆
毛 庆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110)
六十年来,即从1950年至今,作为文学史家,作为文学史文本系统,对宋玉的评介究竟如何?这评介随时代前行有无变化?其中对我们有哪些启示?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反思?这些便是本文想要重点探讨的。
本文选取六本文学史进行对照,这六本文学史为:
游国恩、王起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游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简称“科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简称“刘本”),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版。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简称“袁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①此为第二版。“袁本”第一版为1999年。第二版在第一版基础上作了一点修改,故此处用第二版。该版虽然出了一点问题,如文学史年表中,韩愈为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生,783年(唐德宗建中四年)卒,等于只活了十五岁。但这显系校对、印刷错误,估计是印掉了824年一栏标目。因前韩愈正文明注(768-824),而此处也言韩愈活了五十七岁。总体来说,并不影响该版的学术质量。。
郭预衡主编《中国文学史》(简称“郭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简称“章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关于以上教材版本选取,还需略作说明。“游本”、“科本”、“刘本”,自 1979年后曾先后再版。“游本”、“科本”都只是在技术许可的范围内作过很少的局部的修改,宋玉部分则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故本文仍采用60年代的版本,这样能更准确地反映前三十年的情况。至于“刘本”,1976年出过一本作过大修改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但那是受“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压力所出,许多观点并非出自作者真心,学界亦深知内情,而视此本为废本,刘大杰的代表作仍是1963年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②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9年完整出版,1957年作了修订,学界均言1962年版为第二次修订本。然笔者所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为1963年版。也有学者认为,他的真正的代表作仍是1949年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此处不作讨论。。
如今,各种类别类型的文学史至少几百种,为何独选这六本作为参照?这是因为:
一者这六本文学史均属教材类,教学对象均为大学中文专业本科生,体例、容量相对较为一致,可成统一的参照系。
二者它们均具有普遍性。“游本”、“科本”、“刘本”,20世纪60年代为高校普遍采用教材,“游本”、“科本”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被高校普遍采用。而自20世纪末,“袁本”、“郭本”、“章本”问世后,至今被高校普遍采用——相信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会如此。因而它们具有比其他文学史更为广泛的影响。
三者它们均具有权威性。“游本”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科本”先秦至隋由余冠英主持,唐宋由钱锺书主持,元明清由范宁主持,两本之撰写者都是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研究有年的专家。“袁本”、“郭本”、“章本”之主编者、撰写者也大致与此相类。
对这六本文学史,笔者可说比较熟悉。前三本,因考试或前期研究、教学的需要,笔者曾下过一番功夫;而后三本,曾经——有的至今还在作教材向学生讲授。教学之馀,笔者也常将后三本与前三本作点对照,颇有点不成熟的想法。而对屈原、宋玉,关注当然更是较多。尤其是宋玉,早就认为有的问题该议一议,正好借此会提出来。“杞人之虑”,也许可供方家一哂,而有些具体材料,还可供大家参考。
原拟拙文就硬、软两方面的材料进行分析思考。所谓硬材料,即具体数字、章节变化、刚性断语等;所谓软材料,即观点的改变、重点的迻移,甚至遣词用语的微妙差别等等。由于论文篇幅之限,这里只就硬材料作点粗浅分析。
一
首先就宋玉所占的篇幅作点比较。
“游本”:第94-96页,实际篇幅,二页多。先秦部分:第3-99页(全书1256页)。所占比例为2.08%。
“科本”:第98-102页,实际篇幅,四页多。先秦部分:第3-103页(全书1142页)。所占比例为4.04%。
“刘本”:第125-127页,实际近二页。先秦部分:第3-127页(全书 1345页)。所占比例:1.60%。
“袁本”:第121-122页,实际一页多一点。先秦部分:第21-127页(全书1516页)。所占比例:0.93%。
“郭本”:第157-160页,实际二页多。先秦部分:第1-162页(全书1636页)。所占比例:1.23%。
“章本”:第159-161页,实际近三页。先秦部分:第65-161页(全书 650页)。所占比例:3.09%。
“游本”:17 页,17.5%;“科本”,13 页,12.87%;“刘本”:19 页,15.2%。平均比例:15.19%。
“袁本”:18 页,16.88%;“郭本”:32 页,19.75%;“章本”:23 页,23.71%。平均比例:20.11%。上升比例:24.46%。
以上比例基数,均不按屈原所占章节计算,也就是说刨除了宋玉和其他有关论述所占页码,是屈原实实在在所占页数。假若以章节所占页码计算,那这一数字将更大。宋玉比例下降,屈原比例上升,二者的相对差度达到56.45%,也就是说达一半以上,确实惊人。
再者,庄子、孟子等在前后三本中所占比例几乎没有变化。比如庄子在后三本中只是极轻微地降低,若按降低比例算,只有1%至2%,可以忽略不计。
由此可以说,先秦著名作家中,在文学史上所占比例下降最大的,应是宋玉。
还有一种情况。历史上有的作家相对于本段文学史所占比例并不一定比宋玉高多少,然实际所占页码却比宋玉要多得多。这是因为他所在那段文学史本身所占页码就此先秦要多很多①总的来看,六本文学史中先秦所占比例均略低。而且就笔者所见,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似乎都有这个问题。这可能与20世纪西方某些观念的引进,以及我们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有关。当然这问题此处无法论及。。如唐代李商隐,六本文学史中,他在唐代所占的比例总体略高于宋玉,然实际上所占页码宋玉却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仅以章本为例,李商隐占2.89%(唐代),宋玉为3.09%(先秦),宋玉的比例还略高于李商隐。但实际页码李商隐占近8页,是宋玉的2.6倍,具体阅读效应当然远大于宋玉。如果说,文学史家(在本文中主要指文学史的主编)和文学史撰写者主要是考虑该作家在所属那段文学史中所占比例,那也不尽然。李白、杜甫是仅次于屈原的两位伟大诗人,在前三本文学史中所占页码基本与屈原相等①此是就总体平均而言,具体数字略有差异。如“游本”李白、杜甫各占20页,比屈原的19页多一页。,而在后三本文学史中均比屈原少,以致他们在唐代所占比例远低于屈原在先秦所占比例。这说明,文学史家很注意诗人作家在文学史中所占页码的绝对数字,也就是说很注意他们在整个文学史中所占比例(姑且简称为总比例)。这样一来,宋玉的总比例就比唐代与之大致处于相同层次的诗人作家低很多。
二
下面再观察宋玉在六本文学史中章节安排的情况。
“游本”,先秦共分五章,第五章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楚辞》,该章共六节,第六节《宋玉》。
“科本”,《战国时代文学》下共分四章,第四章为《屈原和其他楚辞作家》;该章共六节,第五节《宋玉》。
3.气滞血淤。睾丸逐渐肿大、坚硬,疼痛轻微,舌暗边有淤斑、苔薄白,脉弦滑。治法:行气活血,散结。方药:橘核、木香、枳实、厚朴、川楝于、桃仁、延胡索各30 g,昆布、海藻各25 g,木通25 g,生地、元参、菊花、蒲公英各35 g,鹿含草30 g。湿热下注,发热恶冷,睾丸肿胀疼痛,质地硬,小便赤涩,大便干,舌红苔黄腻,脉弦滑数。治法:清利湿热,解毒消痈。方药:黄芩、栀子、木通、车前子、泽泻、当回、生地各30 g,柴胡25 g,甘草20 g,龙胆草25 g,金银花、川楝于各30 g。
“刘本”:先秦共分四章,第四章为《屈原与楚辞》;该章共五节,第五节《宋玉》。
“袁本”:先秦共分五章,第五章为《屈原与楚辞》;该章共五节,第五节《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此节下又分四小节,第一小节《宋玉等楚辞作家》。
“郭本”,先秦共分六章,第六章为《“楚辞”与屈原》;该章共四节,第四节《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而在该节中论述宋玉。
“章本”,先秦共分四章,第四章为《屈原与楚辞》;该章共六节,第六节《宋玉等其他楚辞作家》。
可见,就宋玉而言,后三本对于前三本的变化是:在屈原一章中,宋玉丧失了独占一节的地位,而与“其他楚辞作家”共处一节。而在“其他楚辞作家”中,他还是主要的。
接下再看一看宋玉作品的确认。
《招魂》非宋玉所作,已详前节。其馀十二篇(按指《风赋》、《高唐赋》等),除《九辩》外,都是后人所依托,决不可信。
我们认为《文选》中所谓宋玉赋的体制、风格和语言都与楚辞迥异,倒和汉赋相近。这从辞赋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宋玉的时代是很难出现的。而且这五篇赋都作第三者叙述口气,又直称“楚王”、“楚襄王”,明为后人假托之词,不是宋玉自作。综上所述,宋玉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九辩》一篇,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以上两自然段见“游本”第94-95页)
宋玉又从屈原所创造的骚体变化出赋的体裁,写出了《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几篇作品。(“科本”第101页)
《古文苑》成书最晚,其真实性本不可靠。《文选》所载各篇,其中叙事行文,也多有可疑之处,最重要的是那种散文赋体,宋玉时代当难产生……宋玉的作品,最可靠的是《九辩》。(“刘本”第125页)
现在可以基本认定为宋玉所作的,有收入《楚辞》中的《九辩》,收入《昭明文选》中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
后世署名宋玉所作的还有《楚辞》中的《招魂》、《古文苑》中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等,可以基本判定为伪作。(以上两自然段见“袁本”第121页)
但《招魂》应是屈原的作品,而《文选》及《古文苑》所载诸篇,风格、体制不似先秦之作,叙事行文也多可疑之处,学者多认为出于后人依托。真正可信为宋玉所作者,只有《九辩》一篇。(“郭本”第158页)
以上,《招魂》已基本断定为屈原作品;《文选》中另五篇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争议,而且持否定意见者居多,所以我们也存而不论。因此可以具体评述的,又只有《九辩》一篇。(“章本”第159页)
前三本与后三本中,均只有“一本”认为《文选》中的《风赋》等五篇作品确为宋玉所作,其馀四本都认定可信者只有《九辩》一篇。在这一问题上,后三本对于前三本而言,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状态。而若《文选》中《风赋》等五篇作品都不属宋玉,绝对会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三
以上材料,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应该肯定,随着屈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学界对作为“诗祖”的屈原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影响及地位之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和发展,其深广无垠之内涵和深刻卓伟之意义也不断被人们发掘、理解。而作为“国魂”的屈原在我们民族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心理史、精神史上的巨大意义和重要地位,也随着这些领域研究和屈学研究的进展,随着新的内涵和意义的阐释、发现,进一步得到高度肯定。而这些领域的新的肯定,也反过来促进古代文学学者对屈原在文学史上影响和地位等方面更进一步的认识。因此,相对于前三本而言,后三本文学史较大幅度地增加屈原在先秦文学以及在整个文学史上的比重——基本是所有作家诗人中比重增加最多者——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也无疑是正确的。并且,细读后三本文学史,对屈原及其作品意义和作用等的评述,尚有全面深化和拓展的必要——故仍存有以后增加的较大空间。这点此处便不再议及。
然而,对宋玉在文学史的以上方面的变化,却难以用正常与否、正确与否来加以评判,也难以用各时代思潮、趋向不同来解释——它有着较复杂的学术原因,反映出专学研究和文学史撰写互进互动、研究成果被采纳以及专学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宋玉的文学史定位。
六本文学史对宋玉的定位均是:屈原以后的(杰出)楚辞作家。这一定位当然无误。可六本文学史对宋玉都同是这单一定位,这样问题自然就来了。一方面,后三本文学史中屈原的篇幅较大增加,楚辞一章也自然增加篇幅;另一方面,由于“唐革”赋的出土①关于“唐革”赋的作者,有两种意见。李学勤、朱碧莲考定为宋玉作,它是宋玉失传了的《御赋》。谭家健、赵逵夫、刘刚定为唐勒作,称为《唐勒赋》。汤漳平先认为作者为唐勒,后同意李、朱的考定。然不论作者是谁,“唐革”赋的出土,确实引起了学界对其他楚辞作家的注意。由于以上情况为学界熟知,也为节省篇幅,这里一概不注出处。,加之原唐余知古《渚宫旧事》等典籍学界越来越重视,其中也有点唐勒、景差的内容,文学史家和撰写者觉得对宋玉以外的其他楚辞作家还得说几句。而宋玉的楚辞作品又只有《九辩》一篇,这样双向挤压的结果,便是宋玉所占篇幅的压缩。可知,今后若宋玉仍是这样单一的文学史定位,篇幅和所占比例的压缩当是必然趋势——文学史家们只能如此处理。
然而,凡熟悉宋玉作品的,总会为宋玉受到如此“待遇”抱点不平——难道自魏晋以来“屈宋”并称的宋玉在文学史上就只应是这点地位吗?难道宋玉对文学史的贡献就只能占这点篇幅,且这篇幅还该存在被继续压缩的危险吗?相信所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学者又都会觉得不该、不对。可是以上趋势却是实实在在的,几位权威的文学史家在三本重要的文学史教材里都如此处理,就绝非个人兴趣、偏好所致。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笔者以为,首先就出在单一的文学史定位上,并且就出在“单一”上。笔者还以为,有的学者对古人“屈宋”并称的理解,狭隘了一点,片面了一点。他们以为,“屈宋”并称,就是在楚辞、在诗歌领域(在整个文学史领域暂且不论),宋玉是和屈原并肩的,宋玉有着与屈原同等的成就、同等的贡献,因而应有同等的地位。现在宋玉的地位太低了,应予恢复。但这看法确实有偏颇。在楚辞和诗歌领域(在整个文学史领域暂且不论),宋玉是无法与屈原相比的,其成就、贡献也无法与屈原相提并论。不仅不能与屈原,在诗歌领域还无法与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辛弃疾相提并论。在这方面,宋玉的地位是,也只能是:屈原以后的(杰出)楚辞作家。
然而,古人的“屈宋”是一个内涵非常深广的文学史概念,它既含指楚辞、诗歌,也含指韵文甚至整个文章,同时还含有不同文学风格和对称的美学范畴的意义。刘勰的“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辩骚》),其中“枚(皋)贾(谊)”、“马(司马相如)扬(雄)”,均为赋家,足见刘勰所言“词人”,至少应包括诗人及辞赋家。而杜甫的“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屈宋”,既指他们的文学成就,也指其风貌气骨。因而,笔者认为,宋玉在楚辞上的成就和贡献都是极大的,但他更大的成就和贡献是在赋上。屈原是“诗祖”,宋玉可称为“赋祖”。可以说,宋玉对赋的贡献和影响,不亚于屈原。而在赋作之经典性及示范意义上,还要大于屈原。然而如此议及,问题就来了:屈原称“诗祖”是毫无争议的,若将宋玉称“赋祖”,则必涉及一些复杂的学术问题。
首先是汉赋的继承对象。一般认为,汉赋继承对象有三个。一为屈原骚体赋,二为荀子四言为主之赋,三为宋玉散韵相间之赋:三来源宋玉只占其一。而且,这三来源对汉赋的影响究竟是并列的,还是有主有次的?如果有主次(就艺术规律而论,一般应有主次之分),谁为主?谁为次?诸如此类问题,都是应该认真深入探讨的。但探讨这一问题,必先涉及有关文体的争论。
这即是辞赋是否同源,早期是否同体等问题。在古人的理解中,尤其是汉至魏晋至唐人的理解中,早期辞赋是同源同体的。所以屈原的作品,既可称屈骚,也可称屈赋。屈原又是楚辞体的创始人,他的作品当然也称屈子辞,现在更简称屈辞。这种称谓一直延续至今。但辞与赋毕竟有区别,这一区别汉以后即开始受到重视。现在更有一批学者主张辞、赋不同源①如费振刚,他在多个学术场合和多篇论文中均提出这一观点。如其《汉赋概说》,《广西大学梧州分校学报》2002年第2期,等等。,并认定汉时就已开始注意这一问题,且举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为例:“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唐勒、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句中“辞”与“赋”对举,说明他已注意到辞与赋之差别。然这一观点也遇到问题,因就在《屈原列传》中有“乃作《怀沙》之赋”句,证明司马迁认为《怀沙》是赋。而《怀沙》当然又属楚辞。不过这一矛盾似乎也还可以作出较合理的解释。由于笔者对此没有研究,不敢妄言。只是因长期研究楚辞艺术缘故,总感觉这确实值得研究,是一个很有学术意义的命题,不属于死钻牛角尖。而且,笔者还感到,似乎赋之研究者更愿意把对汉赋的主要影响归于屈原,自然宋玉对汉赋影响就放到次一等的地位了。而宋玉往下一退,又遇到另一位比较对象。
这位对象就是荀子。宋玉赋与荀子赋若从艺术上比较,究竟如何?对汉赋之影响究竟谁更大一些?依笔者有限的见闻,这方面研究得似乎较少。而荀子是古代以“赋”名篇的第一人,历来被视为赋体的始祖之一,至今还留有五篇赋作,赋的研究者对此评价不低。笔者对此也无研究,不能多言。只是感觉《文选》不选荀子之赋,必有其道理。
以上问题,笔者以为都是宋玉研究必须着力探讨、分析并努力解决的。或许,随着这些研究的进展,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所占篇幅会有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应仍是在“屈原以后之楚辞作家”这节中,而应是在赋的部分。也就是说,对宋玉的成就可分两处评述之。此做法并非标新立异,就在六本文学史中,“游本”、“袁本”、“章本”对柳宗元就是如此处理的。“游本”在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之第八章《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以《柳宗元的散文》作为第三节;又在第九章《中唐其他诗人》,将《刘禹锡、柳宗元》作第三节。“袁本”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之第六章《韩孟诗派与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以《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诗歌风貌》作第四节;又在第八章《散文文体文风改革》,将《韩愈、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作第三节。“章本”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之第三章《杜甫与中唐诗歌》,以《刘禹锡 柳宗元》作第五节;又在第四章《古文运动》,将《柳宗元与古文运动》作第三节。三本文学史都是将柳宗元的诗与文分开评述,且均无重复、累赘之嫌。同理,宋玉之辞(《九辩》)与赋(《风赋》等),也完全可以这样处理,不过处理起来比柳宗元要麻烦一点——需要跨朝代:楚辞在先秦评述,赋多在汉代评述。然而这仍是可行的。之所以六本文学史均未如此作,恐怕主要不是技术上的原因而是宋玉赋作的确认。
第二个问题:宋玉著作篇目的确认。
众所周知,今存宋玉作品,主要来自三部典籍:《九辩》来自王逸《楚辞章句》,《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来自《文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来自《古文苑》。前已叙述过,对这些作品之著作权,六本文学史均是区别对待的。《古文苑》的六篇,全都否定;《楚辞章句》的《九辩》,全都肯定;《文选》的五篇,“科本”、“袁本”肯定,“游本”、“刘本”否定,“郭本”、“章本”存疑——还是怀疑者居多。这样,尽管“游本”、“袁本”肯定这五篇作品,也不能不考虑学术界对此的存疑之风。因而敢于放手评述介绍的,也就只有《九辩》一篇——这叫文学史家如何另辟条目评介。
只是,后三本文学史编撰出版之时和此前几年,也正是宋玉研究较前代大有进展并取得显著成绩之时。由于银雀山汉墓“唐革”赋的出土,那种“宋玉时代不可能产生那样的散体赋”之观点彻底倒台,一批学者,如李学勤、谭家健、汤漳平、朱碧莲等,发表了肯定宋玉赋作的一批文章。专著则有袁梅《宋玉辞赋今读》、朱碧莲《宋玉辞赋译解》、金荣权《宋玉辞赋笺评》等②袁著为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朱著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金著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时间均在后三本之前。另,高秋凤《宋玉作品真伪考》于1999年出版(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吴广平《宋玉集》于2001年出版(长沙,岳麓书社),吴广平《宋玉研究》于2004年出版(长沙,岳麓书社),刘刚《宋玉辞赋考论》于2006年出版(沈阳,辽海出版社),时间虽晚于后三本,但后三本均有再版,它们再版时应可作参考。,但这些成果似乎对后三本文学史宋玉之撰写影响不大。
不能认为,后三本的文学史家,尤其是具体撰写者未注意到这些成果,这不合常理。文学史教材所以要经常修订,甚至重写,就是要吸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跟上学术的发展。后三本文学史撰写者,在具体动手撰写前,必广泛搜集资料,对最新学术成果必特加注意。何况,以上论文大多发表在重要学术刊物上①如:谭家健《〈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发表于《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汤漳平《宋玉作品真伪辨》,发表于《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都是撰写者必然会注意到的。
由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宋玉作品考证的成果,尚未能达到足以使文学史家及撰写者改变以前学界主要观点的程度。在这点上,专学研究者与文学史家是有区别的。专学研究者考订某一作家的作品,一般不会去考虑其他作家作品的真伪如何。比如说,考订宋玉作品之真伪,不会去考虑庄子、墨子作品之真伪如何,更不会去考虑魏晋人、唐人作品之真伪如何。文学史家则不同,他在考虑某一作家作品之真伪时,就是必须考虑其他作家作品之真伪。比如若考虑宋玉作品之真伪,就是要考虑庄子、墨子以至魏晋人、唐人,甚至明人、清人作品之真伪。文学史上考订、辨伪的事太多了,他必须作通盘考虑,必须就此与撰写者商定一个大致通用的标准,然后统一施行。估计按照这一标准,有的撰写者认为还是维持学界原议为好。
那么,这一标准、准则究竟如何?估计会因不同的文学史版本而有区别,细则也不得其详。但同类别之文学史面对同一作家作品的处理通则,当有共同部分。笔者观察,前三本中,“游本”、“刘本”主要依据怀疑否定之理由,即“战国时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散体赋”、“称谓、口气多有可疑”等;而后三本中,“郭本”、“章本”则主要依据争议双方数量之多寡——标准明显有了变化。然这一数量多寡并没有较完善统一的统计。很有趣的是,谭家健在《〈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文中曰:“50年代以后,不断有人提出反驳,其中以胡念贻《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一文辨正最力。目前多数人已相信是真的,少数人仍存疑。”②按:胡念贻《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发表于《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胡念贻考定《文选》所选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确为宋玉所作,而《对楚王问》为后人伪托。但是,前面所引“郭本”、“章本”,明言对《文选》中宋玉的五篇作品,多数学者仍取怀疑、否定态度。并且,谭文所言“目前”,是“唐革”赋未出土以前;“郭本”、“章本”所指时间,是在“唐革”赋出土以后。当然两方面可能都有所据,不过结论却是完全相反。
这就需要学术团体出来做调查工作了(没有学术团体,学术会议组织者也行)。可以拟定几条标准,面对面或通过书面形式向有关学者调查,由此可得到较准确的数字,切实地解决多数人赞成还是否定的问题。
也许有学者会提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学术争论不能以人数之多寡来判别。这当然是对的。不过这里是讨论文学史的编撰问题,而且是教材类文学史的编撰问题。教材类文学史不同于专著类文学史。专著类文学史尽可以发表你本人的观点,骋其一家之言。教材类文学史却主要考虑稳妥,对最新学术成果的反映要注意客观全面,必须要考虑学术界的意见,这样一来,对那些久论不休、争而未决的问题,采取以上态度还是合适的。
笔者从来不怀疑《文选》所录宋玉五篇作品的真实性。因笔者认定,我们对本民族留传下来的宝贵文化古籍,应有一基本原则。即对传世的古籍,尤其是传世的可信的典籍,其所载内容,非有铁证,不可轻易怀疑,更不可轻易否定。仅据留存至今的一点极有限极少的先秦两汉文章,就断定战国时期不可能产生宋玉赋那样的散体赋,这是极其危险的做法,本身就违背考据原则。这正是那种以点统面、以小否大、以上位概念反疑下位概念的疑古思潮泛滥时期的做法,其思维方法显然是错误的,逻辑上也说不通,文化态度更不在这儿评判。他们那些“大胆的结论”一个一个被20世纪以来的考古材料所推翻,是理所当然的事。果然,“唐革”赋的出土,就把“战国时期不可能产生宋玉赋那样的散体赋”的论点击了个粉碎。
第三个问题:宋玉辞、赋的艺术特色。
笔者认为,近二、三十年来宋玉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无论是其作品真伪之考订,作品文句之注释,还是篇章内容之阐解,内涵意义之阐发,都较以前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有一方面显得很不足,即是宋玉辞、赋的艺术研究。毕竟,宋玉辞、赋是文学作品,它在文学方面的特点、特色、影响以及文学、文化意义等,都是需要着力探讨的。近年来这方面也发表了一点论文,然而总的看来,研究方法、方式、理论有点滞后,文学眼光与艺术感悟有点停滞迟钝,相较于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几个方面,显得太弱。六本文学史中后三本的反映,也多少说明了这点。
就研究的具体问题而言,宋玉辞、赋究竟有那些独到的艺术特色?《九辩》与其赋之间有何联系又有何区别?《九辩》与屈骚又有何联系与区别?宋玉之赋对后世究竟有何影响?宋玉之赋与荀子之赋对后世影响有何不同?宋玉能称“赋祖”吗?由屈原倡发又由宋玉完成的“悲秋”母题,在文学中的承继一直由古至今,那么对中华文化的心理影响呢?凡此种种,我们都有所涉及又均嫌不够深入。
即以“屈宋”并称为例。前已叙及,在古代应是一内涵深广的概念。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文学成就上的二人并肩同等,而是文学风貌和审美范畴上的互映互衬、互美互补。若以拟人概括二人之文学风貌,则屈骚为伟男,宋赋为美女;若以传统美学范畴概括之,则屈骚为阳刚,宋赋为阴柔,二者共同组成完美的审美观念,代表了南方文化的美的特质。笔者早有感于此,又因不专研中国古代美学,便从文学风貌和创作心理入手,发表了拙文《论宋玉辞赋的女性美及其创作心态》(《山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文中明确提出了上述观点。近年来,好几位著名美学家提出楚骚美学为先秦美学之一大派,有的并进而提出儒、道、骚、禅为中国美学之四大支柱,但也有著名学者反对①提出以上观点者如李泽厚、刘纲纪等,可参见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先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反对者如敏泽,可参见《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卷第四章《中国美学思想体系的形成》,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然不论肯定者还是反对者,均对宋玉的这一美学作用及意义注意不够。而笔者认定,若没有宋赋之阴柔只有屈骚之阳刚,楚骚美学必然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屈宋”并称在这里显示了极其重要的美学意义。
笔者原计划对宋玉辞、赋艺术特色作点系统研究,以上拙文只是其中一篇,但总觉精力无法顾及,故一直停顿至今。作为楚辞学者,研究宋玉责无旁贷,上述材料及分析,既是提供给学界同仁参考,更是一种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