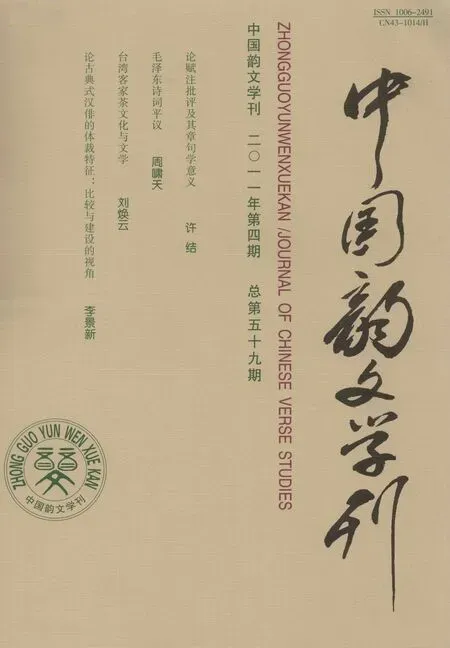柔金软玉、吹气如兰——彭孙遹词与词论
2011-11-20李有强
李有强
(上海体育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438)
彭孙遹,字骏孙,号羨门,又号金粟山人,浙江海盐人。彭孙遹,才情富瞻,工词章,《清诗纪事初编》还称赞他“各体皆备,世独赏其香奁艳体”,《清稗类钞》称其“才富学赡,王阮亭、朱竹垞皆自叹不如”。彭孙遹与王士禛齐名,号“彭王”,存诗1500首,著有《延露词》、《金粟词话》等。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四年(1660-1665),王士禛赴扬州任推官一职,凭藉诗余之地的文脉传承,加之王士禛本人的才能和领袖气质,广陵得以团聚一大批优秀的词人,成为清初最为重要的词学活动中心,史称“广陵词坛”。虽然“日了公事,夜接词人”,“之数载广陵,实为斯道总持”的王士禛[1](P128),“江南北词学交流的重要人物”[2](P65)的邹祗谟发起并主要承担了当代词选《倚声初集》的编辑工作,但邹、王二人的创作实践与其理论主张始终有较大差异。相比较而言,彭孙遹的词与词论,贯彻并发展了邹、王二人力图倡导的理论主张,是广陵词坛词学理论与实践的杰出代表。
一 艳情与雅正
在邹祗谟、王士禛二人的词论著作中,词之“尊体”是突出强调的问题。不过在为小词寻找一个合适的文体地位时,如何处理其中占较大比重的“艳情词”便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邹、王二人不约而同地从古诗、乐府的爱情作品中寻找其远祖,并试图在二者之间建立合理的联系,进而确立艳词是其苗裔的传承关系。王士禛云:“诗余者,古诗之苗裔也。”邹祗谟云:“诗之为体,肇于风”[3]。而这样的论述,本身便透露出对词体独立性的不自信。彭孙遹在《金粟词话》第十则中颇有气度地“就词论词”,指出词之为体,“艳丽”乃其本色,这是词体特性的必然要求。虽然处在词学理论发展初期阶段的彭孙遹,没能精微地提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4](P44)的体式特点,但也没有生硬将这种本质特性强拉到诗之言情传统上。这其实已经在词之“尊体”上较邹、王二人更进了一步。因此,当大家还在为《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一首词是否出自“冰心铁骨”的司马温公之手而喋喋不休的时候,彭孙遹却能跳到局外,从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指出“真赝要可不论也”。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上,彭孙遹不排斥艳情词。但在主张艳词本色的同时,彭氏也立主雅正之说,这就是避免了因过分强调情的因素而使得词作浅俗。彭孙遹在《旷庵词序》中说:
或谓语涉言情,不嫌刻画,审尔,则色飞魂艳之句,将不得擅美于词场耶?不知填词之道以雅正为宗,不以冶淫为诲。譬犹声之有雅正,色之有尹邢,雅俗顿殊,天人自别,政非徒于闺襜巾帼之余,一味儇俏无赖,遂窃窃光草阑苓之目也。昔扬子云尝有言矣,曰“诗人之赋丽以则。”
这段话的一开始便抛出一个问题:既然你强调词的言情作用,果真如此的话,那些写艳情而“色飞魂绝”的词作是不是就不得“擅美”词场了?这实际上指出那些等而下之的“艳情词”的弊病,而元明以来学艳词而入元曲一派者皆病于此。面对这样的问题,彭氏这里又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观点。他指出词之一道当以雅正为正宗。他借用西汉扬雄在《法言·吾子》中的论赋的观点:“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强调艳情之作要有节制,否则便会入于淫亵。
在彭孙遹的作品中,艳词占其中绝大多数,这些艳词非常讲求情景关系的处理。既有“前段写景,后段言情,洵词家射雕手”的《解语花·题美人卷子》“湘裾漏月”,更有融情于景,景中含情的“吹气如兰”的《浣溪纱·踏青》:“翠浪生纹涨曲池”。但在彭孙遹的创作实践中之所以能够将如此高比例的艳情词写得艳丽而不失雅正,不光是其技法上刻意追求而成,更和他词中情感生发的具体指向有关。广陵词坛三位核心人物中,王士禛写艳情词往往是无中生有,凭借想象来创作。邹祗谟的艳情词则主要是怀念自己一段无果而终的感情,这段感情的指向是一个歌伎身份的吴姓女子。彭孙遹艳情词的感情则指向自己的原配妻子朱氏。这样的作品因为受着伦理纲常的约束,就必然要求情感表达的节制性,因此即使是拟女性的口吻,也不能写出柳永词中“针线闲拈伴伊坐”的句子。关于彭孙遹其人,很多词话中都记载他终身没有侧室。如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国朝彭羡门孙遹《延露词》吐属香艳,多涉闺襜,与夫人伉俪圻笃,生平无姬妾,词固不可概人也。”当然,这种情况可能有些夸张①《国朝名家诗余》本《延露词》中《鹧鸪天·偶赠》“上社桥头斗彩千”一首后湘尹评语云:“此羡门赠冯容作也,名士倾城,故当不愧。”这里的冯容很可能是一个与彭孙遹交好的歌伎。,不过相对而言,彭孙遹在对待感情上是更加专一,能够做到从一而终的。从他晚年所作的诗歌作品,我们可以窥见他对妻子的感情,如《昨夕竟夜不寐,五更末始略合眼,忽梦南还已到家。才入门,即见朱夫人已坐重庆楼下,西房中见余至,起而相迎,笑谓余曰:君来何暮,我洒扫庭宇待君久矣。余因同坐,相与絮语。语多不可记,但觉朱夫人笑言如平日。而已觉后,枕上忽忽不乐,口占一绝》:“舟中日日数归程,晨夕相偎恍若生。何事到家偏先我,芳魂应是御风行”[5](卷三十)。又如《即事》:“抚棺一酹不胜悲,酒冽泉甘此一巵。君定有知能忆否,少年情事拔钗时。”此首前有小序云:“遣童奴往惠山买新酒酌奠朱淑人,淑人生平不能多饮,而酷爱锡酒,以其甘美也。今过此,适山家春酒初熟,追念死者不胜酸痛”[5](卷三十)。这两首诗作中表现出的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原本不必多做解释,仅从诗题和诗序中每个沉甸甸的字眼中便可清晰地感受得到,这是一种别样的掷地有声。
彭孙遹《延露词》主要创作于京城应试及吴楚飘零时期,多描写夫妻聚少离多的相思之苦,集中诸如《菩萨蛮·京口遣信南归因题书尾》、《浪淘沙·戏赠闺人》、《浪淘沙·代答》、《苏幕遮·娄江寄家信作》等词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夫妻间的深厚感情。如其《浪淘沙》两首云:
戏赠闺人
生计漫匆匆,卖赋临邛。黄金先为贳新丰。伊唱吴趋侬起舞,激楚回风。 此处不留侬,甚处留侬。小朱慵粉若为容。一事与卿权领,取酒诰花封。
代答
晓起弄妆慵,笑指吴侬。白衣夫婿白头侬。今日海棠花下饮,端与谁同。 云雨楚天重,谁系郎踪。任伊梦遍十三峰。解识近来勤入道,懒向花丛。
这两首可以算一组联章体,第一首以男性口吻来揣度女性,用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来比喻自己与闺人,意指两人的生活纵使贫贱,但仍能不改其乐,“伊唱吴趋侬起舞,激楚回风。”自己能够给予妻子的当然不是那些“小朱慵粉”,而只能是“酒诰花封”。第二首则代女性口吻来作答:都说是白头偕老,可我的夫婿今日却在何方呢,“今日海棠花下饮,端与谁同。”纵然自己千般思念,但又如何能够化作那楚天之云,夜夜入君梦中呢?现如今,我已经告别了欢乐,守着一盏青灯“勤入道”了,真可谓“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没有丝毫的怀疑与猜忌,全是一片炽热的衷肠。
再试读其《菩萨蛮·京口遣信南归因题书尾》四首:
绣衾孤拥春寒峭,窗前小玉迎人笑。报道远人回,郎君有信来。 循环都读遍,腹内车轮转。何日却归家,恹恹瘦损花。
中秋月落催兰棹,清明寒食逡巡到。青鸟纵传书,不归仍是虚。 旧欢真似梦,毕竟功名重。含泪待归期,从头细问伊。
去年除夕兰缸下,熏香被酒更深罢。鸣指又嘉平,迢遥蓟北行。 门庭清似水,泪滴鸳鸯被。夜夜捧心眠,何人著意怜。
断红小颊芙蓉浅,檀痕新渍香襟煖。雁字下平芜,还胜雁也无。 情知归未得,不是轻抛掷。寄语好加餐,春来风雨寒。
这四首词情感真挚,“报道远人回,郎君有信来”、“循环都读遍,腹内车轮转”、“青鸟纵传书,不归仍是虚”、“雁字下平芜,还胜雁也无”、“情知归未得,不是轻抛掷”之句,不仅情思缠绵,还有古乐府敦厚之意,而且其情感也合乎夫妻之伦常。词后湘尹评语云:“四词情真调雅,文君白头吟,苏氏回文锦俱可不作,又增玉台佳话矣”[6]。彭孙遹的这些情词很多情况下都是出自真实的经历,是有感而发。这些作品不但情景相和,还能够做到艳丽而雅正,是其词作中最动人的部分。
二 自然与雕琢
彭孙遹的词学理论主张以自然为宗,但也主张要稍加雕琢,能够将感情内容上的真挚动人和形式上的精心打磨结合起来的词作方为上品。如他在《金粟词话》第一则中说:“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乃造平淡耳。若使语意淡远者,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彭孙遹对雕琢的界定比较宽泛,举凡用语、谋篇、设境等艺术手法之经营,都可纳于其内。重要的是雕琢要巧、要妙,“但见工巧,都无组织之迹”[7]。
在彭孙遹看来,北宋诸词人之所以胜人一筹,并非仅凭情感之深挚,更是由于设景之秾至,“如温、韦、二李、少游、美成诸家,率皆以秾至之景,写哀怨之情,称美一时,流声千载”[8](序)。范仲淹的《苏幕遮》一首词,之所以卓绝千古,正是因为“前段多入丽语,后段纯写柔情”。以秾至之景和真挚之情的融合程度来作为考量词作的标准,则主张“境由情生,天机偶发,元音自称,繁促之中尚存高浑”[9](序)的云间词风便不足法。彭孙遹在《金粟词话》中说:“近人诗余,云间独盛,然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
然而这种雕琢又不能太过,否则便有“雕缋满眼”之病。彭孙遹在《金粟词话》中还结合具体词人来说明自然与雕琢的关系:
梦窗之词虽雕缋满眼,然情致缠绵,微为不足。余独爱其《除夕立春》一阕,兼有天人之巧。美成词如十三女子,玉艳珠鲜,政未可以其软媚而少之也。
彭孙遹不同意张炎《词源》中的推崇梦窗而贬诎周美成的观点,他认为吴文英虽雕镂刻画,论情致缠绵却有不足。而美成的作品虽然软媚,但如十三女子,玉艳珠鲜,美出天然,所以是上乘之作。这段词论中所推赏的吴文英《祝英台近·除夜立春》一首词,在彭孙遹看来是自然与雕琢妙合无垠、兼有“天人之巧”的作品。彭孙遹《菩萨蛮·除夕阮亭广陵署中守岁》一首词“节序惊心残腊尽,同云襞雨寒犹紧。小暖逼炉烟,江春入旧年。 芳柑传绮席,好事过除夕。香雪动园梅,春回人未回。”谋篇构思,摹情写景,均与梦窗除夕词神似,被王士禛评为“天然淡隽”的作品,体现了他对这一艺术标准的实践。
彭孙遹在追求自然与雕琢的调和中也下了不少的功夫。他强调词作者的知识积累,认为“词虽小道,然非多读书则不能工。观方虚谷之讥戴石屏,杨用修之论曹元宠,古人且然,何况今日。”在《延露词》中,彭孙遹精心结撰,将晚唐词中比较质实的意象,熨贴地连缀起来。如其《归朝欢·秋夜》一首词:
画阁重帘深不卷,铜史黄昏催缓箭。那堪离别在兰时,梧桐落尽迴心院。夜长君不见,漏痕犹比檀痕浅。麝煤残,银筝宝瑟,信手拈来倦。
侧侧寒生霜瓦贱,眼底屏山千里远。南来孤雁已先红,一声天际堪肠断。飘零秋万点,风條雨叶如相饯。最无憀坐愁不寐,绛蜡和花剪。
“画阁重帘”、“铜史黄昏”、“麝煤残”、“银筝宝瑟”等在五代词中格外强调的意象,在这首词中则完全退居次要位置,整篇词作中,情感上的离愁、秋怨可以流丽地转动于词中。王士禛评这首词云:“金粟艳情剪熨,遂觉着诗语不得,真柔金软玉手也。”
彭孙遹还能将诗中的名句巧妙地应用到词作中,虽然词面看起来波澜不惊,但在阅读中却能够引发读者更多的联想,这种点染之功同样达到了巧妙的刻画效果。在词料的选择上,彭孙遹主张要有一定的取舍。他在《金粟词话》中说:“作词必先选料,大约用古人之事,则取其新颖,而去其陈因。用古人之语,则取其清隽,而去其平实。用古人之字,则取其鲜丽,而去其浅俗,不可不知也。”这样就能够将古人作品中最为新警自然的故实用到词句中。如其《柳梢青·感事》一首词云:
何事沉吟。小窗斜日,立遍春阴。翠袖天寒,青衫人老,一样伤心。 十年旧事重寻。回首处山高水深。两点眉峰,半分腰带,憔悴而今。
整首词没有一个生硬的字面,都是自然之语。然而这些自然之语中却植入了唐诗中两个著名的句子。一个是杜甫《佳人》中“天寒翠袖薄”,另一个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江州司马青衫湿”。“翠袖天寒”的植入,使得词作中传达出诗歌中“香草美人”的寓意。这种寓意其实是彭孙遹有意为之的,它在《旷庵词序》中先谈自己难后多作艳词,然后又说:“旷庵年来濩落不偶,亦复有香草美人之感。其所作长短调及和潄玉词,若有所寄托而云然者。”这里说“亦复有香草美人之感”,意思是与自己一样都有“香草美人”之感。因此,他的这些作品中是有一定的寄托味道的。而当王士禛称其为“艳词专家”时,他恐怕真的要“怫然不受”了。而“青衫人老”,则将白居易的“江州司马青衫湿”中“青衫”这个最具意味的词语摘出。在唐朝九品一类的小官才穿青衫,而白居易在写这首诗时也刚好被贬为将仕郎,从九品,故诗中写其穿着青衫。而词中的“青衫人老”则指老而无功。因此,无论是被孤寂、被抛弃的美人,还是老而无功的才子,都是最值得伤心的事。当然,这两者都可指男子仕宦上的得失。因此,在读到这样看似平淡,却经过结撰的句子后,表面上“两点眉峰,半分腰带,憔悴而今”闺怨之情便会退而为次。读者自然会生发出“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感慨。这一点在该首词的几则评语中表露得更为明晰:“程村云伤心语不堪多诵”;“湘尹云怨而不伤,有风人之遗致”;“阮亭云沁人心脾所不必言,即‘翠袖’、‘青衫’,杜白岂非绝对?”
三 “通变观”与稼轩词风
广陵词坛有相当开放的词学态度。广陵词人不仅看到晚唐、北宋词的好处,也能看到今人词的好处;不仅懂得欣赏小令,还要懂得欣赏长调;主张婉约词,但同样不排斥其他风格的词作。彭孙遹在这些方面也持大抵相同的看法,在批评词时他虽然以“艳丽”为本色,但却并不排斥其他风格的作品。彭孙遹在主张“艳丽”为本色的同时,又颇为赞赏辛弃疾的豪放词,“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措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轩一字,辄纷纷有异同之论,宋玉罪人,可胜三叹。”
但彭孙遹论词最具慧眼的地方在于:发现同一个词人身上并存的不同风貌。比如他在评价宋代词人时,并不因袭前人判断,而是注意看到异中之同:“柳耆卿‘却傍金笼教鹦鹉,念粉郎言语’,《花间》之丽句也。辛稼轩‘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秦、周之佳境也。少游‘怎得香香深处,作个蜂儿抱’,亦近似柳七语矣”[10]。这其实是指出,词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面孔,并不能对词人作单一的评判。因此,他在词话中指出,即使是晚唐词也有如柳七郎风味的尽头语,“牛峤‘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是尽头语。作艳语者,无以复加。”而柳七也同样有高浑的作品,“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这句评语中谈到的柳七词,即指柳永《八声甘州》这样“不减唐人高处”的词作。
正因为有这样的通变观,彭孙遹在词作创作中便更加自然地摆出多副面孔。有时他会学习柳永词中意境高浑的词作,而为《八声甘州·秋怨和柳七韵》,邹祗谟评曰:“柳七‘关河冷落’三语,坡公亦服为唐人佳句,六百年而金粟以‘西风旅梦’二语胜之,乃知太白咏凤凰台终是胆怯司勋也”;有时则学习李清照集中那些“词意并工”的“闺情绝调”,而为《醉花阴·和漱玉词同阮亭作》词;有时则得飞卿之遗意,如其被王士禛评为:“如诵后主小窗诗,一片酸酸楚楚”的《河传》一首词;有时又能学南宋史邦卿咏物词,而几无分别,如其《宴清都·萤火》与《一寸金·莲花》两首,尤侗评云:“羡门萤、莲二词,咏物之工,何必老杜。”
彭孙遹对于“通变观”的贯彻,主要表现为他在主张“词以艳丽为本色”,大量创作了表现夫妻情感的艳词的同时,还注重对稼轩词风的师法。关于彭孙遹学习辛弃疾,在清人的词论著作中便已经注意到了。如李调元《雨村词话》卷四:“羡门《延露词》多悲壮,不减稼轩。如《念奴娇·长歌》四首,《沁园春·酒后作歌》四首是也。”又如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延露词》亦有两副笔墨。如华逊来生日云云,长歌云云,酌酒与孙默云云,又时带辛气。”这里面的两副面孔,则精确地指出彭孙遹词中艳丽与豪放并存的局面。不妨通过其《念奴娇·长歌》四首及同时人评语来感受羡门词中的稼轩气息:
长歌当哭,把琅玕击折,珊瑚敲碎。悔不当初多弄戟,领取中郎都尉。鹊印累累,蝉冠岌岌,忍见人皆醉。雕龙何益,算功名偶然遂。 等闲付与儿曹,三旌已矣,返我屠羊肆。吴下秋风归去好,饱啖菰羹鲈鲙。病藉神君,巧资天女,无计袪穷鬼。夜珠休探,怕骊龙未成睡。
知音寥落,任壁间弦绝,市中琴碎。万卷诗书何所用,不抵一钱程尉。入手杯浓,抬头月艳,人好千场醉。长卿倦矣,问宦游几时遂。 此去四壁犹存,当垆涤器,卖酒临邛肆。春雨绿蓑三尺艇,钓取霜鳞雪鲙。假贷为生,送人作郡,怕杀揶揄鬼。不如秉烛,夜深长伴花睡。
湘尹云淋漓痛快,使人起舞。
壮心难抑,将乱丝斩断,连环搥碎。七贵五侯今已矣,说甚粉郎香尉。公醒而狂,臣饥欲死,待觅墦间醉。平原何在,自媒终笑毛遂。 晓来网得霜螯,横行屈强,吾力犹能肆。脆白肥黄堪一饱,绝胜吴王残鲙。露气高浮,羽声慷慨,痛饮歌山鬼。元龙卧榻,肯容余子鼾睡。
程村云肆字妙押。
丈夫立意,宁兰摧蕙折,璧沉珠碎。宝剑摩娑如好女,请试玉门军尉。虎帐论兵,龙泉知己,卮酒安辞醉。沙场百战,看奇勋一朝遂。 笑谈指顾封侯,宛珠随宝,入室纷成肆。行马歌钟新赐第,狼藉金齑玉鲙。贵客称觞,美人当夕,室瞰高明鬼。拂衣归隐,学希夷五龙睡。
悔庵云四词慷慨悲凉,唾壶欲碎。仆常谓吾辈今日正索块垒人亦不可得。荆卿、渐离相乐相泣燕市,止两人耳,辄和二章以志同感,不足为外人道也。
云客云四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最得情性之正。
阮亭云盗跖之言曰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仆十年来身在忧患之中,乃知跖不欺我。羡门歌乎,仆犹能作羽声和之。
虽然在早期的词学活动中,彭孙遹曾经参加过广陵词坛掀起的偏于豪放的“偶兴”唱和,并有两首和词。但早期学习稼轩“不吐不快”“吞吐无余”的风格在其创作成熟以后则变得更为蕴藉。“偶兴”唱和中的词作,主要是从文字中寻找一种略为解脱的办法,参与者的心态存在着一定的戏谑成分。尽管彭孙遹的这组词的创作初衷也是如此,但最终他却没有超脱,正像他在词序中所说:“雨窗独坐,百感茫茫,因信笔成百字令,自歌且自和之。白太傅谓长歌之哀过于恸哭,此语诚然。以今观之,不诚然耶。”序言中,他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对古人“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的判断进行了反驳:“自歌且自和之”的长歌,不但没有减少心中的痛苦,反而使其愈加沉痛了。因此,如果把那些超脱的“偶兴”唱和时的词作比喻成可以用来浇愁的烈酒的话,那彭孙遹这组长歌便是亟待浇淋的块垒。
多少年来,师法辛弃疾的词人无数,但多半流于叫嚣,因为他们在呼号呐喊的声音背后缺少沉甸甸的块垒。因此,正是在清初那个特殊的背景中,横亘彭孙遹心头那难于说破、又无法释怀的士子情怀让他对稼轩词风的本质特质有了最切身的理解,从而也使其词风得稼轩三昧。“学而优则仕”,是古代士子们永远也无法解开的情结。他们都希望通过科举考试缙绅,从而实现自己一定程度上“兼济天下”的理想。然而,在彭孙遹的词作中,我们却无法看到士绅阶层转换的通畅渠道。他在词中说:“雕龙何益,算功名偶然遂。”又云:“万卷诗书何所用,不抵一钱程尉。”“雕龙”指雕琢文字的读书活动。而“一钱程尉”用到了《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骂程不识“不值一钱”的典故,自嘲读了万卷书,但又有什么出路呢?即使当了程不识那样的高位,还不是一样不值一钱吗?言语之间吐露出对读书报国信念的否定。而那些通过“武功”缙绅的方式自然就成其羡慕、懊悔的一个参照对象,所谓“悔不当初多弄戟,领取中郎都尉。”又“虎帐论兵,龙泉知己,巵酒安辞醉。沙场百战,看奇勋一朝遂。”这样,不但可以“鹊印累累,蝉冠岌岌”,还不用作一个“忍见人皆醉”的大苦人。可是,在词作中,彭孙遹将这重新来过的理想又亲手浇灭了。在第四首词中,他先设想了武将功成名就的场面:“笑谈指顾封侯,宛珠随宝,入室纷成肆。行马歌钟新赐第,狼藉金齑玉鲙。”接下来,他却说“贵客称觞,美人当夕,室瞰高明鬼。”即使是有贵客、美人相伴,还是一样无法全身而退,因为“高明之家,鬼瞰其室”[11](P2005)。然后怎么办呢?自荐吗?“平原何在,自媒终笑毛遂。”又觉得在这样一个没有平原君的时代,毛遂自荐终究只能博人一笑。逃禅呢?“病藉神君,巧资天女,无计袪穷鬼。”纵使可凭籍神君治病,凭籍织女弄巧,但现实中种种因为没钱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又怎么解决呢?所以,这组词真的是道出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困惑。而这些块垒说的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真实,自然就成为被尤侗认可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块垒人”。而且在王士禛看来,这困境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一段时期的大困顿。因此,他在评语中自然就想到了自己这些年的种种苦难:“盗跖之言曰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仆十年来身在忧患之中,乃知跖不欺我。羡门歌乎,仆犹能作羽声和之。”
虽然在广陵词坛最重要的五年时间内,彭孙遹不是结社唱和的发起人,也不是词坛选政活动的推动者,甚至他流传下来的《金粟词话》也只仅有寥寥数语。但他对广陵词坛主要理论的深化却足够深远,无怪乎谭莹在《论词绝句》中推崇彭孙遹“大科名重千秋在,开国填词第一人”。但在具体的作词实践中,彭孙遹以对亡妻的真挚感情来写艳词,以自然与雕琢的恰当拿捏作为考量词作的标准,以心中之块垒来体味辛词,从而造就了其个性鲜明的“柔金软玉、吹气如兰”词风。
[1]顾贞观.论词书[A].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3]邹祗谟.倚声初集序[A].邹祗谟,王士禛编.倚声初集[C].影印南京图书馆藏清顺治十七年刻本.
[4]王国维.人间词话[M].济南:齐鲁书社,1981.
[5]彭孙遹.松桂堂全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彭孙遹.延露词[M].国朝名家诗余[C].清康熙孙氏留松阁刻本影印本.
[7]陆求可.月湄词·瑞鹧鸪芭蕉[M].国朝名家诗家[C].清康熙孙氏留松阁刻本影印本.
[8]彭孙遹.旷庵词序[A].陆野.旷庵词[M].平湖陆氏求是斋蓝格抄本.
[9]陈子龙.幽兰草词·序[A].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幽兰草词[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10]彭孙遹.金粟词话[M].别下斋丛书清道光丁酉刊本.
[11]扬雄.解嘲[A].文选(第5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