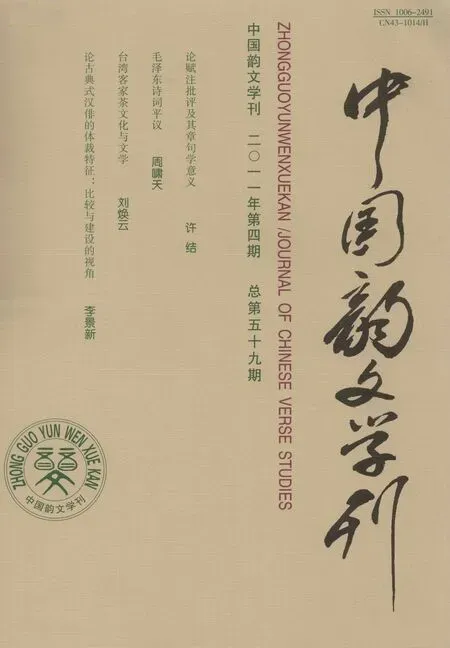清初词人焦袁熹及其论词词
2011-11-20裴喆
裴 喆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以诗词论词是词学理论与批评的重要形式,清人借鉴杜甫以来论诗绝句的传统,以组诗、组词的形式论词的现象蔚为大观,或评骘词史,或表达自己的词学观念,其重要性并不在词话与词集序跋文字之下,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是目前词学界的热点之一。这两种形式招致群起效仿分别始于厉鹗和朱祖谋,然而清初词人焦袁熹早在康熙末年,就已经以大型论词组词的形式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词体观念和词史观念,可称以组词论词之第一人。他的这一论词组词以创作时间而论尚早在厉鹗的《论词绝句》之前。在浙西词派风靡词坛之际,其论词能不随时趋,推尊柳永、周邦彦,尤值得研究者阐幽发微。本文希望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发掘,揭开清代词学史上被尘封的一角,进而有助于思考清代词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问题。
一
生活于康熙、雍正时期的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焦袁熹(1661—1736),字广期,号南浦,康熙三十五年(1696)举乡试第十三名,两应会试不第,以祖母与母年迈不复应试,康熙五十二年(1713)诏举实学之士可备顾问、雍正元年(1723)诏举孝廉方正,皆辞不应;康熙五十七年(1718)授淮安府山阳县学教谕,亦不赴,以著述终其身,事迹详见其子以敬、以恕所编《焦南浦先生年谱》①《词苑萃编》卷八引《幻花庵词钞自序》中提到“征君焦夫子”(《词话丛编》本“幻花庵”误作“勾花庵”),《词话丛编索引》以“焦征君”立目,即焦袁熹。。焦氏在当时以经学家名世,“为一代之名儒”(陆锡山《公举崇祀乡贤呈》)[1](p420),其制义尤负盛名,其诗直抒胸臆,不屑摹仿他人,沈德潜称其“孑孑独造,不侪流俗”[2](P716),亦能词,所著词集名《此木轩直寄词》。
对焦袁熹的词学宗尚,或谓其“未脱浙西派窠臼”[3](P212),这种归类,或许是因为焦氏词中不乏瓣香朱彝尊一类的话头。细按焦氏词风,虽曾广泛学习包括姜夔、张炎等人在内的南北宋词人,却一直保持着自己出语劲直的特点,与浙西词派风貌相去甚远。陈廷焯选《云韶集》,称其“词非一格,奄有众长”,又赞其“小令尤工”,“语似劲直,意则芊婉”[4],实是恰切的评价。《云韶集》时期的陈廷焯尚是浙西词派的忠实信徒,显然并不认为焦词可以归入浙西一派。焦词的追求从其“直寄词”的命名即可表露一二,从他的几首论词词中更可看出与浙西词派的不同:
阳春白雪,哀弦清脆,敢望南唐北宋。莺儿燕子语惺忪,也只是舌头学弄。 亡来朱十,不知年月,觅了瓣香惶恐。寻常言语总难工,又那得许多骨董。
愁城不破,睡乡难住,默默昏昏谁共。江花老去未全枯,把一寸心灰重种。 诸余无分,空中传恨,风月无端嘲弄。泥犁万一不相饶,不是吾侬作俑。——《鹊桥仙·自题直寄词二首》
零珠碎玉,残膏剩粉,似国风、删后无篇什(谓自金元已下)。宋玉微词,叹前辈、风流难及。艳煞人、又生朱十。 前身欧九、本师柳七,付歌喉、浑无生涩。团扇钟情,也则是、三生结习。便泥犁、拼将身入(朱自云“玉田差近”者,谦词耳)。——《解佩令·题江湖载酒集》
从这些论词词中可以看出,焦袁熹心目中的词学高峰,并非南宋的姜、张,而是南唐北宋。他自称瓣香朱十,但是他所师法的并非《茶烟阁体物集》,而是《江湖载酒集》;并非“倚新声、玉田差近”的朱彝尊,而是“前身欧九、本师柳七”的朱彝尊,与浙西词派“置《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于不讲,而心摹手追,独在《茶烟阁体物》卷中”[5](P3415)的风气大异其趣。他所取于朱彝尊的,一是以嘲风弄月、抒写艳情来“空中传恨”,一是词作的“付歌喉、浑无生涩”,也与浙派中人心目中“平视《花间》,奴隶周、柳。姜、张诸子,神韵相同”[6](P1503)的朱彝尊形象大异其趣。凡此皆足以证明焦袁熹实未尝入“浙西派窠臼”,而足称浙西派之诤友。在浙西词派已经风靡词坛的康熙中后期与雍正时期,这种持论实为空谷足音,其独到性与针对性皆表明焦袁熹的词论值得予以认真的发掘和阐释。
更为系统地表达焦袁熹的词体观念和词史观念的,是他的论词组词《采桑子·编纂〈乐府妙声〉竟作》。在讨论该组词之前尚需简单介绍一下焦词的版本问题。《此木轩直寄词》较为常见的是清乾隆间李枝桂所刻二卷本,《全清词·顺康卷》即据此本。然而二卷本并非《此木轩直寄词》的原貌,据《焦南浦先生年谱》所附《此木轩全集总目》,“《直寄词》三卷又附旧作一卷”[1](P435),笔者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见题为《此木轩全集》①此本虽题“全集”,而内容仅包括文集三卷、诗集七卷、直寄词四卷、历试草一卷,与《此木轩全集总目》所云“诗集十六卷、文集十卷”不符,而文仅序、书后、跋、论数体,实非全豹。另《此木轩直寄词》卷首残缺。本文所引焦袁熹作品除注明者外皆引自此本。中所收《此木轩直寄词》四卷,恰为“附旧作一卷”的本子,两相比较,焦袁熹的旧作一卷八十一首在二卷本中完全未收,前三卷中亦有一些词作不见于二卷本,如本文所欲讨论的《采桑子·编纂〈乐府妙声〉竟作》组词,在二卷本中为四十七首,而在四卷本中则为五十六首②所缺诸词见本文附录。。《全清词·顺康卷》及《补编》没有参校此本,因此焦袁熹词漏收很多。二卷本刊行于焦袁熹去世十余年后,其去取并非出自焦袁熹之意,文字亦有所改易,因此以后整理和研究焦词当以四卷本为主,参校二卷本。
焦袁熹的《采桑子·编纂〈乐府妙声〉竟作》组词五十六首可分为两组,一组四十八首分论李白、李煜、和凝、韦庄、冯延巳、陶谷、赵佶、范仲淹、晏殊、晏几道、宋祁、欧阳修、张先、柳永、苏轼、黄庭坚、秦观、贺铸、周邦彦、万俟咏、向子諲、张元干、岳飞、康与之、辛弃疾、刘过、刘克庄、姜夔、陆游、戴复古、史达祖、张榘、吴文英、蒋捷、周密、王沂孙、张炎、卢祖皋、高观国、张辑、李清照、朱淑真、朱敦儒、朱希真、萧观音四十五位词人及咏梅词、寿贾师道词与《绝妙好词》,或一人而系词数首,或一词而合论多人,如论及苏轼、柳永,先有一首合论两人,又分别有一首予以专论;论辛弃疾,除一首与刘过、刘克庄合论外,又有两首专论辛词。除韦庄、陶谷、戴复古三首以咏事为主,其他诸首都集中于论词。另一组八首则从各个角度表述焦袁熹对词体特征的具体认识。五十六首中论李煜、赵佶、黄庭坚、岳飞、康与之、史达祖、萧观音及《读宋季寿贾相及题壁词戏作》、《见诸咏梅之作什九说着和羹,故有此解》九首不见于二卷本。据《焦南浦先生年谱》,康熙五十六年(1717),焦袁熹五十六岁,“是年选定《乐府妙声》”[1](P363)。《乐府妙声》是焦袁熹所选的一个唐宋词选本,目前尚未发现,通过焦袁熹所题组词,可以约略推测其面目,而焦氏论词之要旨,则已基本体现于这组论词词中。
二
焦袁熹论词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重新提出了“尊柳”、“尊周”。
明代词风深受《草堂诗余》的影响,周、柳词风被视为词坛正宗,浙西词派的兴起,首先针对的就是这一风气。被视为浙派先河的曹溶提出:“豪旷不冒苏、辛,秽亵不落周、柳者,词之大家也。”[7](P729)自浙派提倡姜、张词风,周邦彦、柳永被视为秽亵词风的代表,地位一落千丈。至常州词派兴起,两人的词坛大家地位才逐渐得以恢复。焦袁熹早在康熙末年已在其《采桑子·编纂〈乐府妙声〉竟作》组词中称赞柳词“绝代超伦”(《柳耆卿》),称柳永“大唐盛际诗天子,穆穆垂裳。乐句琳琅。宋代王维柳七郎”(《柳耆卿、苏子瞻》)。焦袁熹对柳词的定位需结合其他文献来解读。在他的论诗绝句《戏题绝句》中,有两首专论王维,云:“王维自是诗天子,穆穆垂裳宣玉音。好教杜甫作宰相,李白终当入翰林。”“王维自是诗天子,天表龙姿众目惊。人王却拜空王座,一事还将累圣明。”(《此木轩诗》卷五)对王维的诗坛地位推崇无以复加。因此其以柳永来比拟王维,即是确认柳永为词坛至尊的地位。这可说是历代词论中对柳永的最高评价。
焦袁熹对柳永的具体评价从组词中也可得其大概:首先,正如王维诗被视为“盛唐气象”的代表,柳词也正是北宋“盛际”的表现,而这种“盛际”也只有“穆穆垂裳”,如焦袁熹他处所说“盛德之至,动容周旋自中乎礼”①焦袁熹《答钓滩书》,转引自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阐释》,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8页。者方能表现,此即如宋人所谓柳词“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黄裳《书乐章集后》)[8](P239);其次,从宋词作为“换羽易宫”的音乐文学来看,柳词能够创为新声,“乐句琳琅”,使“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9](P674),又能够做到“当场动人”,这些从演唱和传播的角度来看正是“倚声之当行本色”②郑文焯《清真集批语》云:“柳以善歌为北宋词家专诣……要皆出于乐府遗音,实倚声之当行本色,非专家不能为之。”见郑文焯著,孙克强、杨传庆辑校《大鹤山人词话》,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故其专论柳永的一词说:
井华汲处须听取,驻得行云。落得梁尘。三变新声唱得真。 香山灶妪君知否,俚俗休嗔。绝代超伦。只在当场动得人。
焦袁熹对柳词的评价,是建立在比较基础之上的。焦袁熹比较柳永与苏轼,从“本色”的角度否定苏词:“谁交铜铁将军唱,不是毛嫱。却似文鸯。可笑髯苏不自量。”(《柳耆卿、苏子瞻》)张先在当时与柳永齐名③晁补之《评本朝乐府》云:“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能改斋词话》卷一引,《词话丛编》第一册,第125页。,明人亦常视张、柳二人为“柔声曼音”的代表,如孟称舜说“作词者率取柔音曼声,如张三影、柳三变之属”、“幽思曲想,则张、柳之词工矣”(《古今词统序》)[10](P437—438),焦袁熹在评价张先时比较二人之词云:“露华倒影谁堪比,窃恐非伦。莫斗喉唇。好与中书作舍人。”认为如拟柳词为天子,则张先只是中书舍人之材。在《采桑子》组词中焦袁熹用到“绝伦”一词评价的另一人是姜夔,却又批评姜词“未免清贫”,亦不足以与柳词相媲美。通过这些比较凸现了柳永词的至尊地位。
焦袁熹对柳词的评价并非对明代词论的简单回归,而是有其现实的指向。这在其评论姜夔时说的尤为明白:
范家一队当先出,白石粼粼。未免清贫。制得新词果绝伦。 诚知此事由天纵,一片闲云。野逸天真。寄语诸公莫效颦。
这一评价,需结合焦袁熹对“清”这一范畴的阐释来理解。焦袁熹认为所谓“清”是“研炼之极”的表现,是诗美所必备的品质之一,“清”包括“事清”、“境清”、“声清”、“色清”而以“声清为要”,“声之清浊,气之类也,声气在人,似有天分,得之清者,所谓天才也,事半而功倍矣……使其人能深辨乎此,加意研炼,未必不可变浊为清也,惟其天分有限,于此无所用其力,故其成就仅若是而已尔”④焦袁熹《答钓滩书》,转引自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阐释》,第47页。。由此来看本词,可知焦袁熹认为姜夔的“清”是出于天分,而当时学姜夔者无此天分,故不应效颦一味追求“清”,其矛头直指浙西词派。在评价张炎时焦袁熹又指出:“白云何处堪持赠,寄语诗流。闲淡清柔。到得伊家也合休。”亦直指张炎词他人无从学起,末句在二卷本中作“到得伊家满意不”,虽锋芒稍藏,其意依旧。白石词已“未免清贫”,学姜、张词者如一味求“清”,又不能至于“清之极”的“凄寒肃杀”⑤同上注48页。,则只能向“轻圆”方面发展,这种“轻圆”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背离了“清空”这一审美追求。所以焦袁熹评论张辑时说:“亦知绮语真清绝,白石传衣。分付红儿。多恐轻圆不似伊。”(《张东泽》)⑥此处引文据二卷本,在抄本中末句作“多恐声牙不似伊”。这虽是对词史的观照、描述,却也不期然而然准确地预言了浙派未来的发展趋势。
焦袁熹对柳永词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他发现柳永词价值的中介是周邦彦词。在编选《乐府妙声》之前,焦袁熹对宋词的评判是以周邦彦为第一,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答曹子谔廷第二书》中焦袁熹尚认为:“唐人之诗,右丞有天子之目,李、杜大家,但可为其辅弼,举右丞则他诗之美无以逾之矣……他如骈体之推任昉,诗余之首周邦彦,其道小,其故愈难言。”①焦袁熹《答曹子谔廷第二书》,转引自《焦南浦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八八册,第346页。在《乐府妙声》编选完成之后,焦袁熹对宋词的认识有了变化,“平日论词推周美成,选竟,以柳耆卿为第一,谓犹诗中有摩诘、曲中有马东篱也”[1](P363)。这种变化,应是认识到了周邦彦与柳永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后来为两人翻案起了重大作用的周济说:“清真词多从耆卿夺胎,思力沉挚处往往出蓝。然耆卿秀淡幽艳,是不可及。后人摭其乐章,訾为俗笔,真瞽说也。”(《宋四家词选眉批》)[11](P1651)两人词在以赋法为词上实有明显的承继关系。而焦袁熹最终确认柳永高于周邦彦,并非是因周济所说“秀淡幽艳”,而恰恰是从“俗”上着眼。这仍需结合焦氏其他文论来理解。在《戏题绝句》中焦氏评论白居易诗云:“清音吐出借诗人,嶰谷柯亭合有神。莫笑香山真入俗,白头老妪是伶伦。”“粗豪气象真伧父,轻靡音情不丈夫。要使元声谐律吕,洋洋盈耳解听无。”(《此木轩诗》卷五)认为白诗可谓“元声”,而“香山灶妪”恰恰是真正的解“元声”之伶伦。柳永词介于“粗豪”和“轻靡”之间,其俗正是以“元声谐律吕”,而周邦彦较柳永为雅,却离“元声”稍远,所以以“香山灶妪”为伶伦来评判,周邦彦之与柳永,正如沈宋争胜,终有一线之差距。
焦袁熹推尊柳、周,但并没有以此为唯一的标准来否定其他词风。他批评苏轼“一生不奈专门学,天雨才华。乱撒泥沙。唱出尊前别一家”,但对苏词的旷达则称赞云“比似吾累旷达些”,对辛弃疾、陆游、刘克庄、张元干等人他都颇为欣赏。其评辛词云:“辛家乐府知何似,起舞青萍。四座都醒。羯鼓声高众乐停。 胸中块垒千杯少,发白灯青。老大飘零。激越悲凉不可听。”对辛词的评价颇为准确。又云:“痴儿騃女知何限,学语幽呜。滴粉搓酥。看取堂堂一丈夫。 二刘未许曹刘敌,而况其余。湖海尤粗。总与辛家作隶奴。”“二刘”指刘过、刘克庄,“湖海”指陈亮。认为他人皆不足与辛比数虽是陈言,但他对辛弃疾词的评价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豪放词存在的合理性。这与焦袁熹论诗虽认为王维诗为第一却并不因此而否定其他诗学倾向,他自己为诗更是“不求似古不求工”②焦袁熹《戏题绝句》:“吾爱明初袁海叟,不求似古不求工。”《此木轩诗》卷五。的倾向是一致的。
三
焦袁熹对词史的评骘基于他对词的体性的认识。他认为词是以“嘲弄风月”来“空中传恨”。“空中传恨”之说来源于朱彝尊,严迪昌先生指出:“‘空中传恨’可说是浙派创始人自律的关于词创作应具的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相融汇的要义。”[12](P233)焦袁熹在《鹊桥仙·自题直寄词二首》中亦说:“诸余无分,空中传恨,风月无端嘲弄。”表明他对此说的认同,他将词集命名为《此木轩直寄词》,其“寄”即“空中传恨”之意。
焦袁熹认为词是以传情为主。他说:“生生死死尘缘在,长短离亭。欢会飘零。人到中年百事经。
今来古往情何极,一例惺惺。夜雨淋铃。清唱哀弦字里听。”他认为“情”是古往今来长存而人人都能感受到的,词体即是将“情”用“清唱哀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另一首中焦袁熹又说:“人间不少闲风月,落叶飞蓬。聚散匆匆。蝶梦醒来更恼公。
何人解道心中事,换羽易宫。对语秋虫。烛焰今宵吐似虹。”这也是说明词是以“换羽易宫”,即音乐文学的形式来写风月之情。明末清初人多认为周、柳为以词传情的代表,而以苏轼为使才的代表,如吴骐说“文章专论才,词兼论情。才贵广大,情贵微密,苏长公词有气势而少缠绵,才大而情疏也。柳耆卿、周美成缠绵矣,而乏气势,情长而才短也”③《百名家词钞·玉凫词》引,《续修四库全书》第1721册,第275页。,焦袁熹推崇周、柳,而批评苏轼“天雨才华。乱撒泥沙”,正是基于认为周、柳词长于传情而苏词“逢场作戏三分假”(《苏子瞻》)。
对于词中所写“风月之情”,焦袁熹也将之解释为“空中语”。焦袁熹在评论向子諲说:“若为忏得泥犁罪,扰扰匆匆。暮鼓晨钟。颂酒吟花是事慵。
心持半偈空诸有,若论真空。未数涪翁。只有芗林是个中。”胡寅评《酒边词》,谓其“以枯木之心,幻出葩华,酌玄酒之尊,而弃醇味,非染而不色,安能及此”(《酒边词序》)[13](P524),焦袁熹云云,实取胡寅之意。在另一首词中焦袁熹亦说词中所写,是“空花解道无根蒂”。焦袁熹在评论友人黄之隽的香奁诗时,对“空中语”存在的合理性曾做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指出世人“彼非无志,所志维何?货利而已矣。凝水燋火,千状万端,痿痺之疾,中于心腑,人之死生,我何有焉,犹且饰为礼法廉正之谈、性命粹微之说,用盖其私而厚其毒,所谓以诗、礼发冢者,则皆其志为之也”,“有宋大儒之言,忄佥邪借之以杀人者,无过是物也”,而“若耽蛾眉则顿忘饥渴,眄罗袜乃几役梦魂,倾彼国城,胡然天帝”的“空中语”反倒是“以疗痿痺不仁沉痼不可为之大病”的“万金良药”,“物之就槁者,嘘之使生意复回;人之必死者,收召魂魄,使归其宅,而乃庶几有起色矣”(《堂先生集唐香奁诗序》,《此木轩文集》卷上)。在清初提倡理学的氛围中,以一位“醇儒”的身份,直斥“有宋大儒之言,忄佥邪借之以杀人者,无过是物也”,而以“空中语”论证写风月之情的合理性,其理论价值亦不可轻忽。
焦袁熹超出前人的贡献是提出词中所传之情应是无可奈何之情。焦袁熹说:“奈何辄唤真无计,万颗秋莲。一茧春绵。借取江毫写一篇。”在《绿窗小草序》中焦袁熹对这种无可奈何之情表述得更为清楚:“乃若欲言未敢,有怨必盈,揽春物以沉吟,对秋辉而怊怅,忧深思远,谁可告诉者,烟墨之间,亦云寄而已矣。”(《此木轩文集》卷上)这种无可奈何之情产生的词境焦袁熹描摹为“溅泪花边。半醉灯前。飒沓萧寥风雨天”,“虚廊坏槛萧寥夜,万绪填膺。感咽难胜。独自闲行独自凭”。清末民初况周颐描述词境时说“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鼎相和答。据梧暝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14](P4411),与焦袁熹所描摹者若合符契。焦袁熹此论较况周颐早了近二百年,其开拓意义自不可低估。
朱彝尊总结出“空中传恨”作为词的“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相融汇的要义”,然而“‘传恨’,若太质实,固乖背清空、空灵的审美趋求;然而清空、空灵若无‘恨’传出,必成空枵,浙派不少传人之遭訾议,弊端正在此”[12](P233),焦袁熹提出词所传者是无可奈何之情,正是为了对治浙派末流的无情可传。常州词人认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15](P1630),焦袁熹的无可奈何之情,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焦袁熹自成年以后,基本处于所谓“康乾盛世”,他在诗文中对清王朝也不乏歌功颂德之辞,但在内心深处,却一直有一种疏离之感。他中举时不过三十六岁,两应会试不第时亦不过四十岁,此后即绝意仕进。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奉养祖母与母亲,在其诗中却偶尔表露其实际心态。对于士大夫文人艳羡的词臣生涯,焦袁熹感慨:“清时才藻集鸾麟,左史摇毫雨露新。一领锦袍旋见夺,可能容易作词臣。”(《咏古》,《此木轩诗》卷四)如果说这还是对历史现象的普遍概括,他针对“近有旨举博学宏词”表示:“圣明张铁网,肯起应词科?”(《酬虞皋见赠二首》之二,《此木轩诗》卷二)表明焦袁熹对清廷收取名士以笼络人心的政策有着清醒的认识,“铁网”二字颇能表达词科的严酷一面。
虽以经学著称,焦袁熹却并非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号称“盛世”的康、雍两朝在焦袁熹的笔下展现了其另外一面:“连岁遭大祲,田毛存者稀”(《村人食糠》,《此木轩诗》卷二),“客行路欲迷,客心多惨凄。圣恩大赈赡,急病无良医。自遭昏垫后,千里树无皮。皮尽树则死,斩伐靡孑遗”(《莘贤自北归,述途中所见,又出归途唱和诗见示,因赋一篇聊记百一》,《此木轩诗》卷一),“仓颉作书鬼夜哭,世间万事多反覆……东南数郡困征敛,十载逋租难料检。皇心烛照惩奸萌,洪赦欲下迟迟行。催趱文簿堆满案,阴雨溟濛闻哭声”(《纪郡城一异》,《此木轩诗》卷一);“饥疫死者既多,鬼不时现,或凭人作种种语言,不可具述”(《纪事六首》之三自注,《此木轩诗》卷二),“村民馁死者累累有之,死则缚稻草周尸体,略似棺形,号曰柴棺,埋之浅土。往岁有停尸六七日者以为大戚,今更可免矣”(《柴棺诗》自注,《此木轩诗》卷二);康熙帝“玉辇巡行间岁出,江北江南呼万岁”,而“千乘万骑如云屯,县邑供帐非容易……本为百姓不为官,官今要尔纳皇费”(《纳皇费》,《此木轩诗》卷五)。焦袁熹无力去改变这些,清王朝的高压政策又使得他只能“扪腹吾侬在,书空若辈为”,“投笔”“缩手”,“而无出袖时”(《缩手戏题》,《此木轩诗》卷二)。作为一位真性情的“狷者”,这些现实中的感慨都化为一种“抑塞”之气,焦袁熹自称“下愚成性,抑塞颇多”,而“华胥无通梦之期,麴蘖非得全之地,隆坻永叹,远壑徒盈,虚室幽忧,素弦长绝,坐对白昼,匪日而年”,因此主张以词作为消其“蓬蓬然于胸中,日积而盛,无以消之”(《消夏吟题词》,《此木轩文集》卷下)之气的一种手段,“欲言未敢,有怨必盈,揽春物以沉吟,对秋辉而怊怅,忧深思远,谁可告诉者,烟墨之间,亦云寄而已矣”(《绿窗小草序》,《此木轩文集》卷上)。
在清代文坛,焦袁熹是一位应当得到足够重视的文论家,据《此木轩全集总目》所记,他关于文论的著作有《论诗汇编》八卷、《论文汇编》五卷、《论制义汇编》四卷,此外尚有词选《乐府妙声》等,这些著作目前尚未发现,但其诗、词、文中尚有大量的相关论述可资研讨。不仅著作数量众多,其论述亦颇多建树。最早重视焦袁熹文论建树的是蒋寅先生,他曾称焦袁熹论述“清”这一诗学范畴的一篇文章“是真正对清加以深入探讨的力作”,认为焦袁熹的论述“在融合前人见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显出相当深刻的诗史眼光,也显出相当自觉的理论意识”,并感慨“这样的论文沉睡在文献中的一定还很多,有待于批评史研究者去发现”[16](P46—48)。本文对焦袁熹论词组词的发掘和对其价值、意义的简单论述,可以视为对蒋先生呼吁的一个小小回应。
[1]焦以敬,焦以恕.焦南浦先生年谱[A].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八八册)[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2]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十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马兴荣,吴熊和,曹济平.中国词学大辞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4]陈廷焯.云韶集(卷十七)[M].清稿本.
[5]]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七)[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6]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7]沈雄.古今词话[A].词话丛编(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8]黄裳.演山集(卷三十五)[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0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9]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10]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A].续修四库全书(第1728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严迪昌.海宁查家词话——兼说“浙派”中期词研究[A].严迪昌论文自选集[C].北京:中国书店,2005.
[13]向子諲.酒边词[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7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14]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A].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蒋寅.清:诗美学的核心范畴[A].古典诗学的现代阐释[C].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