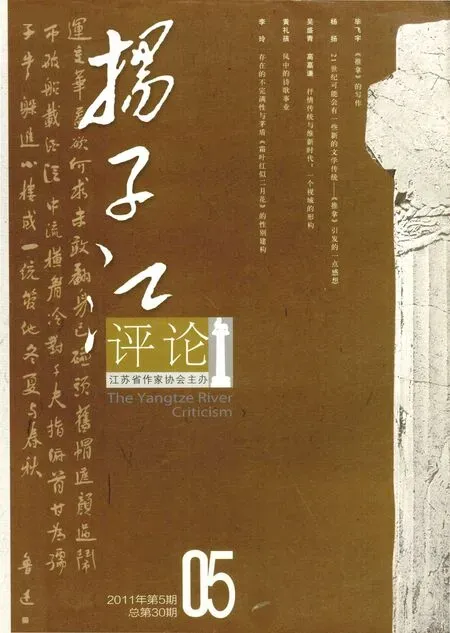苦难人生 血泪文字——编余琐忆:从维熙印象
2011-11-19徐兆淮
徐兆淮
在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在《钟山》杂志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期间,曾有幸结识过一批颇有才华又活跃于新时期的“右派”作家朋友,并与他们有些书信和稿件往来。其中,有些人我读中学时即知其名,大学时又读过他们一些“获罪”的代表作品。如王蒙和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绍棠和他的《青枝绿叶》,刘宾雁和他的《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而另一些“右派”作家,或者知其名,并未读过他们的作品,如邵燕祥、邓友梅,或既不知其名,更未读过他们的作品。如从维熙、李国文、林希、柳萌等人。而张贤亮则属于见过面约过稿,却无缘拿到他的稿件的作家。
根据我的办刊经验,我以为,作家与期刊之间的稿约,似乎也有一种特殊的缘分。上世纪新时期之初,我是读到被称为开“大墙文学”之先的那篇《大墙下的红玉兰》,得知从维熙其人其文的。不过,当我欲要去京拜访从维熙时,未料想却发生了一件让他颇为恼火的事情:创办《钟山》杂志社的江苏人民出版社辑集出版一本全国短篇小说年度选本时,未能事先征得作者同意就擅自收录了一篇从维熙的短篇。从维熙当即写信表示强烈义愤。得知此事时,我即通过刚参加完《钟山》举办的太湖笔会的刘绍棠向从致歉,并随即补寄了稿费。此令人不快的事才得以及时地平息。当时我即觉得,从维熙是位颇有个性、为人直率的作家。
《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发表,为从维熙赢得了较高声誉,也吸引了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们的目光。大约在1980年前后,我赴京组稿,专门找到东四附近一条叫做魏家胡同的小巷,对从维熙作家庭拜访。记得那段时日里,一些发配外地劳改的“右派”作家们,大都已陆续返京。刘绍棠回到府右街那单门独院的宅第里,王蒙则从新疆伊犁回京,暂时住在一所招待所里栖身,而从维熙则住在一小平房内,房间大约只有十多平方米,家中还有老母亲盘坐在炕上,儿子似乎在一所大学里学雕塑不住家。足见家中的局促狭小,真不知从维熙怎样在这样的环境里写下那些中短篇小说的。
只要是熟悉新时期文学史的人,大约都知道,一批富有才华又长期遭受磨难的“右派”作家们,一旦获得平反的创作条件之后,他们如同火山迸发般的创造力,使他们很快就成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主力军,而从维熙又是其中特别活跃、个性尤为突出的作家之一。而当时刚刚创办的《钟山》只不过是一家省级地方刊物,影响远不如《十月》、《收获》、《人民文学》等名刊,因而,我向从维熙、王蒙和刘绍棠这样知名度的作家组稿时,便需要特别的热忱、耐心和韧性,还有适当的方式,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并进而为《钟山》撰稿。
准确地说,如果撇开组稿的两三年,从维熙与《钟山》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第2期,《钟山》以“作家之窗”专栏的方式,推出从维熙中篇《春之潮汐》的同时,还发表了他的创作谈《要认识你自己》,此外还同期发出了陈辽先生的评论《从维熙论》。从1980年前后的组稿,到2000年从维熙为《钟山》“凡人素描”专栏撰稿,我们的友好合作长达20年左右。
尽管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从维熙就已创作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和一本长篇小说,被视为“荷花淀派”的文学传人。但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各种生活磨难和挫折之后,1980年他重新拿起笔时,他已不可能再有田园牧歌式的情趣,因而正如他在创作谈中所说:他现在要寻找和认识的文学作品,乃是“力图通过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命运,来揭示我们国家所走过的一条泥泞道路”,和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历程。如写十年内乱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及发表在《钟山》上的中篇新作《春之潮汐》,还有随后发表的《第十个弹孔》,便都浸满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思潮的色彩,且都产生了轰动性效应。
按照《钟山》“作家之窗”专栏的体例,除发表作家新作和创作谈、作品目录、作家小传之外,《钟山》还特请省内资深评论家陈辽先生撰写了《从维熙论》。评论从分析从维熙几十年创作经历和有影响的作品入手,充分肯定了“从维熙以其置身社会最下层的丰富的生活体验为基础,以其对新中国历史命运的深入思考作指导,卓有成效地参加了我国前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历史的写作工作”。从而在现实与历史的层面、思想与艺术的层面,对从维熙的创作作了中肯准确的评价,并赢得从维熙的首肯。
从维熙与《钟山》的友好合作从“作家之窗”专栏开始,之后的十几年来,他先后主动来信大约三、四次。这些来信来稿不仅显现出了作者为人为文的情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作家独特的创作风貌,展示了从维熙在一代“右派”作家中特殊的文学地位和价值。
时隔三四年之后,1988年10月12日,从维熙在给我的来信中,热情地推荐了一篇纪实体小说《方城门》。作者张沪乃是与从维熙一道打成“右派”一同被发配到山西劳改农场,共同经历生死磨难的前妻。《方城门》以血泪文字记录的,正是“文革”中这对患难的“右派”夫妻在同一所劳改农场里所经历的惨绝人寰的悲惨情景:妻子不堪凌辱,宁愿喝农药自杀,丈夫闻讯非但无法施救,反倒被拷、批斗,真个是陷入了求生不得求死无门的人生苦难之中。新时期以来,我曾读过不少令人心痛的“伤痕文学”,可极少读过从维熙夫妇如此令人心碎又让人沉思的作品。
读着这组“女囚系列小说”,连同从维熙的“大墙文学”,不能不使人体味到新时期初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某些特征:真实地展示“文革”中人们身心所遭受到的严重摧残和伤害,深沉反思酿成这一幕幕人间惨剧的社会原因,并进而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国策而发出强烈的呼唤和呐喊。
读着从维熙夫妇的这些纪实体小说,我不由地想起阿尔·托尔斯泰的描写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里的那段名言:知识分子在咸水里泡三次、盐水里煮三次之后,方能成为革命者。读罢稿件,我遂决定,将《方城门》安排刊发于《钟山》1988年第6期头条。并在要目简介里推荐道:你想知道非常岁月里一个女政治囚犯自杀后的真实感知吗?请读读此作吧!
继从维熙的中篇《春之潮汐》和张沪的《方城门》之后,维熙又曾经想把他后期的力作、纪实体长篇小说《走向混沌》也交《钟山》发表,可惜当时因正决定发表另一作家的长篇新作而未能接纳。事后想来,我仍不免有后悔莫及之慨。事实上,从维熙的这些作品不仅是汇入伤痕和反思文学大潮的代表作品,而且也集中体现了从维熙在这一文学大潮中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位置。从而使得从维熙的创作有别于同时期其他“右派”作家的作品,显示出自己的独特色彩和风格。
新时期文学主潮中的一批“右派”作家,原是个性各异、才华卓绝的作家群体。王蒙的智慧灵动,刘绍棠的乡土风味,张贤亮的浪漫飞扬,李国文的博识深思,都显示出各自的创作个性与艺术特色,而从维熙借助《大墙下的红玉兰》、《北国草》、《走向混沌》的创作,却体现出鲜明的灾难意识和纪实文体的感人魅力,对历史悲剧的反思具有沉郁的悲剧美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新时期的文学画廊中,甚至在新时期文学史里,从维熙创作所涉及的文学题材,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显然都占有不可或缺的一页,兴许这也是曾经责编过从维熙小说的新时期文学编辑们的共同体会。
继《方城门》之后,从维熙又先后给《钟山》和我寄来两封信和两篇稿件。一篇是悼念96年逝世的文坛元老陈荒煤先生的。从在信里写道:他和冯牧是新时期文学的主帅,对许多作家有过帮助。其功是其他文艺领导无法取代的。写此文章,完全是感情和良知使然。可见,从维熙对新时期文学是充满感情的,对新时期文学的领导人是十分怀念的。其实,在从维熙写完《走向混沌》等纪实性自传性小说文体之后,近几年来他所致力写的散文里(如2010年9月发表的《自读和忏悔》),就充分表达了对“反右”运动中积极整人,“文革”后首先“自读”和“忏悔”的老一代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华君武和张光年)的谅解与尊敬,对“永无忏悔”者的愤懑与不满。这些晚期散文也充分展现了从维熙的良知与胸怀,颇值得人们一读。
对待“反右”运动中蒙难的“右派”作家,我一向抱着尊重与理解的态度;对于像从维熙这样经历过劳役般苦难历程的知识分子,我尤其敬佩不已。2000年,我主持筹办反映普通大众民生疾苦的“凡人素描”专栏时,再次想到了长期沉浸在生活最底层的从维熙。我致信他不久,即收到了他的来信来稿。信中他诚挚地写道:“从南京飘来的几个字,我竟久久地凝视了好一会,大概是‘心有灵犀’之故吧”,随信他寄来一篇状写劳改“右派”浪人王臻传奇经历的一篇短文《不死鸟》,并附寄来王臻小照一帧。他当时正忙于写一长卷,竟忙中抽空,特地及时为我为《钟山》赶写了此稿寄我,这不仅表现了这位著名作家对凡人小事的关注与情感,也体现了他与期刊与编辑的真诚友情。
从维熙的几次来信来稿,让我读懂了这饱尝人间苦难的作家,对生活的热爱,对苦难的沉思;与维熙的几次接触又让我明白,这位屡遭挫折的作家对友情的珍惜,对底层人士的关切是那么真挚深沉。
是的,一个忧国忧民的作家,他的心里,不可能没有对假丑恶的憎恨,也不可能没有对人民大众的热爱。可以说,从维熙夫妇的苦难人生,在他们的笔下,全部化成了血泪文字。因而,这文字也便显得特别珍贵,特别沉重。
近几年来,我分明能感受到,年事渐高之后,从维熙似乎已经很少再写小说,再到处参加文学活动了。他正在以直接抒发心灵的散文文体,将自己在苦难人生中获得的生活感悟记录下来。他仍在用手中的笔墨表达着对国家对人民的爱,也宣扬着人类的民族的忏悔精神。这说明老去的维熙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仍然用笔墨、心灵坚守着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人生信念。
自打退休之后,又有多年没见到这位文学老人了,而我手头偏又没有与他的合影照。但我仍然偏执地相信,我们都会长久地珍惜当年作家与编辑友情合作的日子。记得上世纪末,一次我去京团结湖从维熙家中拜访,他曾当着自己新婚妻子的面笑说道:“我现在是南京的女婿了!”果然,前两年这位南京女婿来宁省亲,我们竟有幸欢聚在江苏某宾馆,同坐者还有陈辽先生。一晃之间,时光又逝去了两年,如今我们只能将彼此的思念,永远地存放在心中,记录在文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