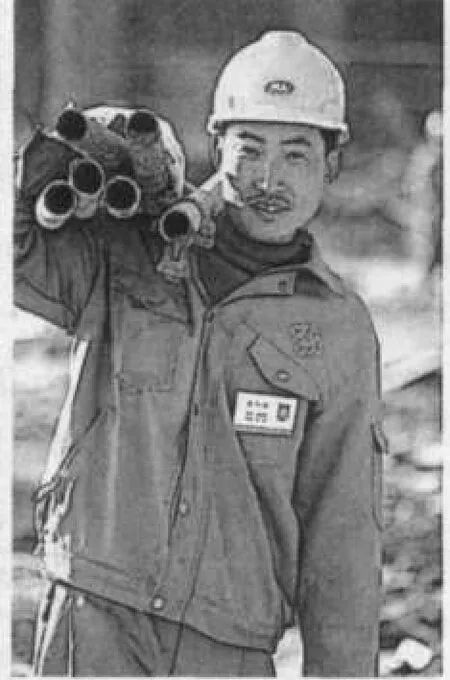劳动者的矛盾特征和矛盾处境
2011-11-18王江松
王江松
劳动者的矛盾特征和矛盾处境
王江松
作为劳动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作为劳动的一个最为重要和关键的要素,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们不可以盲目地迷失于一片对劳动者的赞美和歌颂声中。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一下劳动者的真实状况,就会赫然发现劳动者处在相当困窘的内在矛盾和相当尴尬的外在困境之中。
一、劳动者的矛盾特征和矛盾处境
如同劳动是一个悖论,劳动者也是一个悖论,具有一系列自相矛盾的特征。虽然劳动者是劳动体系和劳动过程的起点和终点,但在整个社会生活体系和过程中,劳动者,不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个体,其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实现性、个性的发展程度,相对而言都是最低的。
1.劳动者为整个人类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其自身的主体创造性和精神文化程度最低
复杂劳动当然具有较高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即使是简单劳动也具有最低限度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不过,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而言,劳动者的主观方面或主体方面的发展程度仍然是最低的,这是因为劳动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抽走了而变成劳动过程的外部动力,以至劳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机械的、被动的、单调的执行过程。席勒、黑格尔,尤其是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劳动的这种异化性质:科学知识和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同劳动和劳动者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能力、权力和属性,比如,在机器生产体系中,科技知识和管理知识表现为一种由资本家加到劳动过程之中的、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只是机器生产体系中的一个被动的环节,以致在自动化程度极高的企业,工人将逐步成为多余的。到了20世纪,布雷夫曼等人进一步详细地研究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去技能化——设计、构想、计划过程与执行过程相分离,知识集中于管理者手中,留给工人的只有一种重新解释过的并且不幸是不充分的技能概念、一种特殊的灵巧、一种有限的和重复进行的操作,等等。通过对工人劳动的这种去技能化、同质化、碎片化,资本得以同时实现三重目的:降低劳动力价格、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对工人的管理控制能力。这种去技能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去精神化、去主体化、去创造化、去目的化的过程。
2.劳动者为人类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准备了经济条件,但自己的劳动却主要是甚至不过是一种谋生活动
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求。即使是在奴隶主强迫奴隶劳动的情况下,每当奴隶克服自然界对人类构成的困难而创造出种种人间奇迹时,奴隶们也会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马克思把这种对外部自然界的克服看作是人的“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在这里,马克思看到了劳动的双重性质:谋生性、被强制性与自由自主性、自我实现性。但马克思在其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始终强调的是,有史以来直至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都不过是在必然王国争得一点点自由,他们的劳动主要是一种被迫的谋生活动,即使他们也具有自由自主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很少有机会得到满足。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基本属实。20世纪以研究和倡导自我实现而闻名世界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实际上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因为他拿来作为范本和典型的自我实现者、高峰体验者,绝大多数都不是劳动者,而主要是一些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
3.劳动者为人类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前提,自己却被模式化、同质化、平均化、标准化
受制于社会分工的必然性、阶级统治的强制性和谋生的被迫性,劳动者的个性自然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相反,他们为了能够活下去,不得不在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的劳动生产体系和过程中从事一份被规定好的工作,承担一项高度片面化和专业化的职能,成为机器体系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只有在劳动过程之外的业余生活中才有可能发展一点自己的个性、兴趣和爱好。劳动者中当然也有一些非常富有个性的人,但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应当承认,无论是所占数量的比重,还是整个阶层的个性发展程度,劳动者都是最低的。
4.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最后分配到的人均财富却是最少的

自然资源是财富的重要来源,不过,自然资源是通过劳动才转化为人类可以享用的财富的,况且自然资源是大自然平等地、一视同仁地赐予所有人的。因此可以说,劳动者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没有劳动,人类至今还处在与动物一样茹毛饮血的阶段。然而在财富的实际分配过程中,劳动者所得到的相对份额是最少的,其人均财富占有量是最低的。社会存在着种种“抽血机制”和“输血管道”,源源不断地把财富从劳动者那里转移到其他社会成员那里。马克思等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所揭露的剥削(或对剩余劳动的掠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差别只在于剥削程度有高低之分,剥削方式有粗暴和巧妙之分。劳动者积极的或消极的反抗程度高一点,剥削程度就会低一点,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达到了消灭剥削、真正平等的状态。
5.劳动者支撑了整个社会大厦,但其社会地位最低,社会权利最少
即使在现代工业社会,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终日流汗劳动的人,不仅经济收入最少,而且享受不到政治权利、思想文化权利、社会保障权利,享受不到作为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他们的前辈——奴隶、农奴、依附农,情况就更为悲惨了。
6.劳动者人数最多,但却成为社会弱势群体
没有哪一个阶级或社会群体比劳动者数量更大了,但劳动者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全面地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仿佛像中了魔咒一样,默默地挣扎在社会的底层、下层,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上升到中层而已,除非他们摇身一变而成为非劳动者。
二、劳动者特征和处境的历史变化
以上对劳动者矛盾特征和矛盾处境的描述看起来是令人悲愤和悲观的。不过,也正是在这种矛盾的特性和处境中,孕育着新的萌芽和希望。
1.劳动者不仅保留了人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而且使之得到了新的发展
劳动者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核心、基础和腹地,非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劳动。只要劳动承担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功能和职能,它就必定成为人类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的熔炉、储藏所和助推器。一旦劳动者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被摧残殆尽,劳动就不成其为劳动了。从黑格尔对主奴辩证法的深刻论述中,可以揭示出劳动的这种陶铸人性的作用:正是在严酷的、艰苦的、被强制和压迫的劳动过程中,奴隶成为依靠自己的主体力量而生存和发展的人,倒是主人由于长期脱离劳动而坐享他人的劳动成果,导致其主体力量的衰退和萎缩,最后成为依赖于奴隶而生存的寄生虫。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运用暴力控制和镇压奴隶的话,他们早就会成为奴隶的奴隶,而奴隶就会成为这些昔日主人的主人了。
经过漫长的劳动过程的陶铸,从原始的集体劳动者,到后来的个体劳动者,从古代的奴隶和依附农,到近现代的工人,总的来说,劳动者的精神性、主体性、创造性、目的性是在不断提高的。马克思是资本主义最严厉的批判者,但他也看到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恩格斯肯定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一变化趋势:“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的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调动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随时可以利用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的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这种趋势并不是资产阶级大发善心的结果,而是由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决定的,资产阶级只不过是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了这种规律而已。
2.劳动者的自由自主性、自我实现性和个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虽然迄今为止,劳动者的需求结构总体上仍然以物质需要等较低层次的需要为主,但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锻造成长的巨大的主体精神潜能和创造潜能也正在转变为一种内在的、必须得到满足的需要和冲动,并且要求作为目的而得到实现。在现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劳动者要求作为“自我”、作为“个人”而得到表现和实现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使仅仅把工人当做工具和资源加以开发和使用的泰罗主义和福特主义的管理,向更多地重视劳动者的人性尊严、自主和创造、参与权、发言权的后泰罗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管理转变。劳动过程的人性化、雇佣关系的人性化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不仅如此,劳动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自由时间大大增加——工时的一再缩短就是证明。在这些自由时间里,劳动者可以摆脱谋生的强制性而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才能和个性。实际上,不是劳动者的日益贫困化和由此产生的革命要求,反倒是他们在主体力量和个体力量上的发展,才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实际上,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最早看到了这一点:“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挥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出发,完全可以得出另一种不同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资本主义的改造路线,从更高的人本主义要求出发改变资本主义的劳动制度和生产关系。
3.劳动者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地位和权利有所提高,弱势状况有所改善
奴隶的命运比被杀甚至被吃掉的俘虏要好一些,依附农的命运比奴隶要好一些,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劳动力所有权的工人的命运比依附农要好一些,这些都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资本主义经济不同于此前任何一种经济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资本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就要全面而深刻地开拓整个自然界,就要大规模地发展和利用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为此,就需要大量能够运用和操作先进的生产工具的劳动者。不言而喻,工厂工人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所拥有的劳动生产力和所达到的劳动生产率,远远地高于此前的任何劳动者。工人在劳动和生产过程中客观地位的提高,加强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可以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资本的扩张和利润的增长依赖于对市场的横向的和纵深的拓展,而市场的实质和核心就是有购买力的需求。没有这种有购买力的需求,所有商品都会因为其价值得不到实现而变成废品,投资者因此也会血本无归。劳动者人数众多,是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最深广的“市场腹地”,如果他们仅有需求而无购买力,市场的规模和深度就会急剧萎缩。因此,资产阶级即使毫无人道主义动机,仅仅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也要不断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和实际的购买力。这样一来,劳动者即使在社会财富这整块蛋糕中所分割到的比例并不公平,但其绝对总量却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工人阶级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状况也在不断改善。19世纪下半叶,在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落实了工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社与集会权、言论与出版权、罢工权等一系列政治权利。到了20世纪,劳动者基本的文化与社会权利又得到落实,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教育、劳动保险、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立法和执行体系。二战以后,这一体系得到加强和完善,以至这些国家自称为“福利国家”和“社会国家”。
无论劳动者还在遭受多少剥削和压迫,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劳动者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不仅在主体力量方面,而且在客观社会地位方面,劳动者所取得的成果,几乎超过了此前全部历史发展所取得的成果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