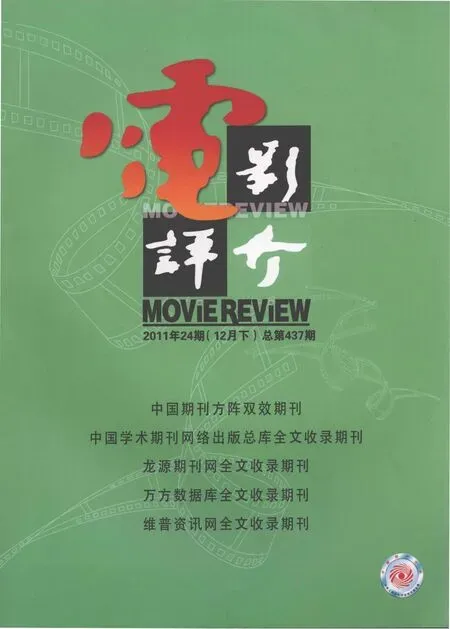男权意识掌控下的女性生存状态——《全球热恋》解读
2011-11-16广西大学胡
广西大学胡 媛
“男权中心”一直是男女两性关系的最初解读,随着社会发展,这个矛盾也由之前赤裸裸的表现形式转变为内在的隐藏形式。然而不管这个形式是显相还是隐相,我们发现“男权中心”的本质没有变化,哪怕是在今天,女性地位得到极大提高的情况下,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仍以其他的形式出现,或赤裸裸,或若隐若现,或暗藏不露。通过男女两性在《全球热恋》中生存状态的分析,我们发现,所谓的“热恋”只不过是男性在“爱情面纱”的掩盖下对女性的继续奴役,而女性在“爱情”的掩饰下,节节败退,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场没有自我的奴役。导演站在男性的立场,以男性的眼光塑造了男权意识掌控下的女性形象,在男权的掌控下,她们的生存状态直接证实了“男权中心”从未消失过,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罢了。
一、大宝:拔刺的玫瑰
大宝最终成为一朵无刺的玫瑰,这是导演塑造的银幕形象,也是女性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男权意识形态中“自愿而又无意识”地陷入了男权设置的女性形象的想象中。大宝代表了那些有文化有主见有理想的女性知识分子,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在男性导演的意识形态中,她们同样难逃传统男权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
大宝与迈克的戏虽不多,却是影片中最具张力和感染力的表演,它直接带动了接下来的两个爱情故事。故事很简单,两个相爱的人因误会而分开,两人虽身处太空并朝夕相处,但是同样倔强的性格让彼此不肯先低头道歉。不管是故事本身的设置还是人物性格的塑造,大宝无疑是女中巾帼,就凭她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宇航员来说,她的能力以及处事的沉着冷静,足以证明她的才能和卓识。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子,她可以为事业把爱深埋心底,可以为了面子拒不先道歉,可以为了尊严而不轻易掉泪……然而她的倔强、好强、不屈在迈克似梦似醒的梦呓中慢慢地瓦解。她明知道没有刺的玫瑰就不再是玫瑰,但是在迈克给她一次生命机会的时候,之前所以的坚持与矜持开始溃不成军,她生命的全部和意义就在于:“给他生个孩子”、“给他洗衣做饭”,以成全男人的生命和价值。在这里,我们分析一下男权中心是如何消解女性的自我意识而甘愿沦陷的。迈克对大宝的爱,“从未在清醒的时候,认真说一次”,只是在似梦非梦的状态中不断地述说,这对于深知其性格的大宝而言,再相比自己死守金口的态度,大宝无疑是被感动了,至少知道他还是爱她的。然而单有感动是不行的,这还不足以让大宝拔完身上的刺,回归到迈克所要求的贤妻良母。于是在爱情的最后,两人在太空舱外作业时,大宝的安全带脱落,飘出太空时,迈克为了救大宝而放弃了生命……故事到此达高潮。不管迈克是为了爱放弃生命还是无私的舍己救人,不变的是迈克的形象骤然崇高、伟大起来了,他成了无私的捐赠者。波伏娃认为“男人在梦想自己是一个施予者,解放者和救世主时,仍渴望女人服从……征服比馈赠或解放更令人向往。”[1]在这,男权制与时俱进,以“馈赠”的形式实现了对女人“文明”的征服,由此获救的大宝在无意识中接受了迈克的馈赠,也就接受了男权的安排,因为这个生命是男性赋予的。所以大宝回归传统家庭是必然的,因为生命是由男性“馈赠”的。
透过大宝与迈克的爱情故事,不难发现大宝在迈克的攻击下其感情是怎样发生微妙变化的:抗争——容忍——妥协,得出相对应的结果:分手——发展——相爱。由此透露一个信息,女性的挣扎是无为的,只有肯向男人低头善良贤惠的女性才能最终得到爱情或者说幸福。在男权意识下,男性以其“崇高”,倒压女性的柔弱和娇小,女性无处可逃,只能回归男权制下的正统世界,这才是女性的唯一出路。诚如玫瑰,必须拔完身上的刺才能温顺不扎人,然而没有刺的玫瑰还是玫瑰吗?
二、二宝:失香的玉兰
二宝一出场,就以一个洁癖症者的姿势控诉男人的罪恶,她是一个以其说被爱伤害不如说是被男人伤害的女人,可见女人在男人的世界里,一开始就溃不成军。受伤的二宝由此衍生的洁癖症不仅拒绝了爱情,也拒绝了这个世界,她把自己包裹起来,包括玉兰花香。二宝代表那些被爱伤害过,但仍渴望爱情的女性在男性救赎下,获得了重生但最终成为他人的被包装物。
然而世事难料,患有洁癖症的二宝爱上了一个捡垃圾的男生,在这场貌似滑稽的博弈中,二宝陷入了两难中:爱与不爱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艰难抉择。她去看心理医生,重新学会说出“I LOVE YOU!”,但那只说明她心中还有爱也渴望爱。当回归到现实,捡垃圾男朋友与她的意识理念中的“干净”形成了强烈的冲突,而这又不是她所能控制时,她退缩了,她克服不了洁癖对她的控制。但是垃圾王男友没有放弃对二宝的爱,他一遍遍告诉她,他对她的爱,她可以克服这个病症,躲在角落的二宝听得热泪盈眶,在这,男人用语言成规来构筑他们的王国并使之实现。于是二宝开始了自残式的尝试,把那些自认为肮脏无比的颜料往身上涂,经过努力,二宝克服了洁癖症。带着欣喜去找垃圾王,却发现他在约会另一个女孩,故事到此陷入了低谷,伤心欲绝的二宝离开了美国唐人街回到了中国。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垃圾大王一路追随,追到了中国……故事到此皆大欢喜,然而在结局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爱情的伟大治愈了二宝的洁癖症,垃圾王的爱给了二宝第二次生命。果真如此吗?表层上是这样,而深层境遇下,影片却传达了这样的意识:男人是女人的救赎者,只有男人才能把女人从水深火热中就出来,没有男人的救赎,女人其他的一切尝试都是枉然。而女人呢?在男性拯救的过程里,她愿意为他改变自己,因为没有他的救赎,就没有她的重生。诚如女权主义作家说的,“两性中总有一方是包装物,另一方是被包装物。”[2]无疑,女人是那个被包装物,因为女人要靠男人的拯救才能实现真正的完整性,作为回赠,女人必须改变自己,适合包装物的款式。哪怕这个包装物奇臭无比,作为香气熏人的女人也要装进去,玉兰与垃圾王不正是这层意思的呈现吗?
纵观二宝和垃圾王的爱情故事,男性是如何包装女性,并最终使之成为他的被包装物的呢?在影片里,二宝的感情经历了:彷徨——尝试——退缩——尝试——改变。第一次尝试是二宝为爱的自我尝试,结果失败了,第二次尝试,是垃圾王介入后二宝为爱的再次尝试,结果成功了。两次尝试都是“以爱的名义”进行,而男性主体介入与否成了事件成功与否的关键,男性直接主导了事情的成败。女性成了一个展现男权制的载体,她是一朵玉兰,但是她只是男性的附带品,是为了适应男性要求而存在的被包装物。
三、小宝:退色的牡丹
银幕红人黄牡丹一直活在与现实脱节的表演中,从经济人到司机黄叔,他们直接掌控着黄牡丹从人生之路到现实生活的走向。以致一开始,小宝(黄牡丹)就走得步履维艰,她渴望突破男人的包围圈,找到真实的自己,然而她走出了这个包围,却陷入了另外一个重围。小宝的爱情故事是典型的男权中心对女性的野蛮的占有和控制,是男性无从解脱现实、文化困境后转移对女性征服的表现。
当红花旦小宝遇到落魄书生闻风,爱情之火不点自着,他倾慕她的清纯,她仰慕他的真实。然而她只是为了体验平民生活,想找回一点真实自我才来到咖啡店打工,而他确确实实是生活所迫,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分离。她最终还是回到了舞台,而他一直痴痴地等待她归来,却不知她就是当前银幕红人。当谎言揭穿,他歇斯底里地指责她欺骗了他,她惊慌失措地求原谅。好戏才刚开始,就已经弥漫了一层男权意识:作为男人,闻风可以气急败坏地斥责小宝,而小宝如一只受惊吓的小鸟,蜷缩在无望的舞台上。我们追问,闻风一个连自己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文弱书生凭什么理直气壮地指责舞台红人小宝呢?而小宝为什么如此惊恐呢?影片没告诉我们原因,而透视故事的整个过程,我们发现男人对女人生来是享有“特权”的,对女性的占有是男性的“专属”,不需要理由,哪怕是男性处于经济的弱势,他仍觉得自己高于女人一等。影片在无意识中彰显了传统男权的专横霸道:男性生来的优越感就应该高高在上,而女性就应该卑微地活在男人的视野里。影片最后的安排:小宝为爱放弃舞台放弃事业放弃了自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男权对女性的绝对胜利、绝对占有和绝对霸权。在看似大团圆的形式背后,隐藏了赤裸裸的男权欲望,是对女性自我的直接抹杀。
牡丹的火红与鲜艳在男性视野中是淡色的,这层冲淡是男性的强权描绘也是女性的自我放弃。小宝经历了:突围(男性世界的包围)——独立(真实的自我)——沦陷(放弃自我)的情感经历。而这段看似美好的爱情,完全是放在男性对女性的霸权上,是对女性从思想到意识的完全霸占。
纵观三姐妹的爱情故事,我们发现,男性总渴望按照自己的欲望、眼光、思想等塑造符合规范的女性,不管是“玫瑰”、“玉兰”还是“牡丹”,女性所具有的本质在男权控制下全部消失。我们一直在探寻和追求的两性平等关系仍然不存在,女性生存仍然在男性视角和男权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如果早前是赤裸裸的暴力性男权控制,那么到现在,在《全球热恋》中它则以媒介传播的方式传达了男权的意志,含旨女性在社会中的挣扎和反抗是一种无为的表现,或者说导演根本没有给女性任何反抗的机会,而是以“爱情”作为掩护,直接宣布了男权对女性的占有和胜利,使女人的臣服成为现实。而“‘新女性’(一个历经一世纪已然消失的称谓)现代社会中女性便只能是现代男人等而下之的复制品与摹本。” [3]
[1] (法)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