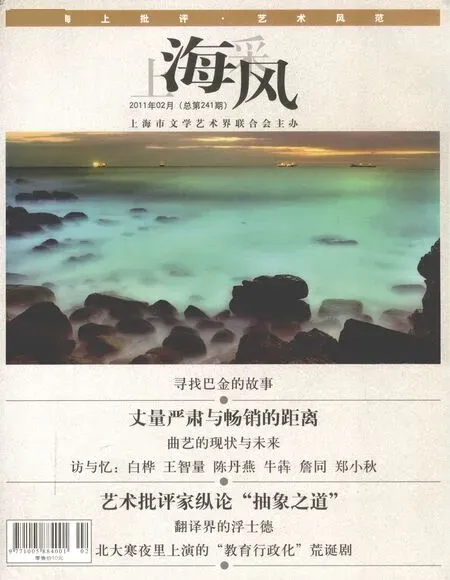王智量:一本书,半辈子
2011-10-18刘莉娜
文/本刊记者 刘莉娜
王智量:一本书,半辈子
文/本刊记者 刘莉娜
王智量
1928年出生,江苏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理论研究,1985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主要翻译作品有《叶甫盖尼·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黑暗的心》《我们共同的朋友》等,编写有《外国文学史纲》《比较文学三百篇》等,并创作有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等。

我做过很多采访。每次在去被访者单位或者住宅的路上,虽然人已经离开了编辑部,可是心里多少都带着些工作的情绪,心心念念着选题选题;然而去采访王智量先生却有些不一样:先进得华东师大熟悉的大门,再经过文史楼前阳光融融的草坪,然后从出版社那个路口转弯,就进了师大一村,上楼,进屋,对笑眯眯迎上门来的老先生叫一声“王老师”,一时间人也恍惚了,仿若自己还是当年那个师大学生,心里莫名的就松弛和快乐起来。
今年已经八十多岁的王老先生看起来非常矍铄,性格也很是爽朗,常常说起自己做右派下乡改造的笨拙事情就哈哈大笑,可是下一秒钟说到父亲母亲却因此为他拉扯幼子艰辛度日,最后竟在上海饿病而亡时,他几近哽咽,毫不掩饰地差点哭出声来;而正当我为这一笑一哭如孩子般天真纯粹的情绪不知所措时,他却擦干眼角又笑了,说:“我年纪大了,已经应该忘记很多事情了,现在我只想记得那些经历中快乐的那一部分。”我问他,那么你会忘记为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所经历的艰难么?他正色说,“这本书是我在六十一年前(1950年)开始阅读,五十五年前(1956年)开始翻译,四十九年前(1962年)译出初稿的。后来又经过多次修改,过了整整二十年,直到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出书的。直到今天我也常常会翻看和斟酌它。它是贯穿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五十年的一本书,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五十年变迁,我永远不会忘记与之相关的一切。”
1956年,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刚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陆定一代表中央所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报告,大家都意气风发,跃跃欲试。中国作家协会在酝酿创办两个刊物,一个搞散文,一个搞诗歌。散文刊物的创办任务是交给何其芳先生的,他当时是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而30岁不到的王智量正在他手下工作。一天,在谈论一份稿件时,因为其中写到普希金,何其芳先生随意地说起自己最喜欢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青年王智量便顺口用俄语背诵起其中的诗句来,何先生对此特别惊讶和赞赏,于是鼓励他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当时我还只有二十多岁,虽已走上俄国文学专业道路,但是还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也不曾译出任何一部大的作品来,《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文学的皇冠,我怎么敢初出茅庐就去触摸它?”王智量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和心情如实地告诉了何其芳先生,没想到何先生却对他说:“我是认真说的,你翻嘛!你能翻!全中国有几个能把它从头到尾背出来的人?你怕是第一个。你能翻!”停一停,何先生又说:“胆子放大,态度老实些,多花些工夫进去,你能翻得好,不要怕!”正是何其芳先生这番语重心长的鼓励,让王智量觉得不容辜负,于是开始了他《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漫长翻译历程。
然而几个月以后,也就是在1958年的初春,当王智量翻到第二章的中间,大约只译出六十几节诗的时候,大难临头了—— 他被定为了右派分子,“白专道路”是他的罪名之一,他悄悄进行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亦成了批斗会上一个具体的罪证。我相信那一刻所陷入的巨大痛苦和迷惘一定深深刻在了他的灵魂深处,因此即使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谈起这一刻,王老先生依然双目含悲,他说:“我那时候的处境,用十二个字可以概括——妻离子散,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我茫然不知所措,原先痴心追求的一切都顾不得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更是不得不忍痛丢在一旁,不敢再去碰它。我被划为三类右派分子,工作、工资……都没有了,还要被送去下放改造。”
正当王智量心灰意冷的时候,还是何其芳先生给了他坚持的勇气。1958年的5月,就在王智量要被送往河北东部太行山区改造的前一天中午,他在空无一人的厕所里“碰到”了何其芳——至于是偶然还是特意,他到如今也不清楚,可是那一天的一切却依然历历在目。“那天天气炎热,中关村科学院社会楼第三层里安静极了,好象除了我这个等待被放逐的坏人以外,一个好人也没有。我坐在原本归我使用的研究室办公桌前,桌上和抽屉里已经一无所有,我面前的墙壁上贴着一张不知是哪位革命左派同志写的、勒令我老老实实去劳动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大字报。这张桌子和这张大字报在告诉我,我从此将永远不能再和我心爱的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有任何关系,我心中苦不堪言,感到万念俱灰。”周围空间里的一切都那么触目,让他倍感压力,为了逃避和舒缓情绪,王智量跑去了无人的厕所,可正在这个时候,他感觉有人随后进来了。
“我(因为自觉自己是坏人)头也不敢转一转,眼睛更不敢斜视去看他,可是我忽然就感觉到,他一定是何其芳!我多想跟他说一句话啊,至少是对他说一声再见。可是我不敢。他是所长,是所里的反右派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好人们和我之间的界线是划得分明的,连楼里的勤杂工对我都不予理睬,更何况是他。我动也不敢动,心中只盼他赶快走掉。而同时又真希望他不要走掉。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处于十分紧张难受的状态。”而先开口说话的正是何其芳。让当时的王智量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在那种时间,在那种地点,何先生低声地、匆促地、也是认真而严肃地,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自己说了这样一句话:“《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时隔五十多年,王智量在回忆这句话的时候仍然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出那种四川口音,我想,这句话,这声音,已经深深刻在他的心里了吧。说到这里,王智量说还有一个细节他也总忘不了:就在说完那一句短短的匆忙的言不尽意的话以后,何其芳立刻昂起头,作出似乎并不曾理睬过自己的样子,转身走出厕所。而在他临出门的那一顷刻间,“我看见他先是探头向外,看看走廊里有人没有,然后才若无其事地大步地走开。”这一刻老人与我无言对视,我想,我们都想到了一些复杂又无法言说的东西,关于勇敢,关于软弱,关于正直,关于曲折,关于善良,关于险恶——人性是多么复杂的东西。而那一刻的青年王智量自然是被勇敢和正直的力量感染了,他好像忽然感觉到万念俱灰的黑暗处境里有了一线光亮。“他的这句话在当时对我是一个让我重新直立起来、勇敢做人的精神支柱。我过后越来越理解到,在当时,对我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在他又是多么的勇敢,承担着怎样的风险啊。他不正是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吗?我不正是一个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阶级敌人吗?我觉得,其芳先生为人的一颗善良之心,他对当时反右运动中的一些观念和做法(也就是当时的政策)在内心深处的判断和评价,在他对我所悄悄说出的这一句话中,全都坦率无遗地表现出来了。”心头的激动催出他眼中汹涌的热泪,从厕所奔回研究室,年轻的王智量俯在他已经空无一物的写字桌上痛哭了一场。哭过以后,他回到宿舍,打开已经封存的书箱,取出俄文普希金全集第五卷(有《奥涅金》的那一卷)和已经译出的部分稿子,把它们塞进第二天下乡要带的行李中……
于是,下放到乡下改造的那些日子,他都是一边干农活,一边心里在默默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说起这些艰苦的日子,王智量却一脸神往的笑容:“我现在一闭上眼睛,还能清晰地看见,在太行山麓那个名叫小米峪的山村外,有一天,在蓝天白云下,我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刚刚种下旱稻稻种的田垄(为了把土踩实),一边借助这一动作的节奏,默念着《奥涅金》中四音步的诗行,再一句一句地把原诗在心中翻译成中文,也要它和着我脚下的节奏,均匀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来……”是的,那样的劳作应该很苦,可是我听老人这样舒畅地娓娓说来,却分明洋溢着一种温柔的幸福感。经过白天的推敲和酝酿之后,到了夜晚,他再把白天想好的译文写在从墙上撕下来的糊墙报纸上,报纸不够了,就写在卫生纸或香烟盒上,总之,利用手边一切可以书写的小纸片,王智量始终坚持着他的翻译。“直到1960年底,当我失去了干部身份、健康、甚至户口等等,只剩下头上一顶右派帽子来到上海时,我随身的行李是一袋书和一只盛满各种各样碎纸片(都是一节节《奥涅金》的译稿)的手提包。我到上海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已经全部译出的《奥涅金》整理抄清。”
细节总是让人难忘,半个世纪过去了,王老先生还清晰记得当时用的纸张,他饶有兴致地说:“记得我用的是一种像土制卫生纸似的非常粗糙的纸,当时我只买得起这样的纸。我抄了两份,一份寄给其芳先生,一份作为投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自己留下的‘底稿’则是那堆不成样子的零碎纸片。” 然而磨难和考验并没有结束,接下来又是十年“文革”。文革中寄出去的稿子自然杳无音讯,而等这场大运动结束后,出版社给王智量的答复却是,这场浩劫里,许多稿子都没了,“我们也没法负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的国家又需要文化了。大约在1980年前后,有关方面计划重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在考虑《叶甫盖尼·奥涅金》采用哪个译本时,我国研究俄国文学和普希金的老一辈专家、一向关心后来人的戈宝权先生为“前右派”王智量的译文争取到了一个“那就拿来看一看吧”的机会,这一看,就是它了。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终于从文革劫后的残余文稿中找出了王智量当年投寄给他们的《奥涅金》译稿,带来上海让他修改。也是这一年,当时的中央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王智量终于从《英汉大辞典》编辑部的临时工转为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他在本职工作之余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对译稿再做加工,次年,这部历经磨难的译本终于出版问世了。
用了几乎一个下午的时间,坐在王老先生并不宽敞的小客厅里,我觉得我听完了一个无比曲折的故事——那些荒谬的遭遇真像故事,那么不真实——原来一本书的背后,会有一个人为了一种信念,承受了那么多凌厉的打击,而哪怕只有一次他放弃了,我们看到的都不会是眼前这一本。
——我觉得我要好好再读一遍《叶甫盖尼·奥涅金》。
book=52,eboo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