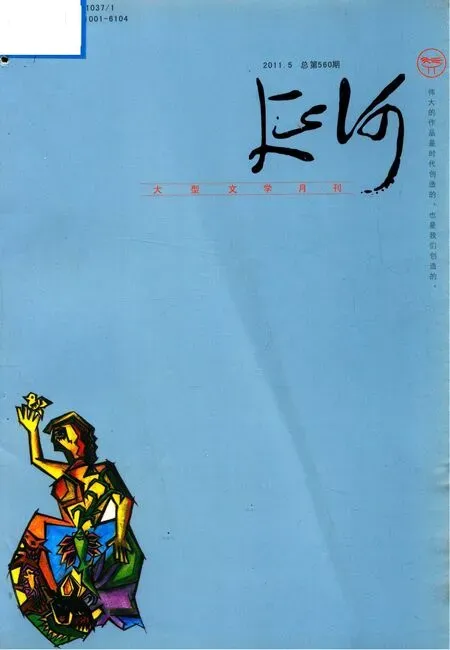蛤蟆镜
2011-10-09小昌
小昌
蛤蟆镜
小昌
1
我很想看到她的眼睛,她却戴了一副蛤蟆镜。镜片很大,里面能看到我小小的影儿,当然还有高楼和天空。高楼在我的后面,天空在我的头顶。我们握手,说话。
她的上嘴唇很薄,弯成弧形。我知道她很想给我一个顽皮的笑容。
她说,应该抱一抱。我躬身上前,贴了上去,可还撅着屁股。
三天前,她联系了我,一听到她的声音,我才发现日子过了那么久。三个月前,我做了一场春梦,她在我身上像马儿一样欢快,醒来后看见另外一个女人躺在我身边,我很愧疚。三年前,我跪在她的面前要她留下,她不停地摇头,我从她身边站起来,决定跟她老死不相往来。三十年前,我刚刚出生,她还没有出生……
我又多愁善感起来,咖啡烫了我的舌头。她就活生生地坐在我的对面,她刚才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只好问她。

白壁 王济远 1920年代 油画
她问,丁当好吗。
丁当是我梦见她时,躺在我身边的另外一个女人,如今是我的妻。
我说,不好,老毛病还没改,又有了新毛病。
她笑起来,双肩颤抖,蛤蟆镜想要掉下来。她说,你还是那样喜欢挑别人的毛病,老毛病也没改呀。
我说,你能不能把眼镜摘了。
她的眼睛有些浮肿。我说,我以为海枯石烂也见不着你了。她说,你为什么不去找我,也许我一直很想看到你。
跟你一起的时候,天天找你,找烦了。她说去你的。
长久没有话。
她又问,有小孩了吗?
我说,天天想,丁当不想要,说一生孩子艺术生命就结束了,你说一个破舞蹈老师哪来的艺术生命。
她笑了两声,又马上收住了,额头上残留了几道细密的皱纹儿。我继续说,找一个跳舞的女人做媳妇,唯一的好处是她能用脚趾头指着你的眉头,她从不用手指。我竖起中指接着说,她只消身子一动,腿一抬,大母脚趾就点住了我的眉心,紧跟着一句呵斥,戴上。
她问,戴上什么?
我说避孕套。她捂住了嘴,周身都在抖动。我也跟着她笑。下午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漫过来,落在我们中间,像点起了一道火焰。
她突然说,我是不是老了。
我忙回答,怎么会呢,才过了三年。她叹了口气。
就跟上辈子一样,你知道我常想起哪个场景吗?我说是不是小旅馆里的209。你还是老样子,不改初衷,我们在学校后门埋头吃羊肉串,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只记得小旅馆,你能吃好多羊肉串,我从此再也没见过那么能吃羊肉串的人。我说那是因为你再也不吃羊肉串了。
真的像过了一个世纪,她说。
难道我给你的印象就是呆在209里的模样吗。我说不全是。她问还有呢。我接着说最后一班公交车。她又问什么公交车。
我说,这都忘了,看起来你没有答应我留下来是多么英明,我们一起搭最后一班公交车,我记得是3路,人很少,你坐在我的旁边,你是不是真的累了,我一直很怀疑,你把头埋在我的怀里,等旁边的乘客都走光了,你解开了我的腰带,你。她打断了我,这就是我给你的全部印象吗,真惭愧。她把手伸出来,放在落满夕阳余晖的桌子上,戒指上的钻石发出微弱光芒。
我有些生气。
我说,好日子过腻了吧你,想在我这寻点开心,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日子是一穷二白,想要个孩子也无从下手,所以你离开我完全正确,我没有什么希望,在我这里你永远可以忆苦思甜。我越说越激动,舌头在口腔里开始发麻。
我说,这下满足了吧,但是我告诉你,我也不是百无是处,现在的我性欲特别旺盛,每天早上一柱擎天,估计这样的状态还会持续很久,不知道你们家那个老帮菜歇了吗。
我又说,I’msorry,触到了你的痛处了。说完我站起身来要走。她忙拉住我。
求你别走,她说。
我说丁当还等着我买卫生巾呢。求你别走,先坐下,她又说。
我一屁股又坐了下去。坐定后抬眼看她,有一滴泪水挂在左眼角上,将滴欲滴,楚楚动人。我说,分手的那天,我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我赶过来见你,完全是一个男人为了兑现诺言,没有其他的意思,更不想忆苦思甜,你说你需要我的帮助,那你说,快点说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拽住我的手,直直地望着我。她说,你不是想要个孩子吗。
我说,是。
她说,我为你生。
我说,什么。
她说,我为你生。
我说,我哪有这福气,消受不起。
她说,能换个地方再说吗。她的声音里有一丝哽咽。
丁当还没有回家,我的手机很安静。她不会知道我正跟着一个戴蛤蟆镜的女郎呆在名贵跑车里相顾无言。在出发前,我告诉丁当去见一个老朋友,她也没问究竟是谁。
丁当认识她,有时候也问我。我说我不知道,老死不相往来了。我想到丁当那时的古怪表情,就心生愧疚。戴蛤蟆镜的女人还在开车,她问我听点音乐吗。问完,音乐就响了起来,很熟悉的旋律。
丁当第一次说那个女人不好的时候,我刚从209的小旅馆里出来。我曾经跟我的朋友们戏言,209就是我包下来的总统套间,即使床板很硬,热水时有时无,还有残缺的窗帘。那个女人也跟着附和嘻嘻地笑。丁当在她背后说她不好,我只把那些话当小女孩的不良居心,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我当然知道丁当喜欢我,她的眼神老是那么咄咄逼人。我问丁当究竟怎么不好,她说不好说,她的意思是让我提高警惕,说完丁当就走了,那天还下着小雨,我想要送她,她说不用了,有人等她。
我和丁当老早就认识了,自然在那个女人出现之前。也有人撮合我们,我说要好早就好了,还能等到今天。她打断我,人家看不上。气氛有些讪讪。我冲她说,要是跟你好了,时间会过得很慢,生命就更加漫长了,我不想活得那么长。她就跳起来捶我,我们俩在桌子周围打得团团转,像两个孩子。
丁当第二次说那个女人不好,我就生气了。我说,你就看不得我幸福。她哭了。她说那个女人真的不好,我眼看着她上了一个男人的汽车,男人还亲了她一口。我说她居心叵测,她说,你要不信,我就再说得详细点,那个男人是个秃头顶。我说够了,打断了她的话。她站在我面前很委屈,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我有男朋友了,你好自为之吧。
丁当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一年,我也从来没有找过她。我不知道要跟她说什么。不过她的话是真的。
那个女人跟我好了几个月,又搭上了另外一个男人。她没有跟我分手,她后来说那不叫移情别恋,心还在我那放着。我相信她的话,她只是缺钱,她问我介意吗。我摸了摸她的脸,又看了看她的眼,说不介意。
我见过那个男人一次,是个秃顶。丁当说得没错。他跟我握了一次手,手大而温暖。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他们俩都很自然,谈笑风生,我觉得怪怪的,我要走,他们也没有拦我。我回头跟那个女人对了下眼,她也希望我走。
突然有一天,她说她要跟那个男人走了,再也不能见我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刚说完一个无聊的笑话。她就倚在嗡嗡响着的电冰箱门上,那台电冰箱如今还在,只不过响得更厉害了,我老说要换,丁当说还能用。她垂着头,不敢看我,我说,你还要再想想嘛。我又说,把头抬起来,看着我想。她没有,扭过头去看窗外。
我扑通跪了下来,我怎么会跪下去,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很想把她留下来。她流着泪拼命摇头,我也相信泪是真的。她说,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有一个位置,不可替代,但是我必须走了,再这样下去,我会疯掉,你太屈辱了,我又不能没有他。她说完我就站了起来,站在她面前,又抱住了她,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我说,我永远有个肩膀供你依靠。她伏在我的肩上抽泣。
我说,祝你幸福。她说,你也一样。
再后来,丁当出现了,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结了婚,丁当变了个样子,头发越来越短,脸却越来越胖,还常常用脚趾头指着我。我只是想要个孩子。
音乐戛然而止。坐在我旁边的女人拍了一下方向盘,就嚎啕大哭起来。我给她递纸巾,她又摘下了蛤蟆镜。
过了许久,她开始说话,断断续续。
她的话我懂了。我说,你不是为我生,事实上,是我为他生,你不就想借个种吗?
她问,他会不会杀了我。她的脑袋耷拉下来,落在方向盘上。
她推开车门下了车,我也钻了出去。太阳还有半个脑袋留在天上。我们一起抬头看,半个脑袋也能红透半边天。
我们站在护栏边,守着悠悠的小河。她指了一个地方给我看,我说能过去吗。她说没问题。她拉着我向前跑。
她让我先爬上去,然后拉她。两人并肩坐在一个透风的桥洞里,大声地喘气。我说,你还是跟原来一样。她没有回应,在衣兜里掏出一盒烟。问我要吗,我说已经戒了,她又让我替她挡风。
风很大。河水流动的声音没有节奏,闹得心慌。她用力抽了一口烟,脸紫了一下。她没有原来好看了,我有点伤心。
我说,你还是跑吧。
她说,他不会放了我,我了解他。
我说,他真的不行了吗?
她说,要行早行了,三年了,都没有动静。
我说,他都不行了,你突然大了肚子,不是自寻死路。
她说,那事他还行,估计种子发不了芽了。
我问她要烟,她又帮我点上。我不想做对不起丁当的事,你可以找别人的,想做这事儿的男人很多,还可以挑选,选个基因优秀的,我不行,我说。
她看得我浑身发冷。
我说,有了孩子就能得救吗。
她说,他不会害了孩子的妈。
我说,我老觉得没那么邪乎,你们不是有感情吗,可以好聚好散的。她回答,你以为是咱们俩可以好聚好散,他会要了我的命,我最近老做恶梦,在梦里他不是举着刀就是拿着枪朝我冲过来,太可怕了。
我说,也许你太敏感了。
她说,要只是敏感就好了,他现在一见到我就板着脸,生怕我会陷害他。她吸了口烟又说,他对那个老女人越来越好了,我是个累赘,而且是个危险的累赘,他怕跟我撕破脸。我问她那个男人不是早就要离婚跟你结婚吗,还没离成。她骂了一句,离个屁,说说而已,何况还有个女儿。
我唉了一声,看了她一眼。她突然双眼发直,冲着我跪了下来。连连叩头,说,你一定要答应我,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信任的男人了,求你了,我快没命了。
风扯起了她的头发,露出了干净白皙的脖子。我连忙拉她起来,她说不答应她就不起来。我颓丧地斜躺了下去,风贴住了我的脸,耳朵也嗡嗡地叫个不停。
我说,我答应你。
她扑过来想要抱住我。我推开了她,她蹲在一边。她说,我就知道你会答应我,你是天下最心疼我的男人,除了我爸,不过他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下你,你就是我的希望。
我说,我不是,我裤裆里的东西才是。她拧了一下脖子,说,有那东西的人很多,我只要你的。
我说,我得回去了,我要对丁当好点。她说,你等等。
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卡,指着我。她说,这里有张卡,事成后,密码送上。我推开那张卡,我说我不要。她呆呆地看我,说,你不要,我就跳下去,不活了。我说,你跳下去,我也不要,我不卖。
她说,你让我瞧不起,这是卖吗,我们要一起生个孩子。我说,放屁,我只是给你一个种,生根发芽都是你们的事。她没等我说完,就把卡硬塞给我。
她还说,这样我会心安。我说好,我可以走了吗。她说还有一句话,事成后,我们就真的老死不相往来了。
我从桥洞里爬出来,又把她抱下来,她冲我媚笑,说我还那么有力。我们越过护栏,她挽着我走向那辆车。
她说,我送你回去。我说,我们家那块地方汽车钻不进。她说钻到哪算哪。
我在车上问她,你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是不是猜中了我会答应。
她回答,我了解你。
到了胡同口,我说下车,她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要我等她电话。小汽车掉头一溜烟走了。天黑了下来,街边的路灯开始发光发亮。
回到家里一眼就看到了丁当。她窝在沙发里冷冰冰地看我。难道她知道我的行踪。我的脸热了一阵,又冷下来。你去见谁了,声音像从地板上冒出来一样。我说没见谁,她又问了一句,是不是去见她了。
哪个她,我说。心抽得紧紧的。
还有几个她,快说,除了给人做小三的她之外还有谁。
我向丁当走过去,伸出手摸她的额头。我说,没发烧呀。她说,你要敢做对不起我的事,小心我阉了你,快去盛饭。她眉开眼笑,身子扭了扭,就贴到了我的身边。
吃饭的时候,我问她,为什么又提起她,不说我早就忘了,又提醒我。她说,就怕你忘了,历史的教训要牢记。我刚想张口说话,她就把一块肉塞到了我的嘴里。我的额头一皱,眼眶一酸,差点挤出一滴泪。
丁当从卧室里走出来,一摇三摆,还穿了一件红色的肚兜。她今晚又想有所作为。我也快速行动起来,忙着好好配合她。
我一切就绪,蓄势待发,灯光慢慢变暗了。她身子一动,腿一抬,我知道她又来了。她的大拇脚趾在我眼前晃,像个狡猾的蛇头。我忙说,你看,都准备好了。大母脚趾又摇了摇,脱掉。
我想好了,我们得有个孩子。丁当说完,大拇脚趾就点了一下我的眉心。她又喊了一句好老公,一把把我拉了过去,玩儿命亲我。我颓在她的身上,想起了那个女人。
三年前,那个女人在209房间里,赤着身子迎接我,又举起红色的文胸使劲摇晃,口里嚷道,欢迎来到伊甸园,欢迎来到伊甸园,一声比一声高亢……
209折磨了我一个晚上。
第二天中午,我接到了那个女人的电话。她说今天晚上八点在香格里拉大酒店B209房间等我。又是209,她也知道209于我的意义。挂了电话,五分钟后她又发来一条短信,短信说,我会举着红色的文胸等你。
我看完就把信息删掉了,合上手机想了想。又把通话记录也删掉了。丁当打来电话说不回家吃饭了,我就草草煮了包方便面。吃完下楼溜了一圈狗,牵回来,它钻进窝里看我,像懂我的心思。我第一次发现家里的老狗很有思想。我拍拍它的脑袋,它仰起头来舔我的手指,像是安慰。
下午我站在讲台上,特别没有自信。说什么都感觉在胡言乱语。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个胆大的女同学问我是不是被丁当老师欺负了,我说,不要污蔑丁当老师,丁当老师是个贤妻良母,她听完半信半疑。
挨过了两节课,我从教室里溜出来,就给丁当打手机,告诉她今天晚上还得出去。她说别忘了回来,还让我保重身体。她说这话的意思今晚还要有所作为。我说好。回家换了衣服就跑到街上溜达,看了看表,6点半,还有一个半小时,我想找个地方吃饭。
万家又开始灯火起来,我脱掉鞋子光着脚丫踩在盲人的弹格小路上,向香格里拉大酒店走去。七点五十我大概就会出现在B209的房间门口,我先敲三下,再敲三下,有个女人的声音要问是谁。我说我是亚当。门吱扭一声开了,门吱扭一声又关上了,夏娃全身赤裸,手上举着文胸嚷着,欢迎光临伊甸园。脚硌得生疼,我开始兴奋。
我目视前方,前面就是香格里拉大酒店,我想在弹格路上跳跃。
突然两个高大男人走近我,分别挟住了我的左右胳膊。一个坚硬的像枪口样的东西顶住了我的腰。我的身子一软,眼神晃了一下,左边的男人开始说话,不要说话,跟我们走,否则要了你的狗命。我看了右边的男人一眼,他也说话了,看个屁,快走。
右边的男人劲很大,我夹在中间像个半身不遂。我说,先让我穿上鞋。他们俩停下来等我。我想跑,左边的男人又掐住了我的脖子,说,别动心思,你跑不了。
我的袜子才穿了一天就臭掉了。他们又用那硬东西顶住了我的腰。我说,你们一定是抓错了人。右边的男人说,没错就是你。左边的男人呵斥了一句,别跟他废话,老板还等着。我又说了一句,你们一定是抓错了人。我的后脑突然感到一次重击,万家就没了灯火。
醒来后,看到了一盏灯,照得我眩晕。我要动动胳膊动动腿,才发现我被捆成了麻花。我想我玩完了,这是绑架。我首先意识到那个女人给我的卡,可我没有密码。我又想到丁当,可怜的丁当还被蒙在鼓里,也许正窝在沙发里看电视剧。我定了定神,看清了周围。周围是一个破旧的公寓,比我们大学里分到的房子还简陋,墙皮斑驳,像一道道伤痕。
有两个男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放着新闻,很有家的气息。我看不清他们的模样。我不能再傻呵呵地束手待毙,我说,我要喝水,他们没有反应,我又喊了一句,我要喝水。他们俩一起站了起来,又走向我。就是他们俩个把我挟持到这里。
电视里的新闻结束了,开始播放广告。
其中一个男人很胖,眼睛眯缝着,长得很可爱。他打开手机,按了一会又合上,接着从桌子上拿了一把刀。另一个男人冲我笑,嘴角上还有酒窝。
我被死死绑在一把椅子上,胖男人拿着刀子在我面前晃了两下,让我老实点。我说,你们是谁,你们想要什么。
有酒窝的男人胳膊一抬,我就吃了他一个耳光。半边脸没了,一只耳朵叫了起来。他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就要你的实话。我说,什么实话。胖男人胳膊又一抬,另外半边脸也没了,另一只耳朵跟着叫了起来。左右声道都有了,像吹了一阵凛冽的寒风,寒风过后就灼灼得疼。他说,别他妈跟我们装糊涂,说说昨天你都干嘛了。
我说,你们是谁。
有酒窝的男人又想抬胳膊,被胖男人挡住了。胖男人问我,你昨天是不是见了个女人。我明白了几分,愣了愣神。那个女人说她要死的话也许是真的,这里面有阴谋。我也被卷进去了,怎么办,可怜的丁当,你的男人正在受罪。
胖男人拿刀柄敲我的脑袋。他说,想什么呢,快说,你是不是见了个女人。我想我不能说,说了更糟。
我横了横脖子,说,我是见了个女人,还跟她睡了觉。胖男人说还睡了觉,又用刀柄敲我的脑袋。一下比一下坚决。我说,是,那个女人我天天见,她就是我老婆。有酒窝的男人差点跳起来,顺手又打了我一个耳光,嘴里嚷着,操,你他妈敢耍我。
胖男人看了我一眼,刀在我脸上滚了两滚。他说,我能要了你的命,信不信。刀又滚了两滚。
我尿了裤子。
有酒窝的男人说,给他点厉害尝尝吧,狗日的嘴还挺硬。胖男人点头。他去拿了个东西又走到我的身后,掏出我的手。他又把一根钉举到我的眼前。他说,再不说,就把它扎进手指里,像这样的钉子可是多的是,你不就才长了十根手指吗。
我哭起来,眼泪从来没有这般汹涌。我泣不成声。有酒窝的男人放开我的手,站了起来说,怂了吧,快说。我说,我能先喝杯水吗。有酒窝的男人就去给我倒水了。
他端着水杯往我嘴里倒,水有些腥咸,也许有血有泪。
我喘了几口气说,我是见了个女人,那个女人也许就是你们说的那个。
胖男人说,她跟你说了什么。
我想还是不能说,说了更糟。也许真得就回不去了。
我接着说,她是我的老同学,她说她有点失眠,问我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在大学里我就是个出色的心理辅导师,谁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都找我倾诉。
胖男人又问,还说什么了。
我说,后来我就告诉她很多治疗失眠的办法。
他接着问,就这些。我说就这些。
他问,今晚你是不是去见她。我答,有光着脚丫子去见美女的吗。
有酒窝的男人插了一句,又在狡辩。他弯下腰抓住我的手。扎吧,我活该,你们扎吧,扎也只有这些。钉子挨到了我的手指,我皱起了眉头。
卧室的小门突然开了。
那个女人走了出来。她依旧戴了一副蛤蟆镜,让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她冲我拍起了手。
我说,你他妈混蛋。
她让那两个男人为我松了绑,我又说,你真他妈混蛋。两个男人扭头走了,关上了房门。电视里放起了电视剧,正是丁当每天晚上看得那部。
她躬下身子单膝跪在我面前,一面哀求一面摸我的脸,求你原谅我,三年了,你一点也没变。我推开她站了起来,两条腿筛了筛,走到那边把电视关上。回头看了看她,我说,老死不相往来。我拉开了门。
她跑过来又拽住了我的胳膊,蛤蟆镜里有我变了形的脑袋。我说,能不能摘掉你那狗日的眼镜,看看我这张被吓黄了的脸。她拉住我的胳膊,摇了摇,让我坐回去。我说沙发不敢坐,还是坐在受刑的椅子上吧。我坐了上去,翘起了二郎腿,才发现裤子湿了很大片。她把蛤蟆镜摘下来,又单膝跪在我的身边。
她说,你没有变,你还是那个三年前的你,我相信你。我说,我不相信你。她把胳膊肘支在我的腿上,她说,你相不相信我,不重要,但你要知道,我永远不会伤害你。我说放屁。
她说她只是害怕受到伤害。
她说三年过去了,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看了看表,快十点了,丁当还在等我。我说我得走了。我站起来,她还拽着我。她说,你原谅我了吗。我说回去好好想想。她说她要送我。
我没让她送,她却从后面抱住了我,口口声声求我原谅她,还说明天晚上会在B209等我,像三年前那样。
我头也没回地走了。
丁当躺在床上等我,说我身上有骚味儿,是不是见了不该见的人。我心想尿了裤子能不骚吗。她在床上穷折腾,咬住了我的嘴唇,咬出了血。松开我后,就质问我有没有撒谎。为了搞清楚我有没有撒谎,她一直说到半夜。该做的事没有做成,天就亮了。
太阳又出来了,明媚得吓人。我给学生们讲课,声音嘶哑低沉,像一口破钟。有一对男女坐在后排,趁我不注意互相调情,我的余光看到了他们。我没有制止,他们的行为令我羡慕。我在上学的时候就很想那样做,可是一次都没有做成。我一边照本宣科,一边回忆过去,我把头低得很低,像个罪人。
突然一声响彻的“滚”若秋风扫落叶般响起。余音还在绕梁,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同学一跃而起,大步流星逃了出去,又使劲关了一下门。我傻了一阵。同学们也傻了一阵,都在看我,我笑了笑说,继续上课。同学们很不满意闻惊雷而面不改色的我,开始交头接耳起来。
我说,别大惊小怪。
话音刚落,一个男生从后排站了起来,像个麻花扭了两扭。跟我说,老师,我怕她出事。我嗯了一声,他就像箭一样冲了出去,留了个大开的门。
教室再也没有安静下来。
一天下来,我接到那个女人三个电话五条短信,言辞唯诺,语气暧昧。下午我在校园闲逛,看到了女院长,她没有穿内衣。我对她笑了笑,从她身旁走过,一朵白云就横在了我的眼前。那一刻我做了决定,打开手机给那个女人发了条短信。
到了晚上七点半,我又出发了。香格里拉大酒店就矗立在我的面前。
2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一个月多几天,那个女人打电话告诉我她怀上了。我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说她要请我吃饭见最后一面,我告诉她没有必要,别弄巧成拙让人发现。她说必须见,不见就成了过河拆桥。我说见了也是过河拆桥。
她说很惭愧。我说我也很惭愧,她问我惭愧什么,我说丁当没怀上。我说这话的时候,想起了配种站,我原来一直以为那些骑在母兽身上的公兽幸福得让人羡慕,如今才发现它们都很疲倦,不一定快乐。这一个多月我有了它们的感受。
我把这种感受又在电话里告诉了她,她笑得差点挂了电话。我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我接着说了很多话,有点形而上,不像我说的话,我说我知道了什么叫成熟,成熟就是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但又发现没有那么美好时的感受。她却跟我理解的不一样,说成熟是你得到了你不想要的却发现如此美好时的感受状态。我说也对。
她好像有些累了,她说见面再说。绕来绕去,我又答应了她。
丁当没有怀上,感觉很懊恼,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应该去医院做个检查,万一有个好歹,及时发现及时处理。我反问应该没问题吧。她说,你怎么知道没有问题。那个女人刚刚打来电话说怀上了,而且是我的种,我确信我没有问题。可我冲丁当做了个鬼脸,赞成了陪她一起去医院检查的建议。她撒起娇来,好老公,下午帮我买卫生巾,老牌子,我又来了。
她还说让我好好休息几天,新一轮的战斗快要打响了。我坚定地冲她点了点头。在她转身离去的时候,突然有个问题冒出来,丁当最近在忙什么,老早出晚归。
我买好了卫生巾又去见那个女人。不像头几次见面就脱。她又戴上了蛤蟆镜,斜阳映在镜片上,有点苍凉。我坐在她的名贵跑车里,摇下车窗,风吹着我的头发,甚是惬意。音乐又响起来,很欢快。我喜欢上了这种气氛。
我们驶向郊区,驶向田野,又从田野转回郊区,又回到城市。城市的灯就亮了起来。她问我要不要做点什么,我说还能做点什么呢,我指了指她的肚子。她冲我妩媚地一笑,又挂上了档。
我们重新驶向郊区,驶向田野。我问她要干什么。她说随心所欲。车子停下了,她把手伸了过来。三十分钟后,她的高跟鞋踩得车顶铛铛作响。她依然戴着蛤蟆镜,那张脸扭曲在车座上。
她送我回去的时候,告诉了我那张卡的密码是209209。我说别他妈是张空卡。她说,你还这么不相信我。我说,你也不怎么相信我。她又说,你是天下让我最信任的男人。我下了车。
她摇下车窗,说了一句,祝你好运。
第二天上午,有一个女学生闯进了我的办公室,她要跟我说悄悄话。很多老师扭过头来看我,眼神异样。我说,有什么话可以当面说,干嘛要说悄悄话。她挤了下眼睛,又咧起了嘴,意思是那话必须悄悄说。我跟她走了出去,我知道我的背后一定挂着一串眼睛。
我们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她开口说话了,牙齿很白。我才发现她就是在课堂上秋风扫落叶似地喊了一声“滚”的那个女孩。她问我认识她吗。我说知道。她说,老师,你要遭殃了。我的眼睛大了大。
她继续说,我的男朋友一直在跟踪你,他知道你背着丁当老师做了坏事,他说那个女人老戴着一副蛤蟆镜,长得很漂亮。我快听不下去了,浑身痒起来。她接着说,您不要紧张,他还没有告诉丁当老师,他说只要您听他的话,他就永远不告诉丁当老师,所以他老在我面前吹嘘,说即便考个零蛋,您也不敢不给他及格,他想要多少分就是多少分。我说,你为什么告诉我。
她说她觉得我很可怜,值得同情。
而且她还说,我要跟那个坏小子分手,跟他呆在一起太危险了,他有窥私欲,说不定哪天就跑到了我的屁股后面监控我的自由,我要甩了他,一定得甩了他。她咬了咬牙,鼻孔里冒出一口粗气。
草地上有个白色的饭盒儿被风吹得滚了又滚。
我让她先回去。她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老师您别怕,我跟您站在一起。她往前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说,我叫黄莉莉。我说,谢谢你,黄莉莉。
饭盒儿滚到了羊肠小路上,被一个学生又踢了一脚,四零八落。
我回到家里不敢看丁当的眼睛。我又在想,那小子是不是丁当派过去的间谍。我的心像被穿了个洞,所幸他还没有把消息公布,得先稳住他。
我为丁当做了一桌好饭。丁当说是不是又要贿赂她,或者做了什么亏心事。我说都没有,声称她需要补充营养。她说,下周一跟我一起去体检。我算了一下还有四天,我说行。她说这些天不准干那事,精子检查需要禁欲7天。
又过了一天。我去找那小子谈了一次话。他在我面前扭来扭去,我问他是不是学过跳舞。他说是,而且是丁当老师的学生。我想我当时的脸一定灰了。
我跟他说了会儿闲话,只字未提跟踪的事。他要走的时候,冲我一脸坏笑。好像在说,你跑不出我的手心。我想象自己举起一把手枪,朝他的背后一指,扣动扳机,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心脏,又飞向远方。
我没有手枪,我只有一双无力的手,还没有举起来。
星期一的早上,我有一节课。黄莉莉和那个坏小子没有坐在一起,却都趴在桌子上埋头睡觉。我走到那个坏小子身边,他冲我翻了下白眼又睡下了。我走到黄莉莉身边,她揉揉眼睛撇撇嘴,直起了腰。
下课后,我回到了办公室,还没开口说一句话,黄莉莉就跑了进来,站在我面前。她又要跟我说悄悄话,两只眼睛想要洞穿我。很多老师瞧着我们俩。我只好带着她一前一后走出了办公室。她说,老师你要救救我。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他不会放过我,他要跟我鱼死网破。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她用袖子抹眼泪儿。有微风吹过来,几缕刘海儿被扯了扯。我发现她很美,很想抱住她。我说,等会说,这人多。
我们走到了操场上,黄莉莉说操场上人更多。我说,人确实多,但都不注意咱俩。我就开始问她那小子打算怎么鱼死网破。
她说,他要给我认识的所有人发短信,说他已经睡了我,说我是个婊子,包括我的爸妈,还包括您。她又说,尤其是我的爸妈,他们要知道,我就不想活了。
我说,他不敢。
他敢,他什么都敢,他是个禽兽,黄莉莉冲我喊了起来。
我说,小点声。
我的手机响了,我知道丁当催我了,让我跟她一起去医院。我告诉黄莉莉先稳住他。她临走的时候,眼神凄楚,连连说,老师您要帮帮我,我最信任您了。
丁当在校门口等急了,脸都绿了。当她的脸慢慢变黄,我才敢跟她说话。我问她,那个东西怎么采集。她没好气地告诉我,人家大夫会告诉你。我说,你能在旁边帮忙吗。她说,瞧你一脸色相。
我哪有一脸色相。我想起了黄莉莉在风中落泪。
医院里的人比学校还多。我站在长长队伍的末尾,丁当坐在不远的地方玩手机。终于轮到我了,后面的人还挤着我的屁股。负责挂号的大夫是个女人,皱纹儿很深,看也不看我,就问我挂什么科。她也穿着大夫的白大褂,不过已经泛绿。我说挂妇科。她抬头看了看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的话,我嗯了一声。

巴黎蒙马特 王济远 1939年 油画 49×63cm
我说,我还挂一个。她问再挂什么。我说检查那个的。她又问检查哪个。我又说了一遍,检查那个的。她还问检查哪个的。周围的人开始看我,我的脸也许红了。后面挤我屁股的中年妇女救了我,她说,不就男科吗,有什么害臊的。
我拿了票从人群中钻出来,拉起了丁当的手上楼。上了楼左拐是男科,右拐是妇科。我左右徘徊。我拽了拽丁当的手,低声说,我怕我弄不出来。
丁当不说话了,眼睛不眨地看着右边。我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发现了一副蛤蟆镜。蛤蟆镜下面的一张嘴弯成漂亮的弧形。那么熟悉,又分外陌生。
她喊我的名字,又喊丁当的名字。丁当靠在我身边像一个坚硬的物体。蛤蟆镜里有我跟丁当一对小小的影儿。
丁当身子一扭,摆脱了我,站在我的前面,我们三个人差点站成了一排。带蛤蟆镜的女人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她告诉我们她怀了孕。丁当回头看我,眼睛眨巴了一下,挤出一片光。她也指了指自己的肚子说有了。
我挑了一下眉毛。
丁当问,你老公怎么舍得你自己来。带蛤蟆镜的女人摸了一下她还平坦的肚子说,他爸太忙。
蛤蟆镜从我们身旁袅娜地离开,踩得地板嗒嗒作响。我在想都这样了还穿硬跟儿的皮鞋。丁当说,一个二奶牛什么。我说人家没你牛。我就去摸她的肚子。她一把打开了我的手。她推着我让我快去弄。
大夫冷冰冰地送给我一个瓶盖一样的器皿。我就钻进了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对着白色的墙壁。我的脑袋里冒出带蛤蟆镜的女人,举起红色的文胸,嘴里嚷着,欢迎来到伊甸园。有人铛铛地敲门,我喊了一句有人,他也跟着喊了一句,快点。
我快不起来。在风中擦眼泪的黄莉莉也钻进了我的脑壳,风还在吹,泪还在流,我却止不住的颤抖。
我快了起来。
我跟丁当从医院里走出来,瞧了瞧没有太阳的天,又看了看各自的化验单,丁当捶了我一捶,问我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到了晚上夜里三点,丁当突然扭过头来把我叫醒,说,你是不是在想那个女人。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里有一段又一段温和的声音。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有这样声音的中年男人,我想应该不是个坏人。他最后一句问我能否赏光,我没有拒绝的力量。我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他就是带蛤蟆镜的女人的男人。听说他有很高的职位,有很多的钱。我曾经见过他一面,那时候她也在旁边。他又想要跟我见面,这次没有她,不过我想还跟她有关。
他要跟我说什么,他知道了什么,他不应该知道的。
我打电话告诉她,你的男人要见我,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她说连她怀孕的事他都不知道。她也很疑惑。而且他竟然知道我的电话。挂了电话,我开始紧张,额头上老冒汗。
我紧张了一阵儿,丁当打来电话说她又不回来了。我问她老忙,到底忙什么。她让我别问了,反正是好事,到时候给我个惊喜。她连个再见都不说就挂了电话,她老这样,三年了我还没有习惯,总觉得话没说完,等见到她又没话可说。
我牵着那条狗在楼下晃悠。自从那天我看到了狗眼里的深刻,就给它穿上了衣服。衣服有些大,在狗肚子上垂着,倒看出几分大气来。它在前面小跑,我在后面跟着,我拼命想那个男人要与我见面的理由,他刚才说只是为了叙叙旧,谈谈她。我总结的理由如下:
第一,就像他说的,叙叙旧谈谈她。
第二,约我出去臭揍一顿,然后警告我,让我离他们远点。
第三,酝酿一场阴谋。
第一个理由很浪漫,第二个理由有点下三滥,唯有第三个理由合情合理。我手里还攥着牵狗的缰绳,手心里全是汗。
我在去赴约的路上开始想阴谋。想着想着,满脑子都是关乎阴谋的电影,而且搞阴谋的人下场都很惨。
我到了。我看到了他。
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手大而温暖,我还能记起三年前的感觉。他的脸非常干净,头顶上还有几根头发倒在一边。他冲我笑,很谨慎,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嘴角又抖了抖,显着不安。像他这样的大人物,我老以为出场的时候会头顶光环身披祥云,没想到会这样。
他开始说话了。话说得很慢,说话前总要想一想。说话的内容与她无关,与我也无关。他在谈茶。
我不懂,我洗耳恭听。我蹲在茶馆的包厢里听他谈了半个小时的茶道。我的耳根好像清净了。他确实在讲经论道,可一点也不像,倒有几分跟我商量事儿的样子。
不知道在哪个节骨眼上,话锋一转,他问我,你还爱她吗。我怔了怔。说了这么多,才开始谈她。
我说我有老婆了。他说,你在逃避我的问题。他又问,你还爱她吗。我说,我不知道什么叫爱。他搓了搓手,许久没有说话。我说,这个问题对我们俩都没有意义。他说,对我有意义。我问他。他继续说他可以成全我们。
我又说我有老婆了。他温和地笑笑说,我也有老婆。
他掏出一盒烟来,问我介意他抽烟吗,我说也给我一只吧。我们俩分别点上,他吐出一口烟,我也吐出一口烟,两口烟在我们之间相互交融又四散开去。
他说,你老婆叫丁当吧。我说,你真是神通广大,什么都知道。他回答说,现在是信息社会,谁都藏不住秘密。他继续说,我见过她,人很漂亮,身材更好,她现在为我做事。他看了看我僵掉的脑袋,接着说,你不用紧张,她在我们公司旗下的一个剧团兼职,她舞跳得很棒,你眼光不错。他说话一句一顿,听得人心急。他把话接下去,剧团的团长她也当得了,我看她有这个能力。
我才知道丁当都在忙什么,原来还有第二份工作,连这也不告诉我。
他又冒出一句,你跟她是不是见过面。他看了一眼我发直的眼睛,说,不用紧张,老朋友见个面很正常,我不会怪你。
我问,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熄了烟说,我要你去追求她。
他又从兜里掏出一张卡放在桌在上。手指落在卡上,敲得咔哒响。他说,她要跟你走,这就是你的。他把卡往我这边推了推。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我想甩了她,她有点让我烦。
我说,丁当怎么办。他说,那就看你的了。我横了横脖子,晃了晃肩膀,我告诉他绝对不行。他笑了笑,我越来越不喜欢他的笑。他说,你跟她一样,不喜欢思考。
他顿了顿,指着我说,我选择了你,你别无选择。他又喝了一口茶。我说我不怕威胁。他说,我只是在为你想个办法,当然归根结底是在为我自己想办法。他又说了一句,你不想鱼死网破吧,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他语速开始快起来,他说,小帅哥,我要是想鱼死网破,也就不找她做小情人了,你说是不是呀。
我说我的心里有点乱。他说,那你回去考虑两天。他又推了推那张卡,接着说,卡你先拿上,下次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密码。
我走了出去,站在街角就给那个女人打电话,我说我要见她。她说不方便,他要来。我跟她说了中年男人告诉我的话,她沉默了一阵说让我等她的消息。挂了电话,我看了看表,还不到九点,我不想回家。我在街上走着。
手机又响了,黄莉莉打来的电话。我一接电话就听到那边的抽泣,她边哭边说,老师,快点救救我。我说怎么了,她说那小子在她宿舍楼下喊了两个小时了。我说我马上到。挂了电话,抬头发现电线杆矗立在我的面前,近在咫尺高高在上,发出嗡嗡的电流的声音。
我回到了学校,一路小跑到女生宿舍楼下。发现女生宿舍楼的每一个窗口都挤满了脑袋。我看到了那个小子,举着个扩音喇叭,大声地叫喊。黄莉莉,你赶快下来,你要不下来见我,我就喊一夜,让你们所有人都不得安生;黄莉莉,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没有你我根本活不下去;黄莉莉,你要问我有多爱你,我告诉你,月亮能够代表我的心;黄莉莉,你在干嘛,你怎么还不下来,你伤透了我的心。
他扯着脖子喊呀喊,我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他身上有浓浓的酒味。他是喝了酒。我使劲推了一下他的肩膀,没想到推了个趔趄。他看了看我,没有理我,又举起喇叭喊起来,说,老师也来了,老师也管不到我们相爱。我又推了他一下,我说,你要再喊,就把你抓起来,赶紧滚蛋,别在这丢人现眼。他又喊,老师,你哪有资格管我。他刚想说话,我一个耳光打了过去,高音喇叭落在了地上。我的手麻了一阵又疼起来。
你敢打我。我说,我打的就是你,不要脸,快点滚蛋。学校里的两个保安也走过来了,一高一矮把他带走了。我举起高音喇叭喊了一声,别看了,都回去睡觉。
我还没回到家,黄莉莉又打来了电话。她说谢谢我。她又问我,老师,我该怎么办,他一定会群发短信,骂我是个婊子,我爸妈也会知道的。鬼才知道怎么办,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告诉她先好好休息,明天再说。
回到家里,丁当竟然又穿起了那件红色的肚兜。我没有心情看她,躲在阳台上抽烟。发生了好几件事儿,就像好几个线头,理也理不清,乱成一团。丁当笑嘻嘻地走过来,还举着一杯红酒。她要我陪她跳舞。我们俩在客厅里跳完了一曲,我就搂住了她。把她抱得很紧,她都喘不过气。
她又把我拉到床边,说要赏我。我说为什么。她就把兼职的事情告诉了我,还说她已经当上了剧团的副团长,工资是在学校当老师的三倍。她握紧了小拳头冲我举了举,说她的艺术生命又重新开始了。
她过来亲我,又摸我。我刚刚俯下身去,她身子一动腿一抬,大拇脚趾又点住了我的眉心,接着呵斥一声,戴上。我说,不是要。大母脚趾在我眼前晃了晃,她说她改了主意。我一头歪了下去,再也没起来。
第二天,上完课,我就找那小子谈话。我们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他在我旁边站都站不稳,浑身抖着。他还没等我开口,就先说话了。他说,你也不要劝我,先想想你自己吧,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说,我的事,你随便,但关于黄莉莉的事情,你是在犯罪,我们可以报警。我还没说完,他就把话抢了过去,你们,你们,怎么又你们了,老师,你可是我见过最花心的男人了,我不知道丁当老师怎么看上了你。
我心慌了一阵,说,还是那句话,我的事你随便,关于你要报复黄莉莉的行为,趁早收手,我在警告你。
他说,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说,我能把你送进监狱。他瞪了我两眼,转身就走了。
没过两个小时,丁当把电话打了过来。我就知道东窗事发了。她说她在家里等我,让我马上回去。
推开家门就发现了我的行李箱。大大的皮箱堵住了门,我从行李箱上跃过去,看到了丁当抽着烟。她把手机扔给我,看也不看我。我打开手机看到了一组图片,是我跟带蛤蟆镜的女人在一起的证据。我把手机放在桌子上,走向她,我说,你听我解释。
她顺手抽出一把刀,举到我的面前。她说,你还记得我的话吗,你要是冲我撒谎,背叛我,我就阉了你。刀尖指向我,闪出一片寒光。我啪的一下解开腰带,裤子堆在地上,我下身赤裸地面向她。我说来吧。刀尖抖了抖,你给我滚,她喊了一句。
我的手机响了。我弯腰从裤兜里掏出电话,丁当又一把抢了过去。
她一接电话,就知道那是带蛤蟆镜的女人的声音。丁当破口大骂起来。我让她冷静。我说,人家早把电话挂了。她一把把我的手机扔在了地上。
我提着行李箱下了楼。关上门的一霎那,竟然想起了那个中年男人。
带蛤蟆镜的女人在我前面走着。我拉着行李箱跟在后面。她走得趾高气扬,我在后面垂头丧气,像一条被阉掉的狗。她让我先住在那个209的房间里。她在那里被我搞大了肚子。
她从包里掏出一副蛤蟆镜,让我也戴上。我们一前一后,都戴着蛤蟆镜,一起穿过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大厅。服务员冲我们微笑致意,我也向他们微微点头。
她一屁股坐在床上,捧着肚子。她说,我告诉了他,我怀了他的种。我问,他相信吗。她接着说,他很开心,他想要个儿子。她低下头摸自己的肚子,说,宝宝争口气,一定要是个儿子。我单膝跪在她身边,也摸起她的肚子,我说,别欺负宝宝,他想是啥就是啥。她扬起胳膊打了下我的头,说,放屁,一定要是个儿子,我们才有更多的钱。
我说,没钱也可以。
她说,要是那样,我他妈的早嫁给你了,还受这份儿罪。
我说,他能给多少钱。
她说,最少一百万。
我说,他要发现了怎么办。
她指了下我的眉头说,你这个没用的男人。
她摘下了蛤蟆镜,露出了浮肿的眼睛。她问我,你还爱我吗。我看了看她的肚子,说了一句,我跟丁当没感情,她老是拿大拇脚趾指我的眉头。她哈哈笑了起来,前仰后合,上嘴唇弯成漂亮的弧形,她说,就因为这。我说,当然不是,要是你们两个相比,我爱你多一点。她问,还有其他女人。
我说,哪有。她又问,那还有谁。我说我自己。她又笑了。
到了晚上,我又去见那个中年男人。还是老地方,他坐在我对面,笑起来,有那么多的鱼尾纹。他说,你是个聪明人,知道审时度势。我说,不要再挖苦我了。我说我恨自己。
他说,从哲学上讲,每一个人的世界都充满错误。
他说,下个月你们就完婚,结婚后离开这里。
我说,丁当要是不答应呢。
他说,她会答应的,你放心。
我说,我对不起她。
他说,不要给我说这些,你走吧,我会把密码告诉你。
他不说话了。摸了摸头顶上的几根头发,让它们倒在一边。
我走出那间包厢,就戴上了蛤蟆镜。蛤蟆镜里的世界都变了色。我开着她的跑车,在街上穿行。我超过一辆车,又超过一辆车,风吹干了我的眼睛。
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来了条短信。我一看是黄莉莉。她说,老师,我喜欢你。蛤蟆镜在我眉头上抖了抖,我回了条短信,别胡闹,抓紧准备考试,老师已经有了幸福。短信又来了,她说,老师,我要考不及格,你能给我及格吗。
3
丁当当上了剧团的团长。是那个中年男人告诉的我。
在我跟戴蛤蟆镜的女人结婚前夕,我们三个人又坐在了一起。跟三年前一样,他们俩仍能谈笑风生。跟三年前不一样的是,我跟她坐在了一排,她有时候还抓一下我的手。
我的感觉还是很怪,很想离开。可我这次不能走开。
他说,她又回到你身边了。
他说,好好待她,还有肚子里的孩子,我会按月给你们汇款。
他说,房子我也给你们买好了,不过在千里之外。
他说,我有空会去看你们。
他说,祝你们幸福。
他说,我老了。
我们俩跟他分手以后,都戴上了蛤蟆镜。我们坐在车里,相视一笑。车子就开了。
过了两天我们就结了婚。在结婚的那天,中年男人也去了,他一个劲地冲我们鼓掌,嘴巴咧向两边,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我还见到了他的老婆,屁股很大,像个要产卵的昆虫。她也向我祝福,说我们是天作之合,不过我老感觉她看我的眼神很怪。
三年前,丁当也像她一样,穿着白色的婚纱挽着我,脸上化了浓浓的妆。我说,丁当你真漂亮。可三年后的今天,我说不出同样的话,也不好意思看她。我跟丁当入了洞房,她依偎在我身边,说,你以后不要冲我撒谎,你要是撒了谎,我就阉了你。我的嘴盖住了丁当的嘴。我跟她也入了洞房,她依偎在我身边说,你是不是很委屈,我说我不委屈,我说我很幸福。
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一宿没睡。
在跟丁当离婚之前,我见了她一面。她拽住了我的手说原谅了我。我说,对不起。她又扑到我的怀里说,你回家吧,我还跟以前一样等你。我抱了她很久,又说,对不起。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还爱她。她又问我,是不是为了钱。我说,不是为了钱。
我对她说,我永远有一个肩膀供你依靠。
她说,你会后悔的,她是个坏女人。
那是她第三次说她是个坏女人。
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那张脸很陌生,我抽了自己几个耳光,留下了几滴泪。
再过三天,我们就要去另外一个城市了。那一天,我们还会同时戴上蛤蟆镜,在飞机上看这个城市,看这个地球。也许我还会想起丁当的笑容,想起她的大拇脚趾,像一个狡猾的蛇头。
我开着她的跑车在学校周围转了一遭,想到了三天后。
我又接起了电话。最近祝福的电话让我应接不暇。我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女人的声音,没有一句祝福。她说她要见我,有话跟我说。我问她是谁,她说见到了就知道了。我说我要不去呢。她说,那你就休想离开这个城市。女人说话的口音生硬,容不得拒绝。她说她在等我,一个小时后见。
我又问了一句,你究竟是谁。她把电话挂了。真是个奇怪的女人。
我到了她说的那个地方,可没有发现她。我给她打电话,她问我是不是到了。她说让我等她一下。
我见到了她,原来就是她,中年男人的发妻。
她一头卷发,蓬松的像个榆木疙瘩。上次见她,头发还没做成这样,她看起来年轻一些。她的脸冷冰冰的,嘴唇有点厚,怎么也看不到牙齿。
我们俩面对面。那是一间西餐厅,因为是下午还没到吃饭时间,所以没有人。诺大的餐厅,只有我们两个客人。
我说,您找我有什么事。
她说,你真是没有良心。
我说,这是我的事。
她说,你就没有丝毫歉意。
我说,这是我的事。
她说,丁当真是瞎了眼。
我说,你到底找我什么事,没有事,我要走了。
她冷笑了两声,嘴咧了咧,还是看不到牙齿。她说,那个女人有什么好,都这么喜欢她,瞧她一副狐媚样儿。我站了起来,想往外走。
她喊了一声,你站住。
我就站住了。她说,你坐下。
我又坐下了。
她说,我想跟你做笔交易。她说完这话,又从兜里掏出一张卡。卡的背面闪着晶莹的蓝光。那张卡在她手里转来转去。
她说,等孩子生下来,你把孩子抱走,然后消失,你会得到更多的钱,是我老公给你的两倍。卡又在她手里转了一圈,指向我。
我明白了。
我说,那她怎么办。她从鼻孔里哼出一口气,说,她,谁管她,自作自受。
她又说了一句,这是她应得的下场。她的双腮鼓起了几条肌肉。
我说,你们真可怕。我的右眼皮跳了起来,止不住。我又说,我要不答应呢。她马上说,也许会有更坏的结果,我问什么结果,她说,我给过你机会。
我说,我把孩子抱走,然后消失,我去哪儿。她说,丁当会在一个地方等你。我的嘴巴张了张,我的眼睛大了大,我差不多是个呱呱叫的癞蛤蟆。我连连叫出几声丁当的名字。
她说,丁当是个好女人,她说她愿意为你养个儿子,哪怕不是她生的,我要是她,我做不到。
她又说,真让我搞不懂,像你这样的男人,为什么都喜欢你。
她接起了电话,她丝毫不避讳我,大声冲电话讲,他就在我对面,你过来吧,你们谈谈。我知道她说的是丁当。
五分钟后,丁当来了。
她竟然也戴着一副蛤蟆镜,她从来没有戴过,或者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走起路来还是一摇三摆,似弱柳扶风。我之前老说她,别那样走路,显得不正经。她每次都说要改,可是双脚一踩上高跟鞋就扭了起来,真是屡教不改。
老女人笑了起来,我第一看见她笑。脖子上的青筋都被她笑了出来,可还是没有笑出牙齿。我想她是不是没有牙齿。她拉起了丁当的手,像一个老朋友。她说,你们谈谈。她又看了我一眼,像看了一眼怪物。
丁当坐在了我的对面。蛤蟆镜里有我小小的影儿。我说,你还是把眼镜摘了吧。她就摘掉了眼镜,圆乎乎的小脸儿像被挂在我眼前。
我说,你最近好吗。
她说,没你好。
我说,你们都商量好了。
她说,我们没有商量,我听她的。
我说,你铁了心了。
她说,嫁给你的那天,就已经铁了心了。
我说,你希望孩子没有妈妈。
她说,谁说没有,我就是个好妈妈,我比她更会照顾小孩,我会教孩子跳舞。
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就说了一句不可能。她直腾腾的身子扭了扭,趴在桌子上,那样看我,双眼潮红。
她说,你要不答应,我就告诉他们,那不是他的孩子,那是你的。一句比一句高亢,我说小点声,别让老女人听到。
我们沉默了很久。她看了我很久。我问她,那个坏小子跟踪我,是不是你派的。她说是。我说操。
刚说完,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来了条短信。我打开它,看到了一组图片,图片里有一个裸体的小姑娘在做各种姿势,图片下面有一句附言,黄莉莉是个婊子。我又说了一句操。我想黄莉莉已经哭得不成人形了。
三天后,我跟我的新婚妻子紧挨着坐在飞机上。我们都戴着蛤蟆镜,我说,我要看看这个城市,看看这个地球。
责任编辑:何超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