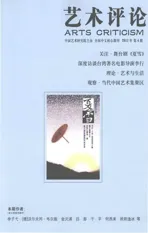艺术如何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2011-09-30沃尔夫冈韦尔施王卓斐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 王卓斐 译
艺术如何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 王卓斐 译[1]
能够参加“文化、艺术与人类发展的中国国际论坛”,并借此良机了解中国的美育思想,对我是莫大的荣幸与乐事。在接下来的阐述中,我自身的观点将难免遵循西方的视角,然而,你们将看到,这样的视角与你们伟大的传统其实是一致的。

一、总论: 审美与伦理的一致性
从西方两千多年的美学传统中,我得到的教诲是:艺术活动并非只与艺术有关、甚至不以之为重心,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正确的生活方式。在此,审美与伦理紧密相连,二者如孪生儿般难分彼此——艺术品及相关活动应帮助人们过上更美好、更人性化的生活。
当然,既然置身艺术领域,那么艺术不可不谈——只有满足了审美标准,艺术作品才有成功可言。但归根结底,审美标准与成功的生活形式是一致的。[2]
诚然,在过去二百五十年里,西方出现了使审美脱离伦理、将艺术视为自律的趋向。众所周知的事实,便是19世纪喊出的“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的口号。然而,在整个西方传统中(亚洲传统亦是如此),占主导地位的信念却是:艺术应为更美好的生活贡献力量。
(一)范例
可以发现,表示“美的”希腊词“kaló n”同时也有“善的”含义。在古典时期,这样的关系通常是不言而喻的——真正的美不仅意味着审美的成功,同时也表示道德的完善。在中世纪,这种关系依然存在,即所谓的“美善合一”(pulchrum et bonum convertuntur)。到了近代,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重新提出,艺术的最终目标不是塑造艺术品,而是推动“生活艺术”(Lebenskunst)的发展。[3]艺术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真正的人类生活。席勒绘制了雄心勃勃的“审美教育”(sthetische Erziehung)蓝图,其任务与旨归,在于使人们首先成为“完整的人”——这不仅指个体的生活方式,同时还包括社会与政治的存在(在文章结尾,我将再谈这一论点)。
20世纪一再出现的情况是:艺术(从蒙特·韦里塔到约瑟夫·博伊斯)的动力不是源于自身,而是来自生活;艺术为了生活而追求超越。“生活的艺术”取代了“艺术的艺术”,该口号意味着艺术乃是生活的手段。在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看来,经过对古典雕像的沉思,典型的结果就是产生了警句“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Du musst dein Lebenndern)[4]。此外,在1987年的诺贝尔演讲中,俄罗斯诗人、异议人士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强调了审美与伦理的鱼水关联,甚至在此称审美为“伦理之母”[5]。[6]
(二)特例?
诚然,也有表面反对审美与伦理联姻的艺术流派和艺术理论。但如果进一步审视,便会发现,它们之所以这样做,恰恰是同样坚信,审美活动应预示美好的生活,甚至或许应在某种程度上去实现它,而起支配作用的道德规范在它们看来是完全错误的,并似乎恰恰妨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于是,正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及对相关艺术使命的捍卫,它们才同这种道德规范展开抗争。对此,19世纪的“为艺术而艺术”运动堪称典范。[7]
二、为何审美与伦理是一致的
现在,根据这些历史线索,让我们系统地思考一下:为什么审美与伦理的一致性是西方美学的基本主题与永恒信念?——当然,对亚洲美学同样如此(无论儒家还是道家,皆有这样的特点)。
(一)古人类学研究: 作为社会黏合剂的艺术
第一种原因是历史性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艺术首先是为了形成或增强社会凝聚力而出现的。古人类学告诉我们,仪式与手工制品最初是用来加强社会团结的形式。于是,从远古时代开始,艺术便铭刻着与人类社会有关的内容。审美与伦理的姐妹情谊,属于美学染色体组的构成要素。
(二)审美与伦理目标实现的结构相似性
此外,更重要的是,在审美与伦理目标的实现要求上,二者有着明显的结构相似性。
1、伦理整体主义
按照伦理标准,个人不应通过对抗社会或牺牲群体利益的形式实现自我,而应首先为集体的成功做出贡献——以这样的方式,其自身也将取得极大的进步。促进社会的安康对谋取个人幸福同属最佳的策略。
亚里士多德
作为西方传统的早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著作《政治学》(Politik)中明确阐述了这种伦理政治原则。他在此指出,政体领导者应关注他们所受托的集体福祉,而不是单单注重一己之利。在后一种情况下,领导者将破坏政体,并最终危害自身。但是,如果他们首先为集体利益而奋斗,那么作为集体的一分子,其自身的事业也将蓬勃发展。这就像船长一样,他必须保证整艘船处于良好的行驶状态,也就是说,使一切(alle)顺利进展——以这样的方式,他本人也将迅捷、安全地抵达目的地。“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乃是更务实成功(无疑也是更好、更恰当)的箴言。[8]
道家思想
对亚洲传统来讲,这种(伦理政治)原则是从道家那里学到的。[9]《道德经》第七章这样写道:“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10]。一个人不应自私自利,而应与社会和谐共处,从社会的角度审时度势。这实际是一种着眼于整体的行为策略。不是从自身出发,而是立足“大道”理解“我”;“我”成为“道”在这儿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在这个地方,“道”是以“我”的形象出现的。如果“我”意识到自身的实际构成并相应地采取行动,就会完全做到依“道”而行,从而也就不再依照一己之利行事。然后,“道”将在“我”这里获得其最佳的形式,而“我”也将为此受益无穷。
2、审美整体主义
(拥有与上述)相似的结构乃是审美成功的关键。比如,绘画要素必须彼此协调,个别要素必须有益于整体,并根据在这方面的表现得到合理的评价。再如,交响乐的篇章必须相互协调,最终形成连贯的整体,使了解整部作品的人几乎在任何位置(在不同的细节中)都能感受到一致的整体效果(某种程度上讲,差不多处处都一样)[11];又如,在芭蕾舞表演中,舞者的各种动作应始终产生整体的形象效果,并在整个剧情的发展中形成连贯的姿态。总之,同伦理的成功一样,实现审美目标的关键亦在于,个别的要素并非仅指涉自身,而是有助于整体的表现。恰恰是整体中的要素(Momente)生成了整体本身。关于这一点,在古典美学中是通过连贯(Kohrenz)、和谐(Harmonie)或协调(Stimmigkeit)的要求体现出来的。
这种审美与伦理目标实现的结构相似性使人不难理解,艺术品同时也能预示正确的生活——就像此前所说的,审美标准本身与正确的生活形式是一致的。[12]
3、有机性—自由—自组织
现在,根据所描绘的审美与伦理目标的实现特点,我想详细探讨一下部分与整体、个别与普遍的关系。在有机物领域,我们发现了这种关系的原型,因为有机物的特点是:在此,部分不是脱离整体独立存在的,而是通常只作为且只能作为整体中的部分出现;反之,整体也受制于部分的运作。这就像人的心脏不是以某种方式从外部置入体内、而是作为身体的一部分生长的;但是,身体同样也对心脏有依赖关系:一旦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么身体的存活也将走向终结。有机物的部分与整体是同呼吸、共命运的:部分之间相互扶持,因而也需要整体,而同时,整体同样离不开部分的运作。
因此,代表审美与伦理目标实现特征的部分—整体关系,是以有机物为蓝本的。与此相应的是,指涉审美目标实现的众多术语也源自有机物领域。所以,部分与整体真正实现互动的艺术品证明是有“生命力”(Lebendigkeit)[13]的;或者说,作品是有“灵魂”(Seele)的;或者说,人们提到的“力的自由互动”(Freies Zusammenspiel der Krfte)乃至“自由”(Freiheit)等各种术语,显然实际上不是来自美学,而是从有机物本体论那里借鉴的。
让我们进一步地思考——体现于有机物并以美的形态呈现的物理学原理是自组织原理。近几年的美学研究愈益认识到,审美成功意识的首要依据在于——我们所体察的形态形成于自组织的过程。[14]对此,人们可以在有机物领域找到明显的例证——从松果鳞片的螺旋形生长纹路到孔雀屏的眼睛图案组合。不过,自组织是超越有机界、乃至回溯到无机界的原理,是自然界藉此形成有序结构的一般(generelle)定律——想想各种星系的情况吧!
(三)本体论背景
这样一来,我们的探讨已超越了审美与伦理成功标准的一致性,触及了普遍的、物理学层面的宇宙原理,而这是产生一切成功形态的基础。自组织是宇宙万物(自大爆炸开始)的一般构成原理,是基本的本体论定律。它生成了有着内在和谐结构的事物(其中,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是协调一致的)。同时,这种和谐关系是事物存在的前提,否则生存便无从谈起。以太阳系为例——它作为一种系统,一面对各种引力关系做出完美的协调,一面对运行轨道与运行速度进行出色的调整。太阳系在约45亿年前的自组织过程中形成并稳定下来,由于其协调的精确性与不断的细微调整,从而得以在极为漫长的年代里存在下来。
如果审美与伦理的一致性依据的是更深层的原理——涉及自组织的本体论或宇宙学定律,那么便意味着,审美与伦理的正确性反映了世界的基本秩序。这样一来,那种认为审美是伦理之母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就像布罗茨基所认为的),反过来,将伦理视为审美之母的见解也是有问题的,毋宁说,审美与伦理皆是世界基本秩序的衍生物。至少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审美与伦理原则完全是人类的造物;可能有时看上去如此,但这却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它们更多地体现了宇宙的基本原理(无论如何,审美与伦理本身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审美与伦理反映世界秩序的观点对亚洲思想并不陌生,并很有希望在西方思想中再度盛行(在现代时期,这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思想家遗忘了)。
(四)依据深层原理的伦理与艺术活动
这同时表明,伦理与审美活动不是绝对自主的;它们无法独自随意制定规则、安排活动,而是必须以本体论原则为依托。
在伦理领域,这一点是通过道德戒律得到体现的:人们不应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世界,而应通过行动推动自然的进程。至少在道家学者眼中,这样的见解是合理的。《道德经》第64章这样写道:“(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15]——这便是“无为”(Tatloses Tun)的内涵所在。它指的是促进万物的发展,而不是进行规约与掌控。
另外,艺术家以各种方式指出,他们无意充当独立的创作者,而更愿把自己视为作品问世的助产师或媒介。[16]这样的观点也许在东方更为盛行,而在西方同样可以找到踪迹。比如,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曾提到,他“不过是受宇宙支配的工具”[17];他越来越清楚:“人不是塑造者,而是被塑造者”[18]。与马勒类似的艺术家渴望忘掉意向与技艺,为的是像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所说的那样,“仅成为感觉的容器……或储存器”:“马勒全力追求着内心的平静。他必须平息所有的偏见,忘却、忘却,平定下来,成为完美的回音”[19]。在中国美学界,彭锋的观点与之颇为相似:“艺术家只有一并忘却其创作意图、技艺、惯例,也许甚至还有创造力,方能塑造出杰出的作品”[20]。炉火纯青的艺术摒弃了一切刻意雕琢的痕迹,就像严羽(约1180-1235)的那个著名比喻——“羚羊挂角,无迹可求”[21]。
三、美与艺术的独特价值
现在谈谈美与艺术的独特性。
(一)美使人体验宇宙的原理
美是这样一种现象:在此,自组织与连贯性——即宇宙的基本法则变得生动可感(sinnenfllig),而美的独特性则由此而来。一切在世间出现并存在的事物均具有自组织与连贯性的特点。因此,上述自组织与连贯性也同样是成功行为的特征。不过,在审美领域、在美的现象中,这种普遍法则是可以感知的,因而也就更容易把握、更加清晰明了,较之其他场景更易令人体验。
柏拉图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美是“最灿烂、最迷人的东西”(ekphané staton kai erasmi ó taton)[22]。他是想说,尽管观念的东西在现象界一般以隐晦的面貌存在,但有一种观念形态却在此光芒四射,这就是美的理念。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最为持久的观念,能够使我们脱离现象界的漩涡,向理念的王国飞升,由此凸现它的宝贵作用。[23]
(二)艺术:表达与多样性
那么,艺术的特色何在呢?
不同于自然的形态,艺术作品中部分与整体的相互依存性是刻意塑造的(eigens gestaltet),从而也就格外可触可感(besonders erfahrbar)。部分与整体的连贯性是艺术品形成的首要法则。创作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是围绕现有成分与创作意图展开的。这样,每个成分都参与了其它成分的形成。因此,在艺术品中,部分成为名副其实的要素(Momente):它们造就了其它部分的形式与意义,并与源于自身的整体构成了依附关系。(比方说,这就是为何同样的音符,随着此前乐曲的行进和其它音符的跃动,可呈现出不同的音质)在完成的作品中,人们仍可以感受到这种贯穿创作过程的部分与整体的动态交互创造关系(即使它在绘画中是以静态的形象存在的),这体现在所有要素之不可思议的极度协调性和作品绽放出的勃勃生机。在时间艺术中,比方说音乐,这种部分与整体的相互纠葛无疑占的比重更大,而且在一切瞬间鲜明地显露出来。
在艺术作品中,不仅是连贯性(源于进程之中,即不是从外部植入,而是内在生成的)、就连自组织因素也得到了清晰地呈现。优秀的艺术品不是某种预设程式(“理念”)的简单复制,而是始终有自己的轨迹,可以说,它创造了自身——不是依照外部的成规,而是凭借自身生成的逻辑。(“在行走中创造道路”"Laying down a path in walking"可谓是对艺术之旅的恰当描述)。
如此说来,成功的艺术之作还始终体现着自由;要素的结合不是来自外部的强制力量,而是自觉自愿的。作品存在方式的特征不是屈从,而是相互制约。——顺便说一下,弗里德里希·席勒率先表达了这个见解:在审美领域,每个要素都被视为目的本身;它与其它所有要素是平等的;不得被强行纳入整体之中,而必须是自愿地行动。[24]从这个意义出发,席勒把“美”界定为自由的显现。[25]
最终,艺术带来了多样性,因为它以斑斓的形态(in unterschiedlichen Formen)教人体验自组织与连贯性。由于这些原理在自然界有着各种不同的现实形态——星系显然不同于贝纳尔对流(Bé nard-Reaktion)、DNA螺旋结构或激光束——因此,它们在艺术中也有着迥然各异的实现方式。艺术不单摹仿自然界中人们熟知的形态,还能凭借无穷的风格与范式彰显宇宙的形式法则。[26]同时,这种多样性还向我们揭示了世界的某些奥秘,这一方面指宇宙法则的无止无休,另一方面指表面各异的种种形态的共通性,即哲学中的“多样统一”。[27]
于是,艺术经验能够教人体会多样性的内涵。在艺术中,我们认识到,相同的原理如何可以形成缤纷多彩的现实形态,而且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这样说来,艺术经验也可以传授生活事务。它唤醒并培育我们的感知力、我们的理解力以及我们对各种世界观和生活构想的包容力。我们开始懂得,不同的形态结构不仅存在于物理与艺术的层面,同时也存在于生活事务的领域——虽说通向幸福的道路千姿百态,然而却都是等价的。在我看来,阐明这个问题,乃是审美教育的一项重要使命。
四、塑造政治生活的结论
按照此前所说,我在文章结尾将再次回顾席勒对艺术活动与政治生活关系的见解。席勒创造了“政治艺术家”这一术语,其核心观点在于,政治也是有意识的塑造活动——甚至是最明确地以塑造生活为目标的活动。现在,如果部分与整体的协调是一切成功塑造行为的准则,那么显然,政治的塑造活动也必须考虑到部分与整体的自由互动关系。席勒指出,匠人与艺术家[28]无需顾及所加工的质料。相反,“致力于教育和政治事业的艺术家”,即教师与政治家,由于所面对的对象不是死气沉沉的材料,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也就必须格外慎重地对待与尊重。席勒甚至认为,在教育和政治活动中,整体必须为部分服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才应当、乃至可以听从整体的召唤。[29]这就是说,席勒的要求是,整体的政治代表必须关注个体的权利,就像个体理应服从整体的要求一样。[30](席勒的这个例子显然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模式。)他的政治目标在于实现部分和整体的唇齿相依,而这也正是我前面描绘的成功的审美形态与自由形态——或许,在这种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尊重中,你们也能看到自己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模式。
注释:
[1]本文译自韦尔施先生在“文化、艺术与人类发展的中国国际论坛”(2010年5月23-25日,北京)演讲稿的德文版“Warum kann die Kunst zu einen gelingenden beitragen?”,为保证表达的流畅性,在翻译过程中同时参考了英文版“How can art improve our lives?”的部分措辞(比如文章的标题)。
[2]此前,我曾探讨过该话题的某些方面,请参阅拙文《美学的伦理内涵及影响》(沃尔夫冈·韦尔施:《美学的拓疆》,斯图加特:雷克拉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34页)。
[3]弗里德里希·席勒:《美育书简》(1795年),载自《席勒全集》(卷五),戈哈特·弗里克、赫伯特·G·盖卜弗特 主编,慕尼黑:汉瑟出版社1980年版,第570-669页,此为第618页。
[4]莱纳·马利亚·里尔克:《古老的阿波罗躯像》,1908年。
[5]约瑟夫·布罗茨基:《异样的面孔》,载自《悲痛与理智》,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吉鲁克斯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8页,此为第49页。
[6]仍是在反向的形式中——在特定艺术流派受到批判的地方,西方传统的伦理立场不时占了主导:这些艺术形态之所以遭到批驳,是因为它们背离了生活的真正目标。典型的例子便是柏拉图对模仿艺术和戏剧艺术的批判。他认为,这些艺术形式不是强化理性的本质,而是通过展示感官与情感要素,误导了人的认知与情感。(请参阅柏拉图的《理想国》,第595-608页。)另外,这种抵制模式跨越了数个世纪:经过本哈德·冯·克莱沃克斯对罗马式雕塑的批判(因为依照其观点,与其说神圣之物受人敬仰,不如说美艳之物更令人惊叹。请参阅:“S.伯纳蒂院长:向S.威廉·蒂欧得里希院长致歉”,载自米涅:《拉丁神父全集》CLXXXII,第 914-916页),直到瓦尔特·塞德迈尔的《中心的丧失》(1948年)。
[7]在象征“为艺术而艺术”的实际宣言——《莫班小姐》(1834年)“序言”中,戈蒂埃抨击了新闻道德卫士关于艺术应促进“道德重建”的无稽之言——这些人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看待情色禁忌问题的。戈蒂埃反对这种将审美教化功能化的做法,并把美与无用性等同起来:“唯无用之物才真正有美;一切有用之物皆为丑,因为它们是需求的体现”。(详阅艾克哈特?霍夫特里希:“何谓为艺术而艺术?”,载自《十九世纪末:世纪之交的文学艺术》,霍格·鲍尔等主编,法兰克福:美茵茨出版社1977年版,第16-29页。)后来的观点仍是这样:对自律性的强调批判了艺术功能化的谬论并摒弃了目的性。艺术自律性应服务于关键性目标,即形象地展现(并促进)正确的生活。到了阿多诺仍秉承这样的理念,他认为,自律艺术提供了极端自我的范例,从而能对异化社会的虚假性做出批判。艺术“由于处于社会的对立面而有了社会性,这种对立的姿态仅在其成为自律物时方会存在。通过凝结成自为的实体,而不是因循现存的社会规范并凭借其‘社会效用’谋取合格的凭证,艺术只通过自身的存在对社会进行批判,而各类教派清教徒的攻击即在于此。作为纯粹的、遵循内在法则的建构物,它(艺术)对贬抑之词做出无言的批判,所依据的状况便是趋向于整体性的交换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只为他者而存在——艺术的这种社会性偏离是对特定社会的特定否定”(西奥多.W.阿多诺:《美学理论》,载自《阿多诺全集》(卷七),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页)。详阅合理性领域(认知的、伦理的、美学的等等)的区分与交织关系:沃尔夫冈?韦尔施:《理性:当代理性批判与横向理性的构想》,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95年版,2007年第4版,第461-540页。
[8]原句为“Nicht Eigennutz, sondern Ganzheitssorge ist die pragmatisch erfolgreichere Maxime”,在此,译者借用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名句译释此句的部分语词。
[9]不过,儒家学说(另一支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美学影响深远的力量)同样从道德立场出发,不仅阐明了正确行动的条件,而且还认清了优秀艺术创作的前提条件。
[10]老子:《道德经》第7章。
[11]我认为,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可谓典范之作。
[12]因此,一幅作品可以同时揭示出理想的社会,尽管表面看来它只关乎审美力量的平衡,并以完全抽象的方式略去所有的内容、特别是这种社会性的内容。蒙德里安的作品就是个典型。因为他的平衡艺术不仅涉及了绘画因素,同时还对生活重量的平衡具有示范作用,这种平衡不仅在所有个体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且对社会结构也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在懂得它们挺进到实践维面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意识到蒙德里安静穆、朴实的作品是完全真实的。蒙德里安本人也把它们视为平衡社会力量的典型,认为它们对民主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同样,人们也可以把蒙德里安的静物画当作隐藏的社会图式。作品对象的排列显然涉及了家庭关系。人们在此领会了等级、接触、恐惧、自我主张、逃避、对照、结合。蒙德里安是立足宏观社会学进行艺术创作的,而莫兰迪则对微观社会学情有独钟。
[13]“生”正是道家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请参阅卜松山(Karl-Heinz Pohl):《象外之象——中国美学史概述》,载自彼得.M.库夫斯主编:《中国:历史的维度》,图宾根:尝试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243页,此为第230页。
[14]请参阅沃尔夫冈·韦尔施:《美的普遍欣赏》,载自《国际美学年刊》2008年第12卷,第6-32页。
[15]老子:《道德经》第64章。
[16]关于造物主的激情与创作的模式问题,请参阅沃尔夫冈·韦尔施:《在创造的零点》,载自《国际美学年刊》2010年第14卷,第199-212页。
[17]古斯塔夫·马勒:《给安娜·冯·米登伯格的书信》(1896年6月或7月),载自《古斯塔夫·马勒书信集》,维也纳:泽尔奈出版社1982年版,第164页。
[18]古斯塔夫·科利安主编:《纳塔利·保尔-莱希纳追思古斯塔夫·马勒》,汉堡: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19]P.M.多兰主编:《与塞尚对话》,巴黎:马库拉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页。同时,请参考约翰·凯奇的观点“进步有可能意味着支配自然,而艺术则仿佛听从自然的召唤”,载自理查德·柯斯特兰尼兹:《约翰·凯奇谈音乐、艺术与我们时代的精神问题》,科隆:杜芒特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20]彭锋:《论中国美学的现代性》(由英文名译出),载自佐佐木健一主编:《亚洲美学》,京都:京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154页,此为第144页。
[21]请参阅卜松山(Karl-Heinz Pohl):《象外之象——中国美学史概述》,载自彼得.M.库夫斯主编:《中国:历史的维度》,图宾根:尝试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再提一下该观点的道家思想背景——“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道德经》第9章)。译者注:关于严羽的这个比喻,原文以阐释性的语句做了描述。为使译文显得更加凝练,译者在此略做调整,直接引用了严羽的原句。
[22]柏拉图:《斐多篇》,250 d 7 - e 1。
[23]美虽然不是至高的理念,然而却是将我们从自己的堕落状态中有力拯救出来的最有效观念。
[24]“美,或更确切地说是趣味,将一切视为目的本身,绝不允许一方把另一方当成工具或套上枷锁。在审美领域,任何自然物皆为与至尊之物拥有同等权利的自由公民,不是为了整体意志被迫为之,而是根本上必须与所有事物保持协调。”(弗里德里希.席勒“论美”,载自《席勒全集》卷五,格哈德.弗里克与赫伯特.克.盖卜弗特主编,慕尼黑:汉瑟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433页,此为第421页)。
[25]同上,第400页。
[26]因此,西方艺术史明显有承继范式转换的特点,在现代时期,这种转换速度再次大大加快。
[27]当然,在艺术中,除了使自组织与协调性变得可感的目标以外,其他目标也能成为中心。目标的多元化同样是艺术范式多元化的内容。但按照我的设想,自组织与协调性却是艺术至为深刻的原理——任何直接和表面受到追捧的范式根本上都要对它负责并遵循它。
[28]按照席勒的术语,即“机械的艺术家”与“美的艺术家”。
[29]如果机械艺术家的手摸到尚未成形的质料,目的是把自身意图的形态赋予它,那么他会毫无顾忌地施加威力:因为经过其处理的自然物并未受到他自己的尊重,他不是为了部分而关心整体,而是为了整体去留意部分。如果美的艺术家的手触到上述质料,那么他同样会施加威力而少有顾忌,只不过他会避免暴露这样的威力。对于所加工的质料,他不会比机械的艺术家多一分敬意;但是,他会试图通过某种反对相同做法的表面迁就,以欺骗捍卫材料自由的目光。献身于教育与政治事业、以人作为材料与使命的艺术家则截然不同。在此,目的回归了质料本身,同时,仅是由于整体为部分服务,因此部分才应听从整体的召唤。与美的艺术家在物质面前伪装出的尊重不同,从国家出发的艺术家必须贴近对象,但这不是单从主观立场出发并追求欺骗性的感官效果,而应是珍惜个性与气质,立足客观视角并显示出探索内在本质的趋向。参阅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四封信),载自《席勒全集》(卷五),戈哈特?弗里克、赫伯特·G·盖卜弗特主编,慕尼黑:汉瑟出版社1980年版,第578页。
[30]但正是为此,由于国家应是依靠自身、为了自身而发展的组织机构,于是,部分与整体的理念是协调一致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由于国家担当了公民心目中纯粹客观人性的代表,因此,它必须立足于与公民相对的立场审视同样的关系,而在这样的关系中,公民是对自己负责的。只有在向客观人性提升之后,主观人性才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尊重。如果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行动是一致的,那么他也将在行动最大普遍化之际拯救其个性。此外,国家将仅是阐释其美的天性,并更明确地表述其内心构想的法规(同上)。沃尔夫冈·韦尔施:弗里德里希·席勒—耶拿大学哲学院理论哲学教授、当代著名美学家
责任编辑:李 雷
王卓斐:德国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