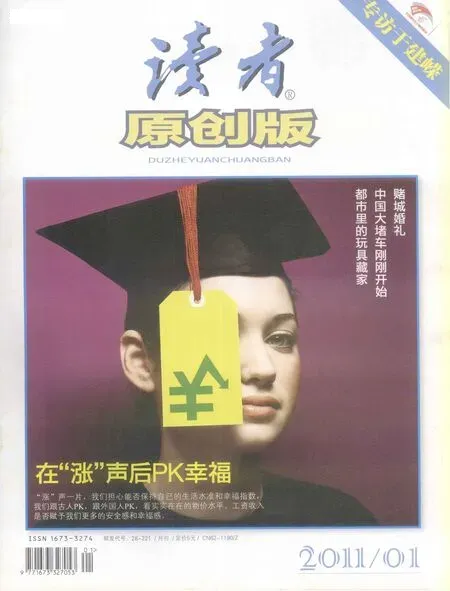后中年期
2011-09-28陈蔚文
文 _ 陈蔚文
纸中城邦
后中年期
文 _ 陈蔚文
“没有一种寂寞,可比拟那种身边有人(有子女、一起生儿育女的丈夫)而明明比路人还不交集目光的。”可这恰是多数中年及后中年期的婚姻场景。
年轻时看朱天心的小说《爱情》,那个年轻的越南侨生仇剑戎,看得人心口发疼:他一天到晚夹着烟,不过剩得老长就掐掉了,也不真为抽烟;房间里总在放唱片,有一搭没一搭的,鱼龙混杂,也并不真为听歌。“她”生日那天,他死了,“心突然不跳了,不是衰竭,纯是突发的……”一个年轻生命在异乡倏然离开,像有事先走一步,来不及招呼。而“她”的哀伤,也有些来不及似的,根本没准备好,手忙脚乱都谈不上,反有些钝掉。
流萤划过的爱情,青春特有的忽冷忽热。
再读朱天心的小说,是2010年夏天出版的《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主角是位58岁的中产阶级女性,由于婚姻里爱情不再而寂寞、恍神。朱天心由此为一对“没打算离婚,只因彼此护卫习惯,感情薄淡如隔夜冷茶如冰块化了的温吞好酒,如久洗不肯再回复原状的白T恤的婚姻男女”探索可能的出路。
当初那个少年恋慕自己的日记,女人一页一页翻读—“才看一页,就知道这将是未来岁月的所有支撑”,她是如此爱着当年那爱自己的少年……而少年早已被如今的丈夫“杀死”,或说被岁月“杀死”—当少年成为丈夫,后者就用一种强酸类时间液体将前者渐次抹除。
假若,朱天心让那位《爱情》中的侨生仇剑戎活着,并和“她”结了婚,他们会不会成为《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中那对如走形T恤的后中年男女?
这假设有些残忍,可比起仇剑戎的死—他从此在“她”心头成了朵云翳,也许,人们更不愿见他们日后变得那样吃力。
“没有一种寂寞,可比拟那种身边有人(有子女、一起生儿育女的丈夫)而明明比路人还不交集目光的。”可这恰是多数中年及后中年期的婚姻场景。当事双方若都可接受这场景,视作天命,合作关系倒也成立,怕就怕一方不甘,通常是女性,并又有那样一本日记作为物证。这“日记”更多非实物,而是潜藏于女人心头死都不肯撒手的昔日回忆。曾经,两人睡在一块也要牵手,仿佛怕梦中走散;现在他为睡眠故,更愿睡客房。曾经,她打个哈欠也引他爱怜;现在她破皮伤风他可视而不见。曾经,她一滴眼泪就令他没顶;现在一吨眼泪也只到他脚脖子……许多个曾经,将落差拉得越大。
且恍神的女人们不仅要面对他前后对照的落差,还要应对自我身体的褪色走样。伴随丈夫温情流失的,还有胶原蛋白与卵巢激素的汩汩流失。这二者联手起来,简直是要将人赶尽杀绝!
至于性—
老女人:你是不行了,还是不要了?
老男人: 这,有差别吗?
老女人:当然有,不行了,我可以接受;不想要了,我会很伤心。

朱天心,台湾文坛重要作家,因《击壤歌》成名,荣获多项文学奖。著有《昨日当我年轻时》《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小说家的政治周记》等作品。
……
老男人: 我们年纪大了,不行,也不想了。
老女人: 所以终归就是不爱了。
那曾令他无比期待、享受的性爱,退潮了,进入枯水期。好吧,允许他六根清净,不要性,只要仅仅是一种注目—瞬息不离的注目,哪怕几秒。不管男人的肾上腺、性腺的供应如何减少,女人希冀温情的心房却是要持续终生。
日子却已被不可违逆的规律驯化。两人在屋内洗碗、整理垃圾、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女人无由接近他,索一个黄昏想要的拥抱,像多年前,两人每次见面,他必孜孜不倦地拥抱。
急了,直想劈面问他:“当初干吗惹我?”
女人设计了一次修补旅程,欲演绎一次当年情。在她的要求之下,夫妻一前一后出门,远赴当年去的东京,却并没令时光逆流:煮熟的蛋又如何返生?
终于走到《东京物语》中那座桥时,女人才明白影片中那对老夫妇在喟叹的是什么:他们喟叹的非岁月之美的寂寥或执子之手的隽永,而是走不动了,吃不动了,一无是处的回忆,而人生将尽。她现在想做的,只是一把搡他下桥!
“真正的生物界,不允许有老年的存在,只要一衰老,立刻就会被自然淘汰。大概只有人,基于道德,会有老年的存在,而且要老好久。”朱天心写下的不只是后中年期的男女关系,也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老法。
这一回,朱天心像是豁出去了!毫不遮掩,图穷匕见,后中年期的包袱尽数抖开。她不手软,也许因为1958年出生的她也是后中年期女人中的一名。3年前她办了场30年高中同学会,花了一整年筹划,这帮中年女同学成了这部小说的资料库。
朱天心的先生唐诺也是作家,两人常一起到台北永康街一座便宜的咖啡馆“上班”。他读她写,他是她的第一读者,并以他良好的文学见解给出意见。他于她,亦师亦友亦“教练”,琴瑟相谐,可说到底,他们也是婚龄不短的一对匹夫匹妇,通常婚姻中有的状况于他们也不会轻易绕过吧。我无意揣度朱天心的生活与小说中女人的重叠之处—“我和唐诺的处境如果和书里头一样的话,我其实就不大敢写了。”天心自己也说过。但作为同阶段女人,“感同身受”是必然,也因此她下笔辛辣,以洞若观火的笔力将这则“去圣已远,宝变为石”的后中年期寓言如剥笋般剥至核心。同是台湾作家的张大春评价此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凶猛的诚实”。
据说,有记者问朱天心,先生唐诺读完这部小说有何评价?朱天心说,他看完只吐了句:“没想到你这样年轻!”
这一句,道出了男人与女人全然不同的疆界!请容我揣度,话中有理解包容,也有轻微讥嘲,似在说:“嗨,这年纪了,还……”

这话,像是秋天对夏天说的话(她是“夏雨哗然有声”,他是“秋风至而声无”)。这话里有女人无法理解的雄性世界的主张与纲领。他用更“高级”的了然看她的苍凉,她的苍凉竟像有几分负气—脱不开性别局限的负气。他们关心的原本是两个世界。她欲申告、抵抗的,在他并不为意,他宁肯关心八千英里外的事端、政治或球赛,甚至不着边际的外太空。他想要她做的,只是希望她能像别的父母(动物)那样全身心于子女,别盯牢他不放。
穷寇莫追!《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中的女人不仅去追,还以一本“他”当年的日记为目标去追—寇未追回,徒耗剩勇。
后中年期,老之将至,女人不是不明白情话不可再充作口粮,却仍巴望一点温情,以证实自己多过钟点工或洗衣机、烤箱的一点魅力,证实自己是心脏迟于肉身衰老的女身,是曾让日记中的少年魂不守舍、有能力粉碎他的一切的女主角!
男人,他恼于女人为何腰腹已松,却仍如少女般难缠。她为何不能承认爱情只是费洛蒙唆使下的活动?就像个性之人,来了就来了,走了便走,再留也是留不住的。为何要把“爱情”这码子事和安全、归属、温暖、道德、责任全搅和在一块?她为何要过度高估“爱情”在人生中尤其是后中年期的戏码?她为何非要求他的注目?她果真不知,她要求他注目的脸,早不是多年前那张!她的面庞之不可重返,就如他肾上腺的不可重返……
从伊甸园开始的永无休止的纠缠,后中年期问题男女的救赎之路究竟在哪儿?朱天心说:“我只是把属于我这个世代的狼狈和不堪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