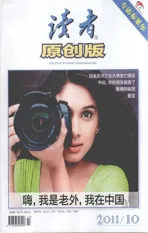“物种猎人”:英雄还是间谍
2011-09-15栗月静
文 _ 栗月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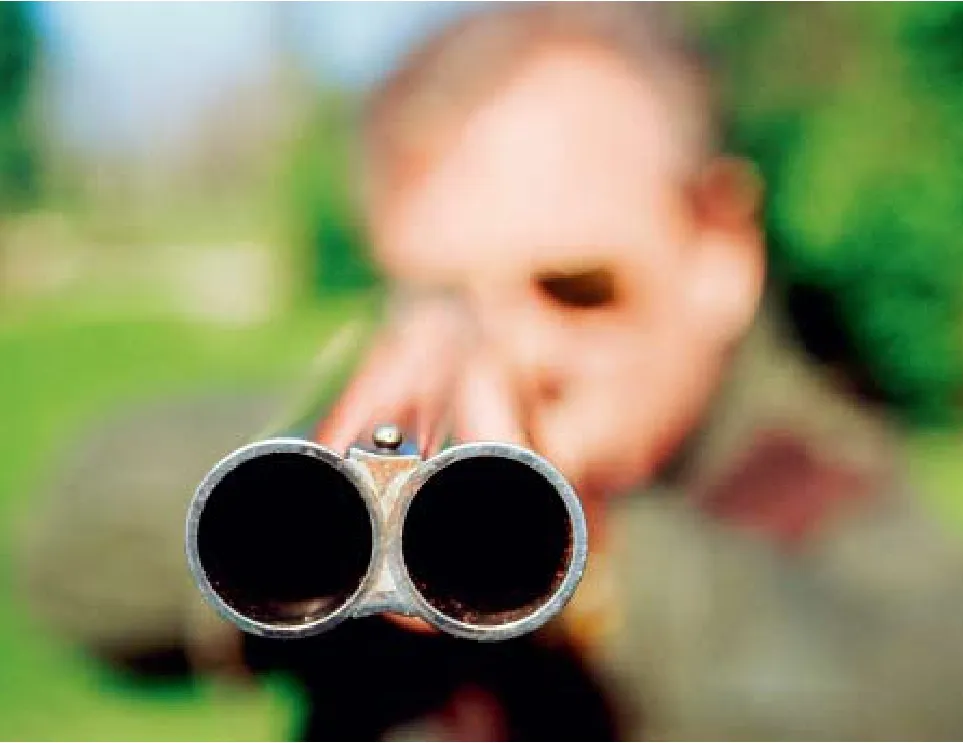
公众总是对外星生物非常着迷,火星上有没有生命的猜测总能吸引大众的眼球,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外星球智能生物,即使是蛛丝马迹的报道都能引起轰动。尽管有些科学家把目光投向了外太空,去寻找新的生命形式,但更多人还是专注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
实际上,每天都有新物种被发现。寻找新物种的这股潮流始于18世纪,当科学家开始收集、描述、分类世界上的物种时,为人所知的只有4400种动物和7700种植物。到了19世纪末期,人类已经研究了41.56万种生物。今天,已经被分类的有200万种生物,而科学家估计,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蓝色星球上,至少还有几百万种生物等待人类去发现。
帝国主义的走狗?
找到并研究新生物并不是人类的新爱好:它是一种持续的激情和令人类在万物中独一无二的职业。
18世纪的博物学家们都是些贵族绅士,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发现上帝的造物,并带回祖国让其他人也能欣赏到上帝的杰作。在科普作家理查德·康尼夫的书《物种寻找者:英雄、傻瓜和对地球生物的疯狂追寻》中,这些“物种猎人”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确立了进化论和生物地理学的基本知识,推动了药物学、自然史、生物地理学的发展。
虽然早期的博物学家坚信,为了把之前西方人未知的一种蝴蝶或者蝙蝠运回国,值得献出生命,但是,对西方人来说是新物种的东西,在非西方文化中早就为人所知。所以有些人把这些物种猎人看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以破坏当地文化为代价寻找新物种。事实是否如此呢?让我们来看看阿芒·戴维的例子。
1865年,一位叫阿芒·戴维的法国人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主要工作则是做动植物考察。他在位于北京南郊的神秘的皇家猎苑,见到了被称为“四不像”的、连动物学家都闻所未闻的麋鹿;1869年,戴维在位于四川宝兴的邛崃山中发现了令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动物—大熊猫。后来,麋鹿和熊猫都作为新物种被戴维介绍到了西方,戴维也因此名扬世界。
戴维还在中国发现了金丝猴。但是所谓的“发现”只是说他把这一物种介绍到了西方,而真正发现它们的当然是中国人。不过,说戴维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显然有点夸张。早期博物学家的工作直到今天还在为挽救和保护濒危的自然资源做出贡献。在中国人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戴维就警告说,对森林的过度砍伐会导致成千上万上帝赐予我们的动物消失,如果不是戴维把它们介绍给世界,包括麋鹿在内的动物有可能早就灭绝了。
1896年,永定河洪水泛滥,南海子的麋鹿仅余二三十只。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德国军队长驱直入,闯进了昔日的禁地:南苑。苟延残喘的麋鹿种群在战火中遭遇灭顶之灾。从此,作为麋鹿故乡的中国,彻底没有了麋鹿。正是因为戴维的引荐,麋鹿才在英国乌邦寺一息尚存。
国家间谍
物种寻找者被认为是间谍的事件早已有之。他们那奇异的收集行为很容易引起警觉,被怀疑为间谍,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很难接近物种的栖息地。有些人还因此被关进监狱,甚至被处死。
间谍有时候确实会伪装成博物学家,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贝登爵士。作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雇员,贝登爵士认为在外国,化装成成天画教堂、捉蝴蝶的愚蠢的英国人是个绝妙的主意,他画的敌方军事设施的地图隐藏在蝴蝶翅膀和叶子的脉络之中。贝登有时候需要把这些素描交给当地治安官检查,这么做也没什么危险,因为这些官僚从来分不清一种蝴蝶和另一种蝴蝶花纹的区别。
博物学家,或者以博物学为副业的人有时候也会做间谍,英国反间谍组织的首脑麦克斯韦尔爵士(邦德的老板M的原型之一),另外的工作就是BBC自然历史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和撰稿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雇了一个名叫大卫·康威尔的年轻人为他的书提供鸟类插图,随后让其加入了军情五处在德国的行动。这个年轻人后来写起了小说,这就是闻名于世的间谍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博物学家天生就是杰出的间谍,为了近距离观察,他们常常花费数年工夫,耐心地让观察的动物对自己熟视无睹。他们善于发现细微差别和微妙变化,而这往往是未来动荡的迹象。
我们已经摆脱了冷战意识形态的笼罩,如今的冲突已经转移到了环境问题上—森林过度砍伐、水土流失、水资源减少、食物短缺和非法的濒危野生物种交易等。不同形式的环境冲突加剧了卢旺达、索马里、苏丹、利比亚、阿富汗的战乱。
博物学家从事野外工作,他们最早发现陷阱和危机,提出预警。他们是真正知道每一种蝴蝶的人,而且也能预知蝴蝶扇动翅膀会发生什么。政府要做的不是把他们变成暗探,而是关注他们的发现,也许这样做就能避免一场损失惨重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