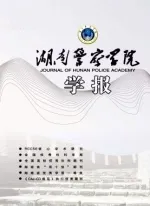农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和出路
2011-08-15李先波杨志仁
李先波,杨志仁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410083)
当代中国农村法治
农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和出路
李先波,杨志仁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410083)
专栏主持人语:三农走向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进程必须跨越的峡谷。
计划经济对三农的束缚尚未彻底解除,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机制已席卷农村。正视农村冲突,梳理农村法治困境,探寻农村政策,反思民间规则,各个角度都使我们在三农这一命题面前惶恐不已。
千丝万缕,唯有一破一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这一思路是明晰的,前景的展示也使人倍受鼓舞。破不易,立更难,在破与立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关注当代中国,请关注当代中国农村!
农村法治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农村法治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为走出农村法治建设困境,加快农村法治建设进程,我国应从以下方面努力: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紧抓发展第一要务,破除城乡二元化格局,实行城乡统筹发展;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农村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尊重农民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确立政府协调、多方推动、共同参与的农村法治建设格局,进一步拓宽农村法律服务渠道;规范基层政权的依法行政工作,努力打造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加强和改进普法教育,建立普法长效机制;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主动依法维护群众利益,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农村;法治建设;困境;出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特别是上世纪90时代以来,法治建设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随着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法治建设成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着力点。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迄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民主法治进程稳步推进。毋庸置疑,法治建设的成绩值得肯定。但是,我国的法治建设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农村的法治建设。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农村法治化占据着重要地位,抓住了农村,也就抓住了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1]
一、农村法治建设的困境现状分析
(一)农村法治建设不平衡性明显
不难发现,我国的法治建设存在较大的地域性差异,法治水平极不平衡。农村法治建设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法治建设明显处于落后状态,农村与城市的法治建设严重不平衡。二是农村之间横向比较,我们会发现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法治建设同样存在差距,不同地区的农村法治建设的水平和发展程度不尽相同,总体而言,法治建设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经济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法治建设的发展状况相对较好,反之亦然。正是由于受限于经济发展状况,相比城市而言,农民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在推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很难参与其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中国现行的法治建设大多数是由具有话语权的城市居民通过各种渠道推动的,农民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要起推动作用,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也影响了农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
(二)与农村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
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对法治进行了界定:“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毋庸讳言,与农村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不够健全,这是农村法治建设中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现行的农村立法侧重于维护农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多数属于原则性的、宣言性的规定,而对于农民具体权益维护等微观方面缺乏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在一些重要领域还没有法律规定,另外一部分法律已经严重落后于农村的发展,没有及时立改废。许多法律规定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色彩,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部分法律位阶较低,完全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2003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八年锁定“三农”问题,一方面说明中央对“三农”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村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健全,还需要用一号文件这种政策形式来弥补相关法律制度的不足。
(三)农村居民法治意识淡薄,信仰权力大于信仰法律
农民的法治意识和观念严重影响着农村法治建设的进程。在农村地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法即为刑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在某些落后地区,一些人仍然将法视为不祥之物,将打官司视为做丢人现眼的缺德之事,尽量远离法律而不是信仰它。在许多人心目中,权大于法是一种普遍的观念。正如有观点指出:现在农民所具有的法律意识基本是模糊的、非规范化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淡薄,对法律存在认识上的片面性,更注重于使用道德力量来调节和解决纠纷,人治意识强于法治意识。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农民普遍接受了性善论,由此导致中国法治文化产生深入开掘内心资源的内倾倾向。这种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农民模糊的、极不规范的法律意识。[3]农民法律意识导致法治观念很难在其内心得到内化和认同,从而不能用法治的观念来规范和指导自身的行为。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4]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在封建社会,国人对权力的崇拜和追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民国时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使这一倾向进一步加剧,建国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破坏,民主和法治遭到严重的践踏,甚至出现了“法律虚无主义”等极端观点。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民习惯了服从于权力,而忽视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权力至上观念较为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观点和思想得到澄清,法律的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法治已经提高到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国人信仰权力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变,这一点在城市体现得比较明显,法律是用来制约权力的法治核心观点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同。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对权力的信仰仍然大于对法律的信仰。这一点可以从以下方面清楚地看出:一是老百姓心中难舍“青天”观念,对于问题的解决总是寄希望于“青天”主持公道;二是农民更喜欢用上访的方式表达诉求,从而寻求问题的解决。在农村,出现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作为受害人的农民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维权,而是通过不断上访反映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实际上,信访反映的问题很多是能够而且应当诉诸法律解决。在法治社会,法律应当是解决一切法律纠纷的最后手段和防线,信访则是解决法律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我国农村地区,使用法律这一武器维权的并不多见,人们对法律缺乏信仰,这是农村法治建设的一大困境。
(四)农民参与法治建设主动性不高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在农村,任何一项制度离开了农民的积极参与都难以顺利推进。可以说,农民是农村法治建设的内在推动力和主要参与者,农民参与的程度直接影响到农村法治建设的成就。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农民对法治建设的关注程度不高、认识不够已经成为了一个较普遍的现象。绝大多数农民对我国整个法律制度体系和诉讼司法体系比较陌生,没有一个比较清晰和系统的了解。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5]从现状而言,在农村普及程度较高的主要是《刑法》和《婚姻法》,对于其他的法律则知之较少,更加没有认识到法律实际上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农民一般不会考虑使用法律武器维权,更不用说主动参与法治建设。
(五)社会矛盾凸显,法治建设难度加大
随着国内外环境境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进入了转型发展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和两难问题日益凸显,利益诉求不断增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管理难度不断加大,这些新特征对我国法治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农村法治建设更是如此。为了化解礼会矛盾,解决突出问题,协调各种利益诉求,维护社和会和谐稳定,各类违法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如部分地方对上访人员采取围追堵截的办法予以阻止,更有甚者则动用司法、行政手段进行不正当干预。在某些情况下,化解社会矛盾、维护补会稳定往往成为了实施违法行为、破坏法治建设的借口。这些观象在法治本就不发达的农村尤为突出,正是这些个不正常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群众对法治的看法,增加了农村让法治建设的难度。
二、农村法治建设产生困境的成因
(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是阻碍农村法治建设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整个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推进,农村的法治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和经济建设和发展水平一样,我国的法治建设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最为典型的是农村的法治建设水平与城市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法治建设领域同样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
法治社会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基础是法治建设的土壤。缺乏肥沃的土壤,法治建设之树定然不能茁壮成长。在我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尚处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较为明显,农村对法治的需求还不够强烈,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法治建设的滞后状况出现。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法治建设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农村地区对法律的需求程度不如城市高,使农村的法治建设与城市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社会经济状况发展的不平衡还会衍生一系列的问题,如受限于经济的发展状况,信息传播速度和方式定然会受到影响。在农村地区,由于互联网的普及程度还不够高,信息传播主要依靠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的途径和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法治建设的发展。
(二)政策的权威性高于法律
在我国,政策的权威性高于法律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影响农村法治建设进程的体制原因。政策是指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和目标而规定的行动准则和行动方向。相对于法律而言,政策具有原则性、可变性等特点,在实施过程中经常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更。依据现代法治理论,法治相对于政策而言,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权威性、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是一种更可靠、更优的治理方式。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更愿意相信政策,相信“红头文件”。在上访等各类反映问题的过程中,依据不是法律法规,而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所制定的有关政策。甚至在一些诉讼活动过程,当事人所依据的也不是法律法规,而是有关政策。不可否认,政策在现代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结构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但是,依靠政策治理农村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由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主体存在多种可能,许多政策没有像法律一样经过严格的程序进行审查和讨论,甚至在合法性方面都存在问题。一些政策,特别是一些地方性政策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法治建设的进程。
(三)农民主体作用发挥不够,多方参与机制尚未形成,缺乏专业法律人推动农村法治建设
在我国农村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农民并没有完全被当做法治建设的主体对待,在许多情况下,农民往往是被动地参与法治建设,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当作法治建设的客体,这严重制约了农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不利于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
任何一项事业要前进和发展必须有推动力量,农村法治建设也不例外。法治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法治建设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顺其自然就能水到渠成的,需要推动者和实践参与者,特别是需要专业法律人的推动。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法律专家、律师、法官、检察官等专业法律人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年来,专业法律人对法治建设的推动和关注多局限于城市地区,对广大农村却缺乏应有的重视。产生这一现象主要是农村地区的法律服务需求不高,专业法律人在农村缺乏广泛的市场。
在农村,农民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受传统伦理观念、利用法律维权成本过高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往往不愿意使用法律这一重要的武器维权。中国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这一点在农村更为明显,一旦发生纠纷首先想到的是找人“了难”,或纠集亲友、族人施压。在熟人社会中,交易并不需要契约,交易双方对彼此的情况十分了解,交易是建立在“情况熟悉”的基础上。正是由于缺乏契约观念,使农村的法治建设举步维艰,正如蒋先福教授指出:“可以把契约文明视之为法治文明的文化源头,或者说,契约范畴是法治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6]中国正是由于“熟人”社会特征明显,“契约”社会的观念尚未完全形成,导致了法治建设发展缓慢。在西方则恰恰相反,罗梭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里,将社会的最理想模式界定为契约社会。可见,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契约观念是普遍存在的,这也是西方法治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如此,导致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出现有关法律事务和纠纷,当事人想到的并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大多数情况下,调解或和解成为了农村解决法律纠纷的重要方式,在当地有威望的人或村组干部往往充当了仲裁者或中间人的角色,专业的法律人根本无法介入其中。许多问题的处理是按照传统的经验,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态度协商解决,没有也不需要专业法律人的介入,纠纷的具体解决也不需要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和法律规定进行。在农村大多数地区,村干部和乡镇司法所的司法员成为了当地的法律权威人士,在解决具体纠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们许多都是兼职,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自身并不见得懂多少法律,整体法律素质偏低。
此外,在农村地区,司法机构仍不健全。农村地区最重要的司法机构是法院的各类派出法庭,然而,法庭也不是每个乡镇都有,在许多偏远的乡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不仅法庭稀少,法官等专业法律人才同样奇缺,许多地方百姓打个官司都可能要跋山涉水,极为不便。法律援助等重要的惠民制度在广大农村地区落实的并不尽人意,除部分刑事案件外,农村居民能够得到法律援助的比例极低。
(四)基层政权对依法行政重视不够
经过多年法制宣传和教育,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法治观念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仍然没有达到让人满意的程度。特别是在农村,部分基层干部缺乏应有的法治观念,对依法行政认识不够、重视不足,依法行政并未落到实处,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仍有发生。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农村地区,征地拆迁和新农村建设在农村如火如荼的进行,绝大多数的事务性工作都落在乡镇一级的基层政权身上。基层政权负责具体与人民群众打交道,他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部分基层政权法治观念淡薄,工作作风过于简单和粗暴,开展工作和执法脱离了法治的轨道,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一旦基层政权不依法行政、甚至出现明显违反法律的行为,将严重损害法律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破坏法治建设的正常进行。
(五)普法教育流于形式
随着全民普法教育活动的深入推进,广大农村地区的普法教育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农民可以通过电视、报纸、各类法律书籍以及法律宣传等各种途径获取有关法律知识,接受普法教育。然而,我国的普法教育并没有完全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开展,许多普法教育往往是运动式的,有流于形式的嫌疑。首先,农村普法教育没有注重其实质内容和效果,没有根据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需要来进行,普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普法注重的主要是说教,侧重于教育农民遵守法律、不要违反法律以及违法的后果等,而不是从根本上培养他们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其次,农村普法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有局限性。各种传统媒体和方式在农村的普法教育中占据绝对统治的地位,普法宣传的方式和载体较为单一,受限于农村的实际情况,像网络这样的新型方式在农村的普法教育中仍然少见,简单的说服教育宣传成为了普法宣传的主要方式。再次,农村普法教育缺乏长效机制。2006年开始的“五五”普法规划首次将农村地区的普法教育作为今后五年的一个重点,对农村普法教育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农村普法教育的长效机制并未完全建立起来。现阶段,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法律的专业性比较强,普法教育还难以做到让大多数的农民能够理解法律的精神实质,许多情况下仅仅是一种机械性的接受,这也是我国普法教育的一个客观现象。
三、农村法治建设的出路
(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紧抓发展第一要务,破除城乡二元化格局,实行城乡统筹发展
农村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是农村法治建设不尽如人意的经济基础,要提升农村的法治发展水平,关键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快农村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发展是解决农村法治建设相对落后的总钥匙。法治建设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能离开经济基础的。要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农村社会经济的飞速和可持续发展。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不仅是市民社会的生长点,而且也是判定市民社会程度的标志。因为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主体的独立与自由,权利和地位的平等,市场经济能增强社会主体的民主法治意识和能力,从而培养农村市民社会的主体。[7]现阶段,可以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借助市场手段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方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农村地区发展,尽量减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为农村法治建设奠定经济基础。
(二)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农村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
完善与农村有关的法律制度建设。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有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有关农村的立法应当与时俱进,及时进行立改废,确保与农村有关的法律制度符合农村发展的需要。一是要废除和修改与农村发展现实不相符合的法律法规,确保法律能够适应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户籍制度改革有关的法律一定要跟上时代的发展;二是要正确处理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尽快将有关政策转变为法律,增加其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特别是那些经过实践检验已经成熟的政策,应当尽快将其转化为正式的法律法规,从而减少政策与法律之间所产生的冲突,维护法律权威。三是要着重制定与农村密切相关的法律,如尽快制定农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将近年来一号文件的有关精神和做法转变为法律规定,弥补制度空白。
建立健全农村司法机构。注重农村司法机构的合理架构。进一步加强人民法庭和基层司法所建设,特别要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个方面加大对农村地区人民法庭的建设,最好是能够借鉴公安派出所的模式,实现警力下沉,确保农村地区司法机构能够正常运行,保证农民能够便捷的行使诉讼权利,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司法为民”。
突出法律在农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一直以来,甚至在将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政策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产生了显著的效果,这是不容否认的。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应当实现从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向主要“依靠法律治理”转变,突出法律在整个农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树立法律的权威,发挥法律的应用功能。
(三)尊重农民在农村法治建设的主体地位,确立政府协调、多方推动、共同参与的农村法治建设格局,进一步拓宽农村法律服务渠道
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是法治建设的主体,这一点必须得到承认和尊重,应当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农民开创农村法治建设新局面。
为了更好地推进法治建设进程,应当积极地采取措施,拓宽农村法律服务渠道。只有让农民从法律之中获得真正的实惠,他们才能真正认识到法律的价值,才能改变对法律的看法,才能理解法治建设的必要性。从现阶段农村的现状出发,确立政府协调、多方推动、共同参与的农村法治建设格局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加大对农村的法律援助力度。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该制度对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有着重要的作用。农民由于受到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亟需法律援助制度的支持和帮助。因此,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加大对农村的法律援助力度。
二是加大法律专业人对农村法治的推动力度。进一步拓宽法律服务渠道应当采取政府主导下的专业法律人积极参与的模式。政府应当在这一过程中起主要推动作用,将其作为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手段,法官、律师、法学专家学者等专业法律人也应当增加积极性和主动性,配合政府的相关行为,将推动农村法治建设作为专业法律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是要进一步推行诉讼收费制度改革。在农村,许多人不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打官司花费过大,诉讼成本不是普通农民所能承受的。政府应根据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采取相应的措施,缓收、减收或免收有关诉讼费用,保障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诉讼权利,不使他们因交不起诉讼费用而被司法机关拒之门外。
四是要支持和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建设,如尽快推行公益诉讼制度。
(四)规范依法行政工作,努力打造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规范基层政权的依法行政工作,进一步改善农村的执法体系是提升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途径和任务。农村基层政府在权力运作中必须规范,要把法律的公正性原汁原味地呈现给农民,做到司法与行政的统一,彰显司法公正。同时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建立顺畅的民意表达机制,让农民有公共政策制定权、意见表达权、权力监督权,促进新农村法治建设。[8]规范基层政权的依法行政工作,首先,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法治教育和培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良好的法律政策制定之后,执行就成了关键,而具体执法的人员则是关键的关键。加强基层干部的民主法治培训,提高他们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有助于法律的良好执行,并能在人民群众之中树立法律的权威,增加他们对法律的信仰,推进法治建设进程。其次,全面规范基层政权的行政执法行为。这一点,我省的有关做法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008年以来,我省先后制定和起草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以及《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征求意见稿)》四个重要法律文件,虽然这些法律文件并非是针对农村的依法行政,但是农村基层政权的行政行为同样是其规制对象,这些规定对农村的依法行政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湖南的做法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来推广湖南的先进经验,规范基层政权的依法行政行为。再次,加强对基层政权依法行政的监督力度。有关公权力机关以及新闻媒体等应当加大对基层政权依法行政的监督力度,促进依法行政在基层的顺利推进。
(五)加强和改进普法教育,建立普法长效机制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加强法治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9]现在,我国政府正在实施五五普法规划,普法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农村,由于信息传播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农村的普法教育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从现状而言,农村地区的普法教育仍然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的必要,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第一,改运动式的普法教育模式为有针对性的模式。我国的普法教育形式上轰轰烈烈,呈现出一种运动式的形式,但是在实质内容上,普法的针对性并不强,并不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导致实际效果甚微。现阶段,农村的普法教育并不适合宣传具体的法律法规,而应侧重于培养农村的法治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农村的具体实际,宣传一些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激起农民参与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要侧重于加强农民的法治意识和思维的培养,不能将农民作为法治建设的客体以及被教育对象,而要将农民作为法治建设的主体来对待。
第二,改进农村普法的的方式和途径。普法并不是板着面孔的说教,而应当采取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如法律咨询的方式就很好,也能够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宣传法律法规必不可少,但不应成为普法教育的全部。知晓法律只是普法宣传的目的之一,农村普法的最终目的是使广大农民知法、守法、用法,进而为农村法治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具体方式和载体方面,要以多元化的方式和载体宣传法律,充分发挥多种宣传媒介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要合理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介来改进普法的方式和途径。
(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主动依法维护群众利益,提升法治建设和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过多的社会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样也不利于法治建设的顺利推进。化解社会矛盾,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法治建设和礼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抓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加大力气,完善农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主动依法维扩群众利益。既要维持农村地区现有的诸如调解、和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机制,同时也要引导农民使用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要注意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创新和发展,有些地方确立的“法官工作站”、“巡回审判点”等制度就属于对诉讼制度的有益探索。要对各种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进行相应整合,实现对接不能将其对立起来,而要建立有机联系、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多元化解机制。
农村法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农村的发展和整个国家法治进程的顺利推进都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积极探索。农村法治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单靠某一方面和某一种力量就能轻易前进的,我们需要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整合相关力量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我们相信,只要全社会高度关注、重视和支持农村法治建设,不断为农村法治献计献策,农村法治定能在不久的将来顺利实现。
[1]阳相翼.农村法治化进程中的障碍性因素分析[J].行政与法.2007,(2):33.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99.
[3]顾明,李树远:论新农村法治建设中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9):80.
[4]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北京: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28.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蒋先福.契约文明:法治文明的源与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9.
[7]李小红:论农村市民社会建构对农村法治建设的价值意蕴[J].商业时代,2010,(3):15.
[8]周忠.苏中地区黄塍镇新农村法治状况调查与研究[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1):15.
[9]邓小平文选(第2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Abstract:The ruling-by-law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socialist country ruled by law.In recent years,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ruling-by-law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while confronting with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To walk out of the predicament an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rural ruling-by-law construction,we should make our effort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fu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ruling-by-law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put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place,break the dual rural and urban structure and plan th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s a whole;strengthen rural legal construction,improve rural legal system,and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of law;respect farmers'supporting status in rural ruling-by-law construction,establish the pattern of ruling-by-law construction with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and common participation,further widen channels of rural legal service;standardize the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of grassroots regime and set up law-based and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Strengthen and improve education to popularize law and establish sustainable mechanism of popularizing law;improving solving mechanism of contradiction and disputes,initiatively maintain the benefits of the mass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upgrad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social management.
Key words:countryside;ruling-by-law construction;predicament;way-out
(责任编辑:叶剑波)
Predicament and Way-out of Ruling-by-law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LI Xian-bo,YANG Zhi-re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410083,Hunan)
D902
A
2095-1140(2011)01-0012-06
2011-01-21
李先波(1963- ),男,湖南慈利人,湖南警察学院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法研究;杨志仁(1984-),男,湖南湘潭人,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