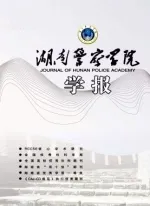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与农村安全
2011-08-15郭亮
郭 亮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武汉 430074)
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与农村安全
郭 亮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武汉 430074)
土地集体所有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为农户尤其是弱势农户提供了规避市场风险的手段,从而保持了中国农村的稳定和安全。然而,由于物权化的承包关系、政治权力对土地权利的干预以及基层组织自身的不作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正在丧失。在这种条件下,土地制度必须从中国现代化实现的战略高度进行重新统筹和安排,避免制度本身的单一与僵硬,以给不同地区农户的土地承包留下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和决定权。
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安全;社会保障
被世界誉为当代中国奇迹的有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地以年均约10%的速度持续增长。显然,这两个奇迹都与中国农村有关,并直接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安排下所发生。对于前者来说,中国的土地完成了基本的生产功能;而对于后者来说,这种土地制度则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输入低成本的劳动力提供了可能。尽管从产权的理论出发,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具有产权主体不清晰的特点,但是这种制度安排所具有的社会效益远非经济效益理论所能涵盖,它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稳定的最关键制度保障。
一、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践与功能
在农村改革时,农村土地制度被政策表述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是农户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和集体享有土地所有权的统一。从农地制度的实践来看,保留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不仅仅具有意识形态延续性的需要,而且具有重要的生产和社会正义功能。在村庄中,土地集体所有有着两种重要的表现形式:第一,村委会或村民小组所代表的“集体”经常性地介入到农业生产中去,进行水利灌溉、农业道路维修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的基本秩序;第二,“集体”根据村庄人口的变化定期地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即所谓的土地调整。在这种制度形态下,村庄中每一位现有的及新增加的成员都享有土地分配的资格,土地就此发挥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功能。因此,尤其是在人多地少的农村地区,农户对土地调整有着更为强大的诉求。从农业部1998年对全国6省824户的调查资料来看,曾经调整过土地的农户为751户,占到总样本的91%,最多的调过8次,全国的平均调地次数达到2.31次。[1]
中国目前有大约2亿左右的农民工,由于无法制度性地融入城市,他们往返于城乡之间。在全球的产业链条中,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处于产业末端而只能享有较低的产业收益,企业通过压低工资水平的方式来取得有限的利润。一直以来,作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农民工之所以能承受这种工资水平,并且不享有任何的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障,正在于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并没有和农村的土地割断联系。一般情况下,20-3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是当前外出务工的主要人群,他们的工资能够满足自己的消费,但不可能在城市中谈婚论嫁、生儿育女。外出务工者自己虽然脱离了农业生产,但他们的家庭成员却仍然在土地上劳作。也就说,正是留守在村庄中的家庭成员和外出务工者共同的辛勤劳作,一个家庭才能正常地维系、发展下去。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缺失了外出务工的收入,农民家庭只能维持温饱;而缺少了家庭成员依托土地的收入,则无疑会极大地增大外出务工者的货币支出,这甚至是打工的收入所不能弥补的。
土地的“非集体化”并不意味着土地保障功能的丧失,而是说,在外出务工的背景下,改变土地资源的配置方式,即由分配转向市场交易的方式将增加农民的生存风险,尤其是对于村庄中的“弱势农民”而言。显然,如果土地的获得仅仅依靠自由交易而缺少行政力量的纠偏的话,那么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使得土地的分配必然产生不均,尤其是当资本下乡时,农户的个体“理性”难以抵挡资本和权力相互裹挟的诱惑和压力。在这种条件下,弱势的农户容易迫于经济需要而出让土地,从而在为自己进城积累资金的同时,也将自己置身在了城市生活的风险之中。在国家和社会不能为其提供保障的现实条件下,他也割断了自己与村庄的制度性联系。与之相反,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下,土地的获得是按照人口定期平均分配的结果,只要还具有村庄的成员权,农户就能获得土地,这保证了起点的公正。同样逻辑,在一部分进城农户真正地“非农化”完成之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就要求他们放弃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将土地保持在村社内部。对于外出务工且终究要返回农村的农户来说,村社的集体所有为其保留了再次获得土地分配的资格,这意味着,即使他们在当下不耕作土地,但这种资格的存在却让他们能够安心地在城市中工作。这样,在农户的个人理性之上,还有一个“集体”在为其保驾护航,这正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衍生出的一个重要功能。
土地集体所有制面临着“谁来代表集体”的问题,在农地制度的实践中虽然不乏村干部谋取个人好处而偏离农户整体利益的事实,但是,村干部的问题却不等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问题,前者可以通过基层组织和基层民主的建设来完成,土地集体所有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却不能因此废弃。在一定意义上,不管是出于国家的主观塑造,还是被动地产生,“出可进城、退可回村”的一种弹性城乡互动机制是改革开放以来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安排,而这种机制正是依靠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来实现。
二、土地的集体所有权的虚化
随着土地承包权“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实施以及税费改革、粮食直接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悄然发生了变更。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虽然仍然被表述为集体所有,但在现实中,这种“集体所有”的内容却已经被架空,其主要面临着三种力量的严峻挑战。
(一)物权化的土地承包关系束缚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表现形态
2002年,我国《土地承包法》出台,土地承包关系上升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关系,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则将土地承包权利界定为物权关系。随之,村组“集体”对土地调整、转包等一系列权利在法律上被杜绝。由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被彻底贯彻,在许多农村地区,一些农户在女儿出嫁之后仍然占有一份土地,而另一些农户在儿子结婚、生子后却得不到新分配的土地,人地之间失衡的局面开始严重。年轻的农民工已经娶妻生子,但新增加的人口却无法获得土地,当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时,村庄却也对他们关上了回去的大门,由此必然会使得他们在年龄较大而不适合继续在外打工时陷入困境。在当前,农户对土地不再调整的情绪仍然较为强烈,围绕着土地调整的上访事件也较为频繁。
此外,土地利益结构的僵化也给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造成了障碍。农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是“水”和“路”的问题,但修渠、修路必须占用耕地。如果土地能够调整的话,被占地的农户可以通过日后的土地调整而重新获得土地。如今在土地变动不可能的条件下,一方面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村委会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而无法对农户进行补偿,而另一方面农户损失一丝一毫的土地都不可能在以后通过土地调整再次得到,农户自然就不愿意以损害自己的利益为代价获得公共收益。在笔者长期调查的江汉平原,因无法达成修路或抽水的协议而致使许多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无路可走或无水灌溉事例并不新鲜。
(二)遵循官僚逻辑的权力介入破坏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保障功能
一直以来,土地的适度流转为中央的土地政策所鼓励。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土地流转更是被提上了各级政府的议事议程。农户之间基于自愿的土地流转能够遵循市场配置,从而弥补土地调整所无法发挥资源配置效益的不足。然而,一旦土地流转成为了“政治正确”,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人为地加速推进土地流转的速度,以实现城市化建设和农业的规模经营。面对政府的行政压力,农户的土地流转与其说是自愿的流转,不如说整个农业生产条件已经被破坏的情况下的被迫选择,这种土地流转的规模和速度显然超过了农户实际的承受能力。而且,和农户之间一种自发的土地流转不同,政府推动的土地流转一般是长期限的土地流转。当土地流转出去的时候,农户即使能够得到一定的租金,这些租金却往往并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正常开支。农户必须直接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生存的风险系数加大。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村委会无法抵抗上级的权力介入。随着土地被大规模流转出去,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村委会不再能通过土地的分配为农户提供安全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流转的速度和规模必须与整个城市化的进程相协调。也就说,城市化的推进不应只是城市地理范围的扩大,而且能够为失地农民和外来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诸如养老、意外伤害、疾病治疗等和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真正实现城市化的发展。在这个前提不存在的条件下,农村社会中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必须要谨慎。
(三)基层组织的不作为极大地压制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随着“三提五统”以及农业税费的取消,农民负担大为减轻。农村的基层组织不再可能通过多收税费等手段侵犯农户的利益,但是,集体积累的丧失也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组织陷入了“半瘫痪”的状态。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力度虽然不断加大,但大部分资金却投向了大型的水利设施、道路建设等,小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只能依靠村委会的组织和动员完成。由于不收取税费,一方面使得乡村两级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捉襟见肘”,只能坐等上级的“项目援助”;另一方面也使得乡村干部没有了为农户解决生产问题的压力和动力。于是,农户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诸如抗旱、排涝等生产问题。2007年笔者在豫东平原调查时发现,为了灌溉和排涝,当地几乎每家每户都买有水泵和上百米的水管,以方便从河道中抽水或放水,这极大地增大了农户的生产成本,而且,对于一些偏远的农田而言,这种方法根本无济于事。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农村基层组织能够经常性地介入到农业生产中去,从而解决单个小农家庭所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以排涝为例,由于缺少公共的排水渠道,如果一户农户要排水的话,就必须要从邻近的农田中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完成如果单独依靠农户之间的自愿协商,就极不容易达成,行政权力的统一组织和协调正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组织保障。在乡村组织退出农业生产领域之后,这种农业生产秩序的完成难度被无限地放大了,个体的小农的劣势被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
三、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与农村安全
在一系列法律、政策以及现实的政治条件下,土地集体所有制度越来越模糊,尽管还保留集体所有的名义,但土地制度的实践却丧失了集体所有的必要内容。在沿海发达地区,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量的土地被征用,村委会作为土地产权的代理人而得到了大部分的土地补偿收益,失地农户则只能得到有限的“青苗补偿费”。基于此,对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质疑以及建构一种私有产权的呼声更是日益高涨。但问题是,土地的被征收与当地的地理位置和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广大的以农业为主的中西部农村根本不具备这种条件,缘何要以牺牲大部分地区、大部分农民的生存保障为代价来捍卫少部分地区、少部分农户的利益?进而,对土地制度的设计仅仅是着眼于解决局部地区的当下问题,还是要从中国现代化整体战略的角度去统筹安排?对这些问题的各自回答正代表着对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不同认识,并预示着对制度走向的不同判断。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必须进行准确的定位,并权衡利弊,否则必将影响到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基础性秩序。
2008年底,全球范围内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我国沿海地区大批加工制造企业的减产、倒闭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量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一度引起政府以及社会普遍的恐慌。然而,农民工的顺利返乡却化解了其有可能滞留城市的危机,农村再次发挥了“稳定器”与“蓄水池”的作用。幸运的是,当前土地集体制度的转型尽管在发生,但其后果还并没有显现出来。而且,在制度表达上,土地仍然为集体所有,这些都为土地制度的及时调整与修正留下了空间。笔者无意于对土地制度的基本走向规划蓝图,但却坚持认为,在差异巨大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设计不能过于僵化,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都应该给农户的土地承包留下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和决定权,从而拓展土地承包的多种样态。在此基础之上,充分认识到土地制度的运行乃是一项社会系统性工程,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权力的运行监督等制度建设对于建构一个良性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制度都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1]赵阳.对农地再分配制度的重新认识[J].中国农村观察,2004,(4).
Abstract: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is of important social function,which provides means of avoiding market risk for peasants especially those in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and thus guarantees th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the countryside.However,due to the contractor-ship of real right,intervention into land right by political power as well as omission of the primary organizations themselves,the advantages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are disappearing.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the land system must be planned as a whole and rearranged from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of realization of modernization,avoid singularity and inflexibility of the system itself,so as to leave certain autonomy option and decision to the peasants'land contract in various regions.
Key words: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rural security;social welfare
(责任编辑:叶剑波)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and Rural Security
GUO Liang
(Law Schoo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430074,Hubei)
D902
A
2095-1140(2011)01-0042-03
2010-11-26
郭亮(1981-),男,江苏沛县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和土地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