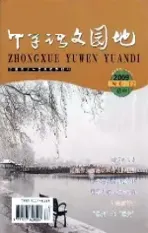毛泽东《十六字令》考
2011-08-15戴筱林
戴筱林
谁都知道,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曾写过著名的十六字令词:
其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谰。奔腾急,万马战欲酣。
其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根据1968年版《毛泽东诗词注解》(贵阳版)第85页记载,此词写于1934到1935年之间。笔者以为:就写作时间而言,两年之间成就三首词的具体时间尚须考证,写作背景也不得而知。下面就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写作背景作一点考证。
一、关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
这三首词到底是某一段特定的时间写出来的还是跨年度写出来的呢?笔者认为是某一特定时间内写出来的比较合理,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文学角度来分析。如果这首词是毛泽东同志两年之间才成就的,段与段之间自然会产生脱节现象,因为跨度时间长,这三首词就不一定能表现出完全相同的主题。“这些词都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从全词来看,这三首词不像是三首而是像三段。不仅三首词主题相同,都是写“山”,而且好像故意安排了层次。第一段写的是人生奋斗的速度和力度,表现出的是一种“快马加鞭”的喜悦。第二段由山势联想到海势,这是站在高原上才会产生的视野,山奔腾似马,像千军万马混战了起来。词中一“酣”表现出军事指挥人员的意气风发。第三段把山比喻为剑,青天都被刺破了而剑锋未损,这是写山的耐性;后一部分赞美了山顶天立地的壮举,天要塌下来的时候,正是山起了“擎天”的作用。三首词或赞美山的作用,或歌颂指挥员的意气风发,或抒发“快马加鞭”的奋斗情怀,显得一气呵成,毫无脱节破碎之痕;而且,一二段可以看成是“因”,第三段是果,三首词因果联系相当紧密,看作是在特定时间内写出的赞美特定事物比较合理。
第二、从“诗言志”的角度分析。上述山的意象为人,在1934至1935之间,毛泽东作为直接军事指挥人员是在“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以后的事,即遵义会议后的苟坝会议,现据史学家费侃如论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应当是1935年3月12日在苟坝成立的,这样分析就和全词的意境紧密的衔接起来了。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被排斥在中央领导集体之外,只挂一个“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虚衔,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后来为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攻取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偃一带之守敌”,才成立三人团。毛泽东同志再次和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不同,有史料为证:“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了。但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促成了苟坝会议的召开,苟坝会议实际上成了继遵义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才真正决定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红军中的核心地位,“三人团是具有最高军事指挥权,‘在当时是全党全军中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正是这种特殊的军事背景和政治背景构成了毛泽东《十六字令》词的生命。不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对打鼓新场守敌和周围敌人的了如指掌,中央红军有可能再一次陷入敌人的包围圈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缜密地分析和注意到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把上面史料作为《十六字令》的写作背景就和主题思想紧密衔接在一起了,山的意象更加清楚,诗的“言志”更加落到了实处。我们据此可以断定,这三首词的写作时间当是1935年3月12日苟坝会议以后,而且是在一段时间内写成的。更何况1934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的毛泽东是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人之外,他本人只能眼睁睁看到红军的大幅度减少,怎么会有“快马加鞭”的喜悦、“万马征战”的得意和“以拄其间”的作为呢?实际上,《毛泽东诗词注释》1968年贵阳版已把《十六字令》安排在1935年2月写成的《忆秦娥 娄山关》之后,很大程度上已经把他定性为1935年的作品,而且是在2月以后,这是有史学根据的。
二、关于这首词写作地点
《十六字令》词引毛泽东原注如下:
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
该书著者说“八宝山,在贵州省雷山县。据《贵州通志》记载,八宝山与太平山‘相连如屏,三面绝壁,无路可登,惟南面稍平,鸟道羊肠,人迹罕至’”。骷髅山无注释。
笔者认为这个注释有待商榷,八宝山不在雷山县而在金沙县。理由如下:
从时间上来讲,我们已经考证出成词时间是1935年3月12日以后,即上述所说“苟坝会议”以后,这时的毛泽东在金沙县内外活动,与雷山县无关。《金沙县志》记载,3月28日,军委三局由遵义底坝出发,入境经老木孔至大岚头宿营。左路由军委领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中央直属队和一军团经底水、弯子场进驻沙土街万守宫。3月31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主力红军经后山抵大塘河渡口南渡乌江,进入息烽县境。12日到28日,中央红军主要进行的是三渡和四渡赤水的战斗(3月16日—17日中午,从茅台附近三渡赤水,21日—22日早晨四渡赤水),之后是南渡乌江的长途行军。上面的行军打仗和雷山毫无丝毫关系,况且红一方面军从黎平进入贵州,连续攻克锦屏、剑河、台江、镇远、施秉、黄平、于庆等八九座县城,没经过雷山,因此不可能将雷山的八宝山写入词中。金沙的八宝山于情于理倒十分吻合:其一是毛泽东同志经过金沙的时间是3月28日—3月31日,是在“三人军事小组”成立之后,于理可讲;其二是八宝山山脉是乌蒙山脉的分支(《金沙县志》72页载,八宝山支脉属乌蒙山系)。县内后山乡和长坝乡之间的马鬃岭、六角大山属八宝山支脉分支。县内最高峰海拔高度为1884米。毛泽东同志所经过的金沙县境基本上都是八宝山支脉的分支。综上所述,《十六字令》当是毛泽东同志1935年3月底所作,词中所描写的即是自己亲自所见、所走过的金沙八宝山。至于骷髅山的诠释,当是乌蒙山为恰当:一来乌蒙山与八宝山的关系正好是上下关系,和毛泽东“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的原注相吻合,二来我们进一步可以想见,一个操湖南湘潭口音的人,会把乌蒙山谐音为骷髅山确实是有可能的。而且,用骷髅山入诗更能增加环境的险恶和诗的况味,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诗歌中惯用的技巧。《十六字令》后,毛泽东于1935年10月在陕北写下了《七律·长征》,乌蒙山得到了正名。
综上所述,毛泽东《十六字令》三首当是1935年3月12日—3月底所写,表现的是贵州金沙乌蒙山脉八宝山支系的盛景,抒发的是东山再起,力挽狂澜的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