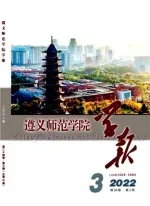新时期黔北文学艺术风格略论
2011-08-15王刚
王刚
(遵义师范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以何士光、李发模、石定、李宽定等为代表的新时期黔北文学于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分析他们的艺术风格,展现新时期黔北文学的魅力,对于当下文学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描写黔北的自然环境,铺叙黔北的风土人情,塑造黔北的人物形象,是蹇先艾、寿生、石果、廖公弦等现当代黔北作家形成的的传统,新时期黔北作家延续了这一传统。他们以黔北的山川河流、乡风民俗为背景,演绎具有黔北风味的故事,刻划像黔北的大山那样朴实厚重的乡民形象,形成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学流派。
一、俊逸与雄奇:心中的黔北乡土
新时期的黔北作家,不管是成熟于20世纪 80年代初期的何士光、李发模、石定、李宽定、司马赤,还是20世纪 80年代中期涌现的赵剑平、戴绍康、宋渤、龚光融,都对黔北的乡土一往情深。他们以虔诚的赤子心灵,敏感的艺术触角,描摹着心中的黔北山川,颂扬着他们的父母之邦。同样是对乡土的映现,何士光、石定、李宽定心中的黔北蕴藉着恬淡而静谧的情韵,赵剑平、戴绍康笔下的山川渗透着险峻而神奇的气质,宋渤、司马赤、龚光融却描写黔北的城镇和市井,在对市民生活的描写中透露出浓郁的黔北风味。
“露水回来了,在清晨和傍晚润湿了田埂,悄悄地挂上了草尖。露岚也来到了坝子上,静静地浮着,不再回到山谷里去。阳光虽然依旧明亮,却不再痛炙人的脊梁,变得宽怀、清澄……。”[1]这是何士光笔下黔北的秋天,淡雅而俊逸,宁静而澄远。李宽定即使写一坝水田,也极力突出它的诱人之处:“春天象一块绿锦,秋天象一匹黄锻;冬天,亮晃晃地象半面大圆镜。”石定注意诗情画意的渲染:“长溪清澄如练,田坝空阔而安宁”,“田湾里浮着薄薄的雾气,浮着快要黄熟的稻谷的清香”,“山径上落叶黄花堆积,恰好是碧云天。”李发模的《斜风细雨》:“如薄暮垂幔,如鸟啼青枝/淅淅沥沥,淅淅沥沥/温柔的斜风细雨/多情斜风细雨。”
显而易见,以上描写流溢着浓郁的诗意和浓郁的黔北乡土味。那是未受现代文明感染的静谧乡村,是古朴而久远的现实,是真实而自然的存在,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向往的家园。经受过“文革”磨难的何士光、李发模、李宽定、石定也在这宁静淡远的自然形态中获得过某种慰藉。那时,他们或许一边惶恐着浩浩尘世的尔虞我诈,一边慨叹着黔北秀美山川宽厚仁慈的胸怀;或许一边虔诚地反省着自己批判着自己,一边在大自然中寻找着生活的力量美的源泉。于是,当他们能够以文字符号作为仕达生活感受的媒介之时,他们就将真情流泻在对黔北山水的描绘之中,就将感受到的大自然美的情韵用精心选择的文字和句式表达出来。因此,尽管他们也写生活的沉重,也写日子的艰辛,但是,那柔美的自然形态总给阴郁的生活抹上一层温馨的色彩,给人以慰藉和希冀。在那些礼赞传统人性、昭示生活希望的作品中,这种对自然的诗意描写更是烘托出柔美轻快的氛围,使作品具有散文诗的气质和品性。
这类作品的文人气息较浓,在艺术上规范化程度较高,对生活的艺术处理比较深入,因此显得端庄秀丽、雅致滢澈,富于诗情画意,有灵气、有风韵。同时,注意语言的魅力,让人们在语言的修辞、词语选择,语言的排列组合、句式安排中欣赏到美,表现出作家们诗化生活的自觉意念。这类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或引起轰动,由此,人们自然将新时期黔北文学的风格定为柔美。
试图突破黔北文学柔美风格,展示黔北山川浑厚壮美一面的是赵剑平和戴绍康。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疾速进程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急剧变化。改革是空前的、宏大的,也是艰难的、凝重的,险峻宏伟的山川才能与改革的宏大气势相对应。在赵剑平与戴绍康的笔下,自然界险峻而神奇——这里峡谷幽深,崖壁峭拔,泥沼无情;这里群山巍峨,洪水湍急,山道崎岖;原始森林中驰骋着熊罴虎豹,自然界里风雪雷电变幻莫测。
除了自然景观的真实再现之外,赵剑平还将大自然视为人类社会的对应物,将人类心灵投射于自然景观,体现某一思想观念,从而让它加入作品的叙事结构,起到组织情节、深化矛盾的作用。《峡谷人家》那闪烁着阴沉光芒的老岩,《两个牛贩子》中荡涤人物心灵的滔滔洪水,《雾峡》里净化人性的漫天大雾,在作品中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戴绍康将自然看作作品矛盾的主要方面之一,在展示社会矛盾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的错综关系和深刻矛盾。中篇小说《在故乡的密林里》表现人对自然的困惑、无所适从和无能为力,显示出传统的黔北人在改革进程中的惶惑和冒进。在《地热》和《滚厂》中,这种困惑消失了,人们用智慧开发利用大自然,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具有刚强性格的改革者。
长于表现黔北市井生活的是宋渤、司马赤、龚光融。黔北的乡镇躲在大山深处,依山势而建,青瓦木房,与世隔绝,自成独立的社会系统,地方风味浓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格局。司马赤所描写的清流镇就是黔北乡镇的典型代表。在这民风淳朴的清流镇上,活跃着许多打上地域烙印的各色人等:有出自民间的县长、局长,更有民间的“铜锣会长”、“礼宾组长”、“口头文学家”、“民间书法家”、“三朝老人”、茶馆老板、屠宰师傅、理发匠、铁匠。通过这些独具个性的人物,通过他们之间发生的生动故事,司马赤为我们描绘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黔北乡镇特有的风情,用文字保留下珍贵的地方习俗和地域生活场景。宋渤以遵义城的自然风物、历史文化作为故事的背景,以发生在遵义城的故事为小说的线索,以生活在遵义城的真实人物为故事的原型。因此,他的小说既描写了遵义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展现了遵义八十年代的风土人情。龚光融写城镇小巷中的市井人生,写补锅匠、马车夫、街道主任,即使写到知识分子,也将他们作为下层社会的一分子来描写,写他们平凡琐碎的生活,形而下的情感际遇。
二、传统与现代:转型时期的黔北人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黔北民众的“观念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的个性与其生长的大山的环境密切联系,他们是大山之子:“雄奇险峻的山水,造就了贵州人胸中具有千山万壑的气魄;秀丽的风景和湿润的气候,孕育了贵州人的灵气和聪慧;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落后的经济,则磨砺了贵州人的坚韧;复杂多变的地形和气候,众多的民族,造就了贵州人的思辨能力。”对于民众,大山既有丰厚的赐予,也有因大山而形成的落后的一面:“在‘造就贵州人胸中具有千山万壑气魄’的同时,说不定又会因山川阻隔而产生某些狭隘的观念;在‘灵气和聪明’的背后,又难免有些固执和憨厚;在‘坚韧’之中,既能吃苦耐劳,又免不了安于现状;富有‘思辨能力’,似乎在理性思维上又有所不足。”[3]
黔北的民众就是这样,他们传承了大山的气魄和灵性,也被大山遮住了视野。他们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浑身散发着泥土的气息,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重负。他们忠厚木讷、沉默寡言、忍辱负重,他们善良纯朴、仗义执言、重义轻利。他们是传统型的人物,有传统的情义美与道义美,有传统的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在新时代的曙色里,他们被新的时代观念潜移默化,产生了对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希冀和追求。黔北作家抓住了时代转型期这一让人心灵激荡的时刻,通过这些朴实山民心灵微妙的变化,表现改革所引起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浓郁的时代色彩。
李宽定、石定注重地域与时代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仅以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为例:李宽定《良家妇女》中的杏仙争得婚姻自主是由于中国政治革命成功的时代背景。然而,作者深刻地认识到,杏仙们的胜利不是追求的结束而是追求的开始,因为大山深处的山民们还有因地理条件形成的因袭的重负。一旦政治出现偏差,时代脱离正常的轨道,沉渣就会泛起,她们就会在风云变幻中无所适从。“文革”中长大的姑娘白素(李宽定《小家碧玉》)就因其出众的姿色被无数双贪婪的眼睛窥视着,权势者们凭藉权力千方百计想成为她的主宰。改革之初,黔北农村的气息还是凝重的:黔北的女儿家缺少追求的自由——春儿仅仅是趁月色下河洗了一次澡,却在村里引起轩然大波,她不得不离家出走(石定《水妖》);云儿不愿按传统女儿家的程式生活,由此被视为异类,默默地承受着孤独(石定《牧歌》)。
黔北山民就这样默默地生活着,他们既要背负起几千年封建观念的沉重包袱,又要受小生产者狭隘眼光的局限,还要受偏离正常轨道的政治的左右。改革初期的黔北,即使有田园牧歌式的温馨,也抺不去因袭的停滞凝重的印痕。
在时代不可遏止的曙色的爆发中,黔北山民从昏睡中惊醒。但是,并非生产责任制一落实,人们就能义无反顾地在改革之路上迅跑。他们面临的经济观念、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的变革。前面所述春儿、云儿的形象已经表现出思想观念转变的艰难,冯幺爸(何士光《乡场上》)、王老汉(石定《公路从门前过》)等形象较为准确地概括出黔北农民心态的这种历史性演进。
这种演进是深刻的、痛苦的,它将舍去人们许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将人们引进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领地;这种演进是细腻的、微妙的,是时代促成的自发现象,是带着心灵重负向过去告别;这种演进又是最普通的,最平凡的,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动作,没有紧张曲折的动人情节。可以说,这种农民的心态难以深刻而形象地表现出来。
然而,黔北作家就在这里显示出他们独特的艺术个性。他们有观察生活的特定角度,感知生活的细腻触觉,表现生活的特殊方式。他们通过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凡人琐事——一次乡场上的争吵,一个普通人家的搬迁,一桩家务事,一段儿女情,寄寓他们对农民的历史和现状的思考,表现农民心态转换的时代主题。这是黔北文学秀美格局的构成要素,也是黔北文学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
何士光、李宽定、石定都善于写变革时期的普通农民,都善于刻划女性形象,都能通过家务事儿女情传达出时代精神。但是,在人物形象内涵的侧重点上和表达方式上,这几位作家有一定的区别。何士光擅长在厚重的历史感中渲染出闪烁时代光辉的现在,又以优美的文字和句式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得到美的享受。石定在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取舍中作出艰难的选择,在预示现代文明的美好前景之时也礼赞传统人性的美德。他以散发着泥土清香的人物形象显示他对黔北山民的深刻把握,又以独特的心灵表达方式刻画了纯朴善良的黔北农民。李宽定擅长写中篇小说,因此能在历史的纵向跨度中刻划人物。他注重故事的戏剧性、情节的丰富性,人物心理描写准确细腻,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色彩。他长于刻画女性形象,这些形象美丽而善良,柔美中透露出刚强的个性。
赵剑平、戴绍康也写传统型的农民,但他们注重表现这些传统农民的刚强个性。他们没有在生活的磨难中磨去棱角,而是以传统的道义为标尺,豪侠仗义,敢于与命运抗争,具有黔北大山深厚而深沉的气质。如赵剑平作品中体魄过人用双手支撑起将要坍塌的屋梁救人的打油匠顺风爷(《红月亮,白月亮》);两手拖散牯牛打架嫉恶如仇的挖瓢匠“大头猫”(《远树孤烟》);曾经手推猛虎下崖并用宽厚胸膛护佑着一对沦落人的土地伯伯《山雪》;戴绍康作品中散发着阳刚之气的歌手和鼓手(《鼓手》);涌动着野性热血在传统与现代的临界点上徘徊的青年杨茅(《在故乡的密林里》)……。
赵剑平、戴绍康对以上传统型人物寄予极大的同情,但是,他们却将现在与将来的希望寄托在勇于改革的新型青年身上。这些青年不是冯幺爸(《乡场上》)式的在争吵中被动地亮相,也不是王老汉(《公路从门前过》)式的在心灵中演习着现代化的幻梦。他们破除陈规,积极进取,年青的心地始终回荡着行动的旋律。他们猛烈地撕裂着封建宗法制的潜网,以新的生活方式动摇着小农意识的根基。这些改革者的出现使作品充满鲜明的时代色彩,他们的奋斗和追求真实地再现了黔北农村改革的艰难历程。赵剑平《峡谷人家》中的茂林、茂森,《在两岔河湾中》的马二厂长,戴绍康《地热》中的田广,《滚厂》中的茂仙,就是这类形象的代表。这些形象的出现和成长是历史的必然——有了老一代王老汉、冯幺爸小心翼翼的思想转换,就必然有茂林、茂森、田广、茂仙这些“小字辈”的果敢行动和大胆选择。历史正是这样承续、演进和发展的。
三、艺术追求:创作手法的探索和现实主义的深化
20世纪 80年代后期黔北的主要作家在题材选择和表达方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何士光、李宽定、石定表现为现实主义深化和发展,赵剑平、戴绍康表现为创作手法上的大胆探索。
在农村题材作品中,何士光与石定观察农民心态的角度有所变化。他们从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考察农民现状,表现改革进程中黔北农民的精神重负。作品中,对生活鞭辟入里的深沉思考取代了过去过于乐观的浪漫情调。何士光《苦寒行》中的朱老大虽然是生活在20世纪 80年代的青年农民,但仍然有一颗懒散而愚昧的心。他的性格传承了阿Q式游手好闲之徒的遗传基因,保留了包国维(张天翼《包氏父子》)诌上抑下的洋奴习性。石定的《天凉好个秋》表现了交织着新与旧、真与假、丑与美、前进与停滞的有过于强烈的辩证意味的黔北农村现实,真正感受和传达出现实社会的真实意蕴。
何士光和石定在题材选择上有所转换。他们多写城镇小人物的生活,将笔触导向过去的时代。何士光“三行”中的《薤露行》、《嵩里行》写城镇小人物的世俗人生,背景转移到“文革”或更为久远的年代。那些被社会贱视的教师、职员、店员各有一个丰富而诡异的精神世界。艰难的岁月无望的生活令他们或者苦中寻乐,或者乔装打扮。他们故作的镇定强装的笑颜中蕴含着令人柔肠寸断的辛酸。这些和生活一样平凡又如生活一样沉重的凡人小事,被何士光细腻的笔触款款道来,显得严酷而深沉,抒情味浓郁又有强烈的理性色彩。石定的系列小说《小城故事》将背景导向凄风苦雨的旧时代,在黔北城镇人物的动人故事中融入富于黔北味的乡风民俗,寄予他对传统文化深刻的理解和思考。
和何士光与石定的题材从现在转向过去的变化不同,李宽定的题材从过去转向现在。他仍然关注女性的心灵和命运,不同的是,他从传统女儿家的描摹转向现代女性形象的再现。《山雀儿》是这种变化的端倪。作者让一位农村姑娘到城里当保姆,从而在传统态度与现代文明的猛烈撞击下产生悲剧故事。长篇小说《浪漫女神》的现代气息更浓。这是一位现代女大学生与一位中年作家的爱情故事。通过它,作家剖析了当代女青年的爱情观和价值观,对当代社会的婚恋问题作出深入的思考。
在艺术表现上,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表达方式,表现出美学上的自觉追求。何士光在短篇成熟之后,致力于中篇创作。他那意味深长的语句让人得到美的享受,他的夹叙夹议使作品妙趣横生,也给人回味悠长的遐想。石定追求简炼、朴实,他省却许多描写和交待,用白描手法抒情叙事,如写意画,留下许多空白让人咀嚼。何士光与石定都注重某种氛围和情绪的渲染。在这种渲染中,何士光偏重于理性思想的深入,石定侧重于诗意环境的再现。与何士光重情绪重艺术氛围不同,李宽定在情结结构与矛盾冲突的戏剧性上下功夫,写出人物复杂隐微的心理,增强作品的可读性,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赵剑平、戴绍康的创作也有所变化。赵剑平的《冲嫂和半截子男人们》、《穷人》等作品的格调显得严峻而深沉,充满隋性的懒散山民取代了改革者的雄风英姿。这些作品中,历史也在前进,但步履缓慢而沉重;先觉者们仍然在率先改革,但更多的是浑浊的观望的目光。他们部分作品的时代色彩淡化,代之以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戴绍康的《头鸭》、《媚爪》通过故事传说和野蛮风俗表现庸众对美好事物的的扼杀,抨击民众心态由于封建残余影响而产生的愚昧残忍的一面。赵剑平的《第一匹骡子》、《獭祭》通过动物习性的描写来暗喻人类社会。前者以失去生育能力的骡子创造生命的渴望,暗示环境对人的压抑;《獭祭》以富于灵性和情感的水獭来讽喻人的无情和残忍。这些作品表现出赵剑平、戴绍康在艺术表现上的追求。他们广泛运用象征,融入变形、夸张等手法,描写上力图凝炼深沉,感情基调由热情转为冷峻。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文化寻根思潮以及现代小说技巧的影响。
30年过去了,黔北文学在 20世纪 80年代的辉煌已然成为过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当下的黔北文学乃至贵州文学中看到它的影响。重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典,总结新时期黔北作家的成功经验,对于当下的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17.
[2] 黄侃.文选平点[M].北京:中华书局,2006.93.
[3] 费振刚.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31.
[4] 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