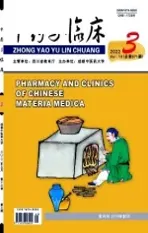试论中药剂量之二律背反——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剂量商榷
2011-08-15杨敏陈勇张廷模黄潇
杨敏,陈勇,张廷模,黄潇
中药剂量问题一直受到中医药业界普遍关注,但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中医不传之秘在剂量”的说法早已众所周知,其实,这是一个误会,不是中医不愿传授,而是影响剂量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无法采用简单的、机械的定量方式以免引领后学陷入思维的误区。临床中医师处方剂量的不确定性,古往今来都是普遍现象,某药剂量的或轻或重皆有其当用的道理。历代本草不言各药剂量,以笔者管见,不但不是其体例的缺失,而正是前人高明之处,他们没有明知其不可为而勉强为之。但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以下简称《药典》)在所载药物的用法与用量项下,明确规定了剂量范围。临床中医师严格遵守《药典》剂量规定,则难以体现和反映出个人用药特色及历代传承的经验,必然影响其应有的疗效;若超出《药典》规定剂量,又有不遵守国家法典并可能引发相关法律纠纷的风险。这就出现了中药剂量的“两难”问题。孰是孰非?怎样妥善处理?值得中医药界及管理部门认真思考,广泛讨论,以求得妥善解决的共识。
1 中药剂量的不确定性
中药剂量,是指为达到一定的治疗目,单味中药饮片在汤剂中成人的一日服用量,又称用量。由于中药大多是组成复方,并制成一定剂型来应用,因此中药的剂量实际包括:单味药用于治疗的常用有效量、药物间的相对剂量、以及药物的实际用量等三个方面。临床医生在确定具体药物剂量时,常常依据自己的应用经验,药物的特性,临床用药的目的,病人的具体情况以及自然环境多等方面因素加以考量。如,药物方面要确定其有无毒性、作用强弱、滋味浓淡、质地轻重、药材干鲜及质量优劣等因素。在应用方面,要考虑配伍形式及用药目的等因素;患者方面,要注意其年龄、性别、体重、病程、病势及职业、生活习惯差异等因素。因此,中药的临床实际应用剂量,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难以消除,也是不能避免的。这是临床情况的复杂多样性决定的,是受到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必然结果。
即使《药典》规定了剂量,编写者对其中的不合理性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不得不在“凡例”中申明:“必要时可根据情况酌情增减”。请问:《药典》乃是国家的法典,其正文规定的内容是可以“酌情”不必执行的吗?这样处理,怎么体现国家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但问题还在于:若用量低于《药典》规定的范围,常可毋庸多论,但若用量超出规定的范围,而这又是普遍现象,该当如何对待?由于药物剂量与其药性、药效直接相关。剂量不同,不仅疗效有差异,其毒性也可能大为不同。如因用药剂量原因产生了伤害(排除辨证诊断及选药等因素),固然医生有责难逃,但实际临床工作中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患者得到了有效的治疗甚至痊愈了,但由于医师用药剂量超出了《药典》规定的范围,会被认为是“违法用药”,患者可能由此提出诉讼。这种 “有理”取闹,又怎样规避?这时《药典》怎样保护医生们的“必要时”呢?面对这样的规定,临床医生只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结果受伤害的自然是广大患者了!
2 常用中药临床超剂量应用的普遍性
超剂量应用,是指处方剂量超过了该药权威规定剂量范围的上限的剂量。收载于国家《药典》的中药,其权威规定剂量是指《药典》的剂量。由于《药典》是国家法典,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和法律的约束性和强制性,因此,中医的一切处方剂量都应无条件遵循。但对照临床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中药的剂量自古至今均具有不确定性。由于中医是几千年薪火传承的医学,带有明显的经验色彩。古方剂量,常是现代用药的重要参考甚至是主要依据,因此,古今临床用药剂量均应是讨论范围。
从古今临床实际应用剂量来看,超剂量应用可谓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如《灵枢》治疗失眠证的半夏秫米汤,方中半夏的剂量为五合,按古代与现代有关半夏容积剂量与重量剂量的换算关系,五合半夏可换算出三种重量剂量。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残卷》的换算法:半夏一升合为五两,重约65 g,五合即32.5 g;按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的换算法,半夏一升合为八两,重约104 g,五合即重52 g;按王琦《伤寒论讲解》中的换算关系,五合半夏重量为55.7 g[1]。无论依据哪一种换算方法计算,该方中半夏的剂量均超过了《药典》现定剂量的上限。
仲景经方常视为中医用药的典范。在《金匮要略》甘草麻黄汤中,麻黄用量为四两,据高晓山先生主编的《中药药性论》的换算方法(以1两=14.42 g计。以下同。若以1981年考古发现的汉代衡器“权”来推算汉方剂量,汉一两=今15.625 g,则剂量更大。)折合为57.68 g;《金匮要略》苓甘五味姜辛汤,细辛三两(折合43.26 g);《伤寒论》桂枝甘草汤用桂枝四两(折合57.68 g)、炙甘草二两(折合28.84 g);《伤寒论》麻黄附子细辛汤,细辛二两(折合28.84 g);《伤寒论》大、小柴胡汤中,柴胡用量均为半斤(折合115.36 g);葛根黄芩黄连汤中,葛根半斤,黄芩三两,黄连三两,炙甘草二两;白虎汤石膏一斤(折合230.72 g)、知母六两。还有很多仲景经方,其量均大大超过药典规定的剂量上限。
检阅历代方书典籍,超剂量用药的现象亦比比皆是。如《备急千金要方》石膏汤:主治“心热欲吐,吐不出,烦闷喘急,头痛”,石膏一斤(折合230.72 g),茯苓三两,地骨皮五两,竹叶一升,小麦三升,香豉一升,山栀三至七枚。生地黄汤:主治忧恚恶心,烦满少气,胸中痛,生地黄一斤,阿胶、甘草各三两,大枣五枚。《千斤翼方》三黄汤:“治卒急腹痛胀满”,黄连、大黄、黄芩各三两。《外台秘要》茵陈汤:茵陈、柴胡各四两,大黄、山栀、升麻各三两,黄芩、枳实、龙胆草各二两;柏皮汤:黄连四两,黄柏二两,山栀十四枚,阿胶一两。《太平圣惠方》苦参汤:苦参一两,乌梅七颗,鸡子清一枚;人参雌鸡汤:熟地黄、阿胶各二两,人参、炙甘草、黄芩、麦门冬、生姜、大枣各一两。此外,《肘后备急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卫生宝鉴》、《校注妇人良方》、《景岳全书》、《医垒元戎》、《疡医大全》、《外科正宗》、《全生指迷方》、《疫疹一得》、《证治准绳》、《医学衷中参西录》等等,均不乏超剂量方药。
中医历代名家,自张仲景、金元四家,直至近现代医学大家,超剂量用药者可谓代不乏人。翻阅各家著述,尚未发现有平生用药而无超剂量者(以现代药典规定剂量考量)。著名的如刘完素、张从正、张景岳、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张锡纯、郑钦安等等,并留下很多医林佳话。
有人对中医药期刊中所提到的临床处方进行抽查,发现超大剂量应用现象相当普遍。在抽查的11250例处方中,约有三分之一处方中有超剂量药物,在同一期刊中,所调查的706味次中药中,超过《药典》剂量上限的有282味次,所占比例约为40%[2]。邱凤邹等从某医院2008年中药处方中随机抽取3901张汤剂处方,采用列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15种常用中药的临床实际用药量与药典规定量进行比较,结果15种中药都有超剂量现象,最高的达到98.89%,最低的为0.54%;最容易超量前5位分别是醋延胡索、柴胡、防风、陈皮、法半夏;偏离药典上限前5种中药分别是醋延胡索、当归、山药、白芍、丹参;超量部分为不连续非正态分布。证明所调查的中医处方普遍存在超药典剂量现象[3]。有人随机抽取其所在医院2006~2008年中医处方3600张(每年1200张,每月100张),对照200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的剂量范围,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2006年、2007年、2008年的超剂量用药处方比例分别为59.33%、62.75%、66.17%[4]。从上述可知,从古至今,常用中药临床超剂量应用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3 对《药典》规定剂量的商榷
中国药典自1953年版开始,即对所收载的中药规定了应用剂量,这一规定直至2010年版几乎未作改动。实行几十年来,对中药成方制剂的剂量固然有严格的要求和约束力,而对临床中医师处方用药的指导性和约束力如何,则少见探讨。但从古今临床实际来看,尤其从现代各种中医药期刊来看,超出《药典》规定剂量的“违法”用药情况绝非少数或偶然现象。这就难免使人产生困惑:如果《药典》规定的剂量是公允、合理的剂量,为何临床中医师“违法”用药现象如此众多,且其中不乏各科临床大家?如此则有必要对《药典》现定剂量进行商榷。
3.1 《药典》规定剂量的依据
中药剂量的确定,既应有历史应用的经验传承,又当对药材品质、患者情况及用药目的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但对历版《药典》沿革进行认真审视,其对剂量的标定并未明确声明其依据。如以历史名方剂量为依据,则不少仲景“祖方”剂量大大超过了《药典》剂量。如桂枝汤、麻黄汤、大承气汤等,其桂枝、麻黄、杏仁、大黄、厚朴等剂量远较《药典》规定剂量为大。而《千金方》、《外台秘要》、《圣剂总录》、《和剂局方》等医方名著亦均载有超剂量方药。如以当代医家临床应用剂量为依据,则《药典》也未言明统计的范围及何时、何地之医生群体或个人。如《药典》最初是照搬了当时教材的剂量,则由于教材提供的剂量仅是较低的有效参考剂量,亦不应作为《药典》现行规定剂量的依据。
不难看出,历版《药典》规定的各药用量,自身就缺乏科学的依据。坦率地讲,《药典》中大多数中药的用量,背离了临床用药实际,其伸缩幅度偏小,高量偏低。以此为据,必然导致有关中成药的疗效不如汤剂,这也是广大医患双方一致的评价。在保健食品研发中,又要求用量要低于《药典》的低量,这对于安全性高、作用平和的“药食两用的物品”和“可以作保健食品的物品”来说,肯定是勉为其难,其产品的保健功能就可想而知了。
3.2 《药典》的使命
《药典》是一个国家记载药品标准规格的法典。由国家组织药典委员会编纂,并由政府颁布施行,具有法律约束力。《药典》中收载疗效确切,毒副作用小、质量稳定的常用药物及其制剂,规定其质量标准、制备要求、检验方法等,作为药物生产、检验、供应与使用的依据。因此,药典的使命是对药物品种、质量规格标准的规定,并无对临床医师用药剂量进行规定的任务。如说是与国际接轨,则参阅《欧洲药典》(EP)、《美国药典》(USP)及《英国药典》(BP)等,这些药典正文部分均未对医师临床用药剂量做强制规定,仅有用药须知之类参考意见。再看《中国药典》用以收载西药标准的“二部”,一直是与国际接轨的,从未对西药的用量进行规定。比如青霉素的用量由当初的几万单位,快速增大到目前的几百万单位,从来不会引发医患对此的医疗纠纷。
如说因中药的特殊性而须传承中药应用的历史经验,则历代本草典籍均无剂量记载,即使是被不少人认作“世界第一部药典”的唐代《新修本草》,亦无剂量规定(惜原书已佚,在此以尚志均先生之辑复本而论)。因此,《药典》对剂量进行规定,不无“越俎代庖”之嫌。如说规定剂量是对药典功能的拓展,则这种拓展反而束缚了临床医师手足,并由此衍生了一些本可避免的医患纠纷。
需要注意一个事实,《中国药典》起步于半个世纪之前,当时中药的现代研究基础非常薄弱,可以作为“质量标准”写进正文的内容太少,不得已将中药的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用法用量及使用注意等列为正文,这样的体例,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其负面影响,随着患者法制观念、维权意识的增强,医患关系的异化,日渐显露。另一方面,中药质量标准的研究,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已取得了长足进展,采用《药典》二部的国际通用模式,已能够保证其质量,并足以反映中药的现代成就和我国的药政管理水平。
3.3 《药典》剂量与用药安全
《药典》规定用药剂量,或许是出于对用药安全性的考虑。但这种规定并非安全用药的万全之策。首先,药物的功效和毒性均以剂量为基础,如为安全而减小剂量,则因达不到有效剂量而有违医疗宗旨;其次,由于个体差异,即使相同或较小剂量,也有可能出现毒性反应。只要医生用药剂量在《药典》规定范围内,如果出现了毒副反应,是否就可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了?再者,中医用药,尚有“有故无殒 ,亦无殒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之说,即不少医家所谓:“有病则病受之”。因此,较大的剂量,对无病之人或病症不符的情况下,固然可能产生毒性反应,而对有病之人,则可能产生良好的治疗效应。而这一现象已是早经临床验证而为古今医家普遍认同的。由于中医用药,历来均遵循《本经》训诫:“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 ”,在有切实经验和明确的用药依据时,才会大剂量使用,并以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等“七情”配伍理论指导处方用药,从而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和有效。如不合理地规定了用药剂量,则难以收到期望的治疗效果,也抑制了医生独到经验的展示和水平的发挥。
在此讨论中药的剂量,绝无忽视中药安全性的意思。将合理的剂量写入《临床用药须知》,对于规范和约束中药剂量的确定,所起的作用应该不会两样;对于医生因剂量失误而产生的医疗事故,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其必须承担的责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代中医临床用药超出《药典》规定剂量的现象较为普遍,是由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似不能简单的认定医生“违法”,而应从《药典》规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上寻找原因。是否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寻求一个妥善的解决之道,从而改变和解除中医师在临床用药剂量上药物的“二律背反”的处境。笔者认为,将《药典》一部各种中药的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用法用量及使用注意等,全部写入配套的《临床用药须知》,不仅可以妥善解决以上弊端,又可提升《药典》的质量和权威性,百利而无一害。切切殷望,有司裁夺。
[1] 许国振,谢守敦.古今中药超大剂量应用集萃[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5.
[2] 关瑞廉.中药剂量刍议[J].中药通报,1987,12(8):29.
[3] 邱凤邹,张斯汉,陆燕萍.超药典中药处方剂量分析[J].中外医疗,2010,29(23):9.
[4] 周李刚.浅谈《药典》对中药剂量的规定[J].浙江中医杂志,2009,9: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