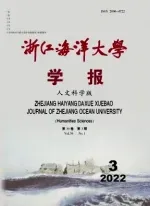论《劝学篇》“中体西用”思想
2011-08-15赖继年
赖继年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1861年,冯桂芬曾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雏形。此后,洋务派以各种方式表达这种思想,并用这种思想与顽固派交锋,“自强运动”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1896年,礼部尚书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此时,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备受质疑,而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弥漫朝野,变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洋务派与维新派就有了一次大的思想论战。1898年5月,在戊戌变法发起前夕,张之洞发表了其重要著作《劝学篇》,以抵制已经汹涌澎湃的维新思想。《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四万余字,从教育的角度入手,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思想,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这标志着洋务运动发展到了最高峰,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本文拟以《劝学篇》为中心,对“中体西用”思想做一番探讨。
一、《劝学篇》与各类评说
“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亡羊;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3]23张之洞希望综合新旧之学,取长补短,避免“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3]23的局面出现,但是张之洞可能没有料想到《劝学篇》的问世却引来了莫大的争论。
《劝学篇》一经发表,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899年,生活于香港的何启、胡礼垣二人合写了《〈劝学篇〉书后》,直接反驳张之洞《劝学篇》中的观点,认为张之洞其书“其志则是,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4]222,“综《劝学》诸篇而观,俱是罪人之言,自难逃识者之鉴别”。[4]260其言辞之激烈可见一斑。严复同样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也,斯其文之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焉望言之而可行乎?”[5]可见,当时一些国内人士对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观点并不赞成,尤其是维新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而与此同时,西方各国也积极将此书翻译成各国文字面向海外发行,他们对于《劝学篇》的评价与国人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1898年法文译本序言中,译者就对张之洞“慎重改革”的精神表示赞许,他认为当时的爱国者有两种,一是激进主义的,如维新派等人,二是如张之洞这样的,以一种更持久的建设进行建设。[6]而译者更赞许张之洞渐进的改革方式。1900年,《劝学篇》的英文版以《中国唯一的希望》(China’s Only Hope)的名字在纽约出版。我们从这一译名中便可看出西方人对此书的嘉许。但是关于“中体西用”之说,有些海外人士也对其提出批评。传教士杨格非就认为“中体西用”之说不过是旧瓶装新酒,最终的结果只不过是两相妨害。可以看出,国外人士所赞许的只不过是张之洞渐进的改革方式,而非“中体西用”之思想。
现代学者冯天瑜先生认为:“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张之洞倡导的‘新旧兼学’中的‘新学’亦包括‘西政’,这比早期‘中体西用’论者的‘西学’等于‘西艺’的观点进了一步,然而,张之洞所说的‘西政’虽扩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诸项,却对‘设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可见,张氏唯恐西学中那些锋芒直逼君主专制制度本体的内容在中国得以传播。”[7]6可以说冯天瑜先生的评价是很中肯的。张之洞既希望国人能够开阔眼界,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又担心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这本就是一种矛盾的心理,在这种矛盾心理的影响下,张之洞一直坚持“中体西用”的理论,认为这是救国救民的最可靠的依据,而忽视了体、用分割所带来的矛盾性。
二、《劝学篇》与“中体西用”
多年来学者们往往把张之洞的《劝学篇》看做是与戊戌维新思想相对抗的纲领,故加以贬斥。近些年对张氏《劝学篇》中的经济、教育思想有所肯定,但仍只认为它是洋务运动理论上的总结,洋务思想的系统概括。诚然,这些说法都有其正确性,但对于其中有突破“中体西用”思想体系的倾向的一面却忽视了。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运动随之宣告破产,其理论支持也逐渐过时,成为维新派攻击的对象,此时张之洞也看到了原先的理论的不足之处,《劝学篇》中的“中体西用”理论相较于洋务运动时期来说理论更加深刻,内容更加广泛了。
首先,张之洞注意到了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不仅提出要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建议,还大力宣传直接到西方国家学习的益处,同时他也注意到用中国的儒学来武装学子的头脑,这样才能为清廷培养“中西兼修”的人才。张之洞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3]可见他更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所谓“纸上学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认为只有亲身体验,才会有更深刻的感触。在学习对象的选择上,张之洞认为去欧美不如去日本,且若再派遣留学人员,则要选择已经学有所成之人,并派使臣加以督导,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样便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再次使公派留学归于一场空谈。在培养人的社会价值方面,张之洞希望能够培养出迅速为社会所用的“中西兼学”的人才,这也体现了张氏“中体西用”的思想。晚清的社会人才匮乏,尤其是缺乏既懂得“西学”又有“忠君”思想的人。张之洞提出应该广立学堂,他向清廷建议各省、各道、各州都要建立新式学堂,并按能力的大小及经费的多寡去建立学堂;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把祠堂、寺庙改为学堂。在学堂里,学生既要学习西方知识,也要学习中国文化。由此可以看出他求变革之心很迫切。再如张之洞认为学习西学时“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3]145可见张之洞考虑的还是比较全面的,已经在考虑建立一套比较现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张之洞也注意到了儒学思想对当时人的影响,但是他没有用极端的手段去强制人去学习“儒家经典”。他在《劝学篇·守约》一文中说欲掌握中学主脉,只先读通《近思录》、《东塾读书记》、《御批通鉴辑览》、《文献通考详节》四书便可,但这四书并非儒家传统的经典著作,只是一些有关心性道德和典章制度的书籍,可见张之洞认为当时社会急需的是有爱国之心且熟悉政务的人,至于一些高深的哲学理论,大可暂且不必关注。这里可以看出,关于教育目的,张之洞的有些做法已经冲出了儒家思想的藩篱,这也表明其“中体西用”的思想与早期有所不同,弱化了“儒学”思想而强化了“西学”思想。
其次,张之洞对于西学的认识也比前人更加深了一步。张之洞已然认识到西学不只是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一些行政制度和管理制度更加适合当时社会的发展。“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3]145这些都是以往的洋务派所没有认识到的。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特别提倡广立学堂、建报馆、变科举、学农工商、兵、矿、铁路等等,并提出要容纳他国宗教,不要一味排斥,这些比之洋务运动单纯的“富国强兵”则走得更远,考虑得更为周详;对于中西之学的关系,张之洞认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3]144我们不能因为张之洞坚守中学不可变的立场而否认这一观点的可取之处。前人在研究《劝学篇》时,总是以此为根据批评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但是在批评的同时我们也忽视了中学并非全是糟粕,西学并非全是先进的东西。无论是顽固派的“中体中用”还是维新派的“西体西用”,都过于偏颇了,顽固不化固然可恶,但是一味的拿来主义也同样不可取。当然这并不是说张氏的“中体西用”之说有多么的正确,而是说在当时还是比较趋于中庸的,注意到了中、西之学皆不可偏废,应取长补短。只是“中体西用”之说人为地割断了“体”、“用”之间的联系,有生搬硬套之嫌,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应该怎样吸取。总之,无论以什么为“体”以什么为“用”,都要以中国社会实际为基础。
再次,张之洞在“中学”的基础上对当时教学的方式和内容进行了改革,引进了“西方”教学的方式和内容。张之洞认为,“今年特科之诏下,士气勃然,磨兴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当之无愧上幅圣心者,盖不多觏也。”[3]143也就是说张之洞认为依靠当时的教学方式,是不能培养出符合国家需要的人才的。中国传统的书院式教学以“四书五经”为教学中心,培养的是典型的士大夫,这些士大夫满脑子“忠孝仁义”却不知变通,无以应对当时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因此,新的学堂应该是按照西方民主国家的模式建立的。从学堂建置上来看,学堂不同于书院,张之洞提出学堂应分为大、中、小三等,这种建置明确了不同学校的不同等级以及不同的教学任务,使得教育有了明确的量化标准,改变了以往私塾、书院教学中的随意性特点。若说教学方式的变革只是形式上变革的话,那么教学内容的变革就应是最根本的变革。张之洞提倡新式学堂应是“新旧兼学”、“政艺兼学”。旧学指“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新学指西政、西艺和西史。西政包括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艺包括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科目。由此可以看出张之洞对于新式学堂教学内容的设计还是很全面的,而且也都是很实用的。作为洋务运动领袖的张之洞,一直提倡经世致用,他认为,“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3]188所以在课程定制上,中西之学亦各有侧重。“小学堂之书较浅,事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致、方言、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学堂书较深,事较多。方言兼各国,算学则讲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余事仿此。大学堂又加焉。”[3]149这里并不是一种明确的课程定制,多少带有建议的性质,但也大致可以看出张之洞对于新式学堂教学的一种设想。在新式学堂里,传统的“四书五经”变成了教学中的一个环节,学堂教学不仅增加了西学,而且也注重中学里原不为人所重视的一些学科,省略了那些于现实无用的知识,①使新式人才的知识结构更加符合现实社会的需要。他还要求教材一定要新,要根据实际内容进行修改,而且不要墨守成规,要大胆地革新教材。
最后,我们不应忽视《劝学篇·内篇》中的内容,这是张之洞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所在。《劝学篇·内篇》篇目虽少,篇幅却较长。在这长长的篇幅中,张之洞并没有一味地进行道德说教,而是用大量的事实阐述自己的思想(虽然这里面有一些美化清政府的内容)。比如张之洞以人种学的知识来说明中华民族是同种同类之人,应同心协力,抵抗外辱。在张之洞的心中,道德永远是最根本的,他认为“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舵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深,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3]146没有道德、志气的人是很难为国家朝廷所用的,即使博学亦不可取,尤其是在国家社会动荡之际。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道德是一个人的根本,而知识是可以后期培养的。
三、余论
《劝学篇》出版不久,香港的何启、胡礼垣二人的《〈劝学篇〉书后》对张氏的《劝学篇》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成为改良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交锋的历史记录。“洋务派和改良派这两个对近代中国影响巨大的派别,其军政外交方略、经济政策、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一系列差异和分歧,在这两部著作中都壁垒分明的得以展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近代化方略。”[7]4从根本上讲,《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立论的基点完全不同,其议论则势必相去甚远,在“中体西用”的问题上则更加是水火不容。
张之洞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汔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3]203这充分说明了张氏对于“中学为体”的坚定性,西学的应用是为了保证“体”不会改变,这是典型的张氏“变”与“不变”的二重思想。笔者认为张之洞这一思想是有一定现实性的。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也就是说,治理一个大的国家,不能经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张之洞分辨了体用之别,以体用来说明哪些可以改②,哪些不能马上改③,哪些是不能改变的。④这样,国家可以在一个渐进的变化下逐步地进行改革,虽然这种改革方式是缓慢的,却可以保障国家在动荡的岁月实现平稳过渡,但是这种改革成功的前提是需要时间的保障。遗憾的是在十几年后,清朝灭亡,改革之说被资产阶级革命所取代,这种改革能否成功只能任凭人们去想象了。
相比张氏的“中体西用”之说,改良派所提出的则是完全的资产阶级改革方案,是建立在西方“天赋人权”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何启、胡礼垣长期居住在香港,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对欧日等资本主义国家有广泛的了解,在《〈劝学篇〉书后》中他们系统地阐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张,猛烈地批判了张氏的民权思想和纲常之说。在“中体西用”的问题上,何、胡二人则认为:“自《同心》至《去毒》,所谓内篇者,细按其自治之法,竟无一是处。由此以观其外,则外篇虽有趋时之言,与泰西之法貌极相似者,苟仿而行之,亦如无源之水,可立而待其涸;无根之木,可坐而见其枯。”[4]300如此之论,随处可见。专制主义的内学妨碍了人们对于新知识的追寻与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讲,何、胡二人的论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弊病在于急于实现其改革理想,改革方案多仿效欧日,缺乏对其可行性的考察,也忽略了中国民众的接受能力——三纲五常与天赋人权之间相去甚远,民众能理解多少?
很多人都认为“中体西用”只单纯强调学习西学而不变中体是隔靴搔痒而已,不能触及国家的根本问题,这是其最大的弊端。但是笔者认为,“中体西用”之说的弊端在于张氏所确认的何为体、何为用,也就是体用划分的失误。张氏将西方的物质文明作为“用”的基础,而将中国的“儒家文化”作为“体”的支撑,在把“体”与“用”联系起来的同时,也把“体”与“用”分离开来。这种将“用”从“体”中剥离出来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学习西方文化制度的同时,也要学习西方的思想价值体系,因为技术制度的背后是文化和价值。“本体”和“功用”不可分离。“体”与“用”貌合神离的弊端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显现。只有把“体”与“用”交融在一起,形成一个政体,“体”与“用”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迅速地向近代化迈进。中学未必全优,西体也未必会扰乱民心,何为体而不需变,何为用而急需变,依然是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什么是传统不能丢(体),什么是糟粕需摒弃(用),还需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劝学篇》是张之洞“中体西用”理论的一次全面总结,他从教育的角度入手,阐述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方案融合他在后面与刘坤一一起提出的《变法三疏》中,便成为实施新政的一种理论指导,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此我们在批判的同时,不能忽视对“中体西用”的正面理解。
注释:
①当然在我们今人看来,“四书五经”亦是于现实无用之学问,但在张之洞看来则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一环。张之洞不仅重视知识培养,更重视道德教育,关于这一点在下文中有详细的论述。
②如学堂、报馆、科举、农、工、商、兵、矿、铁路等。
③如议会。
④儒家经典,封建政体。
[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上海:上海书店,2002:17.
[2]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五卷[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123.
[3]张之洞.劝学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4]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5]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C]//严复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4.
[6]黄兴涛.张之洞〈劝学篇〉的西文译本[J].近代史研究,2000(1):302-311.
[7]冯天瑜.两种近代化方略的论战——《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