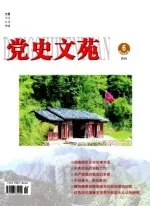论川陕苏区的土匪问题
2011-08-15马建堂苟德仪
马建堂 苟德仪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达州 63500)
土匪问题是近代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匪”字被用作所有为正统社会秩序所不容的异端分子的统称,有土匪、会匪、教匪、烟匪等众多名称。国内外学者对 “土匪”的界定有多种,国内学者蔡少卿认为 “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索为生的人”。[1](P3)而近代社会,统治阶级出于政治对立立场也常常指对方为“匪”,如在一些资料中,国民党污蔑中共为“共匪”“赤匪”,这种出于政治偏见的污称是我们必须摒弃的。川陕交界地区是土匪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川陕苏区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大苏区,其创建与革命斗争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川陕苏区在创建及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土匪问题进行思考及治理,故而有必要对川陕苏区土匪问题的概况、产生原因、治理方法、治理效果及对川陕苏区整体革命斗争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民情的认识与把握,认识中国革命进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只在部分著作中有所论述①,尚未有整体、系统的研究,本文拟依靠相关革命史和地方史志资料,对川陕苏区的土匪问题及其治理进行深入分析。
川陕交界地区土匪由来已久。川陕苏区建立前夕,川东北、陕南地区土匪问题十分严重。土匪四处抢劫焚掠,劫场的事屡见不鲜,土匪劫城更是习以为常,四川“通江、平昌多次遭土匪堵住城门,抢劫一空”,“平昌县52个场镇,曾遭匪劫的有85%上,个别场镇被匪焚毁殆尽”。[2](P15-16)1928年11月,“开江、开县、大竹股匪千余人洗劫开江县城”,劫走县立中、小学师生、居民 200余名。[3](P15)1930年,陕西勉县“连遭荒年,饥民遍野,土匪蜂起,李刚武、王三春、钟振华等占领县城,拆毁县书院”[4](P18)。川陕交界的宁强、城口等县匪害为最。如1928年,宁强 “李刚武匪部100多人偷袭阳平关”;次年6月 “李刚武勾结股匪赵元成率匪2000余人攻陷宁羌,大肆抢劫”;1930年11月,土匪王三春“攻陷宁羌县城,盘踞1月”;1931年8月,大股匪首周树民等,纠合匪众3000余人,于15日攻陷县城;1932年,大股匪何智聪、罗烟灰等常扰县境,劫掳焚杀。[5](P24)1932年秋,“边境土匪数百人进入城口县的高观、菜蒙、岚溪、北屏等地抢劫”。[6](P16)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交界地区,在川陕边区党组织和广大劳动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时期,匪患也极为严重,据徐向前回忆,当时川北地区, “土匪猖撅,啸聚山林,经常打家劫舍,绑票杀人”[7](P253)。 偏僻的地区成为大股土匪巢穴,如“城口、万源大山里是土匪窝”[8](P399)。 1933 年 3 月,一些被红二十九军收编的神团、土匪头目趁军队外出剿匪袭击了马儿崖军部驻地,军队领导人和骨干在战斗中牺牲或被俘后被害,队伍被打散,给革命造成较大损失,徐向前指出其主要原因是 “队伍发展太快,成分不纯。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打乱建制,进行改造,清除反动头目的影响”, “必须坚持依靠基本工农群众的阶级路线”[7](P274)。1933年春,城口县遭 “陕边土匪千余人窜入县西高头坝、冉家坝一带活动”[6](P16)。 1934 年,大竹县匪首徐世成“聚匪数百人”,盘踞东、西山中,时出洗劫场镇[9](P176)。可见,土匪遍地是当时该地区的真实写照。
川陕交界一带较大的股匪有王三春、李刚武、袁刚、李茂春、余海清、韩剥皮、沈西亭等,他们长期活动在陕西的镇巴、紫阳、宁强和四川的南江、通江、万源、城口县等地。巨匪王三春是川陕交界地区匪乱的代表,王幼年因家境贫寒,曾因家境贫寒而负债逃至陕西南郑县,返乡后邀集穷苦人民、散兵游勇,组建“镇槐军”,开始了绿林生活,曾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其匪队迅速发展到2000余众,枪支近千,编了3个团,主要藏于深山密林之中,广泛活动于川陕边区[10](P445-447)。李茂春股匪也流窜在川东、陕南边境,
一、川陕苏区建立前后川陕交界地区匪患概况
曾派匪徒200余人攻打设立在通江的川陕省保卫局机关,杀死红军指导员及无辜群众数十人。[2](P148-149)余海清在民初就是南江的大土匪,后被郑启和招纳为靖国联军授陕第二路的一名团长,李朝宣更是纠集通江、南江和汉中的地痞、土匪200余人,在黑岩塘通往汉中的隘口石少台、鸡巷子一带行劫,一时间“好汉难出石少台,命大难出鸡巷子”。[11](P7)除了几股大的土匪外,隐踞于深山洞穴的零星土匪就更多了。
土匪肆虐是民国时期各地普遍的社会现象,因而川陕边区的严重匪患成为当时土匪问题的一个缩影。
二、土匪猖獗的原因
川陕交界地区匪患严重并不是偶然的,它与本地区各种社会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军阀和地主剥削严重、政府赋税繁多、自然灾荒频发,使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政局长期动荡不平,四川军阀混战连年,军队招匪、纵匪,大量散兵流为土匪;秘密结社匪化严重。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大量农民不堪重负而破产,被迫进入土匪队伍,加之本地边缘化特征,更刺激了土匪滋生。
第一,军阀、地主压榨,农民破产为匪。在川陕边区,地主、军阀占有大量土地,军阀推行税收预征制,肆意加税盘剥,不少农民破产,被迫加入匪帮。在川北,军阀、豪绅和地方保甲合成一体,欺压人民,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且赋税繁多,1931年时,一些区、乡的捐税已预收到了 1972年。[12](P261)陕南镇巴坪落地区,1927年到1932年地主、富农共10户48 人,占有土地 587.5 亩,占耕地面积 75.8%。[2](P12)在巴中县恩阳区旱谷乡东园村,“地富占田土总面积72.81%。平昌县江口四户暴发财主占田地8891亩,其中苟继先一户占田地3850多亩,横跨川、陕、鄂三省,遍及十余县,并仗恃军阀范绍增的势力,开设商号。 ”[2](P12)苏区进行土改前,南江、长赤两县各六个村苏维埃的典型调查:“占总户数10.6%,人口15%的地主、富农占据土地 59%。 ”[2](P12—13)1933 年前,通江县占人口 5%强的地主,占田地 60%左右。[2](P13)故而,在地主的盘剥之下,许多农民被剥夺得“屋里光光,肚里空空”,背井离乡,境地十分凄惨,“而一无所有的赤贫户竟占百分之五六十”。[7](P262)陕南汉中、安康的“破产的农民为侥幸免死起间,大批地加入土匪队伍;土匪的焚掠将富饶地方变为赤贫,转使更多的贫民破产而逃亡”[13](P11)。因而,农民生活十分困苦,在严峻的生存考验下,许多朴实农民也不得不加入土匪队伍。
第二,军队招匪、纵匪,残兵为匪。四川自1918年实行防区制开始,军阀连年混战,社会经济破坏严重,无业游民不断增多。同时期,陕西社会也处于激烈动荡中,陕南人民深受地主摧残、兵祸之害,军队的招匪措施更加重了匪患,残兵为匪者极多。川陕交界地区破产民众无法生活,一些人只得铤而走险,以抢掠为生,于是形成了土匪泛滥的混乱局面。如南江捕获之匪“匪徒中有供称,因军款一元,无法缴纳,迫于生计,以致出下策者”[14](P567)。 四川军阀对土匪多采取招抚利用,在红军进入川陕边时,四川军阀企图进攻川陕根据地时,大肆招抚土匪队伍,如1933年5月,刘湘委任匪首王三春为 “城 (口)万 (源)游击司令部第一纵队司令”,同年8月,徐跃明委任匪首李茂春为“川陕边区独立团团长”。[2](P149)最终导致兵匪一家的恶果,而民众自卫防匪也多是徒劳,土匪的彻底治理只能成为空谈,土匪肆虐成为当时社会最为黑暗的一面。然而在军阀混战的动荡环境下,土匪问题始终未能根治。
第三,自然灾害影响。1930年前后,川东北、陕南地区出现出现长时期的严重干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3月9日,《上海筹募陕灾临时急娠会启事》称:“陕西四载之中,颗粒无收,实为中国今日最大最重灾区。”[15](P266)陕南,一连三年,“颗粒无收”,宁强、镇巴、南郑等地区尤为严重。安康、平利、紫阳、岚皋、汉阴、石泉诸县,“十分之七地亩,一望荒凉”,“统计汉南三百余万人民,死亡在百万以上,尚余垂毙之二百万灾黎”。[15](P268)四川自1920年起,灾荒连年,其中又以亢旱最为严重,如“1921至 1922年,1924至1925 年,1927 至 1929 年, 皆干燥不雨”[15](P289),1927-1929年,川北诸属连旱三年,荒情最重,“赤地千里,粒米未收”。据华洋义贩会报告书称:“本省灾情最重者为川北二十九县”,“其中有秋收全无者,有略获薄收者,更有籽粮尚无着落者。受灾人民约有八百万之众。”[15](P261)因灾荒而加入匪帮的贫农不在少数,1929年旱灾时,通江、南江等县的饥民,“因生活无法维持,群起纷乱,红灯教不畏枪弹,肆意焚杀、反抗驻军”,“附之者已不下四五万人”。[16](P261)宣汉因荒歉“人民饥荒特甚”,“土匪蜂起,抢劫时闻”,又如广安饥荒,“饥民载道,日闻劫掠之事”[14](P567)。
第四,秘密结社蜕变为匪。川陕交界地区,秘密结社形成较早,各种会道门名目众多,不少秘密结社组织蜕变为匪,如“神兵” “红灯教” “盖天党” “扇子会”、 “圣母团” “大布团”等。各类会道门被地方军阀、地主利用,成为危害苏区人民的反动势力,会道门到处烧杀抢掠,残杀红军干部和游击队,并往往以神水咒符欺骗群众,胁迫群众参加,1934年12月,盖天党在南江县平岗乡起事时就宣称 “一人不参加杀全家,一家不参加杀全族”,使当地三百多名群众被迫参加。[17](P127)
第五,川陕交界地区的地理因素。川陕交界地区以大巴山为中心,远离两省政治中心,高山林立、山水交错,政情、民情相对复杂,政治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经济较为落后,边缘特征明显,易于形成行政和法制管理的空白点,加之交通闭塞,易于众多惯匪藏匿,为恶一方。因而该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土匪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尤其是的宁强、镇巴、通江、万源等县成为土匪泛滥之地,正如美国学者施坚雅所指出,“正是在中国的地区边境,地方社会显得最异常,样式也最多: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非汉族的土著部落、还未完全汉化的小股群居点、进行不法生产活动而法律和税官又无法约束的自治群体、从宗教派别到煽动性秘密结社的异端团体和土匪”[18](P378)。该地区土匪攻占县城成为常事,川陕边境的王三春便是这一地区典型的巨匪,其匪部活动于陕南的宁强、紫阳,四川的万源、通江、南江、城口等20余县,其队伍出没于大巴山中,为害川陕边境数20多年,匪众最多时达四五千人。[10](P445-447)
可见,土匪猖撅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本质无疑是民生危机的体现,“穷入无衣无食、无田地种、无活路做,即被迫去当棒老二,造成土匪灾。棒老二不是穷人干的,是国民党逼着去干的”[19](P411),土匪的肆虐迫使许多农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房无人住,田无人耕。故而土匪危害极深,使大量农民脱离生产,甚至反过来破坏社会生产,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川陕苏区对土匪的治理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土匪的治理,毛泽东曾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就指出, “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 “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20](P8—9)。 1933 年 6 月 24 日,《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讨论的斗争纲领》第十条规定,“彻底肃清赤区内的反动民团土匪”[19](P18),明确提出了彻底消灭土匪的主张。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粉碎国民党 “包剿”的决议》指出,“在中国农村的极度破产和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必定发现极多的失业农民走上 “棒老二”式的行动和造成了极深刻的落后封建思想”,对此,党必须 “在文化斗争中坚韧的说服落后农民”。[21](P25)对于棒老二、失业流氓的痛苦,“只有共产党才提出没收军阀家财,救济失业,分配棒老二正当职业和工作”,并必须尽量的影响他们,吸收他们到革命方面来。[8](P354)
为巩固根据地,苏区政府“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依靠群众,消灭土匪”[7](P272),采取了多项综合措施来保卫苏区社会安定。
1.进行政治瓦解,争取土匪自新。川陕苏区认真分析军阀统治下的政情、民情,尤其考虑到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所以决定“对于流氓地痞、滚刀皮、棒老二等,只要他们改邪归正,做工务农,一概不杀”[19](P235)。 1934 年 12 月 5 日《中共川陕省委关于对反动团体斗争的决议》中强调:“对于民团团丁、白军士兵、棒老二里面的弟兄和流神痞子等,一律欢迎其自首,改邪归正。”[21](P160)这些政治宣传对于土匪的主动自新,脱离匪帮,起了重要作用。1933年春天,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在通江北200余里的两河口上面,“将盘据于曲江洞的王三春部职业土匪(棒老二)八十余人,用标语、口号、传单、书信等方式,通过软化、感动而争取投降了”[8](P246-247), 从而摧垮了巴山土匪的老巢。1933年5月,傅钟命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给陕南西乡县黑风洞大匪首袁刚写信,此前武路过黑风洞时已取得了袁刚一定的信任,信中明确指出“要是不顾大义于红军采取对立态度,必定要使他自己首先灭亡”,后来袁刚为保存实力,没有和红军对抗,这封信起了重要作用。[22](P128)
2.开展土地革命,解决人民生计。土地高度集中与地主、豪绅、军阀手中,是农民破产和土匪横生的重要根源。川陕苏区政府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根治土匪问题的根本。苏区政府在土改过程中,注重策略。1934年12月的《平分土地须知》规定:“当过棒老二、土匪、小偷,只要改务正业,有当地穷人担保,一样可以分得土地。”[19](P521)同样,对于众多的会道门组织的成员,也有分得土地的机会,肃反工作规定:“被胁从加入反动团体或反动武装组织 (盖天党、圣母团、扇子会、木刀会、烟户团、清共团、义勇队、自愿队……等)的雇工贫农中农,只要能改过,一律不究,依旧得到土地利益,其家财不能侵犯,仍受苏维埃保护。”[21](P170)这些措施不但彻底的解决了根据地人民的生计问题,还有利于瓦解匪帮,促进土匪从良。
3.通过军事斗争,消灭顽固土匪。苏区政府在加大宣传教育、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对仅靠政治攻势难以奏效的投靠军阀的土匪和长期危害人民的反动民团、惯匪,则进行彻底的军事打击。在红军主力开展三次进攻战役的同时,后方驻军和地方武装广泛进行了清剿土匪的斗争,如“在苍溪、营山、蓬安、长胜、阆中等县即歼灭土匪3000余人。在陕南、万源、城口等地歼灭了不少股匪”,并“将长期盘据大巴山的大土匪王三春赶到了镇巴、紫阳、城口边境”[2](P114)。 1934 年,红军经过多次围剿,最终将长期活动与西乡、镇巴县的山大王高树臣匪帮剿灭,歼灭了其部大部分土匪。[23](P13-15)1933年二三月间,红二十九军多次打击王三春匪帮,“一次歼灭匪部三百多人”[23](P45)。
与此同时,苏区政府还严厉打击了形形色色的反动地主武装、民团、扇子会、神团以及散兵游勇等。1933年10月中旬,以魏福堂为首的地主武装,纠集土豪劣绅杨法清和匪首沈尚清等组织“扇子队”约2000人,盘踞在蓬安县的铜鼓寨上,并进犯红军,被红军“消毙该地反动民团和扇匪1000余人,活捉过来 100 多,少数残匪四处逃散”[2](P230)。 通江反动武装“盖天党”,常在沙溪、洪口一带的庙坝场、铁坪等地进行抢劫、暗杀,前后杀害区乡村干部40多人,烧毁房屋数百间,抢劫民财无数,1934年8月中旬,警卫营“全歼了这股盖天党匪帮,击毙其匪首头子”[2](P230-231)。 1933 年 3 月 3 日,大池大本团杨子布,三元神团冯良谟,通江神团袁有章共2500多人,进攻红军部队,最终“红军击溃了全部匪徒”,敌人伤亡众多[24](P47)。1934年2月下旬,神团郗大恩联络万源神团张文学等共2000多人,偷袭红二九六团某部,茅坪山游击队配合红军采用口袋战术, “毙匪四百多名,俘虏三十多人,缴获步枪、土枪、刀矛三百多件,其余匪徒全部击溃”[24](P69)。这些措施使土匪无力袭击地方党政机关,又巩固了后方秩序,有力的保卫了的人民的生产生活。
4.建设群众武装,提高民众自卫能力。鉴于红军主力部队到前方坚持作战,土匪常常偷袭苏区军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状况,根据地积极发展群众的力量,大力进行地方武装建设,先后建立了游击队、赤卫队、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等组织,充分发挥群众武装的组织作用,这些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军队清剿土匪,保卫苏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安全。如《开展游击战争的决议》规定,各县游击队要“配合当地赤卫军肃清山林散匪”[19](P128)。一般青年要参加红军与地方武装独立营、游击队,“发动游击战争、搜山,到老林中去捉拿棒老二,不容许苏区内有一个反革命份子”[24](P639)。游击队在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无限制地号召雇农分子参加肃清一切地主、富农、土匪、流氓、阶级异己分子,改造游击队的成份,扩大游击队的组织”[25](P730)。陕南苏区先后建立游击队164支,游击队干部、队员7000余人,遍布广大乡村,1932年,赤北县游击队“主动开展四次清匪斗争,活捉土匪14名”,1933年又开展四次清匪斗争,“打死打伤团丁、土匪百余名”[26](P11-12)。1933 年,黄大万区游击队枪决了惯匪高福安,穷苦百姓拍手称快[27](P308)。1933年10月27日夜,赤北县赤卫军发现大批棒老二,将他们“打得大败逃散”,工农群众非常痛快[21](P302)。1935年元月,胡宝玉率领游击队在中仁寨,“歼灭土匪 100 多人,获战马 10 匹,枪械 100 余支”[28](P10)。苏区政府重视地方武装的军事训练,以提高其防卫能力。1933年秋冬,剿灭长赤县大匪首余海清的长赤县军区黄指挥长、红军柴参谋专门给参加作战的地方武装上了 “剿匪课”,“使大家掌握了隐蔽侦察、利用地形地物等必要的战术技术”[11](P174)。群众武装成为了苏区治匪的重要力量。
5.普及文化教育,破除封建迷信。官绅土豪往往利用封建迷信蛊惑人心,组织起各种反动会道门武装,如 “神兵” “盖天党” “扇子会” “圣母团” “大布团” “红灯教”等不下数十种。对此,根据地通过群众识字教育、马列主义宣传、政策讲解等措施,反对封建迷信,提高群众文化水平与分辨能力。1934年4月3日,中共川陕省委提出加紧宣传工作, “揭破红灯教、神团、盖天党、孝义会等的欺骗”,并明确指出: “一切神仙鬼怪的欺骗造谣,都是发财人整穷人的。穷人天天求神拜佛,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发财人天天整穷人,反而有吃有穿。”[25](P789)同时,苏区政府要求 “要多编印关于科学常识的小册子,加紧苏区文化教育运动,办读报班、识字班、俱乐部、阅报室、新剧团、列宁学校,多作科学讲演,提高群众的文化科学水平,深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科学思想来养成群众的正确思想”[29](P348), 从而使群众认识到了反动会道门的真相,提高了根据地群众的辨别能力。
在土匪治理中,根据地往往多种措施并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1933年冬到1934年春,主要就是靠宣传动员发动了群众参加地方武装投入战斗,“又在战斗中靠宣传喊话瓦解敌人和争取不明真象的群众脱离匪帮”,最后取得了平息南江的盖天党和消灭长赤的匪首余海清的胜利。[11](P113)
四、川陕苏区土匪治理的影响
川陕根据地深刻认识中国国情,揭露军阀统治的残暴面目,实施正确的政策措施,较好地治理了川陕根据地的匪患。
第一,巩固了川陕苏区政权。根据地的安定也使红军能全力投入到反围剿的战斗中,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第二,建立安定社会秩序,鼓舞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如渠县,苏维埃建立后,“一面清剿土匪,一面打土豪分田地,解决了农民生活困难,加上肃反杀了一些土匪,从而出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秩序”[30](P74)。
第三,教育了广大群众,壮大了革命政权。由于政策措施正确,众多土匪脱离匪帮,顽固土匪被坚决消灭。同时,川陕苏区的土匪治理作为局部地区匪患治理,也给中共后来剿匪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总之,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的政情、民情,深入解决近代社会转变下的民生危机,在川陕苏区采取政治瓦解、进行土改、军事打击、发动群众、宣传教育等多种措施并用的方法,有效地消除了民初以来就盘踞在川陕边境的土匪势力,使众多民众脱离匪帮生活,重新回归社会生产,甚至加入到革命队伍中,从而创造性的消除了土匪这一社会毒瘤,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革命的深入开展。○
注释:
①关于川陕苏区土匪问题的研究主要有:邵雍著《民国绿林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321页。该著作对川陕根据地土匪的危害与中共治匪策略有一定涉及,但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
[1]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2]中共达县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四川省开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开江县志[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4]勉县志编纂委员会.勉县志[Z].北京:地震出版社,1989.
[5]宋文富主编,宁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强县志[Z].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6]四川省城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城口县志[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7]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8]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四川省大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大竹县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10]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土匪实录(上)[C].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
[11]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2]红色中华[N].第 121 期,1933 年 10 月 24 日。
[13]紫阳县志编篡委员会.紫阳县志[Z].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14]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5]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Z].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16]《蜀北灾重死亡相继》,上海《民国日报》,1929 年 7 月 4日。
[17]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Z].1978.
[18](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
[19]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编委会.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20]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A].毛泽东选集(第一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刘昌福,叶绪惠编.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Z].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2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武平志.秦蜀日记[A].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九辑)[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23]中共镇巴县委党史办编.红军在镇巴.镇巴县党史资料(第二集)[Z].1988.
[2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镇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镇巴文史资料(第 2 辑)[Z].1988.
[25]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编委会.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下)[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26]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六).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Z].1987.
[27]达县人民武装部编.达县军事志[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2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紫阳县委员会编.紫阳文史资料(第 4 辑)[Z].1999.
[29]红色号角编委会.红色号角—川陕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30]中共渠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川陕革命根据地渠县苏维埃资料选编[Z].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