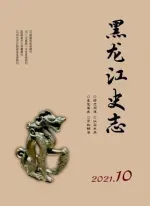第四次中东战争与美国外交
2011-08-15徐孝明
徐孝明
(湛江师范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48)
第四次中东战争与美国外交
徐孝明
(湛江师范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48)
第四次中东战争打破了中东和平僵局,也加快了美国调停阿以冲突的步伐。为达到主导中东和平进程的目的,美国对交战双方推行了两条似乎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既确保以色列不被打败,但又阻止它取得类似六日战争的胜利,迫使其具有谈判的压力和意愿;阻止阿拉伯国家军事上获胜,但确保其国家尊严。通过审慎又坚定的外交活动,美国基本实现了保护以色列、维护阿拉伯国家尊严以及实现军事停火的直接外交目标,这为它主导战后中东和平进程打下了基础。
第四次中东战争空运停火和平进程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绪加剧。为增进对该地区的影响,美国于1970年提出阿以双方用土地换和平的“罗杰斯计划”,但是未能取得成功。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十月战争)的爆发,尼克松政府确定了新的对阿以交战双方的政策目标。对美国在战争期间的政策考察有助于理解它在实现国家利益和推动地区和平进程的政策选择中如何实现平衡。
一
目标一:确保以色列不被打败,帮助它取得有利的谈判地位,同时约束其受到先发制人打击后的强烈报复心态及行为,寻求恰当时机推动和平进程。
尼克松政府第一任期的外交着重于结束越战与推行“缓和”政策,对中东问题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对以色列实施军事打击,宣告了十月战争的爆发。战争迫使美国将外交重点转向中东。尼克松在第二天与刚接任国务卿的基辛格讨论中东局势后,确立了继续支持以色列,确保其不被打败的方针。基辛格声称“我们不能被击败,如果阿拉伯获胜,我们的处境就更糟”。[1](p.521)尼克松要求苏联对其阿拉伯盟友施加影响结束战争,恢复战前状态。他强调美国“一直在考虑使美国将采取的立场得到强有力的支持”。[2](p.953)为确保以色列不至于在不利形势接受既成事实,美国推迟在联合国提出停火呼吁。新任副总统福特对此政策进行了注解:“尼克松总统已经承诺,以色列的切身利益会得到保全,而且要经直接有关各方的同意,以色列才能撤出(被占领土),撤出要以一个建立和平的合同式的协议为基础,它涉及到有关各方予以承认的,可资防御的公平合理的边界。”[3](p.204)美国的目标是:既实现其外交目标又不损及美国利益和形象,尽量避免在联合国里摊牌,动用否决权而使自己陷于孤立。
最初,美国预计以色列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扭转战局。它一面准备安理会讨论停火协定恢复战前状态,一面答应以色列补充其战场上的损失。尼克松政府了解到,以色列不接受逆境下的就地停火原则,而阿拉伯国家亦将坚决拒绝退回到战前状态,于是认定以色列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是实现停火和迫使阿拉伯国家走向停火的唯一途径。基辛格说:“最佳结果是以色列小胜一筹,不过也付出不小的代价,而美国的双手是干净的。”[4](p.378)
阿拉伯军队的火力和顽强斗志使以军反击进展缓慢,陷入了一场沙漠苦战,这大大出乎美以的预料。到第四天,以军损失了大量重型武器,其中有14驾先进的鬼怪式战机,坦克500辆,占以色列从美国所获武器的20%。[5](p.714)以色列总理梅厄向美国提出紧急援助和紧急访美的要求。尼克松政府拒绝了梅厄访美的请求,认为“大战正酣之际,(政府首脑)出国访问将是严重惊慌失措的迹象,这可能使那些仍在袖手旁观的阿拉伯国家全部参加进来……她的出访将会使以色列处于没有领导人的境地”;而且“美国因此必须宣布一项大规模的向以色列供应军事物质的政策,从而毁掉美国举行斡旋的可能性”。[1](p.493)
美国决策层就是否马上援助产生了分歧,一派认为在以色列仍然有充分的作战物质援助存在政治上恶化美国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的危险。基辛格认为,在以色列提出要求时给予满足,能更好地对以色列施加影响,“除非以色列看来正在取胜,否则就不会有停火,以色列要恢复信心,就需要有实实在在的迹象表明美国肯给予援助。”[1](p.494)
争论的结果是决定支援以色列,但要尽量保证不至于与阿拉伯国家发生公开对抗。基辛格试图通过控制支援规模,租用民用飞机运输援助物质的方式来缓解阿拉伯国家对它的敌意。援助因为民航公司担心遭到报复不愿承担任务而拖延了一些时间。以色列对此大为不满,其防长在自传中感叹:“美国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政策,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目前给我们少量武器是暗示我们,如果我们和埃及人达成协议,就能指望签订一项长期提供武器的协议……我们的问题是,美国是我们唯一的朋友——问题就出在这‘唯一’的两字上”。[6](p.456)对于支援的延误,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进行了辩解。
最初,美国计划于12、13日讨论苏联的停火倡议,同时将其“恢复原状”建议改为“就地停火”。10月11日,叙以战局逆转,以军将大马士革纳入了以军大炮射程。苏联为维持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防止叙利亚被彻底打败,开始用大型运输机对叙利亚进行空运。埃及则不希望进展顺利的军事行动就此停下,坚持要求恢复到1967年的战前状况。叙埃两国的战场形势不同,使得两国的利益诉求也不一样。美国希望英国提出停火建议,但遭到拒绝。后来澳大利亚受美之托建议停火,又被苏联拒绝,战时第一次停火努力失败。外交的失利使斗争中心转向战场。基辛格决定放手一搏:“我们不能让以色列打败仗。如果使用苏联武器的一方获胜,我们的处境就会很糟,苏联将控制战后外交。”[1](p.517)
在尼克松的敦促下,美国改用大型军用运输机加紧对以色列空运,批准交付最先进武器,甚至把美军现役的武器拨付给以色列,其规模为苏联此前四天援助的总和。[4](p.384)美国还向葡萄牙政府施压允许其运输机使用亚速尔群岛上的拉日什机场以供应以色列军事物资,后者为此招致了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的报复。美国的大规模空运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总理梅厄承认其“价值是无法计算的,它提高了我们的士气,而且起到了美国向苏联表明自己立场的作用,这无疑使我们的胜利成为可能。”[7](p.413)基辛格对援助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问题的最后解决仍需要通过外交活动,但重启前必须有成功的军事行动,一旦有利于埃叙方面的情况消失后,它们将回到谈判桌,而且美国也难于在联合国长时间阻止停火而又不付出代价。[8](p.163)大规模援助帮助以色列迅速扭转了战局,也加强了美国在战后外交的主导地位。美国要宣示的是:阿拉伯国家不可能靠苏联武器取胜,如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到头来还得同美国打交道。[5](p.719)
为缓解叙利亚的军事压力,埃及于第九天向以色列发动了一场双方有2 000多辆坦克参加的战役。埃及军队由于离开了防空导弹保护圈而遭到重创,以军趁势偷渡运河成功,绕到埃军后方试图包围对手,南方战线形势逆转。苏联再次提出停火要求,并邀请基辛格到莫斯科讨论停火事宜。这符合美国本意,但它企图索取更多的利益,基辛格说,“他们朝我们设想的方向行动了,但还没有完全走到。”[1](p.542)基辛格认为以色列需要48~72小时的行动时间,才能完全占据主动。
美国的支持加强了它对以色列的影响和作为战后阿以和谈主导者的地位。梅厄说:“我们只能向一个国家求援,有时我们也必须对它让步,即使我们知道不应该这样。但它是我们唯一的真朋友,而且是很强大的朋友。我们不需要事事说是,但让我们明明白白地说,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必须向美国让步,这没什么可害臊的”。[7](p.423)从确定基辛格访问苏联到联合国第338号文件通过,美国尽量拖延了停火生效时间,为以色列争取了72小时,使其进一步改善了在运河西岸的军事部署,反过来也加强了基辛格在莫斯科的谈判地位。联合国338号决议也更多地反映了美国的立场,体现了战场形势。出于担心以色列对协议的不予认可,基辛格还直接从莫斯科飞往以色列解释协议,而以色列担心美苏存在秘密协定而损害以色列的利益。然而,美国和以色列毕竟有着不同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当以色列军队趁338号文件生效前后的混乱之际包围了埃及第三军团,埃及为此提出抗议,并要求安理会谴责以色列时,基辛格担心停火夭折,就飞往以色列敦促它“认真”地遵守停火。在美国的压力下,梅厄作出不歼灭被围埃军的保证,允许(尽管是不情愿地)非军事物资通过其防线供应被困埃军。至此,停火得以执行。
二
目标二:阻止阿拉伯国家军事上获胜,但又维护它们的尊严;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联系,尽量避免与它们公开对抗,防止出现普遍的反美浪潮。这一外交目标的实现是通过约束以色列,排除或削弱苏联在埃及的影响,恢复与埃及的关系来实现。
以色列在六日战争的全胜强化了它对占领领土的强硬态度。美国在战前的解决方案也立足于要求阿方接受失败者的现实。基辛格在接见来访的埃及安全顾问伊斯梅尔时说,“埃及是战败者,因此不应要求过高;埃及人不能打仗,否则将比1967年失败得更惨重;埃及应当作为失败者而不是胜利者去行事,埃及在任何一场战斗中都没有获胜的希望。”[9](p.204)阿拉伯国家不愿接受耻辱性的停战,更不愿意将这种状态固定下来,伺机复仇。萨达特认为“只要我们是战败的一方,以色列保持它的战略优势,美国就不会采取行动”。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使中东局势更加动荡不安,阿以双方均深受其害,而阿拉伯国家尤甚。在美国看来,这种状态既加强了阿拉伯世界对美以的仇恨情绪,也强化了苏联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使亲苏阿拉伯国家的影响上升。它开始思考阿方的利益,基辛格说,“没有一次和平解决能使任何一方完全满足。假如一个国家完全满足了,那么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完全不能得到满足。哪里存在一个永远不满足的国家,哪里就永远存在破坏既定秩序的诱因。”[10](p.59)
战争打破了僵局,为阿以和谈提供了可能性。美国开始调整政策。它尽量避免与阿拉伯国家发生对抗,防止因反美情绪的高涨而使战争变成一场全面的阿拉伯圣战,损害它在和平调停中的地位。因此,美国始终拒绝发表谴责发动战争一方的声明,以示对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同时尼克松致信侯赛因国王呼吁约旦不要参战,以阻止战争规模的扩大。为了表示善意,美国最初在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问题上保持低调,答应补充以军损失的军火一直没有启运,直到苏联开始空运和以色列因战争不利而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情况下才启动对以大规模空运。[4](p.380~381)基辛格还表示愿意促进阿以之间的和平。他在给伊斯梅尔的电报中称:“我愿重申:美国将尽其所能协助交战双方把战斗停下来。美国以及我本人,将积极协助有关方面使长期一直困扰着中东的那些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1](p.498)但是,由于以色列不愿在安全得不到有效保证的情况下,接受埃叙两国坚持的前提条件——以色列必须从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埃叙两国在军事行动进展顺利时亦不愿让步,停战未能在最短时间内实现。
就以色列的国力来论,其军事成功依赖闪击战和速战速决;而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地位则使其能够支撑战争的长期化,等待有利时机的出现,只要保持不败,其地位就可以依靠一场消耗战而稳步改善。最初,阿拉伯国家依靠发动先发制人的行动而获得的优势,尚能使自己在停火谈判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然而停火的失败使机会稍纵即逝。只要存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阿拉伯国家就几乎无取胜的机会。当美国支援的规模超过苏联后,前线的战事随之出现逆转,外交主动权也随即易手。
萨达特上台后,埃苏关系趋于紧张。他对苏联在武器供应上的一再食言,以及阻挠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计划而深感愤怒。[11](p.230)萨达特坚决反对埃及购买的苏制武器在使用前必须征得苏联的同意,他说:“试想在以色列袭击埃及腹地的时候,难道在回击以前我必须等待莫斯科的命令吗?我是一个国家的总统,我不能放弃我在行动上的任何独立性。”[12](p.16)1972年7月,萨达特将苏联顾问驱逐出境使埃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埃及开始向美国靠拢,并与之建立了联系渠道。战争使埃苏两国的利益冲突和外交分歧加剧。苏联对埃及要求支援的消极态度坚定了萨达特借助美国实现国家目标的决心,他说:“苏联总是使局势保持高度紧张,但永远不足以解决问题”,并认为中东的“不战不和”局面正是苏联为控制埃及所希望的。[1](p.527)他在回忆录提到埃以激战正酣,埃及急需苏联武器支援而不得时写道:“假如他们给一百辆坦克,历史已经改观了。”[9](p.227)萨达特认为,既然苏联不能帮助埃及实现国家目标,不妨借助美国,把军事停火与其它政治解决联系起来。他邀请基辛格访问埃及,表示苏联不能代替埃及与美国打交道。
但是,美国要求埃及作出妥协。基辛格强调:“一开始就将停火与中东和平问题联系起来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也是不明智的。”尽管萨达特强调停火与撤军相联系,但是恢复与美国的关系,并借助美国打破中东的和平僵局,开始成为埃及首要的外交方针。美国要掌控中东和平进程也需要埃及的支持与合作。因而随着沟通和了解的增多,美埃双方最终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埃及也逐渐接受了美国将停火与和平谈判暂时分开的建议。而苏埃微妙的关系也契合了美国的行动。苏联一方面试图诱使埃及与苏联签订更紧密的同盟条约以阻止两国关系的破裂,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关系以弥补在埃及丧失的利益。
美国在与以阿双方都建立了联系,对它们都能施加一定影响的情况下,如何在这对世仇中保持平衡就成了其新中东政策成败的关键。不言而喻,维持与以色列的战略关系,保证其安全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点,但是在新的形势下,美国必须照顾到埃及等阿拉伯温和国家的利益,作为它们保持与美国友好关系的回报。因此,当埃及第三军团遭到以军包围以后,美国并不愿看到埃及遭受全面军事失败的命运,导致萨达特被推翻或埃及重新“激进化”,使已经松动的美埃关系逆转。基辛格解释说:“乘阿拉伯遭受挫折之机,把它们彻底搞垮不符合我们的切身利益”。[1](p.529)
美国的战时目标是:战火不延续太长时间,避免超级大国的直接对抗,阿以双方都不能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埃及军队不被全歼。[8](p.163)鉴于以色列可能全歼被围埃军,美国认识到必须约束以色列的行为,否则将激起强烈的反美情绪。基辛格特为此访问以色列约束其行动,并与苏联代表一起推动联合国339决议出台重申停火,使停火最终得以执行。
在经历停火——失败——再停火后,中东局势仍十分微妙,只要停战协定未签署,战火随时有可能重燃。为使国家免于可能再次燃起的战火蹂躏,埃及首先让步,放弃了先决条件开始与以色列就军事停火展开谈判,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
诚然,美国的中东政策无疑是以其国家利益为转移的,一旦美国利益受到威胁,它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抵制。10月16日,沙特国王费萨尔警告美国如不改变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美沙关系将受损,沙特副外长则明确宣布要用减产、禁运方式迫使美国改变中东政策。基辛格对此的反应是“不予理会”,他认为对威胁的屈服只能招致更多的讹诈。美国决策者也了解对以色列的支持会招致阿拉伯人的仇恨,但也认定它们更依赖美国,认为阿拉伯人既然不能依靠苏联打败以色列,就只能依靠美国实现自己的主张。
美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政策及其行动集中体现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外交的强权政治性质和大国操纵小国命运的国际政治中不公平的现实。然而,在一个缺乏世界政府的世界里,一国领导人以保护和扩大国家利益作为制订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也是题中之义。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是否也同时推动了地区和平进程,实现了两者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认为,美国通过对以色列的援助以及对阿拉伯国家尊严的捍卫基本实现了外交目标——既维护了以色列的安全,又发展了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美苏争夺对中东影响的较量中占得先机,开始了美国主导阿以和谈的进程。
[1]Henry 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London,Wei den feld and Nicol son:Ltd Little Brown,1982.
[2]塔得·肖尔茨.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下)[M].商务印书馆.1982.
[3]麦克尔·v·多伊尔编.福特言论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4]沃尔特·艾萨克森.基辛格——大国博弈的背后[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p.378.
[5]马文·卡尔布、伯纳德·卡尔布.基辛格[M].三联书店,1975,P.714.
[6]摩西·达扬.达扬自传[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P456.
[7]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自传[M].新华出版社,1986年.
[8]William B`Quandt,Peace Process—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p163.
[9]萨达特.安瓦尔·萨达特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P204.
[10]斯蒂芬·格劳巴德.基辛格——一个智者的画像[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P59.
[11]刘竟等.苏联中东关系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2][埃及]海卡尔.斋月战争[M].商务印书馆,1975,p16.
徐孝明,男,湖南汝城人,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