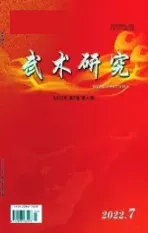武术美学思想探源
2011-08-15蔡宝忠
蔡宝忠
(沈阳体育学院武术学院,辽宁 沈阳 110102)
武术美学思想探源
蔡宝忠
(沈阳体育学院武术学院,辽宁 沈阳 110102)
文章从文化学、哲学、美学视角探索武术美学思想之源,研究认为:武术美学思想是以中国古典哲学为主线派生出来的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的萌芽、形成、发展和完善均植深于中国大文化系统之中,不同程度的渗透着民族风俗、习惯、心理、情感、艺术、文学等因素,同时也受到了儒、道、佛家等思想的滋哺,是一种多学科相互作用的综合产物。
美学思想 武术 仁学 武德 乐 圆 和谐
“武术是个文化现象,是一种高雅的文化。”这种高雅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长时间、多学科文化不断积累和渗透的结果。其中美学思想的渗透构成了武术美学思想体系,它既相同于美学的某些特征,而又有别于美学的某些属性,这是武术文化自身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在以往的研究中多集中在武术的美学特征上,如动作美、姿态美、劲力美、技击美、节奏美、结构美、名称美等。对其美学特征背后的、深层次的美学思想挖掘明显不足,以至于此项研究一直在低水平的徘徊。另外,就是过多的套用美学学科的知识,照搬、照抄的“拿来主义”现象严重,缺乏对武术自身美学因素的开掘,如意韵、形神、刚柔、动静、情趣等。本文试想对武术美学思想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挖掘其深厚的思想根源,从美学角度认识中国武术的本质和特征,以丰富武术文化,促进武术发展。本文欲从以下五方面作出探讨。
1 仁义——武术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武术的真谛是技击,它本质上意味着野蛮和残酷。但传统武术的技击性却被以“仁义”为基本特征的武德观念所抑制和淡化。这种观念至今仍起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说:“仁者必勇”。“义,人之正路也”。[1]所谓“仁”,包含有爱、礼、忠恕、孝悌、信义等。孔子云:“仁者静,克己复礼为仁”,只有克服私欲,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孟子曰:“仁,人心也”,并提出“亲亲仁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2]总之,孔孟仁学的基本思想是以仁慈、忠厚、善良和爱心来待人接物,处理一切人际关系。而所谓“义”,则是指公正、正义、公利、公道等。“义”比忠、孝、节等的范围和施用对象要广泛得多,它几乎包括了处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的思想行为符合相应标准的道德观念。[3]“义”既是一种气节,更是一种精神。仁和义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前者把仁与勇相联系,以仁作为勇的统帅与动力。故孔子指出:“勇而无礼则乱”,“军旅有礼则武功成”,并把“智”“仁”“勇”三者相提并论,当时被称为“三大德”,“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4]而后者将“义德”“义行”“威义”作为“正我”,以对“仁”加以节制,从而达到“立人之道”,也就是说确立自我的道德规范。这在中国武术史料中显示出以“仁义”精神为基本特征的武德伦理美学思想。
武术的“仁义”思想突出表现在各门派对授徒择人的严格规定中。少林《拳经拳法备要》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少林罗汉行功·短打十戒》也强调“强横不义者不传,强横则为乱,无义则负恩”。《峨嵋枪法·戒谨篇》说:“不知者不与言,不仁者不与传。谈元授道、贵乎择人”。苌乃周《武技书》中说:“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为正人君子。学拳宜以涵养为本,举动间要平心气和,善气迎人。学拳宜作正大事情,不可技艺为非,以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这些条目,把对授徒的德行教育规定得十分明确。内家拳五不传中还规定:“心险者、好斗者、狂酒者、轻露者、骨柔质纯者不传”。在历代“少林戒约”、《武士须知》、《青萍剑·剑箴》等中对武德均有记载。这些规定旨在净化习武者兴脑,纯活思想,开阔胸襟,端正作风,光明磊落,为弘扬中华武术奠定基础。正是在这种仁德思想约束和教育下,历代涌现了无数救国家于危难,救民众于水火的武林俊杰。
武德的伦理思想在儒家“仁义”思想的基础上,还融汇了禅宗佛学的“持戒”,“化解”的慈悲胸怀。《峨眉十二庄·龙鹤庄诀》说:“鹤性不争,喻诸风德。是庄为用,持戒礼客;法寓化解,功守两得”。又说:“阿修孚中,慈悲咸备、佛门弟子、律戒诛绝”。在这里佛教的思想烙印是很深刻的,另外,古老的少林武术“十禁约”,就脱胎于大乘派佛教“五戒律”。佛家的大慈大悲与儒家的“仁义”,实质上都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而道教最明显的是“学道之人必须积善、定念、修德、理身”,其中“积善行德”是“仁义”和佛教戒律始终倡导的伦理思想。故武德反映了中华民族善良、诚信、热爱和平的美德。
其实“仁义”是构成武德的基本要素,它只是武德的一部分内容,下面将从更宽泛的角度诠释“德”与“武”的关系,来进一步体现由道德标准和精神价值而产生的美学观念,也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使得中华武术长久不衰。
2 德——武术美学思想的内涵所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是指善良的品行、高尚的品格。只有善良和高尚的,才是最美的。据《释名·释言语》说:“德,得也,得事宜也。”据古文学家考证,“德”字在西周大孟铭文内已有之。《诗经·大雅·烝民》有:“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的记载。殷商时期的《尚书》中多次使用了“德”字,其中《尚书·周书·蔡仲之命》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这些“德”字是指德行、品德的意思。所以,《说文解字》中将“德”解释为“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其要求十分宽泛。也就是说,做事做得适宜,于人于己都过得去,无愧于心。
由于“德”与“道”的连用,便逐渐构成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而“德”与“武”的结合,逐渐构成了武术行业的道德标准。“武德”的连用始见于《国语·晋语九》:“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为正卿,有温德以成其名誉。”这里的“武德”是指军功而言的,只有具备了军功的人,才可能提升为卿大夫。后来的《尉缭子·兵教》中也说:“此之谓兵教,所以开封疆,守社稷,除隐患,成武德。”这里的“武德”,更明确指向军队开疆拓土,稳定江山的政治功能。而后左丘明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中对武德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当时楚庄王认为,“止戈为武”是武备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并由此引发和提出了武德的七条标准。他说:“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公定、安民、和众、丰财者也”。[5]其意是:所谓武力,就是要禁止残暴,制止战争,保有天下,巩固功业,安定百姓,调和诸国关系,积聚财富。这里所说的“七德”,是指七项用兵的道德要求或武力的七种功用。这反映出春秋中期以前军事武德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最早的带有条款性的武德标准。可见,此时武德已基本形成。但真正与武术相连的武德,较早要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习武练剑“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矣。”从历史的角度看,司马迁的这段文字,在中国古代武术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6]短短片言,指出了习武者要遵守“信廉仁勇”的“德”,并将“德”置于“道”的地位上;同时强调强身健体与修德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武德一词的变化,先有军事意义的“责任、义务和军人价值”,逐渐扩展到武术意义的“行侠仗义、扶若济困”等要求,直到后来的门规和戒律等具体化约束。
尽管“武德”一词在古代反复出现,但却无人给武德下个定义。近代也如此。
关于“武德”方面的研究多见于现代,也涉及到武德概念及相关问题。就概念而言,多是现代意义与传统意义的结合产物,而且界定相似。我们在编写《武德与武术礼仪——全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材》时,将武德定义为:习练武术、应用武术、传承武术的言行准则。[7]这个概念将会长期的使用下去。
在武术界有两句话是必须记取的,那就是“未曾习武先修德,未曾学拳先学礼”。这句话强调的是习武之人修德、学礼对武技影响的重要性。这里就“未曾习武先修德”句加以解释。它实质涉及到了武术中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习武者必须讲究武德?不修德行不行?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从武术的本质看,武术是徒手或手执器械搏杀格斗的方法或技艺。[8]搏杀格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制服、致伤、致残,甚至是致死对手。那么,在习武、用武、传武的过程中就要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在什么情况下要制服、致伤、致残、或致死对手,而在什么情况下又必须手下留情,这就是“德”对“武”的自觉约束。如果从矛盾论的角度来看待两者的关系,就是“德”对“武”的必然平衡。随着古今武术价值的变化而这种约束是有很大差异的。古代战争就是残酷厮杀、你死我活的斗争,这表现在军事制胜之道的“力胜”和“威胜”两个方面,而“德胜”才是制胜之道的最高境界。在《资治通鉴》中有一段“在德不在强(武力)”的故事:一次,魏武侯与诸大夫浮西河而下,中流顾问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河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秦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大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群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9]据史书记载,吴起相魏时确实很重视修德,不仅重视政德,而且重视将德和士德,以及武力。强调武与德是相辅相成关系。从现代意义上讲,武术的主要功能是健身、技击、教育和观赏,与古代制服、致伤、致残、或致死对手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在习武、用武、从武的过程中以“点到为止”、“化干戈为玉帛”、“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尚德不尚力为原则。《罗汉行功短打·序言》在论及点穴功法之所以创立时有:“兵刃之举,圣人不得已而为之,而短打宁可轻用乎?故即不得不打,仍示之以打而非打不可之打,而分筋截脉之道出焉。圣人之用心苦也。夫所谓截脉者,不过截其血脉,壅其气息,使心神昏迷,手脚不能动,一救而苏,不致伤人。短打之妙,至此极矣。有志者细心学之,方不负圣人一片婆心也”。使用武术的最终目的并非伤害对手,而只是制服对手。能制服对手就算达到目的,并不要求无限度地使用武术技术手段。
当今,一切对他人构成致伤、致残、或致死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其次,从武术的门规和戒律看,应该说所有的门派开宗明义就强调“修德”的问题。丹鼎派有“内家入门,须明八字”,八字为“功、拳、药、械、法、地、侣、财”。功,不只是通常所指的内功、外功、软功、硬功、轻功等,而最主要的是功德。倘若武术技术落入不轨之徒手中,极有可能会做出各种损人害人之事,贻误后人。所以武术各门、各派将授徒无例外地均严于择人,“德不贤,不与传”。《咏春白鹤拳?懔十戒》强调“戒私斗、戒好胜、戒好名、戒好利、戒骄、戒诈或浮夸逞能、戒弄虚作假、戒挑拨离间、戒为非作歹”。其中有一半内容与谦虚有关。与人为善并不只是态度上的谦虚,而是一个人持身修养的必然。
再次,从“武”与“德”的源头看,有关“武”与“德”的记述早在上古时代就产生了。最早的甲骨文、金文都把“武”字理解为从戈从止,意即持戈作战或舞练。通过对甲骨文“足戈并立”的静态结构,到“止戈竖立”的动态结构,再到金文以来由象形向会意方向变化,并形成“动静”结合的字体,笔划粗细一致,结构相对协调,以适用于人的习惯认识和记忆。[10]从甲骨文中“武”字的变化看,其原始本意并非止戈为武,而完整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或持戈静止而立,注视前方;或举戈而动,欲与人、欲与兽斗,与人斗是争夺地盘和剩余价值,与兽斗是维持生存和生命。[11]至于“止戈为武”的说法,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解。从文献的整体看,古时对“武”字的理解,最直接的即是上要手持兵器,下要步走行军。而其他方面的含义都是后人赋予的,主要是引申意义上的“武”。
简而言之,武与德,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合一,将会达到美之极致。
3 乐——武术美学思想的表现形式
武术从产生开始,就具有“练、用、看”三种基本功能,其中“看”是指它的观赏价值,具有观赏价值的东西一般都含有一定的表演艺术性。通过优美的造型,强烈的动感、均衡的势态、恰当的节奏、和谐的韵律、深蕴的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并引以为乐。
“乐”是个多音字,《辞源》对其解释颇多,最直观的含义要算是“音乐”和“娱乐”。古人谓之乐,指诗、歌、舞三位一体的文化总汇。儒家认为:乐之发生,由于人心爱感于物。所谓“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简单的说就是快乐。《荀子·乐记》中明载:“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这表明人不能没有娱乐或欢乐。要达到“乐”的目的就要寻求美的素材,像咏诗、轻歌、绘画、武舞都是古人追求欢乐和美感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与武术最为密切的“武舞”,要算较早的具有典型表演性质的活动。《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幡,戎有受脉。”有“祀”则“舞”;而有“戎”则“武”。“舞”与“武”融合,才构成了武术套路的雏形。[12]从历史的发展看,“武舞”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武舞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据《尚书?皋陶漠》记载:“予击拊石,百兽率舞”。大意是人们敲打着石鼓,模仿着各种野兽的姿势,翩跹起舞。第二、增添了乐趣和审美价值。据《商书·伊训》记述:“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这说明远在殷商时期,武舞已经常出现宫廷宴乐之上。在祀神祭祖时或在战争获胜时都举行武舞,以表现人们真诚、喜悦、欢快之情。
武舞约略为两大类:一种是表达情感的“大武舞”,其内容在于表现“周武王伐讨之乐”,这种武舞属于文艺范畴。另一种是“练武”的武舞,如“干戚舞”,“干”即盾,“戚”即斧,乃是一种于执盾、斧等器械进行搏斗技击的单纯操练,其动作粗犷,“发扬蹈厉以示勇”,属于体育的范畴。无论哪种范畴的“武舞”与“乐”均有密切关系。
3.1 体育范畴的“武舞”与乐
体育范畴的“武舞”被视为武术套路、器械对练的雏形,是以身体、精神兼修为要旨,提高军事技能为目的。早在夏、商、西周学校的“乐舞”教育中的“小舞”的后三种(旄舞、干舞、人舞)基本上属于体育范畴的武舞。通过这样大型的“武舞”活动,达到强身健体“行列得正,进退得齐”的境地。据《韩非子·五蠹》记载:“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氏乃服”。说的是大禹曾率兵苦练三年,以高超的套路表演征服了苗氏。这种演练形式既是“武舞”者自身技能、技巧的再现,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乐”的素材。《诗经·雏清》有:“象,用兵刺仗之舞”,这种象既可单人舞练,也可集体舞练,是用以训练士兵、鼓舞斗志,去争取胜利的一种手段。春秋时期的武舞,对军事训练起到了积极作用。据《左传》记载,楚文王夫人说过“先君以是舞也,习戒备也”;“旄羽祓,矛戟创拨,鼓噪而至”。这种耀舞扬威的武舞,实属军事训练的情性。随着武舞的发展,出现了“目欢为美,耳闻之乐”的认识,这是美感的飞跃。3.2 文艺范畴的“武舞”与乐
文艺范畴的“武舞”多指宫廷里以音乐伴奏下的助兴活动。在古籍中多有记载,《孔子家录》有:“子路说,授戚而舞”可谓斧术的套路演练。《史记·项羽本记》中的“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诸以剑舞”。[13]这件事除了它的政治目的外,还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剑舞已用于宴会间的娱乐助兴;二是剑术已经有套路独立作舞了。到了汉、晋武术套路有了较大发展,在《史记》、《吴书》、《通典》等史书中均可发现很多关于“剑舞”、“戟舞”、“走戟”、“飞叉”的记载。到了隋唐以后,武舞表演已更风行。大诗人李白《从行军》中有:“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的诗句,说明刀术有时也在音乐伴奏下,以套路形式舞练。《藏书·吴道子传》中说裴旻“驰马舞剑,激昂顿挫,雄术奇伟,欢者数千人”。《庄子?说剑》有“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各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的记载,[14]说明赵文王以搏击取乐。在《梦梁录》、《东京梦华录》等史籍中多见记载。可见武术在唐代已被列入艺术范畴,供人观赏。
两种范畴的“武舞”都是“乐”的外部表现形式,通过“武舞”,使人们“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可见“武舞”是一种欣赏艺术,是欢乐的象征,是胜利的喜悦,是武术美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
4 圆——武术美学思想的核心价值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美学派认为:“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是圆形”,[15]而在动态中以圆的形式出现仍是最美的。圆形无论是静止还是动态的都比其它形体包含有最大的空间和最多的容量,具有均衡、和谐、完善等许多美的特征。圆弧是圆的部分,美的曲线即由圆弧构成,而人体便是曲线美的极致。武术运动正是通过人体不断变化体现多种美学素材的,从武术的产生、发展至今,处处带有“圆”的痕迹。就少林拳而言,它的创始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像“坐禅入道”,戒律互补,“圆”的应用都是“大乘派”的特殊贡献,其中“圆”字是佛教各派僧侣和佛经中表达多种美感的专门词汇,常用的有“圆满、圆通、圆融、圆遍、圆光、圆因、圆果等等。[16]在少林七十二武艺中各武技均要求“圆满”,也就是对套路结构严谨,攻防技术合理,起伏转折、动静、虚实恰到好处而言的。少林拳械的演练要求发力顺达通融螺旋劲,躲闪圆灵多变,技击“滚出、滚入”,“曲而不曲、直而不直”,这些都说明“圆美学”的渗透。太极拳的产生,开创了“圆”的新世界。18世纪末山西王宗岳用《周子全书》中阴阳太极哲理解释拳义,曰“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太极拳论》认为:阴阳思想,既是世界观,也是审美观、伦理观,“圆”的思想贯穿太极拳的全过程,太极图是圆的,太极拳运动路线又多是平面或空间的小圆、大圆、立圆、斜圆、椭圆、半圆、弧圆、螺旋形,其动作又要环环相绕,处处圆活,似曲非曲,似闭非闭,忌直、角、滞、硬。能大圈归于小圈,小圈归于无圈者常以“螺纹”“滚珠”“车轮”喻之,惟妙惟肖,圆活之趣。推手同样以圆形不断变化,实现听、问、化、发劲。《立体几何学》认为:一旦外力作用于圆球上,由于圆球的滚动,外力会顺切线平滑通过,而借力,发力。推手同时讲究“曲中求直,蓄而后发”,这些完全符合宇宙实无始终,大化迁流,天地相继,时空无限不绝的规律。
《八卦拳学》亦说“八卦拳术不外易数方圆二图之理”。八卦掌的主要特点是走转,寓阴阳掌法变化之奥秘于走转之中,圆为艺中之源,圆为术之母,万变不离其宗,竞在一个圆圈之中,所以说“巧从圆中生,妙从圆中得”。表现出了武术美学思想的深刻内涵。圆者,圈也,当手心朝下时为阴掌,要变换为手心朝上的阳掌时,非翻转尺桡二骨和手腕不可,翻既要转,转的本身就必然要形成一个圆的运动,故圆即从阴阳的互易变化中得来的,“孤阳不生,独阴不长”,任何一种拳术的运动丢掉了阴阳变化,互易,就丢掉了圆的运动,也就丢掉了拳理中的艺术和技巧。又如擒拿术中的金丝缠腕,手挥琵琶,单手挥花,顺手牵羊,白猿献果等等都是经过阴阳的互易变化,圆和圈的运动所完成的。离开了圆和圈的运动,就会形成双方力量的较量,而失去艺术的价值。
《峨嵋十二庄》其《天地庄合诀》开篇云:“象天法地,圆空法生,大小开合,唯妙于心”。这四句揭示出功法的哲学,美学思想本源是“天人合一”。古人能用“象天法地”体会到“圆”与“空”是大自然天地的基本特征,因而是动功的最佳方式与境界。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滞、圆而空则能做到活泼自如,循环无阻,变化无穷。这种妙趣横生的拳理,既是武术的重要法则,又是武术美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圆的运动不仅在拳术中,器械中表现得也十分突出,像枪棍的大圆、平圆、刀剑的斜圆与立圆,都是武术完美艺术思想的再现。根据不同的拳种和器械一般分为大中小三圆,在练功程序上:先练大圆,后练收缩,是中圆,再求紧凑,是练小圆。小圆即无圆,就是说从外形上所体现的圆的运动是很不明显,其运转在气,变化在骨,提领在神,故小圆也为上乘功的运用,是技术完美的境地,也是武术美学思想的真正内涵。
圆也普遍运用于技击上。武术有讲究硬接硬打的,但“四两拨千斤”就是以圆化掉对方攻来之力,旋转出拳以此借力、发力,可蓄发出更大的力量。[17]武术界有“对方打来身如球,拧走转换莫停留”。这个圆是立体的圆。要求身体如圆球般圆滑滚转,使对手难以准确寻找击打的位置。一些拳师常讲“以步法打人”。怎样以步法打人呢?形意拳要求“进步退步如球之无端,又进又退如球之相连”;八卦掌要求“环环相扣,势势相连”,“如机轮之循环无间也”;太极拳《乱环诀》则称:“乱环法术最难通,上下相合妙无穷,陷敌深入乱环内,四两千斤着法成”。步法打人,实际是步法灵活胜人也。而这灵活,却离不开圆。
武术讲究一招一式,势正神圆,式正招圆,这“神圆”是指精神状态的完美,招圆是指技术的和谐圆润,二者的统一,将是武术美学高度的升华。
5 和谐——武术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
和谐是指事物或现象各方面的配合协调一致,是一个从对立统一的过程,是事物或现象发展的一种美好状态。它在武术运动中是指所有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通过联系再现出合乎规律的美学思想的本源,和谐是中国古代体育美学的理想,“和”字最早出现在金文当中,并构成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尚书》中有“协和万邦”的做法;《易传》讲究“保合太和”;《诗经》中有“既且和平”;《左传》记载了晏子“和与同异”的观点;《国语》也记述过单穆公“乐从和、和从平”的思想。孔子主张中庸之道“乐而不淫、哀而不衰”,“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庄子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和谐美境地。从道家的“和合万物”到佛教的“因缘和合”;从西汉董仲舒的“和者,天地之正”到宋明理学家的“民胞物与和”。概括起来“和”字至少有四层含义:即和谐、适中、对立统一和和为贵。[18]其中各学派都认同“和谐”,倡导“和谐”。
中国古代“和谐”的审美理想,表现在武术美学思想中,就是人的生命的和谐,即动静结合,神形兼备,内修外练,刚柔相济,阴阳互补,意、气、体三者达到统一。
我国最早对艺术实践经验进行概括的古代美学思想家史伯认为:“美就是和谐,和谐就是美”。[19]古希腊唯物主义美学家赫拉克利特在论述美学思想时指出:“美在于和谐,和谐在于对立统一”。[20]对立统一的事物源于社会实践,古代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是武术产生的沃土,其美学思想是对立统一事物的客观反映。武术中对立和谐统一的美,比社会客观实践所反映的美更全面、更典型、更生动、更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5.1 矛盾对立的统一性
西周至春秋末年被认为是我国美学思想的启蒙时期,它与阴阳五行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武术的美学思想也正是沿着阴阳总纲变化发展的,仔细观察任何一种拳械套路,在由起势到收势的整个节奏上,无不包含着阴阳、动静、虚实、刚柔、攻防、进退、险易、快慢、张驰、轻重、缓急、密疏、广狭、长短、逆顺、收放、伸缩、上下、远近、高低、前后、左右、大小等矛盾的对立统一。[21]这在武术流派分类、练法、技法等诸方面都是同样的,总归起来有两种情性:相互包含,表现彼此吸引的趋势;相互贯通,表现彼此转化的势态。与古代美学的“相成”、“相济”、“相和”思想是一致的。
5.2 内容与形式的和谐
武术的流派众多,内容繁杂,套路形式数以千计,风格各异,其技击内容多以一定形式表现和传播的,这种多样形式是任何项目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是武术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哲学意义上讲,一定的形式反映一定的内容,任何武术内容都是通过具体形式来表现的,当内容与形式有机的结合起来,即是高度和谐统一的美,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5.2.1 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武术的整体内容包罗万象,诸如拳术、器械、对练、集体表演和攻防技术等,局部内容是指某一种拳术、器械等而言的,无论是整体内容还是局部内容,必须通过多种形式加以表现,以保证形式的整体性、适宜性和主从律,才能突出各种拳械的风格和特点,再现美学规律。
5.2.2 局部与局部的关系
武术中某一内容和形式相互协同是取决于整体和谐的关键。任何一种形式必须反映武术的某种内容,而脱离武术内容的形式也是空洞的,无从论美。
5.2.3 内容与形式的变化
武术的内容和形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内容的逐步丰富带来了形式的深化、反复、奇正、参差等规律,以达到相互协调的目的。
从武术发展史讲,宋明前及后段时期,套路极为简朴,是武术意识、击法、技巧、功力高度结合与集中,程式上有起势、承接、高潮、收势等,富有格式化,完整统一。而近代武术套路有了新的发展,在路线布局上讲究直、曲、斜、弧线、圆、“S”形、三角、对角、直角等多方位结构,体现了美学中对称、对比、平衡、均衡、树立、呼应多样的变化特点。另外,在表演器械的重量、长度、地毯、服装色泽、式样以及演练时的配音等都有一定规格,反映了对立的和谐统一。这些都是武术美学的具体体现,反映了社会需要与时代精神的高度结合。
综述以上五个方面,可以看出,武术美学思想是以中国古典哲学为主线,派生出来的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的萌芽、形成、发展和完善均植深于中国大文化系统之中,不同程度地渗透着民族风俗、习惯、心理、情感、艺术、文学等因素,同时也受到了儒、道、佛家等思想的滋哺,是一种多学科相互作用的综合产物。
注释:
[1][4]论语,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35,48.
[2]徐 才主编.武术学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91.
[3]旷文楠主编.中国武术文化概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185.
[5]左丘明撰.左传,左传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58.
[6]周伟良编著.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0.
[7]郭志禹主编.武德与武术礼仪——全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
[8]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武术理论基础[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24.
[9]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0][11]蔡宝忠.“止戈为武”不为“武”[J].搏击,2006(6):1.
[12]马爱民.殷商文字武义追踪与中国武术套路溯源,参见郭新和主编,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 [C].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173.
[13](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52.
[14]陆 钦著.庄子通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26.
[15]编写组.美学向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45.
[16]佛教诗诵必要[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80:10.
[17]程大力著.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43.
[18]广东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组织编写.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概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82.
[19][20]陶功定编著.美学[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10,80.
[21]李德元.武术哲理中的和谐美[J].体育与科学,1987(5):11.
G85
A
1004—5643(2011)11—0001—05
蔡宝忠(1959~),男,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武术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