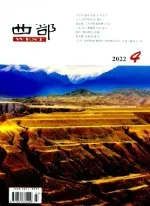跨文体高原上的河
2011-08-15刘湘晨
刘湘晨
跨文体高原上的河
刘湘晨
帕米尔高原是一棵老树,喀什噶尔就是挂在这棵老树上的一片叶子。随手捻起一串喀什噶尔老巷里的掌故,依稀能嗅到两千年间飘荡的烟尘,但却很难找到判断帕米尔高原的凭据。
——帕米尔高原的隆起是地球的一极,距今一亿两千万年,古老得超过能够让人想象的任何常规。曾经发生的,依旧存在的,都会对我们的生存产生广泛的影响,犹如喀什噶尔平原秋后的风,透骨的寒意有刀锋的质感,它来自高原,刚刚从帕米尔群峰叠摞的冰岩之间擦过。
来到喀什噶尔,在这片美丽的“叶子”上,我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找到一家超市,捡了冰糖和袋装茶叶填满了两大塑料袋。
冰糖和茶叶是新疆人标准的“走亲戚”的必备品,俭朴却有捂在手心里的一份浊热。想想很有意思,半生的岁月过去,新疆各民族的习惯成了我人生最自觉、自然的一部分内容,原本籍属的内涵已被彻底改变。
远去帕米尔,第一个让人激动的地方是盖孜,它是高原的起点。
多年的过往,盖孜边防检查站的官兵已经成了我的兄弟,见到我来了,指导员李栋吩咐战士抱来—个大西瓜。
五月在新疆,尚不是瓜果溜街摆的时候,上市的西瓜是来自海南的反季瓜。想想这段遥远的距离,实在让人承受不起。
李栋的一句话让我释然:“哎呀,老兄来了,金瓜也得切!”
不是新疆人,不是在类似于盖孜这样的地方,你很难想象有人会说出这种话,有这样的表达方式——爽透!严酷的环境,望不到天涯的路途,牵着人的一根最脆弱而敏感的神经,何以能表现出性灵之间最挚情的一面,这至今仍是新疆的一个谜。
告别李栋,我嘱他去找找当年的盖孜古驿站在哪儿,我们相约下次见面一起去看看。
1
帕米尔高原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山连绵不尽,山峦相叠。
但是,仅注意山,说明你还是个外来者或观光客,赋予帕米尔高原灵魂的是水。有了水,沉默的高原才有了生气,有了娓娓的叙述。
帕米尔素有“山结”之称,世界上最著名的数条大山脉的缰绳都系在这儿。同时,也是万水之源,每一条山脉都有一条伴生的河。在帕米尔高原东部,塔什库尔干河和札莱甫相河是两条最重要的水脉,我的帕米尔之行实际上就是一次跨越两大水脉之旅。
塔什库尔干河是塔什库尔干河谷之间流量最大、流经线路最长的河流,像是老祖母的一条臂膀,揽着河谷间的大片牧场、农田和塔什库尔干人日月交叠的日子。它的上游有两条河,一条是发源于红其拉甫河谷的红其拉甫河,一条是从卡拉其库河谷流出来的卡拉秋库尔达里亚河。卡拉秋库尔达里亚河上游被称作明铁盖河,再上游分作罗布盖孜河和火石壁河,汇入火石壁的河流还有克克吐鲁克河、卡拉秋库尔苏河、托克满苏河和瓦根基河。每年5月以后,冰莹的雪峰支撑着大片湛蓝的天空,散淡的牦牛和羊群像是铅笔随意涂抹在碧绿草甸上的风景,过了很久也很难改变一下。阳光灿烂,坚硬的砾石石面溅得阳光的鳞片飞迸,空中有隐约的鸣响,阳光下的河流蜿蜒流淌,闪烁着蓝宝石的光泽。
——这是卡拉其库峡谷夏天最经典的高原风光。
在卡拉其库沟口的排依克边境派出所,地图上随意指划一下,我发现那些被称作上游的上游河流就有数十条之多,这还不包括地图未被标识的那些更多的尚在当地人口传系统中的河流——几乎每条沟里都会有一条溢出的流水,密如蛛网,不见经传,却与人的生息紧密相连,除大山之外,这是帕米尔高原尚不被人所知的隐秘。
卡拉其库峡谷水脉疏稀的分布,大致是帕米尔高原河流全貌的缩影和它构成的说明。
在整个高原,塔什库尔干河并不是一条最著名的河流,能够进入传载系统之中唯一的原因是它流经整个塔什库尔干河谷,这是东部帕米尔高原最宽阔、平坦的河谷,舒舒缓缓铺陈近百公里,出峡口后连接塔合曼草甸,抵达如今的卡拉苏一带,这里当年能见到遍地的野山葱。离开中原历经一年或两年多的艰难辗转之后,野山葱是长途旅人有可能吃到的第一口青绿的东西,以干粮、肉食和水为主的简单食谱得到了一次调剂,由此留下一个透着微微辛辣和青涩的地名:葱岭大道。
葱岭大道沿用了数千年,一直到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国际大通道衰落之后的许多岁月。与这个原因有关,塔什库尔干流域丝绸之路年代的遗传最为丰富,从石头城、吉勒尕勒驿站、公主堡、吐拉炮台到南瓦根基达坂连成一线,成了往日文明盛景的明确标志和说明。法尔哈提大渠久经暴晒和风尘的打磨,河床遗迹秃褪,很难看出与山基冲积扇堆积起来的土丘有什么区别。稍经指点,把散落在高原荒僻坡地上互无关联的破碎片断连接起来,它上起达布达尔乡,下至提孜那甫乡的斯塔尔孜,断断续续的地表显露有八十多公里,说明塔什库尔干河谷曾有非常发达的灌溉农业——法尔哈提大渠的修建本身就是帕米尔高原最伟大的奇迹。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样一条大渠,从修建立项到用水管理 (这涉及大面积的农业作业),再到大渠的维护修缮,必须有一个十分稳定的政府机制支撑并能延续许多年不间断的规划与有效管理。在我这次前往高原之前,短短的二三十天里就几次听说县委书记带着人去拦河堵坝,达布达尔乡乡长胡西地力每年夏季最重要、最费神的工作之一就是修被他视作乡脉的一条大渠。两相比较,从运行机制、通用方式到规划的周密性和管理,相去悬殊。塔什库尔干县至今很难找到连续使用一二十年以上的完善的水利设施,法尔哈提大渠历经时日久远而未决,它的有效利用为当时的去谒盘陀国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给和牧业支持——从某种角度讲,法尔哈提大渠是去谒盘陀国盛世的终极原因,从公元200年到公元700年前后,它延续了整整五百年。
沿着公路在塔什库尔干河谷往复穿梭,使我第一次对这一片区域有了较为清晰的地理认识。
以慕士塔格山脉为界,一边是卡拉其库峡谷腹地,一边是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其间分列着四个天然沟口,依次为东克克吐鲁克达坂、西克克吐鲁克达坂、北瓦根基达坂、南瓦根基达坂。其中,南瓦根基达坂就是丝绸之路在帕米尔高原的终端孔道,其间过往的许多声名赫赫的人物都是当时去谒盘陀国的国宾,最著名的有宋云、马可·波罗和当时从罗布盖孜峡谷游学归来的玄奘。
塔什库尔干河谷令人最不可思议的隐秘是吉勒尕勒古人类文化遗址,它与吉勒尕勒驿站相距不过二百五十米,两点相距的时间却有八千年至一万年!
吉勒尕勒古人类文化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用火遗迹,太阳跨过子午线以后,渐渐西斜的阳光使几个在吉勒尕勒古堆积崖上掏出来的洞子有了一天最亮的光照,光照从洞的顶端透进来,像撕开一块大布,先是一条缝隙,然后逐渐扩大,在接近洞子底部的时候,可以看到与上下沙砾堆积层不一样的略带赭色的土层,宽度不会超过两指,这是新疆至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古人类文化遗址,由此,可以肯定帕米尔高原与人类文明最初的约定。那些先人在这儿烤熟了人类在帕米尔高原的第一块羊排,暖暖身子站起来,顺着塔什库尔干河的方向稍作眺望,远处连绵不断的雪峰使他们无法看得更远,自然无从想象在很久很久之后,一位戴着近视眼镜的后人能够轻易地穿过重叠的雪峰,站在他们烤火的地方来揣想他们当年的此时此刻、此情此景。
上述这个判断,使帕米尔高原每一处最不起眼的流水和草甸都有了重新被认识、被描述的必要。帕米尔高原是上帝在自己伸手可触的地方给人类放置的一只摇篮,随着河水延流繁衍的文明愈益走向塔什库尔干河以远,人们也将更清楚地意识到,帕米尔是人类遥远的乡土。
2
前往乌鲁克苏牧场,实际上,是离开塔什库尔干河流域迈向札莱甫相河谷的第一步。据以往的经历,我知道札莱甫相河谷的托库孜布拉克(九眼泉)一带也有丝绸之路的遗存,札莱甫相河谷很有可能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径之一,尽管与塔什库尔干河谷之间有无数的大山相隔。但是,与丝绸之路的隐约关联并不是札莱甫相河比塔什库尔干河声名更卓著的原因,而是它与叶尔羌河有更直接的因缘。
塔什库尔干河仅是数条最终汇入叶尔羌河的支流之一,札莱甫相河完全不同,它是叶尔羌河不同河段的称谓之一,更上游是克尔钦河,由乔戈里山地冰川舌部的冰川融水汇流而来,成为纵横塔里木盆地近两千公里的塔里木河最重要的供水,也是塔里木盆地草木枯荣和植被繁衍最重要的依据。从南缘切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可以看到塔里木河的古河床遗迹,一片相距或近或远的危楼魅影,夕阳之下迎着光照的一面接近赤红,稍经风吹,土沿上轻尘拂动,让人看到岁月流逝的轻盈轨迹。若是掀起一块儿来,我想六十吨的大货车也未必拉得动。如此致密的质感和体积,足以想见塔里木河当年水旺之极的情景和流经的年代久远。这些古河床的残段距今天的塔里木河一百五十公里,这样大幅度的摆动只不过是近二百年间的事。遥想当年,随着塔里木河的龙尾一摆,丝绸之路的繁荣盛景被一扫而空,从此成为往事。但是,人文对水文的依赖仍是几千年间基本未变的事实。
已经接近7月,我第一次目睹乌鲁克苏牧场的状况让人惊愕。看着羊头抵着地面以两排细碎的牙齿薅着草根子啃,隐约觉得一场瘟疫正在迫近。没有水,草荒得重,轻风扫过,能看到淡淡的烟尘腾起。当地人说太冷了,雪水没下来,见不到往年山脚碎石沟里几步外就能看到的水头,听不到充斥在峡谷每一寸空气中不绝于耳的喧嚣。整个乌鲁克苏峡谷是一种被弃的单调,一个有意布置出来的阴谋正在实施。绝想不到,世界范围的气候异常在帕米尔高原夏牧场的一角也表现得如此突兀,让人猝不及防。
在介绍塔里木盆地自然境况变化的时候,我曾反复讲述我的一种悟测:
相对于大量垦殖和对塔里木河水系有效管理的失范,更可怕的是源于地质地理的节律变化,譬如天山六亿年间的数度沉浮和塔里木盆地由大海最终变成沙漠,这样的大剧变,足以使一个地域或更大范围的地球区域被颠覆!乌鲁克苏的严重问题不是雪没有化,在南极大陆冰架不断崩溃的同时,这里的降雪也在大幅度减少——种种迹象都在描述着—个隐约的事实,人们只是不愿意接受而已。
吉普车穿过往年绿色铺地的乌鲁克苏草场扬起一路烟尘,四面透风的车子里能闻到呛人的碱末子味儿。拉开车窗,车轮卷扬起来的烟尘一下子变成了刚从瓶子里钻出来的那个魔鬼,飘摇成一簇在你面前舞蹈。立即关上车窗,车内的所有地方,人的衣裤和手,已落了一层灰。谁能相信,这竟是往年大片绿草的末屑!我几次疑心走错了地方,终于见到零散分布在一条沟里的石房子,才触摸到记忆中的依稀形迹。
我远远地就认出了多里坤和巴奴汗。高原的岁月是一张过于粗粝的砂纸,两三年没见到,这两口子已有了柴根头的质感。我见过几年前十九岁的巴奴汗,称她为“小村名模”,眼前一脸灰黑的巴奴汗比一位生过十个孩子的非洲黑人老妇都更让人震撼。我相信,对帕米尔高原的任何描述真的不能掺一点儿水分,看看我的这些塔吉克兄弟姐妹,他们身上仅仅几年的变化已能说明高原的严酷本质。
多里坤和我行了塔吉克男人之间的吻手礼,巴奴汗以她的唇在我的掌心轻触,只是瞬间的事,我依然能感到她唇间稍含的潮润,尤其是她的头低伏在我的掌心间那种亲切感。我知道,这不但是多年来久居大山之间的塔吉克乡亲们对我的接受,更是一种亲情浓淡疏密的表达。
多年来往于高原,我已熟知塔吉克人的各种礼节,但是,我尚没有以同种方式对待每一个塔吉克人,如何使用他们的礼节更多地说明我的情感指向——就像我对多里坤,我见到大多数人还是以汉人简单的握手来表示问候。多里坤和巴奴汗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两个童齿未褪的女儿刚从羊粪堆里滚出来,我低伏在她们的小脸上逐个亲了一下,心里充满舐犊的温情。山里的孩子,并不比牦牛和羊多见过几个人,她们见到我这位陌生的老伯吓得直哭,巴奴汗一个劲儿地指着我让孩子们叫“汉族爸爸汉族爸爸”。
我再次被塔吉克女人感动。羊群在圈里憋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挤奶,上百只羊的奶汁滋滋地射在一个铁桶里,就在这个时候,小女儿饿了要吃奶,巴奴汗撩起衣服揪着奶头填塞在小女儿的嘴里任由她吮吸着睡去,巴奴汗的两只手不停地捋着羊奶头竟然无暇再扶她一把。扯动的间隙,巴奴汗的乳头被孩子含在嘴里拽得老长。羊圈清静之后,巴奴汗低伏着身子用手和整条胳膊把细碎的羊粪拢成堆儿一捧一捧地往口袋里装,再背起来,两个女儿缠绕在脚前,一步注意不到都绊脚。云层很厚,阳光透过云隙迸射出数十道橘红的光束,巴奴汗一手提着口袋,一手拉扯着孩子慢慢走去,我看不到她的脸,只看到她背上硕大的口袋。
与紧贴着苏巴士达坂的卡拉苏相同,红其拉甫河谷之间也有一处同名的夏季牧场,为麻札种羊场和达布达尔两个乡所共有。听说我的好朋友达吾提一家已从穷托阔依转场过来了,我决定去看看。但是,另有一个隐秘的原因我没说,我惦记着孜雅迪曼,惦记着她那双湖蓝色的眼睛。仔细想想,她今年也该有七岁了。
赶到卡拉苏,住人的石房子前后的雪尚没融尽,达吾提一家还没到,谁能想到我比我的朋友更早地赶到了他在夏季牧场的家。以手抚着达吾提家门边的石头,希望这一刹那的心思过几天之后能让我这次未能谋面的朋友知道。我在邻居家放了一瓶酒,嘱咐邻居一定转交给达吾提。
卡拉苏之旅没见到达吾提已很遗憾,若见不到孜雅迪曼足以让我痛心。她已长到攥着草秆儿能吆喝羊的年龄了,家里人见我来了去大野地里叫她,一会儿工夫我看到一个小孩迎着我跑来。初见这个孩子的时候她才一岁多,支支吾吾刚能说明白几句话,她的奶奶提加大婶答应让我在她七岁的时候来把她接走,这使得这个小孩每每见到我都会睁着一双湖蓝色的眼睛告诉奶奶她的汉族爸爸来了,这一年她正好七岁。
这个孩子实在是灵秀到了极点,当年奶奶一时的心情已使她和我之间有了一种默契,过了这么多年,在她跑到我面前的一瞬,当我亲昵地在她的耳朵根儿吻了一下,她“哇”地哭了,两只眼睛里全是泪。
我看着这位尚未经正式认定的女儿,她的哭声让人揪心,我和周围的人一再说不带走她,才让她止住泪。我把带来的礼物放在她的手里,眼睛里满含着泪水,她自此之后一刻不停地盯着我看,一双湖蓝色的眼睛在我用闪光灯给她拍照的时候都没有眨一下。
我知道塔吉克人就连一只瘸了腿的小羊羔也不会送人,他们那种舔犊之情遍及人、动物和东西。当初想领女儿走,一家人觉得太小,答应等她七岁再说,真到了这—天,孩子的父亲又怨我当初为什么没带她走,我面对我的塔吉克女儿只有无奈。同时,也有一份不着形迹的满足。我想,我只能把拍在相机里的女儿带走了。她的名字很美,孜雅迪曼,意思是好多好多的月亮。我的一位兄弟翻译得可能有点差强人意,我估计,意思是众月之月。
3
印象中,多里坤二哥买买提·托乎提的儿子沙地尔,是一个从来不正眼看人、遇事溜着走的家伙,长成一个近一米八开外的大个子突然站在我面前,我有种生命之根被撼动的震撼。男人的心理很有意思,三四十岁出头的时候,丝毫不会觉得自己比一个二十岁的姑娘老多少,唯遇到这样的时候,我或我同代人的后代突然出现在面前成为一个悬殊参照让你无法回避,一刻间清晰地显示出岁月流逝的速度和结果。
买买提·托乎提是一个大吼一声就能惊得牦牛乱窜的汉子,仅仅几年之后,在翻越盖加克达坂的前一天,我看到他的儿子也能像父亲那样挥动绳索把牦牛逼到一个死角,然后再套住它。在乌鲁克苏牧场,多里坤这辈人大多不做这种出悍力的活儿了,新一代的塔吉克男人成了高原的主角。我看到沙地尔已开始将风雪横飞的高原人生牢牢握在手中,这是一个塔吉克男人面对世界的成人发布。
如沙地尔一般的几个塔吉克孩子送我过达坂,这已是我平生第九次翻越盖加克达坂。初长成的塔吉克男人就是一帮虎狼之子,从达坂下边一直到翻过达坂之后的很长一段路,几个浑小子打打闹闹地在牦牛背上滚过来滚过去从没消停过。不管脚下有多陡,积雪尚没有化掉,他们吆着牦牛在海拔五千五百米的达坂上狂奔,害得我拽着一头牦牛拉也拉不住。
在我心境惬意的时候,绑脚镫子的一根绳“嘭”地一声断了,我脚下登空险些从牦牛背上栽下去。沙地尔给我结好毛绳,晃荡了半个小时绳子又断了。本该引起警觉,在牦牛往一个近于直立的陡坡上拱的时候,两只手抓不住,我一下从牦牛背上掉了下来,陡坡上遍地是从山上掉下来的有尖锐棱角的石块,受惊的牦牛拖着我的一只脚狂奔,只要我的头脸任何一处擦在足以能割断陆战靴靴底的石棱子上,我想我的塔吉克兄弟们将会很麻烦。骑马骑牛,脚套在镫子上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我使劲甩动脚,在牦牛拖着我跑了两百米开外的时候竟然成功脱镫,我的脸一侧整个麻木了,据当时赶到我身边的几个塔吉克孩子一脸煞白的神情判断,想必我撞的惨状很吓人,我的身体撂在几块有着尖锐边角的石块之间,再往前半步就足以让我的脑壳子开花。牦牛一定受到了惊吓,就是在我的眼镜撞掉之后,以我八百度的近视眼仍能看到一头狂躁的牦牛在一片乱石之间蹦跳着,坍了垛子的被褥和一堆乱毛绳缠着它的脚。
费了很大劲儿在乱草棵子间找到的眼镜不能戴了,我拎过行囊翻出一副备用眼镜。头有点晕,不知道颅内受到的冲撞有多么严重,我坚持步行走,若几公里、十几公里没倒下,就说明颅内不会有淤血。据后来照镜子看清楚以后的情况判断,我的左脸侧当即就肿了起来,整个左眼圈乌紫,瞬间变成了另外一种动物。大约十二年前,第一次从天山西段穿过天山山脉抵达库车,突然被告知我的父亲病逝,那年是我的本命年。今年又是本命年,尽管家人给我买了一打红短裤,一劫总是要过的,我想我摔得还不算太重。
听到狗叫声天已经黑透了,我的备用眼镜是一副墨镜,陪我第二次进山的西多克兄弟搀着我走最后一段路。黑森森的树影和形迹隐约的山离得很近,伸手又什么都抓不到,已经开始眼花的西多克兄弟搀着我探着脚往前摸,其间几次脚下踏空,我又一次摔在地上,伸展了胳膊腿在地上躺了会儿,习习凉风吹得我痛灼的脸颊很舒服。西多克兄弟把我拽起来继续走,直到有人打着手电筒出来接我们。
赶到多里坤在依沙布拉克的家,我和他的父亲老霍加行了男人之间的吻手礼,女人们依次吻了我的掌心,唯有都尔那玛大妈出现的时候,尽管头懵、腿沉得拖不动,我依然能感到她的犹豫,我跨前一步紧紧拥抱住她老人家,她搂着我的肩膀又在轻声嘟囔我所熟悉的—串话:蛮乃巴郎子,蛮乃巴郎子(我的儿子)。我以对母亲的方式拥抱了她老人家。在拍完我的纪录片作品《太阳部族》告别都尔那玛大妈后,我曾无数次想到她老人家,一直想着有一天能重新回来。这天晚上在大妈家,是她的二儿媳沙比克给我铺的被褥,这是我在高原十多天里睡得最踏实的一个晚上。
我的时间只允许我在依沙布拉克停驻两天,我逐一拜访了村里的每一户人家,第二天晚上留住提加大婶家。知道都尔那玛大妈不愿意我走,我贪图睡在她家炕上的那种酣然,晚上住在提加大婶家的时候,还数次回去拿东西,坐下喝大妈的奶茶,大妈和她的儿媳几次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碎石头给我。这些石头都是在塔什库尔干河谷和札莱甫相河谷随处能捡到的普通石子,颜色和纹路稍有些特别,口袋里放的时间长了,久经摩拭,石子表面很光亮。
提加大婶是依沙布拉克最勤勉的老人之一。我知道她家门前的一棵杏树结的杏子是村里最甜的,我有一双湖蓝色眼睛的女儿是她的孙女。大婶特地嘱咐家人给我做了汤面条,汤里漂着青苜蓿。在河谷纵深的依沙布拉克小村,这样的饭一年也难得吃几回。在大婶长子乌提库尔兄弟陪我吃饭的时候,大婶进进出出忙个不停,我搁下饭碗之后才明白她在为我忙。
大婶坐在我身边,把一个盘子翻过来,然后蘸着水在盘底上磨一块什么东西。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一种叫札尔莫勒的石头和一种叫札尔其吾的草药,大婶将研磨的药汁涂在我的脸上和眼圈四周,我立刻感到一阵灼痛。这天下午去村里的医生家做客,医生父子俩用一个乡村医生所能有的手段对我的创伤做了全面处理,敷上药膏,又裹了一层纱布,再回到提加大婶家,提加大婶说这种伤口包了不好,以前她儿子包过化了脓。第二天我离开之前悄悄撕掉了纱布,然后让西多克给大婶说我一晚上不舒服。大婶翻过盘子底再次开始研药,然后轻蘸着抹在我的脸上,我看到她老人家脸上已松弛了许多,我和西多克兄弟都认真地听她老人家细述这种药物的种种神妙之处。
4
沿着下行的河水继续走小半天,河水通过经久冲刷形成的峡口流入一望无际的高崖之下,那是由大山渐渐铺陈下来的大片冲积扇经河水冲刷突然坍塌形成的边缘断裂,下面就是极为开阔的河谷谷地,其间乱石杂陈,骑着骆驼或牦牛三五个小时也未必走得过去。河谷几乎就是在天地之间凿出来的一条大沟,两边的山显得低了,让人很难准确判断其间相距的实际距离。像是一笔天书从天涯尽头落笔,然后再蕴力十足地拉下来,蜿蜒流动的一条水脉恣意流淌,那是东部帕米尔高原最著名的大河——札莱甫相河。
札莱甫相河河段和克尔钦河的一部分正好是叶尔羌河上游水脉初孕形成的地方,深切幅度大,河岸景观波澜壮阔,显出自然手笔的十足力量。与我同行的小苏到了一处河湾子甩下鱼钩,不大工夫就钓上来一条足有半条小臂长的鱼,鱼被扔在地上。这时帕米尔高原直接承受正午阳光暴晒的地表,气浪漫舞,有足以烘熟羊排的温度。我看不懂鱼的眼神,只看到它不停地弹起来极力向空中跳,每次弹起来身上都裹敷了更多的沙土。最触目惊心的是它的嘴极尽可能张大的那种状态,不知道是出于惊恐,还是试图在空气中吸吮到最后一口水?估计,鱼儿不知道空气中没有水,只是出于本能的挣扎,它张开嘴向世界做最后一次发布,或者,实在是试图向我们人类讲述最后的一句话。鱼通过极端生命状态告诉我们的最后一句话一定是最极端、最不可不说的内容!
小苏的鱼钩再没有钓上鱼,唯一的一条鱼被放在一只塑料袋里系在驼驮子上带走。塑料袋后来又掉在了地上,由跟在驼队后边走的我捡起来拎在手里。
大约三个小时后,赶到一处有泉水的地方休息,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鱼从口袋里倒出来放在清澈的泉水中给它洗掉浑身的沙土,然后我静静地看着它。若有一丝生息尚存,我一定做主把它放生了,泉水几十米外就是大河,那该是鱼所向往的“鱼生极致”。鱼被泉水推动,几次让我疑是幻觉,我终没看到它在泉底初绿的水草间摆动起来,我想我仅是给这条素昧平生的鱼选了一块墓地。想象稍稍延伸一步是危险的,若是鱼把钩甩到岸上来钓人,它们的饵料一定是人无法抵抗的诱惑,把钓到的人拖入水里扑腾半天再蒙在一只塑料袋里拎在水里走三个小时,即使照样有一条鱼如我一样把人再抛到岸上,随便我们哪个同类还有可能重获生命吗?事实上,我们正在用相似的方式对待整个高原。
从塔什库尔干河流域到札莱甫相河流域,整个帕米尔高原东部的草荒得很重,每条住人的沟里能烧的薪柴越来越少。很难看到雪豹的蹄印了,黄羊依旧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传统美味。在人口稍微密集一点儿的地方,如今各家饭馆最时兴的菜就是河里的鱼。这种珍贵的高寒鱼种,没有三五年的工夫长不到三十厘米以上,它的叫法很有诗意:雪豚。
这条鱼最后的命运是再次被装在塑料袋里拎走,晚上在我们留住的一家被油炸好端上席,连那些从没有吃过鱼的塔吉克乡亲们也盛赞它的肉鲜美至极。
告别依沙布拉克,我依次走过勒斯卡木村的每个居民点,实际上,最想见到的只有两个人。
住在玉鲁克的加玛莱力原是位老师,他俊朗的脸总让我想到美国的老牌影星派克,退休之后过一个山里人的日子。我赶到的时候,他和老伴儿随着羊群刚去了玉鲁克的夏牧场。女儿初长成,和留在家里的奶奶、嫂子掐了鲜嫩的苜蓿尖做了一顿抓饭代爸爸款待我。加玛莱力如今的家是玉鲁克建筑水准最高的豪宅,依着闺女垫的被褥靠踏实了,心里实在为老友一生辛劳的收获高兴,只是不知道等我踏出这道门槛,什么时候再能端着女儿倒的奶茶细细品味。
穹托阔依只有一户人家,是我的好友达吾提足有三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他的老父亲和留在家里务农的弟弟十分吃惊我在卡拉苏没有碰到达吾提。掐指一算,我俩刚好在彼此过往的路上错过。我向老父亲请教,从穷托阔依往卡拉苏转场需要多少时间。老父亲的回答让我咂舌:
十五天到十七天。
这恐怕是我至今所知的新疆最长的转场路线了!
在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大多数地区,牧民们已普遍使用车辆运输羊群转场,相比之下,达吾提一家的转场更显出高原生活状态的悲壮!
在帕米尔高原游走,我曾无数次见到转场的情景,日夜兼程,不断会有羊只掉队,最后死掉——转场是高原畜群的一次痛劫,何况是一条最远的转场线路!达吾提一家会在路上住十几个晚上,雨雪无蔽,路上仅以干馕和茶充饥,这是每一个高原塔吉克人人生着色最浓重的一笔!
在描述西域历史人文景观的时候,学者和专家常有一个重大的笔误:帕米尔高原和整个西域在丝绸之路前似乎是毫无闪光之处,一派沉寂。事实上,直到今天,在那些以“历史大事件”为特征的所有奢华事件未发生之前和其光芒渐渐褪去之后,高原的每条峡谷之间依旧有鲜活的气息流动,不入史册,却无法被勾销,亦如我的好友达吾提吆着羊群从穷托阔依转往卡拉苏,这是高原景观中最生动、最有价值的一次记录。
我想,这个时候,达吾提也该喝到我给他留在卡拉苏的那瓶酒了吧!
5
与盖孜的李栋兄弟如约相见,他找到了当年的盖孜古驿站,我拍了照片。
众山之间,湍急的盖孜河的喧嚣终年不绝,连过往汽车的喇叭声也听不见。河畔一个石圈子围着一幢馕坑状的土屋,二三十步外一块大石头边上有几间没有遮拦的石墙圈,这两个地方是被人指认的盖孜古驿站遗址。
站在任何一座山上望去,今天的中—巴国际大通道都是帕米尔高原东部最为显眼的人为创造,犹如在阿波罗太空船上看到横亘于地球表面的长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很多人把它的起点和终点混同于丝绸之路时代的葱岭古道。
实际上,谬之已远。
被人广泛指认的盖孜古驿站始用于明代或前清时期,甚至更晚。有一点很肯定:这条路始终不是中心位置。
丝绸之路年代的行旅,从英吉莎或莎车的昆仑山口进入高原腹地,那条大道比盖孜古道更靠东南方向一些。
另一个谬误在红其拉甫,过往的人到了这儿都会留影,把这儿当做有地理和历史双重意义的一个重要地点。实际上,在丝绸之路年代,红其拉甫达坂是随时会让人和牲畜失脚滚下去的一条险途,真正的丝绸之路大道在远没有抵达红其拉甫达坂三四十公里之前就西去折向了卡拉其库,始有一条大道牵引着整个世界为之翩跹舞蹈的美丽传说。
其实,李栋兄弟能不能找到盖孜古驿站并不重要。
古往今来,出于种种背景和原因,使人们登上高原或走向高原。我的原因很简单,仅是想去看看我的朋友。隐约有一份牵挂的东西系在心里,亦如高原上的河,从山顶一直流向遥远的地方,经年长久,在岁月中留下痕迹,成为心中永远的风景。
责编:李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