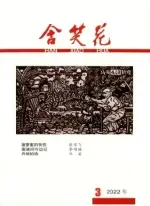记忆深处(二章)
2011-08-15蔡兴贵彝族
◆蔡兴贵(彝族)
记忆深处(二章)
◆蔡兴贵(彝族)
抠门的麻脸股长
二十七年前,我还在昆明读书的时候,县公安局特情股的黎股长曾到警校集训过三个月。其间,出于礼貌,我会隔三岔五地到他的宿舍看看他,并汇报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给他留下了一丝半点农村娃儿憨厚朴实的好印象。参加工作第二年,因为我会玩点舞笔弄墨的文字游戏,这位麻脸股长便要了我去当内勤。
直呼自己的上司“麻脸股长”,我并没有一点恶意,因为在做他部下的那些日子里,我发现黎股长从不忌讳他拥有一张奇丑无比的麻脸,而我在天长日久的仰望后,也不厌恶他那张坑坑凹凹的麻脸了。相反,相处长了,我倒认为他的麻脸比我们有些人的“滑”脸要耐看得多,因为在他的麻脸上看不到一丝狡黠、半点奸诈,犹如浑金璞玉,日见光辉,百看不厌。但是,局里不少人却不愿“瞻仰”和“光顾”他那张凹凸不平的麻脸,跟他说话常常虚光斜视,不敢正眼相看,一来怕他“自惭形秽”,二来怕自己噩梦连连。其实,据我观察,黎股长根本就不为自己有一张麻脸而耿耿于怀。他坦然地告诉我,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一场高烧虽没夺去他的性命,但“成就”了他这张麻脸,筛子般千穿百孔的麻脸陪他走过了大半身,别人的冷眼相向和冷嘲热讽他早就习以为常了。他说,只要保住性命,麻了就麻了吧,那是无力回天的事。他还告诉我,他为有一张麻脸而自豪,因为麻子因其丑陋无比而让人望而生畏,无形中少了很多人缘往来,也少了很多是是非非,减少了很多人际关系中的牵累。细而观之,黎股长的脸确实有些恐怖,但那是别人的事,而他对这种天赐之“丑”却能泰然处之。在一次教我们描述犯罪分子的面貌特征时,他毫不避讳地说:“譬如描述我,你们就要说我长着一张麻子脸,这是我区别于常人的最显著的特征。如果我犯罪逃匿,你们就按这个特征通缉我。”对如此真诚的上司,我岂能不以此心换彼心、不以此情思彼情呢?此后,无论生活中的迷惑,还是工作上的疑问,我都向他敞开心扉,大胆讨教,我们的关系渐渐地处得十分融洽。当然,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不只是黎股长对自己长相的泰然处之,而更多的是他那张麻脸背后许多闪光的人生态度。
我们特情股的业务主要是搜集边境情报,因为那时那场众所周知的局部战争结束不久,中国和某国关系还处在对峙状态,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异常激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有钱是很少搞得到有价值的核心情报的。在这个问题上,情报管理高层毫不含糊,业务所需的费用源源不断的下拨,特情股可支配的钱款数额十分可观。但是,麻脸股长对钱这东西管得十分严格,而且严到每一分钱的支出他都要追根究底。更“抠门”的是,每次接待“线人”用剩的几支香烟他都要叫我锁入抽屉,并以“支数”为单位做好领用和回收登记。股里的同志未经他许可,是不得随便支取钱物的。而他,也不会在没有其他同志在场的情况下使用钱物。每次报销业务费,他都要求报账的同志列举出在场证人,没有证人的休想报销。为此,股里的干警们在私下里送给他一个“麻子老抠”的绰号。
当时的内勤,就相当于今天的部门秘书,既要管文书材料的处理,又要管钱管账管物资,应该是有点自主权的。但有麻脸股长的言传身教,我对待公家的钱物便十分谨慎,从没擅自做过主。这“麻子老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处事清白,公私分明,不徇私情,小事不昏庸,大事不糊涂。譬如,作为一股之长,偶尔用用股里的摩托车办办私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他就是一个较真的人,每用一次都无一例外的要到单位财务室交油费。其实,他不吭声局领导也不会知道,我等手下人也不会去告发。我和他下乡多次,每次途中吃饭都是二一添作五,各开各的钱,他不会帮你多开一分,你也休想为他多付一文,“吃公款”那是一次都不曾有过的。到老乡家吃饭,每人每顿三角钱、半斤粮票那是雷打不动的,有他在的地方,你休想白吃白喝。即使招呼你们吃饭的人家是你的亲戚,他也不会跟着你占便宜。有时,遇到热情好客的主人不肯收钱时,他便急得麻脸上凸起来的肉瘤瘤更凸,凹下去的肉窝窝更凹,让人家难堪得不收都觉得对不起他那张麻脸。
记得,每隔三两个月,我便要随他到边境地区蹲点搞情报。因为车路不通,去来要走两三天的路程,所以,我们常常一住就是半把个月。在蹲点的日子里,为节省生活开支,我们自己生火做饭吃。油盐辣子是从县城买了带去的,米和菜是向当地老乡购买的,柴火是走村串户的时候从路边捡的。每次蹲点的吃喝费用都是黎股长先垫支,等回单位报了每人每天4角5分钱的差旅费后统一结账,盈余或不足部分“多退少补”。有一次算伙食账时,黎股长在办公室当着同事们的面告诉我,他多付了6分钱。我很不在意的说我会记得的,下次我多出一点就是了。他说,“差钱一次做一次地算清,时间长了会忘记。”这话,黎股长可能是“说者无意”,但我却是“听者有心”,羞得我满脸发烧,只得十分尴尬地掏出6分钱,恭恭敬敬的赔给他。黎股长边收钱边振振有辞的告诫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要记住,钱这东西属于自己的少一分不行,不属于自己的多一分不要,这叫亲兄弟明算账,来得清,去得明,谁也不欠谁的人情账。”有了这次教训,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真就不敢拖欠他人一分钱,同时也不无缘无故占别人便宜。
在下乡的日子里,当地村公所的干部偶尔会约我们到农村的集市上去合伙吃“狗汤锅”,或他们在村公所的小厨房里杀鸡宰鸭“打牙祭”的时候邀我们入伙。这种大伙蹲在地上,围着一口铁锅或是一个锑盆大碗喝酒、大块嚼肉的吃法叫“落地响”,亦即一蹲下去就得出一份钱,没有白吃白喝的道理。“落地响”一般是在大家酒足饭饱后算账,吃客都懂这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会当场掏腰包兑现,跟现在的学生哥们风行的“AA制”是一样的。在那个缺肉少油的年代,能吃上一顿“落地响”算是有福气的了,所以嘴馋的我就是借钱也不会放过机会。而抠门出名的黎股长勉勉强强地参加了几次后,便不再接受乡下干部们的邀请了。他告诉我,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不钻草,从此以后“落地响”跟他无缘了。其实,个中原因很简单,就是有一次吃“落地响”结束算账时起了点风波,黎股长说他患重感冒滴酒未沾,不该算他的酒水钱。而算账的说他不喝酒多吃饭,酒钱饭钱大家都应该平摊。黎股长据理力争,说酒钱比饭钱贵。算账的借题发挥,说他狼吞虎咽吃了三大碗米饭、喝了三大碗肉汤、啃了三大个骨头,算起来比酒钱贵多了。一个是凡事较真的“一根筋”,一个是醉意蒙眬的“糊涂蛋”,双方是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只差拳脚功夫没有用上了。在一醒一醉两个人的“攻防对垒”棋逢对手、酣畅淋漓的时候,一老者慢条斯理地走过来主持公道了。“公道”的结果,是黎股长出于对老者的尊重,慷慨大方的开了一份没喝酒的“冤枉钱”。过后,我仔细思量的结论是:黎股长的“抠”不无道理,做人不该有糊涂账,不喝酒的人有什么义务为喝酒的人开酒钱呢!当然,对穷困者慷慨解囊,对病痛者救死扶伤,对临危者见义勇为,对残弱者行善积德又是另一回事,我就无数次耳闻目睹过黎股长对农村鳏寡孤独者的慷慨大方。
黎股长对自家的“抠”,对公家的更“抠”,不该公家出的钱他从不开口。在我身上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天,他从消防队请来一名姓郑的摩托车驾驶员送我下乡行至半路时,这位立场不是很坚定的郑师,终是耐不住我死皮赖脸的缠磨,有些无可奈何地将摩托车交给我驾驶。因身手太臭的原因,我在一转弯处将车弄翻损坏了部分零件。身为现役军人的郑师顿时少了平时的温文尔雅,对我的“失手”歇斯底里、喋喋不休,并恳求我无论如何都不要把翻车一事“赖”到他头上。我虽也惊魂未定,但压根就没有过让人代为受过的歪想,他的大吼大叫反倒让我感觉到人格受了侮辱。于是,为了证明我的敢作敢为,我便带着郑师到附近的村公所给黎股长打电话,很内疚地报告了实情,作了深刻的检讨。在检讨的内容里,我不忘穿插几句从郑师的手里抢夺摩托车钥匙的谎言,感动得郑师不停的给我递烟送火。说实在话,我当时的主动认错还是有点“动机不纯”的,幻想事情会在黎股长那里得到摆平,因为我自认为是他的“得力助手”和“得意门生”。可万万没想到,他竟毫不留情地对我说:“这件事我不会给你保密,也不会包庇你,一定要向局党组汇报,怎么处理由组织讨论决定,你自己要有思想准备。”一个星期后,我办完事情步行回到单位时,局党组会议已经讨论不给我行政处分了,但责令我承担全部修理费。据说,这个结果是黎股长以我是下乡工作违纪情有可原争取到的,不然,组织对我的处理还会重一些。但也有人告诉我,股里面有几个同事帮我求情,叫股长瞒在股里算了,可他不但不买账,还上纲上线地骂说情的同志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这一次无证驾驶事故,我赔了50多块钱的修理费,差不多就是当年两个月的工资。
不过,这次事故教乖了我从此不乱动机械,即便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在多个单位管过车辆和驾驶员,但从来没有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搞过“无证驾驶”,直至今天都还是一个对“方向盘”不敏感的“驾盲”。如果当初麻脸股长包庇了我的话,说不定我就会对违规“闯红灯”这些事情不以为然,难免惹出一些于人于己、于公于私都不利的事端来。
深藏不露的“仇家”
年轻的时候,为在朋友面前抖足威风,我曾违心地干过一次亵渎自己钟爱的职业的龌龊事,现在想来都还有些自惭形秽、自感卑污。
那是我从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不久的一天,一位在乡下供职的本家兄弟找上门来,很是委屈地告诉我,他在自己工作的街市与人发生肢体冲突时,因技不如人被一男性青年踩翻倒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受了奇耻大辱,求我用学校学来的擒拿功夫为他出出这口恶气。
兄弟情深,实难推却,我顺口安慰他说:“小事一桩,有机会哥也让他趴在地上让你解解恨”。
我的话原本是没加思索的信口开河,而在他却信以为真,当即被我的“侠肝义胆”感动得手足无措、涕零泪下。于是,本家兄弟的激动,通过视觉传导催生了我的感动,我那“豁出去了”的决心骤然当机立断、坚定不移了。
得了我的承诺后,本家兄弟便对“仇家”实施跟踪追迹了。终于有一天,报仇心切的他得知“仇家”上了一辆班车赶往县城后,便借故向单位领导告了假,骑着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跟踪四五十公里来到县城,盯梢到“仇家”落脚的住所后,兴高采烈地跑来给我报了信。
“不打不行吗?”我问。
“你答应的事怎能不算数呢!”他有些不高兴地说。
“把人家打伤住院怎么办?”我又问。
“大不了我付医药费。”他慷慨大方地说。
“人家告我怎么办?”我再问。
“你非要穿着警服去和人单挑吗?动动脑筋来个突然袭击,完事后马上开溜,让他屙尿告灰去。”他有些自作聪明的对我说。
“万一出手时分寸把握不好,要了人家的性命怎么办?”我还问。
这回,本家兄弟对我没完没了的“问”没了耐心,有些鄙夷地看着我唠叨开了:“不干就算,亏你还读过两年公安,不过是个说话不算数的胆小鬼,我今晚就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让你见识见识。”
这话虽是对我的激将,但也不排除我这仇火攻心的本家兄弟狗急跳墙,会不择手段地将“仇家”置于死地,到时候他难逃法网,我也脱不了助纣为虐、知情不举的干系。
我冒着一身冷汗连忙制止说:“你不要乱来,我找朋友合计合计,这仇哥为你报定了。”
安顿好本家兄弟后,我便去城郊学校想找拳脚功夫胜我一筹的平老表讨教几招锦囊妙计,因为在关键时候他总是比我有招。找了半天不见平老表的踪影后,有些焦躁不安的我,又不得不去找我们朋友堆里的大哥大朱兄出主意。
素来为人正直的朱兄,对我的轻浮大为不快,但又碍于朋友情面不好拒绝,只得无可奈何地给我出谋划策。我们商量的办法是等到天黑后动手,对“仇家”的“教训”点到为止,只是吓唬吓唬,不能造成伤害,更不能留下引火烧身的把柄。为保证计划万无一失,在我的再三恳求下,朱兄很不情愿地同意了做我的帮凶。
计划确定后,我和朱兄便随本家兄弟钻进一巷道口的小饭店,各自端着一只海碗频频举杯,互相借着点酒性提神打气。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人流如织的时候,有些醉意蒙眬的我们仨,酒气冲天地走出小饭店,大摇大摆地融入沿街闲逛的人群,东张西望、贼眉鼠眼的寻找将要大祸临头的“仇家”。
那时的县城就两条大街,一条叫东风路,一条叫兴隆街,外地来客和乡下来人除了逛逛电影院、百货公司和城边的烈士陵园外,没啥热闹去处,饭后都喜欢到这两条街上悠哉游哉的散步,怡然自得的散心,有意无意的参与制造市井街巷的繁荣与喧闹。
东风路上,本家兄弟走在前面左顾右盼,我和朱兄紧随其后伺机出击。还没走完半条街子,本家兄弟就扭头跑回,慌慌张张地给我们指认走在前面的只见背影而不见尊容的“仇家”了。
有些自作聪明的我,当即小声告诉朱兄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动手,应装着酒醉将目标劫持到僻静处再施恶行。聪明的朱兄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本家兄弟将目标交给我们后,便逃之夭夭,躲进朱兄的宿舍等候战果去了。
我和朱兄混入熙来攘往的人群,宛若两只眼闪寒光的恶狼,时隐时现、忽快忽慢地向“仇家”靠近。行至国营食堂路段,我俩从左右两侧包抄而上,像见到久别重缝的朋友一样,很是“亲热”地对“仇家”搂肩搭脖、拖扯搡拉,旁若无人地将他往国营食堂旁边的一条昏暗巷子里推去。路人误把抱作一团的我们仨当成无所事事的酒囊饭袋,像躲避瘟疫一样快步闪开给我们让路。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仇家”弄得莫名其妙,吓得不知所措,可怜他来不及喊上一声“救命”,便被我们像野猫抓小鸡一样,拽进了一个垃圾遍地、臭气熏天、黑咕隆咚的地方。
那个年代,人们的文化生活相当枯燥,年轻人有事无事的便轮流坐东进馆子,喊破嗓子猜拳行令比酒量。每次饭局,不轰轰烈烈、昏天地暗的喝倒几个拖出门来,大家是不肯收杯的。为此,年轻的醉鬼们在大街上装疯卖傻、哭爹喊娘、指手画脚、仰翻八叉、当街放尿、一路呕吐的情形时有发生,市民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所以很少有人去管这等无聊的闲事。我们选择这样的坏境和方式犯事,肯定不会引人注目。事后,朱兄高调夸我胆识过人、智勇双全,我亦曾得意忘形、沾沾自喜。
话说到了黑暗处,为了速战速决,我一把推开朱兄的当儿,一个扫弹腿扫去,“仇家”旋即乖乖地扑倒在地。早已腿脚痒痒的朱兄等之不及,饿狗扑食般地跳将过来,恶狠狠往“仇家”的身上猛踩猛踏。没了出手机会的我,只得没趣的收回格斗架式,退后几步来到人流穿梭不息的路口上,当起了为朱兄守哨望风的角色。那边,任凭朱兄如何踹踢,“仇家”就像死人一样不反抗、不吱声、不动弹,恰似一只供人练腿的沙袋,悄然无声地任人蹂躏和践踏。一种惹出大祸的不祥之兆忽然蹿到我的心头,吓得我连忙跑来拉开朱兄,带着他飞似的沿着一条很少有人出没的狭窄巷道奔逃而去。
我们气喘吁吁地窜回朱兄的宿舍后,我便有些心神不定、焦躁不安了,开始嘀嘀咕咕地责备朱兄出手不知轻重了,说他对其“点到为止”的诺言出尔反尔了,怪他可能弄出难以挽回的祸端了。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俩,倘若“仇家”有个三长两短,我们都得进牢房、上刑场、吃枪子、进地狱,一个也跑不脱、逃不掉。进屋就在本家兄弟面前眉飞色舞、夸夸其谈的朱兄,立时被我的牢骚满腹吓得有些战战兢兢、魂不守舍了。本家兄弟早已吓得两腿筛糠、面如蜡纸、挥汗如雨了。于是,我们三个狼狈为奸的好事之徒,像三只漏了气的皮球,马上无精打采地瘪了下来,躺倒在沙发上各自叹息了。在他俩陷入心慌意乱、一支接一支地燃烧着“金沙江”的时候,我冷冷地说:“如果真的出了大祸,你们就跟着我投案自首去”。说完,我借故上厕所,独自摸到我们做案的现场观察动静,在确认“仇家”已不在现场后,才慢慢吞吞地返回来,把“仇家”恐无大碍的情况告诉惊魂未定的他们两个。
因为从犯事到逃遁不过几十秒的功夫,我的脑子里根本来不及留下“仇家”的丁点印象,想必他亦可能没看清我的嘴脸。这次作恶,我原以为做得天衣无缝,不可能会有报应,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自己的过错忘得一干二净了。谁料,善恶终有报,是祸躲不脱。
五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热闹的场合,一张酒桌之上,一位万贯腰缠的老板,一碗辣酒下肚之后,一种咄咄逼人的口吻,把遭到我和朱兄黑打之事娓娓道来。其描述绘声绘色、有鼻有眼、活灵活现,惊得我有些心惊肉跳、呆若木鸡,也惊得在场诸君目瞪口呆、面面相觑。我的正人君子形象瞬时荡然无存,俨然一只落入猎人之手的衣冠禽兽,被剥脱得一丝不挂,清晰地露出了心腹肠肚中的肮脏。好在事隔多年,我早存悔过之心,加上被他逼得没了退路,情急之中,我只得不顾体面地演绎一番江湖习气,在列位看官的见证下,坦坦荡荡的向他鞠躬认错、赔礼道歉。
我的临场表演,感动得满座高朋纷纷击掌鼓舞、频频举杯言和,也感动得“仇家”立马收敛话锋,仰起脖子豪爽地吞下了半碗白酒。
借着酒性说到投机处,我们便有了以下轻松愉快、风趣幽默的调侃:
“你当初为何要欺负我兄弟?”
“是你兄弟先出手打了我兄弟,我和你一样是帮兄弟的忙。”
“我们抓你时,你为何不喊叫?”
“我的手在挣扎中碰到了你身上的手枪,便知道你是公安,我若喊叫你就说我是逃犯,群众只会帮你,不会帮我。”
“你为何那么不经打,我一绊你就倒地不起?”
“你们不是想打倒我才过瘾吗?我是故意借着你的腿力来个前扑动作安全倒地的。”
“难道你也会功夫?”
“我连看了十七场《少林寺》,还在部队当过侦察兵。”
“有那么好的功夫,你为何不还手?”
“我还手,说不定趴在地上的就是你。但是,如果你借口正当防卫,我这条小命不就玩完了吗!”
“你为何躺在地上装死不动?”
“我不装死吓跑你们,可能还会挨得更惨。”
“你事后想过向我报一箭之仇吗?”
“不仅想过,而且还跟踪了你好几天,后来我兄弟劝我说你是公安,惹恼了你们没好果子吃,我也就算了。
“你可以到我的单位告我呀?”
“我想过告你,但又想到若把你的饭碗告砸了,你饶得了我吗?”
“无商不奸,你这种处处为人着想的人,能赚到钱吗?”
“警察缺失了正义便枉吃了皇粮,商人丧失了良心便丢失了商机。”
“……”
“……”
“为了你的大度,为了我的无知,干杯!”
“为了你的问题,为了我的答案,干杯!”
我们各以一碗回味无穷的烈酒,结束了这段令我汗颜与尴尬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