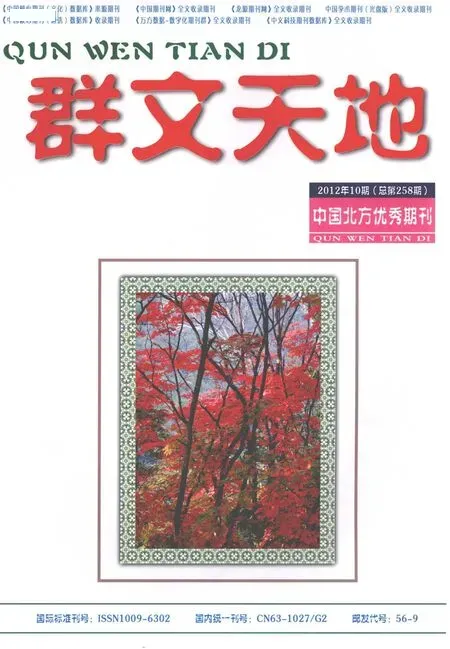简论苏轼乐观旷达、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
2011-08-15王利娜
■王利娜
苏轼的一生坎坷不平,遭受许多不幸和打击,尤其是后半生被贬黄州、惠州、儋州,生活极其的困窘,但他从未被苦难困境压倒,而是善于排解,随缘自适,随遇而安,不为世俗的祸福苦乐所拘牵,不为得失生死所烦恼,而是表现出坚定沉着、乐观旷达、超然物外的自由境界,显出其超乎异常的人生态度。
苏轼是一个“奋厉有当世之志”的文人,正如马斯洛所说:“自我实现的人的一个特点是很少有自我冲突。他不会跟自己过不去,他的个性是统一的。这使他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创作。”苏轼的一生坎坷不平,遭受许多不幸和打击,尤其是后半生被贬黄州、惠州、儋州,生活极其的困窘,但他从未被苦难困境压倒,而是善于排解,随缘自适,随遇而安,不为世俗的祸福苦乐所拘牵,不为得失生死所烦恼,而是表现出坚定沉着、乐观旷达、超然物外的自由境界,显出其超乎异常的人生态度。
苏轼获罪贬黄州时,他却说“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美竹连山觉笋香”,多山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闲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竹声”。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被贬潮州,柳宗元被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而苏轼却显旷达之气。他在《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先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中:“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醉,野老苍颜一笑温。己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从诗中可知诗人能随遇而安,不以之为悲,豪放旷达,没有了“闲人”伤感,现实的苦闷也在心灵中得到了净化。又如最令苏轼津津乐道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作者手持竹杖,脚穿草鞋,透露出作者喜好自然,无拘无束的性格,虽然有来自各方面的打击,但他仍然泰然处之“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足见他的胸襟和气度。下片写自然是变幻莫测的,亦有阴晴变化,更何况是人生的际遇?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再如他的《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同样写得奇肆开阔乐观旷达,作者面对“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狂涛处之坦然,认为“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如果我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及吾无身,吾身何患?”再大的风再大的浪也不能使我恐惧忧虑,一定会引起我“快哉此风”之感。同样他的另一首《浣溪沙》写得清新活泼,朝气蓬勃,“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全词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然而上阕结句的子规啼声,隐隐折射出词人处境,下阙一扫伤时叹老的调子,展现乐观旷达的精神状态。这些诗词中更多的展现的是诗人对苦难的傲视和超越。
被贬惠州时,见到遍野的荔枝林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足见他的乐观之态度。而他的《纵笔》诗更是洒脱超然:“白头萧萧清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作于绍圣四年,诗人此时已经六十岁了,居住在嘉祐寺,尽管他政治上屡次遭受打击却还能安稳的睡觉,这体现出苏轼不为境遇所左右的独特心境,据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载,此事被当时宰相张惇看见,为苏轼仍能安稳地“春睡美”而恼怒,于是,把他从惠州贬到更为偏远的儋州。
在被贬儋州之前,他从李德裕的“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中了解到儋州的环境,诗中的“毒雾”、“ 蛇草”、“沙虫”、“燕泥”显然是写海南环境极其的险恶,是一片荒凉之地,但是,他在自己还没有被贬海南之前就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并没有因之而惧怕。当时其弟苏辙正被贬为雷州,离他不远,便日夜赶路,并在途中给苏辙写了《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尚在藤也,日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一诗,最后四句这样说道:“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做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他表示要把即将贬往的穷荒之地当做自己的故乡,可见苏轼旷达洒脱的心胸,这种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这便与李德裕“生度鬼门关”的悲叹形成鲜明的对照。
面对接二连三的政治打击,仕途上的坎坷不平,荆棘丛生,苏轼的立场是坚定的。正如他所说的“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不改其度”则说明了苏轼不论遭受怎样的排挤和打击,他都会操守自己的政治信念,坚持自己超然自得的处世态度;他还反复说道:“胸中亦有翛然处也”,此处的“翛然”,表现出诗人的无拘无束和自由自在;“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流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付与造物”则表示他已经把一切置之度外,一切听从于造物者。在其一生中,他始终以如此不屈的精神与政敌破坏相抗争,因此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他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其旷达性格,其脱于世俗生死苦乐观念显而易见,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对人生种种困境,诗人不仅努力适应,而且又主动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乐趣,他的乐观旷达胸襟是其他文人难以达到的。他坚信苦雨凄风必将过去,并以苦为乐笑对人生,达到“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
苏轼之所以能在艰险的人生道路上,以超旷的态度处之泰然,同他年轻时从佛道二家的思想中吸取精神养料是分不开的。佛老思想成为他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精神武器,追求“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超脱境界。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苦大悲之后,特别是经历了黄州、惠州、儋州时期“流离僵卧,九死之余”的生活之后,才有了真正的人生感悟而进入到一种常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正如他在《迁居》一诗中写道:“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个有际。”诗中写到世间的万物都是在瞬息间一生一灭,都有其生存的规律,是我们无法左右的,宇宙再大也是有涯际的。那么,一个人的痛苦和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无需感叹和暗自悲伤。他能乐天知命,在一般人很难忍受的贬谪生活中寻得闲适之趣,做到胸无芥蒂,超然物外,不为世俗的名利、穷达、荣辱、贵贱、祸福、忧喜、苦乐所拘牵,不为得失生死所烦恼,便达到了所谓旷放、超然物外的境界。“任性逍遥,随缘旷放,但尽凡心,无别胜解”,是对这种境界的高度概括。他在《前赤壁赋》中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表现了苏轼的乐观旷达、物我相忘的精神境界。作于三个月后重游的《后赤壁赋》中,作者面对月夜山河,不禁忧从中来,临风长啸,心中感怀“怅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萧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一只孤鹤把词人的感情引向旷达超然。“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这只孤鹤成为东坡由悲转向超逸旷达的情感纽带,其后进入梦境,以道士化鹤结束,词人由乐转悲,由悲转逸,又由逸转空,从而传达出苏轼面对人生之变的旷达与适然。同样他的《西江月》也折射出苏轼物我两忘,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可知,他的贬谪生涯使其具有冲和淡泊的心境,他的精神陶醉于大自然的景色里,融主观与客观为一体,眼里所见,笔下所写,自然而然的传达出大自然景色的韵致,创造出一种诗的意境。从而达到沉着坚定,不受外物羁绊的、超然物外的自由精神境界。从这样的精神和艺术境界中,我们也可以真切的感受到苏轼的超然的人生态度。
总言之,苏轼能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忠君爱民积极用世的理想,老庄何思何虑的旷达境界,自己的通达的心境及坚毅的创作意志,自觉的调整心态,达到全身心的平衡,这也就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人生态度。人们应该学习苏轼的进退自如、兼收并蓄的人生哲学,为自己开拓一个身心兼顾的广阔的精神空间。
[1]张志烈,张晓蕾.苏轼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