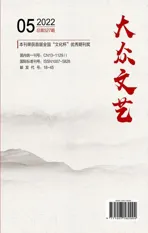苦难歌者的独特叙事
——了一容论
2011-08-15冯英涛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冯英涛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苦难歌者的独特叙事
——了一容论
冯英涛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新时期西部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回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作家的审美经验和汉语写作成为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补充和组成部分,也是西部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新近活跃的东乡族作家了一容,来自底层生活的亲身体验和悲悯精神,形成其刚健质朴、或说苍凉悲郁的小说叙事特色。所以本文主要从 “流浪”小说的独特叙事、生存苦难的批判审视、生命坚韧的女性形象等几个方面来研究讨论了一容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了一容;流浪;苦难;人性;坚韧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部文学崛起并日益显示出它的独特魅力,尤其是回族文学获得了极其独特的乡土抒写和审美张扬。新近活跃的东乡族作家了一容刚健质朴、或说苍凉悲郁的小说创作,再次让我们感到震惊。从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了一容比较石舒清的温和细致、内敛和宽容,多了民族血性的悲怆倔强,多了直面生活的桀骜不驯和孤独感奋,也看不到霍达描写穆斯林生活过于成熟的文化趣味,比较张承志趋向民间的精英知识分子心态和理想张扬,了一容多了来自底层生活的亲身体验和悲悯精神。所以了一容的存在,我们已经无法回避。王蒙在批评第三届春天文学奖获奖者时说:“了一容的小说,简洁而具有风骨,在描写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村生活状态方面颇具特色,这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有一种高贵而不屈的品质。”
本文主要从“流浪”小说的独特叙事、生存苦难的批判审视、生命坚韧的女性形象等几个方面来批评讨论了一容的小说创作。
一、“流浪”小说的独特叙事
文学成为了一容流浪生活最大的精神补偿和人生寄托,西海固贫困生活和少年流浪的打工生涯,亲身体验底层生活的艰难,目睹苦难生活的人性沦丧,经受生存底线的压迫和死亡威胁,这些经历不仅成为他写作的生活基础和主要内容,也养成了一容小说叙事的底层意识和平民思想,产生了《出走》《去尕楞的路上》《绝境》《出门》《在路上》《一截飘扬的黑头发》等以叙述流浪经历为主的小说作品。在了一容的流浪小说的叙述中,他既是文本的叙述者,又是被叙述的主要对象;同时又是“故事”的亲历者,这样的小说叙事弥漫浓厚的自叙色彩。“自传性以及由自传性而获得的真实性,的确构成了他小说压倒性的价值取向。”[1]这是一种追问灵魂的文学写作和生活省察,让我们想起许多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
《去尕楞的路上》写一位跑青海的东乡族年轻人与一位撒拉族老人,结伴而行“去尕楞的路上”的故事。荒僻阴森的路途上黑马驹的死亡,令人恐怖和伤感。古道热肠的撒拉族老人却在半路上贪念起小伙子身上带的财物,在小伙子喝水时突然在背后举起一块面目狰狞的石头。然而善念在瞬间突转,并且以野兽的惨叫印证、暗示并影响人物的心理意念。共同的命运感悟。瞬间经历生死的严酷现实,在温暖着人心、在鼓励着生活的勇气,在拉近人的情感。撒拉族老头从沉痛中醒转过来,以令人振奋的坚强说“我们上路。”在旷远的西北,在青藏高原,“去尕楞的路上”,本身包含着悲壮而苍凉的情调,透出对人世苍茫的孤独隐忧的悲怆之感。这篇作品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精神上它们是相通的。《老人与海》选取的故事极其简单,出场人物仅老人桑提亚哥和小男孩曼诺林两个人,情节仅围绕老人一次“失败”的出海捕鱼活动展开,就是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中,我们却感受到了海明威对现实、对人生、对命运非常深刻的理解。而《去尕楞的路上》向读者展示了生活的尖锐斗争,金钱与人性、自然与生存,生命的旅途充满了未知的险恶,但是只要信念坚定,人就会走向希望。小说的结尾如是说:“在生命的旅途中,人的信念是压不垮的。”小说的深层意蕴,同时与现代作家艾芜的创作精神也有相同之处,艾芜的许多作品如《南行记》,也是以他六年漂泊生涯为题材,反映底层人民的苦难和反抗意识,以及积极反抗人性和黑暗的生活态度。如《人生哲学的一课》中,“我”身无分文来到昆明,走投无路了,不得不变卖唯一一双草鞋以度日,却还坚决地表示: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 正如了一容《绝境》也表达了“一个人在绝境中,方才觉得世上凡是与生命无关的东西都是假的,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的了”的思想,表现了流浪的人在漂泊中却警觉到生命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
生活带给作家创作的激情和责任感,所以,了一容的流浪打工生涯成为独特的穿越苦难、考察生活和聆听生命的心路历程,如作者在《在路上》里所说的: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指望,都还有某种可赖以活下去的东西,都还有某种可以开开心的事情。像我这样的人四分之三都是九死一生才生存下来的。所受的各种惊吓、损失与灾祸已不胜枚举,备尝了无家可归的痛苦,忘掉了人类的一切尊严,肉体和精神都已疲惫到了极点,我们最大的理想是找到和享有人类理应有的最后一点残余的安宁。我们一次次魂飞魄散地奔走在路上,一次次陷入绝望。我们偶尔渴望求得那些幸福的,因为从未尝到这一切苦难而暗暗得意的人的庇护,我们有时为仍然活在世上而偷着高兴——谁还去管今后怎样呢!度过今夜,明天我们也许将面临新的威胁。也许会又一次陷入生死莫测的处境和绝望。
这段自白,可以看作是作者内心情感和精神的真实袒露,有一种决绝和悲壮的情感内蕴,有战胜一切不幸和打击的坚定信念,也就意味着心灵对于苦难和不幸的某种超越,所以了一容小说维护人性尊严的精神力量通过心理情感的深层揭示得以彰显。流浪本身就是一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形式,在变幻莫测的社会里面,在复杂多样的人生中间,它一方面反映了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另一方面又反映了生命的冒险和真实。《在路上》《一截飘扬的黑头发》《沙沟行》等作品都体现出非常强烈的写实特色,作者在文学的自我审视中,深化了精神、情感和思想,在苦难煎熬和生存挑战中刻画作者本人的精神信仰,呈现出人生穿越苦难的悲壮情怀,带给小说独特的叙事特色和艺术力量。
二 、生存苦难的批判审视
少年亲历的生活最容易浸润作家个人的心灵体验和思维方式,这种心灵体验在作家进行创作时,甚至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作家自身的情感结构、透视生活的深浅以及作家的悟性,则决定着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态度。“西海固”和“流浪”生活带给了一容小说生存苦难的主题,要比其他作家强烈和深刻。
首先,了一容充分揭示苦难带给底层人和女性生存理想的沉重打击,以及这种打击下的艰难反抗。
《沙沟行》是作家的早期创作,小说以朴素的文风讲述“我”和牛娃子在外流浪的生活中结下生死友谊,后来一起回牛娃子“西海固”老家沙沟的故事。这是一个荒僻的小山村,人一直处于无法解决温饱的生存底线,贫困肆无忌惮地困扰着日常生活。一碗待客的“浇注着葱花的浆水面”,引得光着下身的孩子们久久观望和守候,最小的孩子,看着我将要吃完的时候,竟然哇的一声哭了!黄土般深厚的穷困令人吃惊。生活在西部边僻荒凉地方的人们,一生遭受的就是饥饿和贫困。面对如此惨烈的生存环境,牛娃子的父母待客的热情却那么虔诚和羞涩,这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作者以冷静的笔触,把生活的苦难浓缩于三代人的生存情景:父母守候在贫困的故乡,出门讨生活的“我”和牛娃子却时时遭受欺凌、几乎性命难保,幼小的孩子们饥肠辘辘,衣不遮体。“咱们这里的人,啥时能吃顿饱饭,能美美地吃一顿白面饭就算是在世上没白活”;“山里干得连根蒿子也不长,粮食种进地里,发不了芽,发了芽却结不了籽”“那麻雀也跟着打工的人上新疆讨生去了”“因为穷,到手的媳妇也跑了”,现实生活对于西部底层人民,对于西海固群众,就是如此残酷,生活愿望和生存理想在时时遭受打击,让人深刻体会这种生存绝境带来的沉重压抑和感愤绝望。小说中描写的情景并不荒诞也不夸张,却揭示了一个真实的西海固生活,这是作者对人的生存境遇充满紧张和焦虑的文学透视。《样板》写得更加冷静悲愤,大狼窝人遭受绝境生存和官僚虚夸的双重打击,现实的暴虐和生命的轻贱,触目惊心,却又熟视无睹。《大姐》《颠山》都是苦难沉重的生活描写,女性遭受的生活打击和人性压迫更为惨重。艰苦生活中能干的“大姐”,几乎毫无反抗生活的能力和希望,当然比祥林嫂坚韧、沉默和“幸福”。生存的贫困和女性的苦难湮没了生活的所有希望和亮色,“颠山”和走向远方——农村女子去上海能谋生和保持独立生活吗?显然不可能。作者很清楚,前面的路并不乐观,所以悲伤地暗示:“路途显得凄迷”。“颠山”的母女,最后验证了鲁迅“娜拉走后怎么办”的启蒙悖论。苦难对于贫困的人群和贫困人群中的女性,不仅仅是心灵和精神的压迫,可能是永远的命运和打击。
其次,了一容在描写生存苦难的审视批判中发现,偏远地区的生存境况远比想像的严酷,苦难不仅仅挑战人性尊严,而且造成更深重的人性愚氓和生活悲剧。
从自己的内心情感出发,透视严酷的生活现实,用人性的尊严烛照生活的苦难,发掘社会底层和苦难的深层原因,这是了一容以苦难为主题的小说叙事的新开拓。《挂在轮椅上的铜汤瓶》中老奶奶坚强地活着,就是要守护小儿麻痹瘫痪的儿子。为了给瘫痪的儿子尤素福治病,母亲不顾自己的尊严,以乞讨为生。生命悲苦已经是那么深重,而尤素福的哥哥们在生活的贫困中丧失了基本的道义人性和良心尊严,“只要一听说母亲和尤素福乞讨上了钱,就把他们接回家,殷勤地‘侍奉’,等到把他们身上的钱花干花光了,便又把他们赶出家门”。面对真正的苦难和生活,我们高高在上的指责和批判是虚伪的。“挂在轮椅上的铜汤瓶”,不仅体现了母爱的坚韧和博大,而且在作者和读者的心里得到升华,那是心灵洁净和信念坚定的精神象征。又如《日头下的女孩》,小说中的阿喜耶姐妹生活贫贱,特殊的地域文化、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剥夺了她们做人的起码尊严,在贫困的现实境遇,她们想本分地活着都是一种奢侈。阿喜耶的大姐二姐被强暴后自杀,三姐四姐五姐接连失踪,阿喜耶有一天也在玉米地里被村霸强暴,她想到了自杀,“恶劣的环境和辛苦的劳动并没有把她的腰压弯,没有把她累垮,可是屈辱以及被践踏了的尊严却使她想以死的方式进行反抗”。叙述的真诚和自觉超越了浅薄的感伤与悲愤,作者用近乎残酷的直白描写,呈现出在形而上的探索。所以作者在一些作品忍不住议论说:“人活着就是为了个自由”“她要逃开那些‘小’,到‘大’的地方去。”(《颠山》) 《向日葵》也是生存苦难挑战人性尊严的“孤岛”坚守。“表现底层,书写苦难,关怀弱势群体,是当下被反复吁求的文学主题”,[2]但在许多作家的文学写作中这样的主题和追求,已经蜕变成点缀的材料和温情的面纱。而了一容以逼视和干预现实的血性,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自我悲悯的意义上,深刻反思和批判生存苦难带给底层人的人生悲剧和人性愚氓。
最为可喜的是,我们看到,生活的苦难和文学的追求,已经带给了一容生活和人性反思的现代意识。
了一容近两年的创作加强了对弱势群体生存病态的思考和揭示,以此反映人性与苦难双重变奏的主题。人性,是一个亘古的话题,“理性不可能向我们指示通向澄明、真理和智慧的道路”[3]。贫穷和欲望却会使人失去理性,致使人丧失起码的尊严和道德良心,导致人性的黑暗和残暴。正如王西平有关“小说二题”(《民兵连长的鹞子》和《饥饿精神症》)的批评分析,了一容以奇特的人物形象和荒谬情景唤醒那个特定时代的民族记忆,人性在大“话语”背景下被荒谬的观念操作,发生令人吃惊的变异,以细节的真实呈现苦难时代的荒谬性[4]。民兵连长木厂元和生产队长尕喜子为代表的任务和特别生存景观的小说呈现,写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定的人生状态,显现了群体的自我意识的沦丧和虚妄。为了更为深层地揭示生存的苦难和人性的复杂,了一容借助忠实于生活的魔幻夸张和隐喻象征锻打自己的小说叙事。《废弃的园子》,是一种生活荒诞的写真和人性极度自尊的心理把捉,直指人的思想和心灵。了一容曾经说过:我说的苦难,并非单指物质上的贫困及肉体上的折磨,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因为人类自身的缺陷、不完美导致人类总是走不出自我的羁绊,要知道,作家内心的苦难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忧患意识。所以,了一容的许多小说,在描述惊心动魄的生存苦难和人性黑暗的同时,包涵了生命的极限悖反中向上的精神。《绝境》《去尕楞的路上》《宽容》《挂在轮椅上的铜汤瓶》都有这样的暗示和象征意义。《火与冰》是了一容发掘人性深层意义和价值最为大胆的探索,对人性群氓的无知和卑俗,以及极致悖反的不可知的力量,进行了深刻的解剖。显然,《天使》《火与冰》《废弃的园子》等作品就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空间的拓展,还小说以想象与神秘的魂灵,同时又不过分地追求叙事的变形和荒诞,表明了一容在创作道路上积极探索个性化小说叙事的自觉和努力。
三、生命坚韧的女性形象
当生存的苦难超出想像,穷困造成人性最为普遍的黑暗时,了一容直面现实生活的小说叙事指向了生命坚韧的女性。一个真正富有同情心和生活敏感的作家用文学观照这个世界时,最为熟悉和同情的对象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了一容也不例外,他早先创作的《大姐》《妈妈》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就是缘于他对西海固这片土地和生活的熟悉,构成了他笔下独特的女性形象:朴实美好、隐忍坚强。
充分体现了一容悲郁情怀的是《日头下的女孩》《大姐》《妈妈》,还有《挂在轮椅上的铜汤瓶》,能够在逼仄的生活困境和命运的残酷打击中展示人物、尤其是女性的悲剧和崇高。“女性的所有悲剧来自人类文明的偏见,来自她们周围的社会压力和男性霸权。”[5]文化的边缘身份和生活被压抑的性别角色,女性必然承担沉重的人性压迫。《日头下的女孩》,就是女性所有生存权利和人身权力被践踏的真实写照,体现了人性的残暴和黑暗。“恶劣的环境和辛苦的劳动并没有把她的腰压弯,没有把她累垮,可是屈辱以及被践踏了的尊严却使她想以死的方式进行反抗”。隐忍地活着就是女性最大的坚强。能更为广泛地反映女性这种隐忍和悲剧意味的生活存在,是《大姐》,远比毕飞宇小说《玉米》的悲剧意蕴深厚。大胆能干的“大姐”心灵手巧,却少有女孩子天真烂漫的生活,除了劳作,好像就是遭受母亲的责打和生活的苛刻。大姐的一生显示出女性温恭俭让的所有传统美德,恪守教义妇道,显然这是作者笔下最为亲切的勤劳美好的女性典型形象。生活有时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真实和黑暗,令人沮丧。善良厚道的大姐没有自主的生活,婚后的生活更加黑暗,她通常“被丈夫用棍棒打得身子像个紫檀布布,她的嘴被打得肿肿的,丑陋地垂吊在一边,眼窝也青着”。她将这一切深藏在心底,不想让人笑话、不想让亲人为她担心。丈夫爷俩赌博成性、粗暴野蛮,长大的儿女穷困寡情,苦难伴随着大姐一生。然而作为贫贱保守的普通女人,大姐却又死心塌地地一辈子顾着那个家。作者对大姐生活的真实描写,在凸显“大姐”勤劳美好和忍辱负重精神的同时,也充分揭示了偏远落后地区女性难以超越的悲苦命运。当今社会像“大姐”一样不幸的女性很多,就像方方《奔跑的火光》所写的温热惨烈的生活悲剧一样。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往往只落得个无地彷徨、身心两残的结局,隐忍坚强成为女性唯一的反抗路经,
在人性的黑暗和生活的苦难面前,人的良知会受到谴责,而一个女性的坚韧和博爱却是无法估量的。“妈妈”(《妈妈》),也是一个宽容、美好和坚韧的女性。亲生母亲难产去世后,“妈妈”养育我长大,而我的倔强和不愿意去理解“妈妈”,甚至“误解”妈妈,使我不愿意喊一声妈妈。然而许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让“我”愧疚万分。我生病时,不顾泥泞陡峭的道路,妈妈硬是送我去医疗条件更好的县城医院,她一次次滑倒跪在地上,“她的膝盖被铺在路上的风化石割烂了,流着殷红的鲜血”,我却对此无动于衷。而我因为少年的倔强和反叛把别人送我的球鞋掉在了河里,妈妈坚持要我找回来,我却认为是“后妈”的冷酷无情。可是我交不是学费时,妈妈却把自己心爱的辫子剪了换钱替我交学费。我在学校里因为打架,对方家长不依不饶时,是妈妈,一个“从不向生活低头”的女人,竟然给那个家长下跪。普通的女性没有表达自己情感的习惯,但却具有女性最崇宽广胸怀,妈妈没有怨言的无私爱心,终于让我明白自己是多么任性。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西部乡土人生中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更是显露出永恒的人性意义,”[6]所以在了一容所有的小说中,最充分地体现生命坚韧和母性崇高的,是《挂在轮椅上的铜汤瓶》。年轻的母亲一直陪伴着自己残废的儿子,乞讨流浪。几十年过来了,风烛残年的母亲为了儿子,仍然坚强地活着。推着轮椅的苍老母亲成为了一容笔下不可磨灭的动人雕像。作品具有一种击穿心房的艺术力量,令人从心底升起一种庄严和静穆之情。“挂在轮椅上的铜汤瓶”,成为生命不屈和平凡伟大的精神象征和文化象征。
“走向极致是生活的大忌,却是小说写作追求的佳境。”[7]了一容的小说也许有粗粝和直白的地方,但也是逼向绝境的生活写真和生命独白。了一容的小说叙事忠实于生活,呈现女性卑贱命运的苦难本真,虽没有多少曲折情节,却以生活的真实强化了小说的感染力和人物的形象意义,真切朴素地表现了女性隐忍乐观的生命力量。这和石舒清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着极大的区别,石舒清的《节日》《旱年》《果院》、等小说也刻画了女性的美好形象,她们生活淳朴,性情美好,内心的情感活跃丰盈。就是隐忧伤感的《小诊所》《堂姑》,含蓄内敛地有意淡化悲剧性,她们很少像了一容笔下直面生活的女性那样承受生活的苦难和人性的压迫,也就缺少揭示现实的深刻性和感染力。阅读了一容描写女性生活和命运的小说,深刻地意识到生存的艰难始终压迫着中国人和中国女性的精神与情感,却又深刻地表现了她们的坚强和仁厚。
注释:
说明:作品参考与原作引文主要依据了一容小说集《去尕楞的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另有选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2007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牛学智:《文学:去掉“自传”以后——了一容小说创作的一些基本走向》,《小说评论》2006年4期。
[2]汪政:《了一容的苦难美学》,《长江文艺》,2006年第5期。
[3]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4]王西平:《一个荒谬的存在——了一容<小说二题>解析》,《民族文学》 2005年第12 期。
[5]李生滨:《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的多重悲剧意蕴》,《北方论丛》2004年第1期。
[6]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1976-2005)》,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7]马正虎:《生命的律动—东乡族青年作家了一容小说的特质》,《民族文学》2002年10期。